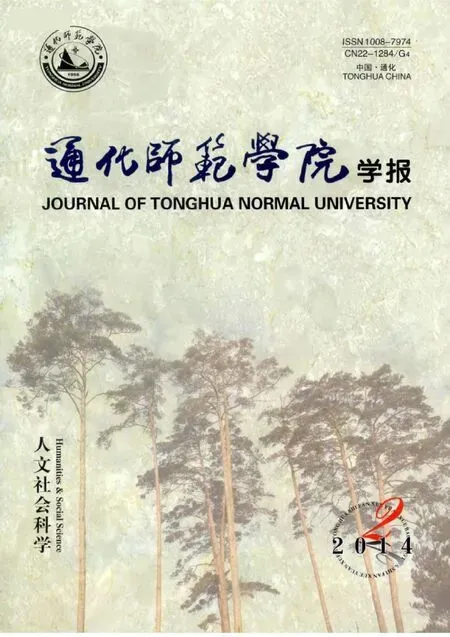赫塔·米勒的異質(zhì)書寫
——以《人是世間一只大野雞》為例
任巖
(通化師范學(xué)院 外語學(xué)院,吉林 通化 134002)
赫塔·米勒的異質(zhì)書寫
——以《人是世間一只大野雞》為例
任巖
(通化師范學(xué)院 外語學(xué)院,吉林 通化 134002)
《人是世間一只大野雞》是德裔羅馬尼亞籍作家赫塔·米勒參照自身境遇書寫的一個斷斷續(xù)續(xù)的移民故事。小說通過對異質(zhì)群體生存狀態(tài)的悲情控訴向主流文化提出了赤裸的質(zhì)詢。以社會學(xué)理論和后殖民文學(xué)理論作為切入點(diǎn),深入分析了赫塔·米勒小說創(chuàng)作的異質(zhì)特征,解讀了她憑借語言表達(dá)的非常規(guī)技巧確立異質(zhì)群體話語權(quán)過程中的若干文學(xué)要素,闡釋了異質(zhì)身份對其創(chuàng)作風(fēng)格的影響。
異質(zhì);抗辯;質(zhì)詢;話語權(quán)
2009年諾貝爾文學(xué)獎的得主德裔羅馬尼亞作家赫塔米勒(Herta Miller)的作品《人是世間一只大野雞》(Der Mensch ist ein grober Fasan auf der welt)創(chuàng)作于1986年。與其他早期作品相較,《人》在生動地展示了作者獨(dú)特的藝術(shù)才華的同時更加突出地展現(xiàn)了對流亡主題的反抗特寫。由于譯介的關(guān)系,這部作品被我國讀者接受較晚,然而部分國內(nèi)學(xué)者仍從不同角度對其加以關(guān)注,先后考察了作品中的文化雜糅現(xiàn)象、文學(xué)鄉(xiāng)土性、政治話語權(quán)、隱晦虛構(gòu)及詩意表達(dá)等方面的文學(xué)特征,這些成果在一定程度上豐富了我們對這位非主流作家的認(rèn)識,但就小說中所表達(dá)出來的“異質(zhì)”抗辯內(nèi)涵及影響方面的研究尚少涉及,本文重點(diǎn)挖掘了赫塔米勒小說創(chuàng)作的這一特點(diǎn),深入探討她通過移民事件前后經(jīng)過的描述為自己以及所有受到齊奧賽斯庫時期羅馬尼亞政府排斥的社會群體提出的抗辯,并在此基礎(chǔ)上以《人是世間一只大野雞》的片段分析為例闡述作者的異質(zhì)身份對其創(chuàng)作風(fēng)格的影響。
一、異質(zhì)身份的揭示
“異質(zhì)(hétérogène)”一詞常用于生物學(xué)領(lǐng)域,指那些本質(zhì)與周圍事物完全不同的物質(zhì)。20世紀(jì)法國思想家喬治·巴塔耶(Georges Bataille)從社會學(xué)角度將其特征定義為“他們是‘不能同質(zhì)化的’。同質(zhì)的事物可以構(gòu)成秩序,構(gòu)成生產(chǎn)活動,而異質(zhì)的東西將被‘排泄’。反過來,同質(zhì)世界只有不斷吸收和轉(zhuǎn)換異質(zhì)世界,使其‘同質(zhì)化’,才能維系同質(zhì)世界的存在。”(1991:99-100)巴塔耶的這段描述反映了社會對異質(zhì)存在的兩種態(tài)度:一是排泄,二是同化。這其中存在著一個顯而易見的矛盾,即異質(zhì)之所以被稱為異質(zhì)正是因?yàn)樗牟豢赏裕运遣豢赡鼙煌模^“同化”只是理論性地存在,實(shí)際上異質(zhì)只有一種出路就是被徹底地排泄掉,以保證同質(zhì)社會的正常運(yùn)行。
《人是世間一只大野雞》恰恰集中體現(xiàn)了這一異質(zhì)被排泄的過程。小說雖然講述的是一個關(guān)于移民的故事,但是從頭至尾都沒有片言支語交待為什么要移民,只是說溫迪施一家焦急地等待著當(dāng)局同意他們?nèi)獾脑S可,越來越多的羅馬尼亞鄰居離開了村莊,而他們還在漫長的等待中,后來女兒阿瑪麗決定用肉體換取當(dāng)局的公章,直到故事結(jié)束始終也沒有告知是否獲準(zhǔn)離境。美國社會學(xué)家彼得布勞(Peter Michael Blau)曾指出“異質(zhì)是社會分化的一種形式,而禁止與某個群體成員進(jìn)行互相交往的歧視行為將導(dǎo)致階層群體的流動,”(1989:78)我們注意到《人》創(chuàng)作于赫塔米勒遷居德國的前一年,主人公溫迪施和女兒一心想移居海外的念頭很可能正是赫塔米勒真實(shí)思想斗爭的再現(xiàn),她已經(jīng)意識到自己的不可融合性,打算主動疏離,但是處境不允許她逃走,逼迫她自我同化,去做她不可能完成的事情,她對此感到無助,卻又找不到出路,所以只好有意不談及這個問題,然而她的憤怒是顯而易見的。
對于一個出生在羅馬尼亞的徳裔作家來說,特殊的身份和成長壓力造就了她精神上雙重的無所寄托。作為一個羅馬尼亞人,她因曾是納粹的子女而受到歧視和監(jiān)視,失去了內(nèi)心的平靜和人格的平等。作為一個德國人,她又受到東歐語言和文化的熏陶,她雖然會講德語,但是她的表達(dá)顯然在有意無意地對抗著繁復(fù)陰郁的母語,民族、祖國和家鄉(xiāng)在她的信念里缺失了確定的涵義,代之以具體、簡單、迅捷地直抒胸臆,生活在她的筆下是一連串反抗的思考和行動,也許互不鏈接,但卻是異常的真實(shí),涵蓋了一切“隱而未言”的東西。(Herta Miller’s Life and Writing,2010:55)
正如羅賓·科翰(Robin Cohen)所言:“對個體創(chuàng)傷事件的記憶有助于離散者通過想象積極構(gòu)建真實(shí)存在的家鄉(xiāng)的真實(shí)樣貌。由于這種理想化使得他們自然而然地將處境的根源歸結(jié)為一種充滿敵意的且被主動行為實(shí)施的迫害的結(jié)果”(Global Diasporas, 1997:125-126),米勒的異質(zhì)狀態(tài)是在不平等的社會壓力下被動形成的,她所謂的“隱而未言”即是她被社會異質(zhì)化后的自我抗?fàn)幣c辯白,對移民避而不談不是因?yàn)椴粺釔圩约褐蒙淼膰摇⒁膊皇且驗(yàn)槔碛傻谋旧聿豢裳哉f,而是痛失主體身份后的一種無可奈何,她用“沉默與迫害教會我寫作”(Herta Miller’s Life and Writing,2010:57)來控訴異質(zhì)身份對她的影響。
二、異質(zhì)群體話語權(quán)的確立
蘇迪·米薩(Sudesh Mishra)揭示了被異質(zhì)化的群體在意識領(lǐng)域的普遍特征,她指出“離散者通常較為深入地關(guān)注那些使其陷入離散境地的集體意識,他們往往沉浸在家鄉(xiāng)與寄居地的選擇性躊躇之中,將意識深處的記憶以表格形式羅列總結(jié),或通過諸如繪畫、音樂、電子創(chuàng)作等具有審美意義的文化生產(chǎn)表達(dá)形式驗(yàn)證暗藏在其意識深處的主張,這使他們更深程度地陷入了社會組成與文化生產(chǎn)的糾結(jié)之中。”(Locating Diasporas,1996:108-128)
作為異質(zhì)化個體,米勒體會到如何被同質(zhì)世界排斥的痛苦,她被自己熟悉的社會隔離,在焦慮中尋找自身的價值,試圖明確建立所屬群體的話語權(quán)。1973年米勒曾就讀于羅馬尼亞著名的蒂米什瓦拉大學(xué),大學(xué)所在地靠近南斯拉夫和匈牙利,文化和教育都比較發(fā)達(dá),許多居民都會講三種語言:羅馬尼亞語、匈牙利語和德語,豐富的語言環(huán)境為米勒提供了不可多得的養(yǎng)料。她甚至能夠像講德語那樣自如地運(yùn)用羅馬尼亞語,這對于一個作家來說無疑是份得天獨(dú)厚的無價之寶。她本人也曾坦誠地認(rèn)為在羅馬尼亞學(xué)習(xí)德語和羅馬尼亞文學(xué)的成長經(jīng)歷對她的寫作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在此基礎(chǔ)上,米勒經(jīng)歷了大量的文學(xué)體驗(yàn)和嘗試并從中提煉出清晰明確的個人創(chuàng)作理念,即“藝術(shù)是反抗的特寫”。 (Herta Miller’s Life and Writing, 2010:96)為了實(shí)現(xiàn)這個宗旨,她從形式到內(nèi)容都做了大膽的改革和創(chuàng)新。在敘事技巧上,她采取了超越文字的方法,通過精妙的細(xì)節(jié)、混沌的時間、虛構(gòu)的驚愕以及旁白的宣泄混雜在一起制造出一種奇異的和聲,并恣意地放縱它們在心靈的傷口上彈奏平凡而壓抑的神經(jīng),指使它們到生活的場景中拿捏病態(tài)思想的延伸,她的文字與其說是寫作的工具,不如說是意識的抽象裸現(xiàn),每一個主題之下的小小篇章都像是一幅充滿奇思妙想的立體畫,盡管它的格調(diào)總顯得憂郁低沉,但卻在光線和角度的協(xié)助下不斷地暴露出靈魂對現(xiàn)實(shí)的種種質(zhì)疑和譏諷。
比如“針”和“大麗花”兩段描述了這樣一個事件:細(xì)木工的母親死了,她的棺材就停靠在兒子起居室的一角,此時,細(xì)木工并沒有表現(xiàn)出對母親的追思和悼念,而是在和妻子縱情嬉鬧。時空錯亂間又回到母親去世前,她正提刀砍去院子盡頭一株盛開的大麗花,在她看來這花早該完蛋了,可它沒有脫落,于是她用刀子幫它結(jié)束殘局,然后她用刀子在地上挖了個洞,把花埋了起來。接下來她又去井里提回一個冰鎮(zhèn)的甜瓜,用尖刀挖出紅色的瓜肉,大口地咀嚼吞咽著,紅色的汁水淌了一身,她還在邊吃邊抱怨著夏天太熱,只有這瓜能讓她涼下來。葬禮結(jié)束后,兒子對鄰居說甜瓜純粹是個借口,大麗花才是她的災(zāi)難,而女鄰居則強(qiáng)調(diào)大麗花是一張臉。(133)在這段時空混亂的敘事里,精巧的細(xì)節(jié)描寫將母親與兒子之間難以磨合的種種矛盾暗自隱藏起來,文字的表面看上去好似精神病人的絮語,代表作者眼中混亂不堪的社會現(xiàn)實(shí)。內(nèi)容不銜接,邏輯不通順使語言的傳統(tǒng)表達(dá)功能幾近喪失,一片狼藉的符號中僅存若干可以用來連接表象的蛛絲馬跡,將讀者引領(lǐng)到作者想集中展現(xiàn)的心理現(xiàn)實(shí)。棺材里的母親無法接受兒子對她的疏離,也無法表達(dá)自己的憤怒,所以我們看到了掛在椅子腿上一根牽著灰色線的針尖晃來晃去;她的遺像慘淡地露出垂死的微笑;還有她砍掉的大麗花以及血紅的甜瓜瓤和流淌在手臂間鮮紅的汁液。(141)這些普通的不能再平常的細(xì)節(jié)描寫的精妙之處在于它立于文字之上表達(dá)了超乎文字的意義:生命在無奈間的抗拒總有它獨(dú)特的表達(dá)形式,無論多么超乎常理,它總是存在著的,而只要它是存在的,就應(yīng)該受到世人的理解和關(guān)照。
維亞·米薩(Vijay Mishra)認(rèn)為“離散者希望通過護(hù)照確認(rèn)其市民身份,然而,身體樣貌的區(qū)別又將其排除在單一種族政治認(rèn)定標(biāo)準(zhǔn)之外,所以他們確定身份的愿望遁入對‘第三時空’的想象之中。所有的期望都駐足其中,時空脫離了現(xiàn)實(shí)的一般意義的存在形式變得虛無散碎。”(The Diasporic Imaginary, 1996:189-237)。《人》中時間的混沌使小說呈現(xiàn)出令人無法忍受的迷茫的局面,主人公溫迪施日復(fù)一日地進(jìn)行著單調(diào)乏味的工作,在毫無生機(jī)的境地里懷著一個虛妄的希望打發(fā)日子,時間對于他來說已經(jīng)失去了記錄的準(zhǔn)確性,年份和日子被隨便地拆解,兩年也只有兩百二十一天,意義在數(shù)字間消失,等待變成了無休無止的煎熬。混沌的時間不再是虛擬的概念單位而是一種內(nèi)心風(fēng)景的參照物,它讓我們看到了“每天早晨,當(dāng)溫迪施形單影只地騎車穿過街道奔向磨坊的時候。他都數(shù)那個日子。他在陣亡戰(zhàn)士紀(jì)念碑前數(shù)年分。當(dāng)自行車駛過第一顆白楊樹,徑直駛向那同一片洼地時,他數(shù)日子。而到了晚上,當(dāng)溫迪施鎖上磨坊門的時候,他把年份和日子再數(shù)一遍”“溫迪施在陣亡將士紀(jì)念碑前數(shù)到兩年,在白楊樹前面那片洼地里數(shù)到兩百二十一天”。(97)米勒非常敏感地抓住了時間這個敘事要素,象擺弄魔方那樣把它翻轉(zhuǎn)疊挪到希望放置的空間,以配合整個立體圖形的需要。人的思想與時間形成了一對抗力,互不讓步、永不妥協(xié)地僵持著又彼此塑造著。仿佛兩個相近質(zhì)量的天體在抗衡,兩種意志得到了同等程度的關(guān)注和表現(xiàn)。
虛構(gòu)是小說創(chuàng)作的常規(guī)藝術(shù)手段,但在米勒的筆下,它用來編織敘事的功能消失了,代之以驚愕。“黑斑”一開始是寫實(shí)的場景“櫥柜是一個白色的正方形,床是白色的邊框,那之間是墻上的黑斑”,“掛鐘在壁爐旁留下一個長長的白色斑痕。時間就掛在壁爐旁邊。時間到頭了……時間沒有指針。只有黑色的斑痕在旋轉(zhuǎn)”。(221)但是隨著時空和光線的變化,這塊黑斑被異化了“只有黑色的斑痕在旋轉(zhuǎn),時間擁擠著從白色的斑痕里溜走,順著墻壁掉落。那黑色的斑痕就是其他房間里的地板……地板將顏色沖到房間的墻邊,其他房間里的時間涌進(jìn)來,黑色的斑痕一起游動……它們在靠近,在觸碰。它們沿著自己那瘦長的裂痕落下,他們變得沉重,而大地將破碎……溫迪施張開嘴。他覺得它在臉上長大,那個黑色的斑痕。”(225)米勒借助光線的變化將時間虛構(gòu)成鬼魅般的陰影,時而攀爬在墻壁上,時而流動在角落里,時而惡獸般吞噬周圍的一切,時而獰笑在人的臉上。隨著米勒筆觸的延伸,驚愕不斷地侵?jǐn)_著人的感官,最終匯聚成古典悲劇落幕時那種無以償付的凄涼和極具警示力的莊嚴(yán)。溫迪施臉上的黑斑其實(shí)是長在心里的,一種空洞的未來耗盡生命分分秒秒的隱憂和無奈,在這種情況下一個人的意志最容易被吞噬,米勒認(rèn)識到這個危險,于是她結(jié)文字為鞭繩不斷地抽打著日漸麻木的神經(jīng),使他們在驚愕間保持清醒的抗拒。
在被異質(zhì)的世界里有些痛苦是直接而鮮明的,但更多的是不便講明的,米勒使用旁白對此加以宣泄。皮革匠的兒子因?yàn)閰⒓恿T工被送進(jìn)大山里的集中營,他去看兒子,回來對溫迪施說他在一家玻璃工廠工作,談話間他似乎一度忘記自己撒的謊又提到了那個集中營,甚至某個政治犯出了車禍被撞死,最后他又講到墓地,講到了兒子讓他帶給母親的那個小盒子,可是這盒子也不知放到哪里去了就是找不到。這段敘述里皮革匠的妻子一面傾聽丈夫和溫迪施談話,一面擔(dān)當(dāng)著旁白者,為丈夫的謊言遮掩“山區(qū)應(yīng)該很不錯,就是太遠(yuǎn)了,我們沒法去,魯?shù)弦不夭粊怼保欢瑑鹤拥乃雷鳛橐环N傷痛是很難掩飾的,盡管不便明示,但她還是找到了宣泄的對象“這雞蛋太老了,打出來的蛋液有點(diǎn)兒苦”。當(dāng)丈夫起身試圖出示兒子帶回的“禮物”,她極力配合道“我們會找到它的”,(276)事實(shí)上,那個禮物是兒子空空的骨灰盒,怎么能夠示人呢。掩飾構(gòu)成了旁白者講話的動機(jī),小小的尊嚴(yán)在掩飾中似乎得到了保護(hù),實(shí)際上卻袒露出更深層次的痛苦。
三、異質(zhì)情感的非常規(guī)表達(dá)
威廉·薩弗蘭(William Safran)認(rèn)為“通常僑居在國外的少數(shù)群體只是部分地被寄居地所接受,而祖先的家園作為心中的神話才是他們能夠最終獲得滿意的安全感的歸宿。種族意識和孤獨(dú)感并行存在于他們的觀念和社會聯(lián)系中”(Diasporas in Modern Societies,1991:83-99)對于米勒而言,既不能從父母那里獲得信仰的支撐,又不被寄居地的法律認(rèn)可,危機(jī)感和孤獨(dú)感成為了她潛意識里最想擺脫的現(xiàn)實(shí)。于是她選擇了機(jī)械地拼貼來書寫人與環(huán)境的永久性疏離。“溫迪施朝馬路望去,草地在路的盡頭沖進(jìn)了村子。有一個人在盡頭處走著。那人行走在草叢里像一條黑色的線,突進(jìn)的草地將他托起在大地上。”(155)作為主體的人與作為客體的景物被完全倒置了,人失去了能動性,受到了環(huán)境的擺布,無力掙扎,被迫淪為陪襯物。原有的自然和諧的或者說是合乎常理的主次關(guān)系在這里變得生淡冷漠,完全一副被強(qiáng)大的外力硬拉進(jìn)來才不得已湊在一起的樣子,路、草地、村莊和人之間莫名其妙地產(chǎn)生了一種神秘的力量,排斥與抗拒仿佛永恒之力在諸多因素間僵持著。
如上文所言,異質(zhì)者一旦意識到自我身份的特殊性,必然會積極主動地參與重新建構(gòu)自我的努力之中,通過對特殊處境下靈魂扭曲度的凝視,剝離虛假價值觀的負(fù)面影響,展現(xiàn)鮮活生命的詩意存在,從而確立自我的嶄新價值,但是由于要面對強(qiáng)大的社會壓力,所以他們從一開始就知道自己發(fā)出的呼喊注定是無法等到回應(yīng)的。米勒采用意境的比較、轉(zhuǎn)換和抽取來表達(dá)這種絕望的思想和濃厚的情緒。《洼地》一節(jié)關(guān)于二戰(zhàn)陣亡將士紀(jì)念碑周圍的環(huán)境描寫展示了生死之間一種獨(dú)特的抗拒關(guān)系。“紀(jì)念碑四周是一片灌木叢,是玫瑰花叢。盛開的小白花蜷縮著,像紙一樣,壓得身邊的青草好像透不過氣來。樹叢發(fā)出簌簌聲。黎明時分,天快要大亮了。”(102)米勒選取了色彩意象的轉(zhuǎn)換將現(xiàn)實(shí)的壓抑與想象中的浪漫作對比,抽取使二者產(chǎn)生永久隔閡的矛盾,并最終將其推入混沌的時間接受煅打和研磨。壓抑、煩躁的情緒在這種氛圍里凝結(jié)發(fā)酵成沉默的反抗,傷感的格調(diào)背著歷史的十字架呻吟前行,憤懣令其迷失在渺茫的未來之中。
米勒曾說 “人在極端困苦的情況下甚至?xí)褜?shí)實(shí)在在的物體擬人化,一個人什么都沒有了,就會特別注意周圍的每一樣事物。他們對于事物的看法已經(jīng)超出一般人的理解了,而這些事物也定義了人本身。”于是許許多多眼前可見的事物被零零散散地搭配在一起,構(gòu)成了異質(zhì)群體的一種獨(dú)特的意義表達(dá)。在米勒看來正是由于這種帶著孤獨(dú)感動的陌生性才能產(chǎn)生意外的錯位效果,人們的感官只有在受到物質(zhì)世界的剝奪之后才有可能徹底脫離傳統(tǒng)印象的束縛,產(chǎn)生新的理解和反射印象。題目“人是世間一只大野雞”就是很典型的一例。米勒以極其意外的修辭將人的自然屬性與社會屬性鮮明的對立起來,十分醒目地宣告了她所要譴責(zé)的尷尬現(xiàn)實(shí),即原本歸屬于社會的人迫于某種壓力不得已變成了一只雞,人的社會屬性被自然屬性所置換,并最終淪為異質(zhì)。人的靈性、稟賦、尊嚴(yán)和自豪感在這里遭到了嘲弄,社會作為迫害人的罪魁禍?zhǔn)资艿搅顺坏ǖ淖l責(zé)。
瑞典文學(xué)院將米勒的風(fēng)格描述為 “詩歌的凝練與散文的率真”。(Herta Miller’s Life and Writing, 2010:201)然而,米勒創(chuàng)作的文學(xué)意義卻遠(yuǎn)不止于此。她的文字常常令讀者在頃刻間獲得感官的頓悟,抽象的時間與具象的事物彼此鏈接,互換形體,彼此交融,坦誠地描繪著人既無未來可追尋亦無現(xiàn)在可立身的雙重的無所寄托之痛。異質(zhì)抗辯作為赫塔米勒小說藝術(shù)的獨(dú)特表達(dá)帶我們走進(jìn)了異質(zhì)群體真實(shí)生活體驗(yàn)的最深處,聆聽他們面對壓迫時抑郁的喘息和每一聲質(zhì)疑的心跳。她寫作中凝練出的生活的影子將每一根神經(jīng)所承受的負(fù)擔(dān)徹底地釋放,任由他們在微弱的顫動中傳遞對主流文化的赤裸質(zhì)詢和對自身存在狀態(tài)的悲情控訴,為更深刻地理解異質(zhì)文化提供了更鮮活更豐富的視閾。
[1]赫塔·米勒.人是世間一只大野雞[M].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 2010.
[2]胡蔚.政治·語言·家園——赫塔·米勒的文學(xué)觀[J].探索與爭鳴,2010(01).
[3]李銀波,蘇暉.2009年諾貝爾文學(xué)獎得主德國女作家赫塔·米勒初探[J].外國文學(xué)研究,2009(05).
[4]李麗琴.赫塔·米勒作品的時代隱喻[J].當(dāng)代文壇,2010(04). [5]陶家俊.身份認(rèn)同導(dǎo)論[J].外國文學(xué),2004(02).
[6]張霽.異質(zhì)與邊緣的表達(dá)——論赫特·米勒創(chuàng)作的跨文化視野[J].深圳大學(xué)學(xué)報(人文社會科學(xué)版),2010(01).
[7]Georges Bataille,Trans.Robert Hurley.The Accursed Share: An Essay on General Economy,VolumeⅢ,Sovereignty[M].New York:Seminar Press,1991:99-100.
[8]Herta Miller.Pheasant Human[M].London:HarperCollins Publishers Ltd,2010:97,102,133,141,155,221,225,276.
[9]Nicholas Mudish.Herta Miller’s Life and Writing[M].London: Wordsworth Classic Ltd,2010:55,57,96,201.
[10]Safran,William.Diasporas in Modern Societies:Myths of Homeland and Return,Diaspora[J].11,1991,83-89.
(責(zé)任編輯:徐星華)
I3/7
A
1008—7974(2014)02—0069—04
2013-10-30
任巖(1973-)女,吉林通化人,副教授。研究方向:英美文學(xué),世界文學(xué)及文學(xué)理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