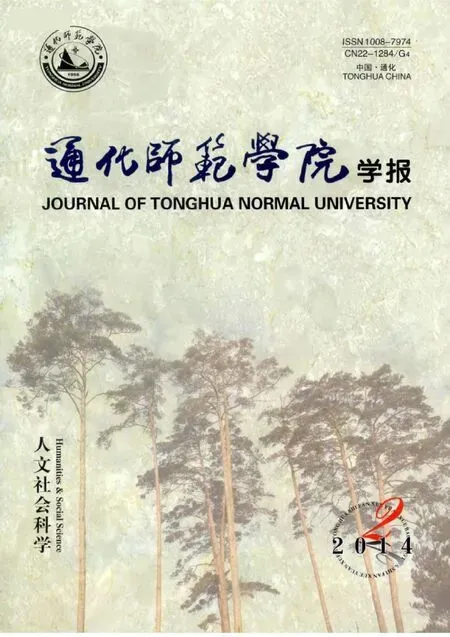論唐傳奇中人鬼戀小說的母題演變及發展動因
趙 妍,楊 雪
(吉林師范大學 國際文化交流學院,吉林 四平 136000)
中國古典小說發展到了唐代,傳奇可謂大放異彩。它前承六朝志怪,后啟宋元話本,而與前朝小說相比,唐代傳奇的筆法更為細膩精妙,故事情節更加豐富離奇,人物情感亦更加濃烈奔放,是中國古典小說走向成熟的標志。
唐代中期是唐傳奇的繁榮時期,從作品內容上看,大致可分為神怪、愛情、歷史、俠義等題材。其中有些作品內容相互交叉,如神怪兼愛情類的題材就很多,人鬼戀故事即屬其中。這類題材并非始于唐代,早在漢魏晉南北朝時期它就以清晰的面貌和鮮明的個性完整地出現在的志怪小說中。而作為前朝志怪小說的繼承和發展,唐傳奇中人鬼戀小說的著眼點已從鬼神之“怪”轉向人事之“奇”,通過描寫人與鬼的婚戀來反映世俗愛情。
一、人鬼戀小說的題材類型
唐傳奇中的人鬼之戀小說將近20篇。有學者將其分為以下幾大類:一類是在魏晉志怪《列異傳》中《談生》、《辛守道》的情節結構模式基礎上進行演繹。如《廣異記》中的《張果女》、《王玄之》;第二類是古代冥婚風俗在作品中的升華。故事背景在女方死后展開,生前與該女子或相識或素昧平生的男子進人墓冢與女鬼相愛,終成“眷屬”,并為封建家長所認可。第三類,展示男女主人公生前相戀,死后續緣的過程,情節曲折,情韻悠長,可以稱之為真正的生死之戀的浪漫小說。代表作品有《李章武》、《唐煊》和《華州參軍》等;第四類小說在更為廣闊的社會背景下展開,著力描寫“現代”男子與古代女鬼之間的愛情,情節更加荒誕離奇,比之前三類,道教的精神在這類小說中有更明顯的體現。如《崔煒》、《張云容》等。
二、人鬼戀的故事原型
“鬼”在《說文解字》中的釋義為:“鬼,人所歸為鬼。從兒,由象鬼頭;從么,鬼陰氣賊害,故從么。”靈魂永生的觀念在源遠流長的中華文化中早已根深蒂固,它是創作人鬼戀故事的靈感源泉。源于靈魂的永生觀念,故在民間就誕生了冥婚這一獨特婚姻形式的發生。
所謂冥婚就是為使生前未婚的亡魂在陰間也能過上夫妻生活而舉行的婚禮。這種風俗由來已久。《周禮·地官·媒氏》中記載了有關條文“禁遷葬者,與婚殤者”,唐代孔穎達疏云:“遷葬謂成人鰥寡,生時非夫婦,死乃嫁之。嫁殤者,生年十九已下而死,死乃嫁之。不言殤娶者,舉女殤,男可知也。”但因冥婚耗費人力、物力且毫無意義,曾被禁止,但千百年來這種陋俗始終沒有杜絕,即便在現代,冥婚儀式也是有跡可循的。因此可以說,這種風俗的盛行不衰正是一個個凄美的人鬼之戀故事源源不絕的現實基礎。
三、唐傳奇對人鬼戀故事的創新
唐傳奇中人鬼相戀的小說比比皆是,比較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有 《李章武傳》、《華州參軍》、《唐煊》、《崔煒》等。作品在情節上雖然是對志怪小說的繼承,但還是有些創新的嘗試值得我們注意。
1.由談鬼色變到人情味十足
在六朝同類題材小說中,男女主角大都是在男方不知女方為鬼魂的情況下產生愛情的。但當男方得知愛人的真實身份后大部分卻因恐懼而死,小說不自覺地就被籠罩上一絲恐怖的氛圍。而到了唐代的傳奇小說,女鬼們依舊保持嬌好的形象外,被賦予了更多的人情味,她們對所愛戀的男子情真意重,至死不渝。如《李章武》中對女主人公王氏子婦的描寫,“或竟日不食,終夜無寢”,因為李章武離開后,王氏思慕至切,不到二三年便憂傷而死了。而在她死后,對章武的愛戀卻沒有絲毫減弱,仍像生前那樣柔情似水,美麗動人,只是來去倏忽。
“視衣服,乃主人子婦也。與昔見不異,但舉止浮急,音調輕清耳。章武下床,迎擁攜手,款若平生之歡。自云:‘在冥錄以來,都忘親戚。但思君子之心,如平昔耳。’章武倍與狎昵,亦無他異。”[1]
得知王氏非人之后,章武并沒有懼怕而死,而是急切等待他的愛人前來。打破了前朝鬼話小說的恐怖氛圍。
“至五更,有人告可還。子婦泣下床,與章武連臂出門,仰望天漢,遂嗚咽悲怨,卻入室,自于裙帶上解錦囊,囊中取一物以贈之。……款曲敘別訖,遂卻赴西北隅。行數步,猶回顧拭淚。云:‘李郎無舍,念此泉下人。’復哽咽佇立,視天欲明,急趨至角,即不復見。 ”[1]
臨別贈物,再現款款深情,女鬼情之真切,與世間女子無異。
2.由陰陽相隔到生死相隨
這一時期的人鬼戀故事中,不論男女主人公以什么方式相遇,這些女鬼一概是美麗且深情,但這一場場“艷遇”到了最后往往卻因最終人鬼殊途而不了了之。
在這些作品之中,《鄭德楙》對故事結局的處理則有別于其它小說以男女永訣抑或復活團圓收場,那就是在艷遇過后,男女主人公的關系未因為種種外界因素而斷絕,相反,跟女鬼約定的時限一到,鄭德楙竟坦然地安置好家中事務,第二天便“暴卒”了。這一結局讓《鄭德楙》在同類作品中獨樹一幟。
值得一提還有作品《唐煊》。故事發展到最后雖然也是夫妻分別的悲劇結局,但臨別留下一幅羅帕,送給丈夫作為留念,并告之四十年后能相見,這無疑給丈夫一線希望。不像王氏婦子與章武一別,有如石沉大海,永無會期,悲劇色彩更顯濃烈。
四、人鬼戀小說發展的內外動因
人鬼戀小說在抒發作者的愛情理想、抨擊封建禮教、肯定女性對美好愛情的渴望和努力等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這類作品的層出不窮,除了宗教信仰、民俗文化、人們獵奇心理等復雜多樣的原因外,人鬼戀母題本身的文體特色也是人鬼戀故事發展的重要動力。
首先,作品的超現實性符合文人的獵奇心理和創作需要。
“死亡并非生命的結束,它僅意味著生命形式的改變”,靈魂不滅的信仰“是處于所有進化階段的人們中間普遍存在的一種信仰,可以當成一個毫無疑問的真理,很難說有哪一個野蠻人的部落完全沒有這種信仰”。[2]在人類歷史長河中,不死的靈魂總是與我們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奇幻、怪異、擁有神秘力量的“鬼”作為一種非現實的存在,卻一直在人們的思想觀念中糾纏不清,令人著迷而又畏懼。愛情和死亡作為人類文學永恒的主題本身已為人津津樂道,人鬼婚戀這種天馬行空的想象絕對能給人們帶來更加強烈的感官沖擊。
另一方面,超現實性為作家更有效的表達真情實感涂上了一層特殊的保護色。在文風森嚴的封建時代,作者得以于嚴格的正統兩性道德之外,假托無所不能的鬼魂將生活中無法實現的愛情理想盡情抒發出來,為現實中受到重重阻礙和壓迫的自由愛情觀另辟蹊徑。基于以上原因,鬼文學成為自古以來文人墨客慣用的藝術表現形式之一。
其次,社會風尚對人鬼戀故事創作起到了絕對的推動作用,并在其小說創作上打下時代的烙印。
唐朝結束了自三國以后將近四百年的分裂動亂一統中國之后,社會安定,農、工商業都得到長足發展,長安、洛陽、揚州、成都等人口眾多、經濟繁榮的大城市為了滿足各階層娛樂生活的需求,民間的“說話”藝術應運而生。另外,隨著佛教的興盛,佛教徒也利用這種通俗的文藝形式演唱佛經故事以招徠聽眾、宣揚佛法,在此基礎上又產生了大量變文,促進了“說話”藝術的發展。從民間到上層,“說話”受到了廣泛的喜愛。
政治統一、經濟、文化繁榮所帶來的局面就是,各階級、階層還有整個國家、民族都處在欣欣向榮的社會氛圍中。“于是,遠大的政治抱負,強烈的科舉仕途欲望,潛心于詩藝的探求,向往著隱居求仙,以及豐富的生活情趣,放浪的酒色生涯,就構成了唐代這一特定的歷史時期文人階層的社會風尚。”[3]在這種追逐風流的時風之下,人們對色欲的追求已無需在任何掩飾之下,許多作品因而都表現出了濃烈的青樓色彩,《王玄之》中“王試挑之,女遂欣然,因留宿,甚相親昵,明旦辭去。 ”;《李章武傳》中“數日,出行,于市北街見一婦人,甚美。因紿信云:“須州外與親故知聞。”遂賃舍于美人之家。……乃悅而私焉。居月余日,所計用直三萬余,子婦所供費倍之。既而兩心克諧,情好彌切。”等等。唐代崇尚奢靡、放蕩輕浮之風刺激了人們對性的幻想和心理訴求,無疑成為人鬼戀故事創作高峰的外部推動力。
總而言之,唐傳奇中人鬼之戀小說對前朝志怪小說的刻板模式進行了質的突破,其中的人物形象也有了各自不同且鮮明的個性特色。對生死之戀的充分展開,對細節部分的精妙處理和細膩刻畫的藝術手法在中國古代小說史中承前啟后,堪稱“絕代之奇”。
:
[1]太平廣記[M].北京:中華書局,1961.
[2]吳光正.中國古代小說的原型與母題[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
[3]李志慧.中國古代文人風尚——唐時文苑遺聞[M].西安:陜西人民出版社,2004.
[4]鐘林斌.論唐傳奇中的人鬼之戀小說[J].南京師范大學學報,2005(2).
[5]伍微微.人鬼情未了——論唐傳奇人鬼戀故事新變[J].名作欣賞,2011(11).
[6]伍微微.論唐傳奇人神戀故事的人神平等性[J].湖北社會科學,2013(4).
[7]范治梅.悲歡人鬼戀 陰陽兩世情——《聊齋》人鬼戀故事研究[D].曲阜師范大學,2011.
[8]俞佳琪.人鬼·艷遇·成仙——由鄭德楙的去向談唐傳奇所反映的文人心態及人鬼婚戀故事的歷史文化淵源[J].中國古代小說戲劇研究叢刊,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