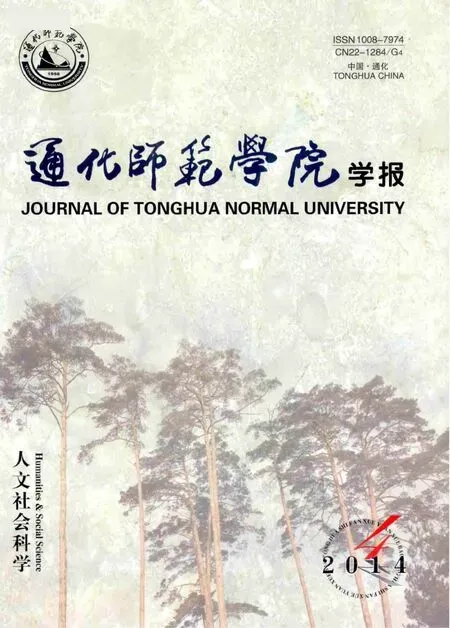小說教:古典小說道德—欲望敘事中的統攝調和機制——以“三言”為例
汪 注
(1.安徽師范大學 研究生院,安徽 蕪湖 241000;2.安徽商貿職業技術學院 宣傳部,安徽 蕪湖 241000)
小說教:古典小說道德—欲望敘事中的統攝調和機制
——以“三言”為例
汪 注1,2
(1.安徽師范大學 研究生院,安徽 蕪湖 241000;2.安徽商貿職業技術學院 宣傳部,安徽 蕪湖 241000)
明清通俗小說的思想教化功能與娛樂消閑功能同時存在,兩者互為犄角、辯證統一,被小說教統攝、調和,達成均勢。以“三言”為例,小說教在其中既倡導友情至上、輕財重義等符合群際利益的行為準則與道德范式,又彰顯變泰發跡的種種可能,借以滿足市民階層對獲得地位、財富的渴望。整體上,小說教借助對因果循環、節制欲望的生動宣講,將本質上沖突的名利觀與財富觀導入遵循天理人心、服從宿命安排的教化軌道,為自身開辟通暢無阻的傳播路徑。
小說教;“三言”;道德;欲望;調和機制
作為中國傳統通俗文學的重鎮,“三言”集結了自唐末至明末逾700年散落在市井街頭、勾欄瓦肆的民間話本與擬話本,包含了豐富多元的思想意蘊,在映射、滿足撰寫者的生活體驗、人生訴求的同時,折現出特定社會環境中的群體心理,并構建出了維系人生與人心的行為準則與道德范式。兩者彼此交織、密不可分,組成“小說教”的“一體”與“兩面”,協同引導通俗文學的敘事思想主線,釋放出參與世俗世界建構的潛在而強大的力量。
一、小說教的基本釋義及功能生成
乍看上去,作為精神范疇專屬詞匯的“教”,與小說這一文學樣式之間并無嫁接、交互的可能。然而,當小說被視作有效的大眾信息媒介,且的確具備促成受眾實現情緒宣泄、達成情感轉移功效,并成為受眾投射自己的理想、信念、意志和價值的話語構造和敘事系統之后,它便有可能反過來被更多的人們視為客觀真實并要求自我及他人去承認,進而使小說被神圣化、信仰化、示范化。最能體現前述大眾文化—心理接受機制所起作用的代表性實例至少有三個,一是由《三國演義》所啟發的中國人的關羽崇拜;二是《水滸傳》由描摹的江湖規矩被次級社會視為圭臬[1]93-97;三是《西游記》、《八仙過海》、《封神榜》等神怪小說中的人物形象、仙魔法器被白蓮教、義和團成員借用,參與歷史的塑造進程[2]67-72。
實際上,清代學者錢大昕早在乾隆年間便首次提出了“小說教”一詞。他在《潛研堂文集》第十七卷、“雜說一”中的《正俗》篇里指出,“古有儒、釋、道三教,自明以來,又多一教曰小說。小說演義之書,未嘗自以為教也,而士大夫農工商賈無不習聞之,以至兒童婦女不識字者,亦皆聞而如見之,是其教較之儒、釋、道而更廣也。釋、道猶勸人以善,小說專導人以惡。奸邪淫盜之事,儒、釋、道書所不忍斥言者,彼必盡相窮形,津津樂道,以殺人為好漢,以漁色為風流,喪心病狂,無所忌憚。子弟之逸居無教者多矣,又有此等書以誘之,曷怪其近于禽獸乎!”在他看來,說部站在以儒家道統的對立面,起到了教唆偷盜、偷情、不事稼穡、荒廢正務等一系列負面作用。因此,“有覺世牖民之責者,亟宜焚而棄之,勿使流播。內自京邑,外達直省,嚴查坊市有刷印鬻售者,科以違制之罪。行之數十年,必有弭盜省刑之效”[3]272。顯然,錢大昕是以皇權專制制度及其衍生的倫理秩序的捍衛者身份,對小說的價值做出了負面論斷,其言辭帶有鮮明的片面性、偏激性。然而,我們也應承認,他對小說所內蓄的誘導、示范作用已具有了清醒的認識。事實上,小說的“魔力”——在不同的歷史時期被創作宗旨各異的寫作者們拿來充當意識形態的再現工具,或借以蒙昧眾生,或借此開啟民智——在清代被多次提及。譬如,地理學家劉獻廷則談到過,“余嘗與韓圖麟論今世之戲文小說,圖老以為敗壞人心,莫此為甚,最宜嚴禁者。余曰:先生莫作此說,戲文小說乃明王轉移世界之大樞機,圣人復起,不能舍此而為治也。圖麟大駭,余為之痛言其故,反復數千言。圖麟拊掌掀鬢,嘆未曾有”(《廣陽雜記》卷二)[4]72-73。 值得注意的是,在亟需變革的時代,先進知識分子改造、利用小說“魔力”的訴求最為突出。梁啟超在《新小說》的發刊詞《論小說與群治之關系》便將束縛中國社會進步的思想根源直接歸結為小說的惡劣影響(“吾中國人狀元宰相之思想何自來乎?小說也。吾中國人佳人才子之思想何自來乎?小說也。吾中國人江湖盜賊之思想何自來乎?小說也。吾中國人妖巫狐鬼之思想何自來乎?小說也。”),并發出了“欲新一國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國之小說”的號召[5]758-760。可以說,歷代思想家對小說的傳播效應都不乏灼見,但問題在于,無論他們給出的評價是貶抑性的還是中性的,都沒有相對系統、完整地歸納小說教的內涵并就它與紛繁駁雜的民間思想、生活理念之間發生的呼應、互動加以闡釋。綜合以上論述,我們在這里不妨對小說教(或曰小說拜物教)下這樣的定義,即小說(及由小說改編而成的戲曲唱本)中的故事、情節所蘊含的社會理想、群際關系準則、人生價值觀在傳播過程中被閱讀者(觀賞者)接受、放大,繼而被其尊奉為衡量現實人生的思想、道德、行為正確與否的權威標準及仿效范式,終而左右個人行為、思維乃至遲滯/推進社會發展進程的文化學現象。
小說教實際效用的發揮,有賴于小說自身是否具備“代入式”的模仿功能及該功能是否足夠強大。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小說的創作者(及加工者)不僅擔負著編織線索、構設情境、塑造人物、摹寫場面等基礎性工作,更需要勝任調動讀者感官、生成欣賞興趣、滿足接受者對平淡生活的厭倦感和對精彩人生的向往沖動。與此同時,他們還必須尊重既成的社會權力體制,針對公認的(尤其是禮教)文明傳統所倡導的觀念(如忠孝節義等)做適當的讓步。由此,即便是同一部小說,其可能生發出的道德良知約束力與破壞現行政制、社會結構形態的顛覆力也往往會同步存在,從而使文本呈現出矛盾糾結的色彩。無論是《水滸傳》群英的造反——歸順,還是《西游記》孫行者的反叛——皈依,或多或少,皆沾染著回腸蕩氣與回首黯然彼此雜糅的復雜情調,使后人的解讀平添了多義性。
和傳統的單篇小說相比,“三言”的傳播能力顯得得天獨厚:“三言”脫胎于民間說唱藝人的底本,為了在較短的時間里盡可能地吸引觀眾、投合觀眾的欣賞口味,內容的熱辣新鮮、主旨的世俗平易、語言的生動流暢缺一不可。更重要的是,“三言”的篇目囊括了自唐至明的經典(擬)話本,抓住了古代中國民間思想體系中某些最穩定的要素,為小說教的蘊蓄、顯現提供了最大限度的空間。不僅如此,基于作者構成、撰寫朝代、風尚嬗變等情況的千差萬別,小說教的因子在“三言”不同篇目之間、同一篇目內部都有相互印證/彼此沖突的記錄,為窮形盡相地展現小說教的辯證性奠定了基石。綜言之,“三言”是小說教得以寄生、成長的優良母體。以“三言”為觀照對象無疑將為我們深入認知小說教的表象及特征開辟一條富于建設性的路徑。
二、小說教在“三言”中的多維體認及其調和功能
具體來看,小說教在“三言”當中至少表現為彼此相對獨立,間或穿插互證的五個方面:即友情至上、變泰發跡、輕財重義、因果循環與節制欲望。
歌頌友情是中國文學永恒的主題之一。樹立為友盡忠的典型形象的核心目的在于,諷刺、揶揄了建構在物質權利、現實好處基礎上的人我關系,或者說友誼觀。在話本當中,作者對交友之難的感慨被濃縮為題為《結交行》的數首唱詞,如“古人結交惟結心,今人結交惟結面。結心可以同死生,結面那堪共貧賤?九衢鞍馬曰紛紜,追攀送謁無晨昏。座中慷慨出妻子,酒邊拜舞猶弟兄。一關微利己交惡,況復太難肯相親?君不見,當年羊、左稱死友,至今史傳高其人。”[6]37、“種樹莫種垂楊枝,結交莫結輕薄兒。楊枝不耐秋風吹,輕薄易結還易離。君不見昨日書來兩相憶,今日相逢不相識!不如楊杖猶可久,一度春風一回首。”[6]103借以概嘆“末世人心險薄,結交最難”[6]37。有鑒于此,彰顯友誼的忠貞顯然是反擊社會濁流的有力武器。作為《警世通言》開篇之作,《俞伯牙摔琴謝知音》書寫了管夷吾與鮑叔牙的生死交情,這樣的安排從很大程度而言當是編者馮夢龍的有意為之。同樣,以倡揚誓與朋友共生死的精神為主題,馮夢龍梳理、編排了《吳保安棄家贖友》(《喻世明言》第八卷)、《范巨卿雞黍死生交》(《喻世明言》第十六卷)、《羊角哀舍命全交》(《喻世明言》第七卷)、《施潤澤灘闕遇友》(《醒世恒言》第十八卷)等作品,使之成為建構“三言”文本體系的有機組成。在敘事模式上,它們都遵循“雙方結交—友人落難—實施拯救”的寫作理路。細節上的區別在于,拯救朋友的代價或為具有標志性的信物(《俞伯牙摔琴謝知音》);或為數額驚人的私人財產 (《吳保安棄家贖友》、《施潤澤灘闕遇友》);或者是最具終極意義的個人性命。在《羊角哀舍命全交》里,羊角哀為了替亡友左伯桃的鬼魂伸張正義,義無反顧地選擇了以自刎化魂的方式在另一個時空與身為厲鬼荊軻一決雌雄,并在一場慘烈的戰斗之后取得了勝利。
含有倡導重義輕財思想的作品有 《呂大郎還金完骨肉》(《警世通言》第五卷)、《杜十娘怒沉百寶箱》(《警世通言》第三十二卷)、《三孝廉讓產立高名》(《醒世恒言》第二卷)、《十五貫戲言成巧禍》(《醒世恒言》第三十三卷)及《一文錢小隙造奇冤》(《醒世恒言》第三十四卷)等。需要解釋的是,這些作品所指涉的“義”應被劃歸入社會規則范疇,并可以被理解為符合集體性公正—合理原則的廣義道德標準。站在“義”的立場上,對財物的垂涎覬覦、無禮占有都會招致“命定”的災禍,反之,“自覺”放棄意外之財則會“自然”帶來綿延的福澤。《呂大郎還金完骨肉》以對比的方式演繹出了對“義”所采取的順逆態度及其附帶后果。在引子中,浙江嘉興府長水塘地方的吝嗇財主金鐘不肯施舍僧侶,繼而投毒殺僧,反致誤害幼子、家破人亡;而正文里的常州府無錫縣平民呂玉卻能夠不貪圖意外之財,苦苦找尋失主,最終,在失主的幫助下,呂玉找回了失散多年的兒子并發家致富——顯然,金鐘、呂玉所經歷的階級地位逆轉、家庭倫理調整的根源在于兩者是否遵循“義”的基本要求并付諸實踐。這個道理用故事點評者所題的詩歌來表述,那就是,“天上鳥飛兔走,人間古往今來。昔年歌管變荒臺,轉眼是非興敗。須識鬧中取靜,莫因乖過成呆。不貪花酒不貪財,一世無災無害。”[6]237最能踐行“義”的話本莫過于《三孝廉讓產立高名》。在《三》中,許氏兄弟骨肉相愛、妯娌和睦,在家產分割問題上展現出了大公無私、推讓與人的良好品格,恰如其分為“紫荊枝下還家日,花萼樓中合被時。同氣從來兄與弟,千秋羞詠豆萁詩。”[6]9添加了生動的注腳。類似地,《十五貫戲言成巧禍》、《一文錢小隙造奇冤》中的悲劇故事之所以會上演,都無一例外地源于始作俑者對“財”的割舍不下、對“義”的忽略不行。實際上,不貪財絕非“義”的內涵的全部,不違背誓約也是它的構成因子。《杜十娘怒沉百寶箱》、《王嬌鸞百年長恨》故事女主人公的愛情悲劇都與男主人公的背信棄義構成鮮明的因果關系。在《杜》中,出于軟弱、自私的性格和對禮教觀念的屈從,李甲狠心拋棄了從良的名妓杜十娘,使后者在痛斥負心漢李甲、登徒子孫富之后,怒沉百寶箱并憤而投江自盡;而在《王》里,周廷章為青云直上而另攀高枝則釀成了王嬌鸞羞憤難當、抑郁自戕的慘劇。違背承諾的不“義”之舉害人害己、令人不齒。
因果循環、報應不爽構成了“三言”小說教系統的第三個層面。“三言”中的相關篇章文學化、世俗化地解釋了佛教中的因緣果報論,前者并不執著于后者所包含的深奧知識,規避了后者所特有的晦澀用詞(如異熟、等流、增上、三惡道等等),而是以簡單直白的口語講述犯戒與守戒各自意味著什么,并證明果報在冥冥之中早已存在。這樣的話本被集結在《喻世明言》的后半部分,它們分別是《月明和尚度柳翠》(《喻世明言》第二十九卷)、《明悟禪師趕五戒》(《喻世明言》第三十卷)、《鬧陰司司馬邈斷獄》(《喻世明言》第三十一卷)、《游酆都胡母迪吟詩》(《喻世明言》第三十二卷)、《李公子救蛇獲稱心》(《喻世明言》第三十四卷)、《薛錄事魚服證仙》(《醒世恒言》第二十六卷)。其中,《月明和尚度柳翠》講的是高僧觸犯色戒而導致一系列悲劇性的連鎖反應:犯戒者必將墜入輪回道,而誘使犯戒的元兇也將難逃報應的羅網。有道高僧玉通禪師被出于惡作劇心理的柳府尹設計而破了戒,遂坐化轉世,成為柳府尹的獨生女,成人后主動獻身娼門將柳家曾經的清白門風滌蕩地一干二凈,使柳府尹活活氣死,報了前世的夙仇。《明悟禪師趕五戒》則敘述了禪師之間的援救經過。明悟禪師偶入魔道,不得不面對失卻慧根、墜入阿鼻地獄的命運,他的摯友兼師兄五戒禪師與之同日入寂,在來世成為佛印長老與才子蘇東坡,通過佛印的指點度化,蘇氏最終大徹大悟,皈依正途。《李公子救蛇獲稱心》、《薛錄事魚服證仙》試圖證實人應當對動物(生靈)懷有慈愛之心而不可為滿足食欲而狂捕濫殺。《鬧陰司司馬邈斷獄》、《游酆都胡母迪吟詩》借助“文人游地獄”的敘事模式,表明“命運前定”、萬事有因也有果的主旨。對慘淡人生滿懷牢騷的落魄文人司馬邈、胡母迪,被地府的掌管者帶至幽冥世界見證人類的命運安排與其前生、今世、來生的所作所為之間所固有的邏輯關聯。別具意味的是,司馬邈甚至被邀請參與評判、決定昔日的人間帝王、忠臣良將在未來的生命際遇,顯示出了小說本身屬文人小說、寄寓文人趣味的審美取向。
有別于說佛談禪的清淡刻板,變泰發跡故事因其驚心動魄更能滿足市民階層渴望財勢兼收、出將入相的文化品位。在此情形下,與之適配的話本及擬話本應運而生。若按照主人公的政治作用來加以區分,這些故事可分為文人受圣眷入朝為臣(《警世通言》第六卷《俞仲舉題詩遇上皇》、《警世通言》第十七卷《鈍秀才一朝交泰》、《喻世明言》第十一卷《赴伯升茶肆遇仁宗》)、武將打天下風云際會兩類(《喻世明言》第十五卷《史弘肇龍虎君臣會》、《喻世明言》第二十一卷《臨安里錢婆留發跡》、《醒世恒言》第三十一卷《鄭節使立功神臂弓》)。但無論具體分類如何,變泰發跡者愿望的達成都離不開三重因素的促成:其一是他們自身天賦異稟,要么才華橫溢,要么氣力過人;其二是權勢的掌握者能夠在偶然的場合“巨眼識英雄”,且與之結成類似于桃園三義的“兄弟+君臣”關系,共同謀取更大的利益;其三是周圍人群的無私幫助和鼎力提攜。最能體現這三者互動及其影響力的當屬《鄭節使立功神臂弓》。故事中的鄭信曾是罪人,后來因機緣巧合冒死勘探深井,竟意外進入仙境,與嬌媚的仙女成婚,并依憑仙妻的力量成就了蓋世功業。毫無疑問,烏托邦話語在變泰發跡文本中俯拾皆是。幾乎雷同的情節設置、大同小異的敘事脈絡一次次被重復、模仿,但依然可以長盛不衰,被聽者和觀眾所接納。究其原委,踏上便捷快速的上升管道實現衣錦還鄉、光耀門楣的樸素沖動很容易被前述的故事所喚醒重啟,虛擬的“成功者”被現實的百姓視作樣板來加以膜拜、品談,借以為沖淡平凡人生增添一抹亮色。然而,變泰發跡故事存在客觀上的風險,那就是:受眾一旦突破真假之間本來就不明晰的界限(這些故事形象本來便是歷史人物),并從榜樣的“上進之路”中汲取了營養和靈感,把舞臺從瓦肆勾欄直接搬到殺戮戰場,演出“王侯將相寧有種耶”的活報劇,“戲”假“做”真,擾動現有的政治格局和社會面貌。為了制衡、調控這一危險苗頭,“三言”以大量篇幅對節制欲望的人生態度和克己復禮的生活方式予以大加倡導,繼而構建出了維護“三言”小說教系統正常運行的整體安全機制。
蘊含節欲主題的故事不下29篇,依次為《崔待詔生死冤家》、《蘇知縣羅衫再合》、《趙太祖千里送京娘》、《桂員外途窮懺悔》、《白娘子永鎮雷峰塔》、《宿香亭張浩遇鶯鶯》、《金明池吳清逢愛愛》、《趙春兒重旺曹家莊》、《喬彥杰一妾破家》、《王嬌鸞百年長恨》、《蔣淑真刎頸鴛鴦會》(《警世通言》第八、十一、二十一、二十五、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三、三十四、三十八卷),《蔣興哥重會珍珠衫》、《陳御史巧勘金釵鈿》、《新橋市韓五賣春情》、《閑云年庵阮三冤債》、《簡帖僧巧騙皇甫妻》、《宋四公大鬧禁魂張》、《梁武帝累修成佛》、《任孝子烈性為神》、《汪信之一死救全家》、《沈小霞相會出師表》(《喻世明言》第一、二、三、四、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卷),《赫大卿遺恨鴛鴦絳》、《陸五漢硬留合色鞋》、《張孝基陳留認舅》、《金海陵縱欲亡身》、《隋煬帝逸游召譴》、《吳衙內鄰舟赴約》、《杜子春三入長安》、《汪大尹火焚寶蓮寺》(《醒世恒言》第十五、十六、十七、二十三、二十四、二十八、三十七、三十九卷)。這樣一列數目客觀的文本組合彼此呼應,訓誡世人在處理金錢、美色、權力時一不可違背良心、有悖天理,二不可隨心所欲、恣意妄為,三不可不聽良言、執迷不悟。值得注意的是,前面提到的小說教的構成主體——友情至上、變泰發跡、輕財重義、因果循環聯合為節制欲望這一機制提供運轉動力——男女相約,男子縱欲橫死,原是前世冤孽(《閑云年庵阮三冤債》);雁過拔毛、從不仗義疏財者終將自食其果(《宋四公大鬧禁魂張》);英雄身為草莽時便已具有自覺抵拒美色誘惑的成事利器 (《趙太祖千里送京娘》);色欲熏心、狡計百出,欺男霸女得到的只能是“枉送了性命,好一似食盡鳥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凈”的悲涼結局(《金海陵縱欲亡身》)。
總體而言,構成“三言”小說教體系的友情至上、變泰發跡、輕財重義、因果循環與節制欲望五大板塊之間是以彼此交融、相互紐結的形式呈現出來的。它們立足市民文化消費需求,基于一代代文人的加工改良,被揉入了世俗力量與欲望和文化人構筑禮法社會、清明政治的期望。這兩種力量有交集,有抵牾,但最終歸于妥協和修正,穩定、沉淀并固化為“三言”小說教得以合理存在、經久不衰的社會—文化基礎。
三、結語:中國小說近代化演進與小說教的新變
有識者指出,小說教的最大功用在于參與塑造中國民間社會,特別是次級社會(江湖社會構建),或者說,小說教對既有的非主流/離經叛道的思想殘片進行整合并有所創新,結晶出相對完整的思想意識體系,為未來的社會組織重構,乃至政權更迭做好鋪墊[7]16-17,這樣的論斷在學理上無可指摘。而當我們放寬探究的視野之后,將不難看出,小說教的工具性價值是使之被宗法社會、皇權政體同時接納的關鍵所在。誠如馮夢龍所言,“通俗意義”足以使“怯者勇,淫者貞,薄者敦、頑鈍者汗下。雖小誦《孝經》、《論語》,其感人未必如是之捷且深也。”(《喻世明言》序言)。填補單一倫理說教的教條性、機械性所致的接受鴻溝,小說責無旁貸,從書齋案幾走向街頭市井,化為教化宣講的有效載具,體現“文以載道”的終極目的。隨著歲月的演進,時至天演之說席卷海內的近世,小說教所包含的內容成分被先進知識分子視作阻礙中國社會進步、敗壞民族心靈的毒藥而大加批判。為了中國的新生,“雕琢的阿諛的貴族文學”、“陳腐的鋪張的古典文學”、“推倒迂晦的艱澀的山林文學”理應被打倒,而“平易的抒情的國民文學”、“新鮮的立誠的寫實文學”、“明了的通俗的社會文學”必須被建設 (陳獨秀:《文學革命論》)[8]95-98——作為文化先覺者的知識精英不但義憤填膺,并且身體力行,掀起了涵蓋小說、詩歌、散文、戲劇等文學體裁的改革狂飆。在這樣的大潮沖擊下,小說從創作立意到敘事形式都受到了徹頭徹尾的革新,但就小說教的發展態勢而言,它并未消亡枯萎,而是以更換荷載對象/裝填材料的方式繼續發揮其參與歷史、構建社會的核心功能,生動體現出了中國文學泛政治化的本質屬性。
[1]王學泰.游民文化與中國社會(上下冊)[M].北京:同心出版社,2007.
[2](美)柯文(Pail A.Cohen).歷史三調:作為事件、經歷和神話的義和團[M].杜繼東,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0.
[3][清]錢大昕,著.陳文和,主編.嘉定錢大昕全集(第九冊)[M].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
[4][清]劉獻廷.清代史料筆記叢刊:廣陽雜記[M].北京:中華書局,1957.
[5]梁啟超.飲冰室文集點校本(第二集)[M].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
[6][明]馮夢龍編著.喻世明言[M].北京:中華書局,2009.
[7]王學泰.王學泰自選集:江湖舊夢[M].北京:中國華僑出版社,2012.
[8]陳獨秀.獨秀文存[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
Novel Fetishism:Classical Novels'Morality and Desire Coordination and Regulation Mechanism
WANG Zhu1,2
(1.Graduate School of Anhui Normal University,Wuhu,Anhui 241000,China;2.Publicity Department of Anhui Business College of Vocational Technology,Wuhu,Anhui 241000,China)
Ideological education function and entertainment function exist paradoxically in popular novels of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at the same time.They are regulated by the“novel fetishism”in two ways,on one hand,advocating the friendship,prizing righteousness and benevolence which subject to group interests and moral paradigm;on the other hand,showing a variety of possibilities of getting success and richness,meeting the public desire for status and wealth.With the help of the vivid narration of circular causation and controlling desire,the“novel fetishism”guide the essentially conflicting concept of fame and fortune into the predetermined way that constituted by conscience and foreordination.
novel fetishism;Stories from a Ming Collection;morality;desire;harmonic mechanism theory
I207.419
A
1008—7974(2014)04—0055—05
2014-04-26
汪注(1981-)安徽蕪湖人,講師,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國近現代文學思潮。
(責任編輯:章永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