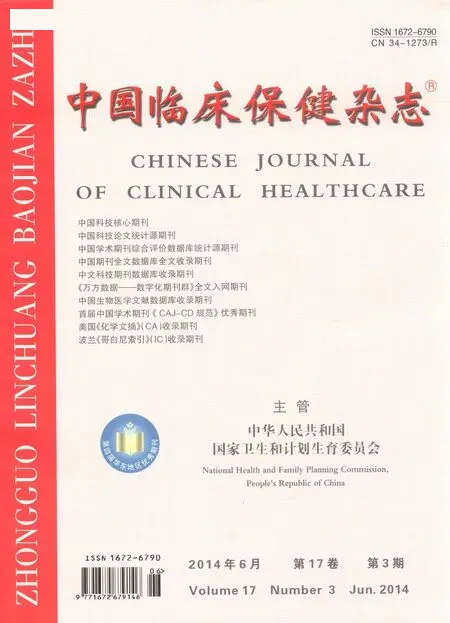住院腫瘤患者死亡焦慮及其影響因素初探
胡成文,丁娜,丁從蘭,曹艷宏
(安徽省腫瘤醫院、安徽醫科大學附屬省立醫院,a西區護理部,b腫瘤內科,合肥 230031)
住院腫瘤患者死亡焦慮及其影響因素初探
胡成文a,丁娜a,丁從蘭b,曹艷宏b
(安徽省腫瘤醫院、安徽醫科大學附屬省立醫院,a西區護理部,b腫瘤內科,合肥 230031)
由于社會普遍缺乏對死亡提醒后嚴重心理反應的應對能力,腫瘤的診斷過程是一個信號極強的死亡提醒,至確診時達極點,當這種死亡必然性被提醒時,患者的內心深處受到死亡威脅,從而產生一種恐懼性情緒狀態,即死亡焦慮(DA)[1-3]。腫瘤的生存期幾乎成為許多患者的苦難期和其家庭的恐懼期、迷茫期和貧困期[4]。在發達國家,腫瘤像其他慢性病健康管理一樣,其“帶瘤生存”的生命數量和質量均得到有效地維護[5-6]。“帶瘤生存”是在以維持機體對腫瘤的反應性的前提下,穩定腫瘤,使其休眠,從而達到延長生存期和改善生命質量的目的,這種腫瘤治療新理念也在我國興起,其前提是具備必要的生理和心理學狀態[7]。本研究旨在了解住院患者的死亡焦慮水平及其影響因素,為開展死亡教育和改善帶瘤期生存質量提供依據。
1 對象與方法
1.1 調查對象 于2013年5月至7月,采用整群抽樣方法對我院內科系統101名住院患者進行了死亡焦慮調查。年齡18~87歲,平均(50.5±15.6)歲;男63例,女38例。均取得患者知情同意。納入標準:①成年、內科系統住院患者;②能夠理解量表內容并能做出相應回答;③愿意接受調查。排除標準:①未成年患者;②接受復雜手術期間;③對死亡主題特別忌諱或不愿介入者;④不能理解量表內容,有嚴重溝通障礙者。
1.2 調查方法 死亡焦慮量表采用經過跨文化調適、修訂而成的中文版T-DAS。該量表含15個條目,采用“是”、“否”回答,總分范圍0~15分,分值越高表示死亡焦慮越嚴重[8]。中文版量表的內部一致性Cronbach’α系數為0.71,總量表重測相關系數為0.831。調查工作由病房責任護士擇機執行,調查環境相對封閉,在患者家屬陪同下由患者獨立完成。
1.3 統計學處理 采用SPSS 11.5軟件進行統計分析,分類資料采用頻數描述和χ2檢驗,數值變量采用t檢驗或方差分析。
2 結果
2.1 患者人口統計學描述 調查對象受教育水平:本科或大學15例(14.85%)、高中或中專22例(21.78%)、初中30例(29.70%)、小學及其以下34例(33.66%);職業:農民52例(51.49%)、工礦企業8例(7.92%)、文教衛生8例(7.92%)、公司職員4例(3.96%)、商業流通3例(2.97%)、其他26例(25.74%);婚姻狀況:已婚狀態91例(90.10%)、其他如單身或離異10例(9.90%);居住:城市39例(38.61%)、農村62例(61.39%);信仰:無宗教信仰82例(81.19%)、有宗教信仰19例(18.81%%),主要是信仰佛教。
2.2 死亡焦慮評價 101例患者DA得分為(6.91(3.30)分(范圍0~14),與國內大樣本(n=500)研究比較[3](6.75±3.04)分,經獨立樣本t檢驗,t= 0.4873,P=0.6271,差異無統計學意義。性別比較:男(6.56±3.33)分,女(7.50±3.21)分,t= 1.40,P=0.1649。
2.3 死亡焦慮主要影響因素 經兩組間t檢驗或多組間方差分析,死亡焦慮得分除了患者居住地在城(39例)、鄉(62例)間差異有統計學意義[(6.03 ±2.81)分比(7.47±3.49)分,t=-2.18,P= 0.0319)]外,其他如受教育水平、職業、婚姻狀況、居住地、目前治療手段、是否有宗教信仰、是否接受過死亡教育、是否參與他人臨終處置、是否參加他人遺體告別、是否目睹過嚴重事故、近5年是否有至親去世、近5年是否有威脅事件組間均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
3 討論
3.1 腫瘤患者死亡焦慮的影響因素 腫瘤的診斷對任何人來說,打擊都是致命性的,中國人的死亡焦慮或恐懼還與中國人特有的人倫未盡的遺憾有關[9-10]。本研究中,農村居民的死亡焦慮顯著高于城市居民,可能與這種差異有關。探索死亡焦慮的緩沖機制,必須圍繞著患者死亡焦慮產生的影響因素,才具有針對性。
3.2 對腫瘤患者死亡焦慮的評價 我國至今仍缺乏構建基于本土化的死亡焦慮評價方法,現有的死亡焦慮評價量表是在國外研究的基礎上,融入的跨文化要素,以北京中醫藥大學、北京大學醫學部、首都醫科大學等三所醫學院校的大學生,北京老年病醫院、朝陽門醫院兩所醫院的臨終關懷科室醫務工作者作為研究對象而產生的[8],可以理解該量表應用于腫瘤患者,還有許多研究尚待開展。本研究可見患者的DA得分與其差異無統計學意義,且在傳統學術背景下的主要影響因素也多為陰性結果,可能該量表的靈敏度和特異度還不夠,尚需從研制DA評價量表開始探索研究,也可能與腫瘤作為死亡提醒信號過強、本研究樣本量較小有關。
[1] Choi JY,Chang Y J,Song H Y,et al.Factors That affect quality of dying and death in terminal cancer patients on inpatient palliative care units:perspectives of bereaved family caregivers[J].J Pain Symptom Manage,2013,45(4):735-745.
[2] 傅晉斌,郭永玉.死亡提醒效應的心理機制及影響因素[J].心理科學,2011,34(2):461-464.
[3] Schmeichel BJ,GailliotMT,Filardo EA,et al.Terrormanagement theory and self-esteem revisited:the roles of implicit and explicit self-esteem in mortality salience effects[J].JPers Soc Psychol,2009,96(5):1077-1087.
[4] 談學靈,曾濤.中年住院患者家屬的死亡態度及死亡教育需求的調查[J].解放軍護理雜志,2012,29(10):6-9.
[5] 楊紅,韓麗沙.死亡焦慮及其量表的研究與發展[J].醫學與哲學:人文社會醫學版,2012,33(1):44-46.
[6] Abdel-Khalek AM.Death anxiety in spain and five arab countries[J].Psychol Rep,2003,93(2):527-528.
[7] 陳淼,郭勇.“帶瘤生存”理念運用的思考[J].中華中醫藥雜志,2012,27(12):3193-3194.
[8] 楊紅.死亡焦慮量表的跨文化調適及其應用的研究[D].北京:北京中醫藥大學,2011.
[9] 鄭曉江.生命困頓與生命教育[J].南昌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2,2(1):11.
[10]王定功.人的生命價值研究[D].北京:北京交通大學,2012.
R395.3
B
10.3969/J.issn.1672-6790.2014.03.037
2014-02-18)
胡成文,副主任護師,Email:huchengwen318@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