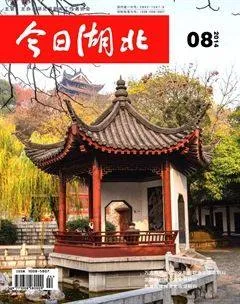虐童行為的刑法定性及虐待罪的立法完善
石建軍 田超群
摘 要 頻頻曝光的幼師虐童事件引發社會的關注,暴露了我國刑法對虐童行為刑事處罰上存在法律空白的尷尬境地。我國現行刑法難以將諸多“虐童”行為合理評價和規制。面對社會中出現的新問題,對“虐童”行為規制的應然路徑應在于對現有刑法進行修正、完善現有虐待罪的條款、適當擴大虐待罪的主體范圍,發揮刑法在兒童等弱勢群體保護上的應有作用。
關鍵詞 虐童行為 虐待罪 立法完善
一、虐童行為的立法現狀
我們國家多年來在保障兒童權利方面所做的工作已經取得了巨大成就,1990年9月中國政府簽署了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及《兒童生存、保護和發展世界宣言》,1991年頒布了《未成年人保護法》,但這些基本上是綱領性的法律,實際操作依據不足,無規制虐童行為的專門立法。浙江溫嶺城西街道某幼兒園教師顏某虐待兒童事件依據的是《治安管理處罰條例》進行的處罰,而行政處罰、治安處罰對行為人來說威懾力有限。虐童行為入刑十分必要和迫切。
二、虐童行為現行刑法的規制分析
(一)“尋釁滋事罪說”及其問題
浙江溫嶺城西街道某幼兒園教師顏某虐待兒童事件中,顏某多次對幼兒園學生以膠帶封嘴、倒插垃圾桶等方式進行虐待,并拍照取樂。公安機關在社會各界的輿論壓力下選擇了一種作為“兜底”罪名的的尋釁滋事罪。這樣認定確有不妥,首先,從侵害法益方面看,刑法規定尋釁滋事罪,旨在保護公共秩序或社會秩序。虐待兒童案中的虐待行為是發生在封閉的、人數特定、與社會公共環境較為隔離的教室內,很難歸結為對社會公共秩序的破壞。其次,在客觀行為構成要件方面,雖尋釁滋事罪的客觀行為也包括隨意毆打他人,情節惡劣以及追逐、攔截、辱罵他人,情節惡劣等內容,把虐待兒童的行為定性成為尋釁滋事行為,超出國民預測的可能性。
(二)“侮辱罪說”及其反思
有學者認為,教師虐待兒童的行為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侮辱兒童人格尊嚴和名譽的性質,應以侮辱罪定罪處罰。是否構成侮辱罪首先要從侮辱罪保護的法益入手,分析虐待的行為是否具有公然性。名譽有三種含義:外部的社會生活名譽、內部的私密生活名譽、被侮辱人本身以為的名譽。虐童行為發生在較私密的場所,不具有公開性。另外,侮辱罪屬于告訴才處理的犯罪。在被虐待的兒童及其家人沒有主動提出告訴的情況下,公安機關不能直接追究行為人的刑事責任。虐童行為構成侮辱罪不甚妥當。
(三)“虐待罪說”及其解讀
對于性質上最接近幼師虐待兒童行為的虐待罪,按照我國現有刑法理論也無法定罪。我國刑法中的虐待罪,是指對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員以打罵、捆綁、凍餓、限制白由、凌辱人格、不給治病或者強迫作過度勞動等方法,從肉體上和精神上進行摧殘迫害,情節惡劣的行為。本罪侵犯的客體是家庭成員在家庭中的合法權益,主要是家庭成員之間的平等權利。教師當然不是家庭成員,不能成為虐待罪的主體。
(四)“猥褻兒童罪說”及其闡釋
猥褻兒童罪,是指以刺激或滿足性欲為目的,用性交以外的方法對兒童實施的淫穢行為。不滿十四周歲的男童女童都可以作為本罪的受害人或猥褻對象。仍以浙江溫嶺城西街道藍孔雀幼兒園女教師顏某虐童事件為例,有學者認為顏某逼迫幼兒之間進行親吻,擁抱等親密動作,目的是滿足自己的性欲,應以猥褻兒童罪定罪處罰。但顏某的行為主要是為了好玩而對幼童進行體罰和虐待行為,并不符合猥褻兒童罪的構成要件。
(五)增設“虐待兒童罪”之不可行
首先,增設“虐童”新罪不是防治“虐童”現象頻發的必要保證。美國早在1974年就通過了《兒童虐待預防與處理法案》,對虐待兒童罪名的認定、調查處理和救濟措施都作了詳盡的規定,現已建立起強制報告、受理調查、必要時帶離監護人、永久安置聽證等完善的應對體系和處理機制,即便如此虐童現象仍然頻發。應以“兒童利益最大化原則”為指導,建立健全我國兒童保護的法律規范,完善我國兒童福利多元化保障體系,才是預防“虐待兒童”行為的最有效方式。
其次,我國現行法律規范體系傾向將“虐童”行為歸入虐待罪。我國修訂刑法和出臺的解釋已體現出擴大虐待罪規制范圍的傾向。2010年出臺的《關于依法懲治拐賣兒童犯罪的意見》第20條規定,明知是被拐賣的婦女、兒童而收買,同時對被收買的婦女、兒童有強奸、傷害、侮辱、虐待等行為的,按照數罪并罰的進行處罰,即按照收買被拐賣的婦女、兒童罪和虐待罪(或其他罪)進行并罰。而收買者并不屬于虐待罪的主體范圍。
三、完善虐待罪的刑事立法建議
(一)擴大虐待罪的主體范圍
與遺棄罪同屬于侵犯公民人身權利、民主權利罪的虐待罪完全可以借鑒現在理論界和實務界都逐漸承認的非家庭成員間也可構成遺棄罪,從而擴大虐待罪主體范圍。將雖然沒有家庭成員之間的關系,但共同生活在一起,形成具有緊密聯系的權利義務關系的成員納入主體范圍,凡是具有長期性施虐行為而又無法歸置于傷害罪調整的侵害他人人身法益的情形,均可以虐待罪進行規制。
(二)“情節惡劣”的規定不應刪除
首先,虐待罪中“情節惡劣”的規定具有一定的模糊性,我國刑法中許多罪名定罪情節的具體內容是通過司法解釋得以明確的,尤其是在司法過程中,更需要對法律規范作出明確的解釋,從而正確地適用法律和公正地裁判案件,以適應復雜多變的審判實踐需要。
其次,“情節惡劣”作為定罪情節,是區分虐待罪與非罪的重要標準。若不以“情節惡劣”作為虐待罪的構成要件,就無法將其與一般的虐待行為相區分。情節犯對復雜犯罪的刑事司法實務具有很強的適應性,情節犯對于加強法律的柔軟性與限制刑罰權的發動也有很大影響。
(三)將“虐童”犯罪作為虐待罪“親告”的例外
如果“虐童”犯罪屬于親告罪,將非常不利于保護未成年人的合法權益。筆者認為,親告罪的障礙并不難解決,可以將虐待兒童行為與虐待致被害人重傷、死亡行為一同作為虐待罪告訴才處理原則的例外,更好地保護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維護其合法權益,同時也體現了刑法對此種犯罪懲罰的嚴厲態度。
參考文獻:
[1]吳允峰.英國:防止虐童立法完備、高效[N].法制日報,2012-11-27.
[2]李慧翔.“虐童”事件:國外是怎樣預防的[N].新京報,2012-11-03.
(作者單位:河北大學政法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