靈魂深度的刻寫與鏡像的自我表達
龔奎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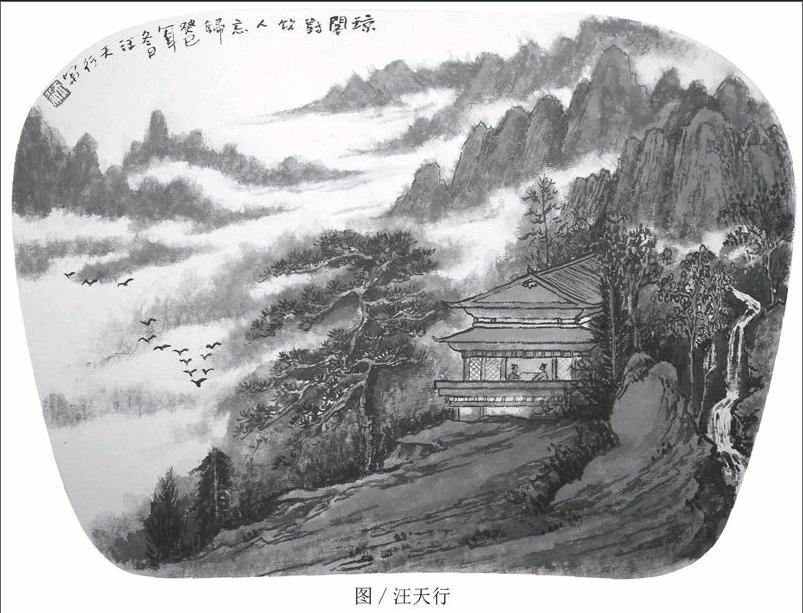
目前江西詩壇主要是靠60后、70后中青年詩人在支撐,能夠接上詩歌棒的80后、90后新銳者不多,導致有點代際斷層現象,值得警惕,這可能與人口基數較少有關,也可能與“孔雀東南飛”相關,還可能與經濟欠發達有關,更主要的還是與詩歌氛圍及媒介缺失有關。
江西沒有真正能夠堅持持久的詩歌刊物,無論是官刊亦或是民刊。所以江西詩壇需要有杞人憂天的眼光,需要有補充新鮮血液的胸懷,尤其需要有刊物對詩歌及詩人的刊載與傳播。如今,《創作評譚》在過去一直關注江西詩歌的基礎上,辟出專欄“詩江西”,以扶持江西的詩歌發展,我感到非常興奮,希望這種堅持能夠一直伴隨江西詩壇的成長!
顏溶、三子、林莉、汪澤、傅菲等都是江西非常有實力的代表性詩人,他們的所思所行也暗含著江西詩壇發展的未來方向。五位詩人的本次作品與以往江西詩壇重鄉土路徑的風格有點不一樣,開始轉向關注日常生活,以人文關懷的眼光、敏感的藝術直覺和個體化經驗,介入時代與物質碰撞的生活低處及經驗世界和歷史想象,挖掘物質與技術雙重壓抑下的現代人的生存狀態、靈魂真空和欲望訴求,進而建構自由的詩意棲居地和審美空間,獲得主體鏡像的自我認同。我認為這是江西詩歌走出地域局限向全國詩壇整體邁進并取得實效的重要一步。
詩歌要感人,首先要引人思考觸及靈魂,打動讀者內心深處最柔軟最隱秘的內核,這就需要詩人在創作中融入悲憫氣質和博愛情懷,顏溶的詩歌就是如此,其詩《修女特蕾莎》、《仰望》、《熟睡的女人》就涌動著愛、悲憫與感恩。正如他自己所說:“一個真正的詩人永遠懷有人類的悲憫與關懷。他應該是高尚的,即使他在這個被時代命名的高尚者中間永遠缺席。”因為人性的殘忍、因為獨裁的貪婪、因為權力者的攀比,天災人禍無時不在大地上吐露自己邪惡的信子,于是,戰爭、饑餓、疾病、災難、旋渦、暗礁、陰霾、蛆、炎癥肆虐著千瘡百孔的大地。
如果說《修女特蕾莎》是詩人仰望的目標,那么《仰望》則是自我的救贖,渾濁的時光、腐爛的星光、善惡的交叉、膨脹的欲望、吸吮貪婪的蒼蠅不僅建構起生存的陰暗,更提供了人性貪婪的暗示,腐蝕著秩序的法理性,理想與道德“正慢慢淪陷”,詩人在這種人生的困境中非常警醒,極力建構起精神保護的屏障,自覺地抵抗“被同化”的悲劇命運。
與上述兩首的沉重不同,《熟睡的女人》則用口語化的語言營造一種溫情而唯美的意境,詩人落筆在生活的細部去咀嚼生命的大愛,直面人生的意義與親情的溫馨,同樣是寫女人,但這個“熟睡的女人”無疑是詩人自我鏡像的呈現,因為兩者之間在血緣的牽連下已經心靈相通,成為“我”呵護及思念的想象性所在。
當下的中國,已經徹底地進入了農耕社會向工業社會轉變的轉型期,現代化機械復制時代的蒞臨一方面推動科技的發展、社會的進步,另一方面也給社會帶來暗傷與苦痛。
三子的《逍遙記》《美人記》詩意濃郁,詩境清新,語言簡潔,其抒情方式安靜、從容坦率而又細膩婉約,把個體經驗轉化為獨具生命詩意與人文情懷的哲思,這種詩意哲思隨著“我”的時空變化和人生軌跡獲得升華,使得其書寫極富現場感和存在感。《逍遙記》書寫“我”對未來、對信念、對美麗新世界的渴望與追求。“我”鄉土養育的,血管里流淌著泥土的芳香,因為“我的春衫是蟲子的蛻殼做的/輕巧的鞋子,是去年的草編的/甚至,包括我的身子,身子里的每一根骨頭/都是用江南最粘密的土,捏的”,這種隱喻化的語言也正表明了“我”所存在的家園與精神的根,但“我就要到遠方去”,“把江山、清風/連同多余的皮囊舍在身后”,詩人通過“我要到更遠的遠方去”句式的反復來強化這種孤絕與悲壯,盡管要“趟過漸漲的河水/翻過丘陵,這就到一次次談論過的遠方去”,但不改自己的志向,目標依然直指前方,這是難能可貴的。雖然詩人沒有說明“去”往何方,也許為了尋找愛情,也許為了尋找更好的棲居地,也許為了尋找詩意的故鄉,也許為了實現自己的夢想,也許為了追求自己的幸福,“遠方”已經成為了一個理想的詞,與現實無關,與經驗無關。
于是“我”輕裝上陣,辭別萬物:“告訴連綿的細雨”,“碰見搖尾巴的狗,說一聲告辭”,“看到田野里站著的一頭牛,道聲再見”,幽默的語言、物化的意象、可愛的精靈、使得詩歌充滿情趣,顯得輕靈飄逸,也呈現出幽隱的透明與志趣。《美人記》語言也較為精致純正,全詩詩意飽滿。詩人以白描寫意和影像透視的言說方式抒懷美麗的精致與個體的艷羨,一輩子的光陰濃縮在短短的詩行,不可企及的傷感也在“我”的遙遠祝福和欲望化注視中彌漫,如同煙霧。
林莉的《嘉峪關》厚重沉郁,呈現出鏗鏘大氣與家國情懷的氣象。詩人走著托物言志、直抒胸臆、以小見大、以古寫今的路子,通過敏銳地觀察、想象嘉峪關的古與今,還原歷史的厚度與現實的廣度,以慷慨激昂的姿態實現自我對自然的力量、歷史的關懷和人類文明史的現實處境的思考、認知和感悟,“撫摸著這些厚實的墻磚,隨風/逐一走上寂然無語的箭樓、敵樓、角樓、閣樓”,感懷歷史,想象當年的英勇多姿,多少勇士以自己的血肉之軀保衛祖國的邊疆,“塵沙陣陣,西去千千里,仍是我的漢唐疆!”換取國家的幸福安寧。但她的經驗沒有局限在嘉峪關這一“小”部,而是通過“小”部細節的不斷膨脹與影像化透視呈現生命的大氣,文化的懷柔遠比武器的堅硬要更重要,“駝鈴聲中,我目送一隊隊馱伏著中華文明的商旅遠行/越過極邊,繼續向西,向西……/日暮后,我偶爾會念想起我的中原故土/淚濕雙眸,似聽到妻兒的呼喚:胡不歸兮,我的夫君,我的父親!”人性的力量與文化的光芒照亮著大地的幽暗與沉重,那種悲壯情懷駐守在詩人內心,并通過夫妻的時空對話呈現出來,極其震撼。同時,詩人在文化地理時空的聚合與流變下,借助古代邊塞雄渾的禮贊來呈現當下的發展:“如今的嘉峪關市,大漠邊緣的一顆明珠/生命和希望的綠洲因為召喚而一刻不停地奔涌著時尚的潮流”,邊疆的和平推動了祖國的發展,唯有祝愿我們的祖國繁榮昌盛、永遠和平。最后一節“嘉峪關/誰是誰的關隘,誰又是/誰的城堡”是全詩之眼,詩意厚實,哲思幽深,具有相當的高度,詩人在語言追問的基礎上注入思想的力量,探求真理的鋒芒。但是,她的開頭兩句“一座關城,吾國脊梁不可缺少的一塊骨節/一座關城,堅守吾族完整意志的巨靈”的說白與全詩的大氣形成反差,降低了全詩的格調,確是可有可無。
別林斯基認為:“詩歌是生活的全部,或者更確切地說,就是生活本身。”但問題在于如何把生活的哲思、深度和廣度呈現出來,這是考驗一個優秀詩人的分水嶺。詩人汪鐸深入生活的細處、事物的內部,關注愛、自然、生命、死亡等話題,介入和體驗社會真實狀態,直陳現代人生活中的孤獨、寂寞、苦痛與陰暗,探索人類靈魂與精神的困境,進而思考人類生存世界的主體秩序,追問痛苦之由、生之意義和死亡之謎。《蟋蟀》、《這些鳥》、《月光下的河流》、《南山》、《祭奠》、《接站人》等詩語言干凈,詩意單純,詩思流暢,矛盾、孤寂、糾結、憂郁和焦慮加深了詩歌張力的深邃,顯現出悲憫的氣質和博愛的情懷。蟋蟀、鳥、河流、南山、野蘿卜花、接站人無疑是自我心靈鏡像的外化投影,更是主體分裂成無數個體在自我認知世界的折射,意象的反復出現不斷深化自我的困境體驗,獲得自我的鏡像認同。“一條河流需要忍受怎樣的屈辱/才能擁有如此圣潔的光輝/一條河流需要經歷多少次苦難/才能獲得今晚短暫的安寧”(《月光下的河流》),詩人用兩個排比句式以直抵靈魂的力量,呈現人類的生存困境與坎坷命運。“一匹馬醉死在歸家的路上/一個人耗盡光陰沒有找到故鄉”(《南山》),則表達出現代人對心靈家園的迷失與尋找。而《祭奠》以“故事化”寫法將生活中的細節抽象化,富于暗示性,把野胡蘿卜花包圍城防堤、城防堤包圍城市進行擬像仿真和戲謔,建構起野胡蘿卜花花圈祭奠城市的狂歡圖景,產生戲劇化效果,形成否定之否定的詩歌張力,從而達到標題所標識的反諷效果。生的悲憫、存在的悖謬、死亡的追問與思考在極度荒誕化的黑色幽默中顯得格外沉重,“每一年,我們都要被野胡蘿卜花/隆重地,祭奠一次”,詩人汪鐸批判物質現代化視閾下的生存困境,直抵人類生命的本質。這一點在與《等待戈多》類似的詩歌文本《接站人》中同樣呈現,沒有結局、沒有終點的等待不正是我們生存狀態的復現么?
傅菲在哲理小詩《薔薇組詩》中發揚綿長、熾熱、天然的抒情優勢,提煉現實的詩意,真誠地呈現出自己對個體生命與周遭世界的感受與思考,不僅語言飄逸,而且意蘊醇厚。尤其是詩人一直以薔薇物象作為意象載體,傳遞主體“我”與客體“你”“他”的心情狀態和心理思緒,深沉地表達生活的感悟和生命的滋味,使得詩歌開合自如,凝重而富有畫面感、細膩更具哲理性。那淡淡的憂傷、惆悵與懺悔在冷抒情的冷艷中異常尖銳,強烈的痛感油然而生,刺向人性的虛空,如“用剩余的三公斤淚水,每日取一滴/澆灌泥垛上的薔薇”(《薔薇》),“回望你的雙眼/恰似一個墳墓毗鄰另一個墳墓”(《薔薇小令》),“帶來塵埃 愛 深呼吸/最后帶來凋謝 不留匆匆一瞥”(《薔薇的悲傷》),“目睹薔薇盛開的人遠去他鄉/閃光之后扔下一片漆黑/像不散的亡靈,纏繞指尖”(《滾過薔薇的閃電》),“生活就是一堵滿是彈孔的墻,我扶墻而歌”(《不是每個人這么幸運,遇見薔薇》),詩人以不露聲色的冷色調和深沉刻骨的悲劇感關注人的生存狀態和生活真相,探尋個體心靈的悸動和苦澀內心的掙扎,具有強烈的人文關懷和對存在與死亡的深度思考。同時,詩人在《手捧薔薇的人》、《十二株薔薇》等詩中傳遞個人生命的體驗以及對生命和自然所發生的溫暖,如“列車離開麻石站臺之前,我留最后一刻鐘給你/不要相擁,不要細語道別。我只想回眸時/看你手捧薔薇,面帶微笑,猶如初見”(《手捧薔薇的人》),“不是愛,但溫暖,偶爾痛/我喜歡你種下的薔薇……晚安”(《喜歡你種下的薔薇……》),生活的駁雜消解了詩意的溫暖與情愛的溫馨,但痛并快樂著,自然的原色、生命的溫馨與心靈的相通在薔薇花的暖色調中依然顯得精神飽滿。
總之,顏溶、三子、林莉、汪澤、傅菲等詩人以各自的意象載體切入,呈現自我鏡像的主體認同,探尋詩歌隱喻層面上的生命本真、存在意義和人類之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