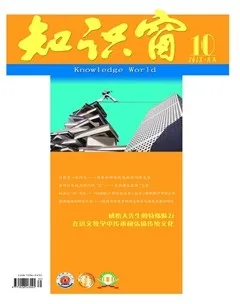感悟大先生的特殊魅力
由潘劍冰先生所著、廣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民國(guó)課堂大先生也挺逗》一書(shū),從道德、文章、人生經(jīng)歷等不同角度,比較全面地介紹了民國(guó)時(shí)期十六位個(gè)性鮮明、學(xué)富五車的大先生。讀罷此書(shū),令人獲益匪淺。
一、學(xué)識(shí),襯出學(xué)問(wèn)之淵博
辜鴻銘,是民國(guó)初年一位頗具影響又很有爭(zhēng)議的大先生,出生于馬來(lái)西亞,游學(xué)于歐洲,通曉九國(guó)語(yǔ)言,能夠精湛嫻熟地使用英、德、法三種語(yǔ)言,英語(yǔ)造詣更是登峰造極,連林語(yǔ)堂先生都盛贊其英語(yǔ)水平在中國(guó)“二百年無(wú)出其右”。 1907年,蔡元培先生到德國(guó)萊比錫大學(xué)求學(xué)時(shí),這位學(xué)長(zhǎng)的大名在萊比錫已經(jīng)是無(wú)人不曉了,甚至還贏得了“到中國(guó)可以不看紫禁城,不可不看辜鴻銘”的盛名。所以,蔡先生在就任北大校長(zhǎng)后力排眾議,禮聘這位學(xué)長(zhǎng)到北大做教授。
第一天上課時(shí),辜大先生就和學(xué)生“約法三章”:我進(jìn)來(lái)時(shí),你們要站起來(lái),上完課我先出去后你們才能出去;我問(wèn)你們?cè)捄湍銈儐?wèn)我話時(shí)都得站起來(lái);我指定你們要背的書(shū),你們要背,背不出不能坐下。這個(gè)“約法三章”無(wú)外乎是在告訴當(dāng)時(shí)的北大學(xué)生:在中國(guó),尊師重道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底線。
對(duì)學(xué)生,辜大先生可謂傾其所有,無(wú)私相授;對(duì)洋人,則是極盡挖苦之能事,以長(zhǎng)中國(guó)人的志氣。早在英國(guó)愛(ài)丁堡留學(xué)時(shí),他會(huì)故意在公共汽車上倒著看英文報(bào)紙,在英國(guó)人嘲笑他附庸風(fēng)雅時(shí),他則用一口流利的英語(yǔ)淡定地回答:“英文這玩意兒太簡(jiǎn)單了,不倒過(guò)來(lái)看,簡(jiǎn)直沒(méi)有意思。”對(duì)那些在北大校園自恃“高貴”的洋教授,他會(huì)先用純正的英語(yǔ)與之“探討”學(xué)問(wèn),再用拉丁語(yǔ)與之“交流”教學(xué)心得,使得這些“南郭先生”只好逃之夭夭,卷鋪蓋走人。
言行舉止的特立獨(dú)行,使得他在批評(píng)胡適這樣的名人時(shí)也是絲毫不留情面。他對(duì)胡適教授的哲學(xué)就做過(guò)這樣的批評(píng):“古代哲學(xué)以教希臘為主,近代哲學(xué)以教德國(guó)為主,胡適不懂德文,又不會(huì)拉丁文,教哲學(xué)豈不是騙小孩?”
另一位大先生陳寅恪,在中國(guó)學(xué)術(shù)界可謂大名鼎鼎,尤其是他的記憶力之強(qiáng)、知識(shí)面之廣,更是令人嘆為觀止。其得意門生王永興回憶恩師晚年失明后,自己給先生念《資治通鑒》時(shí),脫漏一字,大先生當(dāng)即指出,讓他重讀。因此,摯友吳宓稱贊他為“全中國(guó)最為博學(xué)之人”,就連一向盛氣凌人的傅斯年也說(shuō):“陳先生的學(xué)問(wèn)近三百年來(lái)一人而已。”其弟子季羨林在面對(duì)老師早年留學(xué)德國(guó)所作的64本記錄了多達(dá)十幾種語(yǔ)言的學(xué)習(xí)筆記本時(shí),只能用“泛濫無(wú)涯”來(lái)形容老師的語(yǔ)言水平。然而,這位曾經(jīng)在國(guó)外留學(xué)十六年,在哈佛大學(xué)、柏林大學(xué)學(xué)習(xí)過(guò)的大先生,居然沒(méi)有拿到任何學(xué)校頒發(fā)的文憑。恰恰因?yàn)闆](méi)有學(xué)位,當(dāng)清華大學(xué)國(guó)學(xué)研究院成立時(shí),時(shí)任研究院籌備處主任的同窗吳宓向校長(zhǎng)曹云祥推薦陳寅恪擔(dān)任導(dǎo)師時(shí)遭拒;后來(lái),梁?jiǎn)⒊俅瓮扑],大先生還是因沒(méi)有學(xué)位、沒(méi)有著作而被拒。在聽(tīng)到柏林大學(xué)、巴黎大學(xué)的教授推薦大先生,梁?jiǎn)⒊f(shuō)自己的著作還不如大先生寥寥數(shù)百字有價(jià)值后,曹校長(zhǎng)才禮聘大先生為導(dǎo)師。
在陳寅恪先生看來(lái),一個(gè)文化人必須有著獨(dú)立之精神,才能有自由之思想。因此,他授課奉行的原則是:“前人講過(guò)的,我不講;近人講過(guò)的,我不講;外國(guó)人講過(guò)的,我不講;我自己講過(guò)的,也不講。現(xiàn)在只講未曾講過(guò)的。”這才有了已經(jīng)在國(guó)文系讀到大三的王永興在聽(tīng)了大先生講的唐史課后,堅(jiān)持要求轉(zhuǎn)系,拜在大先生門下做弟子。清華大學(xué)的教務(wù)長(zhǎng)潘光旦稱大先生為“教授之教授”,西南聯(lián)大歷史系教授姚從吾也發(fā)出了“陳寅恪先生為教授,則我們只能當(dāng)一名小助教而已”的感嘆。
二、傳道,折射出做人之率真
書(shū)中介紹的十六位大先生,就其出身而言,有前清的秀才、進(jìn)士,有留洋回來(lái)的碩士、博士,還有只讀了半年小學(xué)、中學(xué)輟學(xué)的鴻儒;再看他們講課的課堂,除了章太炎外,幾乎清一色地或在清華大學(xué)、或在北京大學(xué)傳道授業(yè)。
胡適先生以27歲的年紀(jì)被蔡元培先生聘為北大教授后,他的年少?gòu)埧褚齺?lái)了與之年齡相近的學(xué)生們的作弄。北京大學(xué)才子傅斯年有著“黃河流域第一才子”的美譽(yù),其才學(xué)連劉師培、黃侃等老師也深為欽佩。傅斯年可是鬧學(xué)潮、趕教授的一把好手,就此被同學(xué)推舉出來(lái),在課堂上與胡適“探討”國(guó)學(xué)。第一堂課,胡適就被問(wèn)得直冒冷汗,幾節(jié)課交鋒下來(lái),傅斯年失去招架之功,只得繳械投降。
三、人格,彰顯出為師之風(fēng)范
民國(guó)課堂的大先生都有一個(gè)共同的特點(diǎn),那就是他們?cè)趥鞯朗跇I(yè)的過(guò)程中展現(xiàn)出來(lái)的人格魅力。
黃侃在南京中央大學(xué)任教時(shí),有著“三不來(lái)教授”的美譽(yù),即“下雨不來(lái),降雪不來(lái),刮風(fēng)不來(lái)”。而他拜章太炎為師,則源于一場(chǎng)罵戰(zhàn)。內(nèi)急的黃侃不下樓方便,于是“飛流直下三千尺”,這可惹惱了住在樓下的章太炎。于是,有著“民國(guó)罵圣”之譽(yù)的章太炎與黃侃就有了一場(chǎng)罵戰(zhàn)。兩位遣詞造句的頂尖高手發(fā)現(xiàn)對(duì)方功力深厚,罵著罵著,怒氣漸消,互通姓名后,好學(xué)的黃侃立即叩頭拜章為師 ,成了章氏門下第一弟子。就是這樣一個(gè)“狂妄”之人,在北京大學(xué)講“說(shuō)文解字”時(shí),一不帶原書(shū),二不帶講稿,還能引經(jīng)據(jù)典,口若懸河,講得頭頭是道。學(xué)生課后去查書(shū),發(fā)現(xiàn)居然一字不錯(cuò)、一字不漏。而他詠誦詩(shī)章所形成的帶有濃郁黃氏風(fēng)格的“黃調(diào)”,令馮友蘭等弟子羨慕不已,紛紛模仿,成為北京大學(xué)的一道文化風(fēng)景。
胡適早年留學(xué)美國(guó),頂著幾十個(gè)“博士”頭銜的“海龜”,27歲就成了北京大學(xué)的教授。胡適先生能以一種容忍的精神,對(duì)待來(lái)自不同思想領(lǐng)域的批判。1930年4月,胡適先生在給楊杏佛的信中說(shuō):“我受了十年的罵,從來(lái)不怨恨罵我的人,有時(shí)他們罵的不中肯,我反替他們著急;有時(shí)他們罵的太過(guò)火,反損罵者的人格,我更替他們不安。如果罵我而使罵者有益,便是我間接于他有恩,我自然情愿挨罵。”在與魯迅先生分道揚(yáng)鑣后,魯迅先生對(duì)胡適的批評(píng)與諷刺日益增多,他不僅沒(méi)有反擊魯迅先生,反而一再維護(hù)魯迅先生,批評(píng)那些惡意攻擊詆毀魯迅先生的言論。當(dāng)自己的女弟子蘇雪林以潑婦罵街的架勢(shì)對(duì)魯迅先生進(jìn)行“鞭尸”般謾罵時(shí),胡適先生則狠狠批評(píng)了自己的弟子,稱她罵魯迅的話“太動(dòng)火氣,是舊文字的惡腔調(diào)”,并教育自己的弟子,批評(píng)一個(gè)人應(yīng)該持平,“愛(ài)而知其惡,惡而知其愛(ài)”。胡適先生這種國(guó)民風(fēng)度,在今天也是非常少見(jiàn)的。
(作者單位:上饒師范學(xué)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