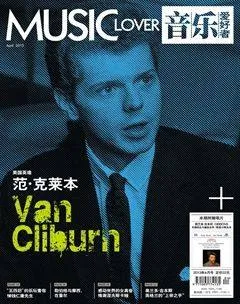我讀《熱愛音樂:德彪西論音樂藝術》
《熱愛音樂:德彪西論音樂藝術》由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張裕禾先生編譯。這位跨越文學、社會學、歷史學的學者、法語翻譯家,也曾翻譯過《梅特林克戲劇選》,熟悉德彪西的樂迷一定會知道,使德彪西確立世界性地位的作品《佩利亞斯與梅麗桑德》,正是根據梅特林克的同名劇本改編的。值得一提的是,這個劇本其實是梅特林克三聯劇中的一部,更令人驚奇的是另外兩部也被創作成音樂作品:巴托克的《藍胡子公爵的城堡》、保羅·杜卡斯的《阿莉亞和藍胡子》(Ariane et Barbe-bleue)。
張裕禾先生作的序可以說是德彪西的小傳,甚至把青年時期德彪西與馮·梅克夫人和瓦斯尼埃一家的交往也敘述出來。這對于德彪西的一生來說是一個轉折點,也間接導致了他后來在沒有修畢第三年的學業就回到巴黎,開始他窮藝術家的流浪生涯。據張先生的說法,德彪西開始撰寫樂評和文章,大概是在《佩利亞斯與梅麗桑德》獲得成功這一時期開始的:“在他(德彪西)初寫評論時,曾借用一個假想人物克羅士先生之口,來表達他不便于說的話。《跟克羅士先生談話》和《反對音樂行家》正是用這種筆法寫的。但不久他放棄了這個虛構的人物,而以德彪西的名義報道巴黎的音樂活動,評論樂壇的新人新事了。這也是他從一個受爭議的樂壇新星,到一個成熟的音樂大家的轉變過程。”張裕禾還形容德彪西的文章“高屋建瓴,縱橫捭闔,坦率直言,文筆犀利,得罪了不少同行”,這句話實在是概括得再精準不過了。
從瓦粉到瓦黑
我想再也不會有比德彪西更專業的樂評了。作為作曲家的同行,他往往對其他音樂家有著兩極化的評判,這在德國作曲家中最為明顯。
暫且不說其他人,他對于瓦格納的評論是最為微妙的。了解德彪西的樂迷們可能會知道,在寫《佩利亞斯與梅麗桑德》之前,德彪西或許可以稱得上是一名虔誠的“瓦粉”。在“我為什么寫《佩利亞斯與梅麗桑德》”一文中,他說自己曾經參加過幾次拜羅伊特的朝圣,但是后來覺得瓦格納的套路只適用于瓦格納一個人,他認為應該探索“后瓦格納”路數。在《德國對法國音樂的影響》一文中,德彪西甚至說瓦格納奴化了法國音樂。他指責瓦格納的藝術虛假,稱他從來沒有報效音樂,甚至沒有報效德國。而恰恰在1908年的采訪中,德彪西私底下與記者聊天時,在他的筆記本中寫下:“我認為瓦格納的旋律線條是完美的。瓦格納現在是,將來仍舊是一位非常偉大的音樂家。”德彪西絲毫不懷疑瓦格納的才華,或許他只是認為當時的觀眾對瓦格納的崇拜過于神化了。我想即使是現在,德彪西的話語仍然有一定功效。
對于巴赫,對于貝多芬,德彪西又從文字中表達了無限的敬意:“巴赫音樂的動人之處,不在于旋律性,而在于旋律聲部的進行,甚至常常是好幾個聲部平行進行,或者偶爾交織……巴赫好似仁慈的上帝,音樂家開始創作之前應該向他禱告,以免寫出平庸的作品。”“貝多芬不是不值錢的文人。他很驕傲,他熱愛音樂。音樂對他來說,是酷愛,是歡樂。他的私生活中極其缺少歡樂。”說完仍不忘踩一踩同場的瓦格納,“老貝多芬嚴肅、合格的大師地位輕而易舉地就戰勝了那些頭頂高帽、資格不明的先生們的江湖語言”。
慧眼識“冷盤”
在《音樂愛好者》2012年9月號中,任海杰先生在隨筆中提到德彪西對里姆斯基-科薩科夫《安塔爾》的贊賞使他欣賞到了一部杰作。而在《熱愛音樂》這本書中,處處可見德彪西對某些冷門作品或者演奏家的喜愛,從中我們可以看到一個音樂家不隨波逐流的獨特鑒賞力,他對于那些音樂家和作品的評價現在仍然生效。
德彪西在隨筆中曾經反復提到拉莫的音樂,甚至還寫了專門的文章介紹他。他在當時就說拉莫被法國音樂界忘記了半個世紀,可現在看來,又有多少人記起他了?德彪西說從來沒有聽過比拉莫更為法蘭西的聲音了,此話不虛。法國音樂在科普蘭和拉莫之后其實就數德彪西和拉威爾最重要了,至于柏遼茲,正如德彪西說的,他是一個怪才,但從他身上看不到多少法國特有的東西。德彪西還推薦了杜卡斯的鋼琴奏鳴曲,這首似乎仍未解凍的鋼琴作品至今還是缺少鋼琴家的賞識,我腦海中能依稀記起的只有古爾德和法國鋼琴家艾塞(Jean Francois Heisser)的錄音了。
我的個人注釋
誠然,張裕禾先生的注釋已經是面面俱到了,通過這些注釋,讀者可以了解那個一戰前夕的巴黎音樂生活,那時的時尚,那時的歷史事件,那時的人物。被德彪西描繪為“名耳朵”的貴族們,即使打瞌睡了,在被叫醒后還是會為演奏家們鼓掌喝彩。我相信包括我在內的許多讀者都會有些憧憬那個時代,因為那個時代的人縱使如同德彪西所說“由于每天聽音樂,而且什么牌子的音樂都聽,便自稱是音樂家”,但他們對音樂的愛是真誠的,我想對于現在的人們來說,這是最迫切的。
但書中提到卡薩爾斯音樂會的札記則引起我另外的興趣。德彪西只是稍稍提及大提琴家拒絕排演德沃夏克協奏曲,那么真實情況又是怎樣的呢?作為愛樂者,我覺得有必要向大家解釋一下。在《弓弦之王:卡爾薩斯》一書中,卡爾薩斯提到了他一生中唯一一次與樂隊指揮合作時的不快。卡爾薩斯坐了一夜的火車到達巴黎,就為了與科洛納(Colonne)樂團一年一度的合作。在排練時,這位指揮在語言上侮辱了德沃夏克這首大提琴協奏曲,而且順帶連贊揚這首作品的勃拉姆斯也侮辱了一番。卡爾薩斯十分生氣,他的拒絕演奏產生了炸彈般的效果,觀眾們也圍上來了。卡爾薩斯發現了人群中的德彪西,希望他主持公道,但德彪西似乎不想當和事佬:“好了,好了,卡薩爾斯。如果你愿意的話,怎么不能演奏呢?”卡薩爾斯失望極了,他特別難受地對德彪西說:“我坦誠地告訴你,我做不到,我拒絕演奏。”卡薩爾斯真的這樣做了,并且吃了官司,而且還接受了罰款。這位指揮后來也希望找到卡薩爾斯進行道歉,但其實在卡薩爾斯述說這件事情時,他已經原諒了他。
一個有血有肉的藝術家
樂評這個行業,究竟是從什么時候開始的?這個我說不清楚,但從我有限的觀察,現代社會樂評家們的規矩好像是離音樂圈越遠越好,盡量不與他們接觸。這或許是避免感情色彩、保持客觀的最好辦法。
而德彪西做到的似乎是既能“入世”,又能“出世”。你說他沒有距離感?他從來沒有告訴記者他作品的細節,甚至對于他作品演出的評價也是幾筆帶過而已。你說他太高高在上了?德彪西就坐在觀眾席中,雖然他的思想早已凌駕于音樂廳之上了。德彪西對于當時法國音樂的發展和關于民眾音樂素養的思考簡直是為當代樂評樹立了標桿。他對于所有演奏者都毫不吝嗇贊美之詞,有時甚至跟普通觀眾一樣,對于外國音樂家是狂熱和熱情的。
作曲家順便寫寫樂評的習俗是什么時候消失的?我也說不清楚,但李斯特的文章我讀過,肖邦和柴科夫斯基的書信我也讀過。李斯特的辭藻華美得就如同關不住的水龍頭,德彪西則更像一個稱職的時事評論員。他曾用同一句詩句形容兩位作曲家的作品,但我們仍能夠區分不同的美!德彪西在評論音樂時,多用當時的詩句和圣經的典故,這與田藝苗女士認為的“只有詩歌和寓言能稍稍形容音樂的感覺”這個觀點不謀而合。《熱愛音樂》一書中到處都可找到德彪西對于藝術的各種“名言警句”供讀者咀嚼,這位永恒藝術的締造者所寫的文字,永遠不會老去!以上種種,都在提醒大家:“功夫在詩外”。
《道德經》里說:大成若缺。德彪西原本跟其他我們熟知的偉大藝術家一樣,好像從來沒有做過什么偏頗的事情,所以譯者似乎有意將德彪西一些“特別”的文章收錄進來。在關于格里格、意大利歌劇等問題上,德彪西帶有強烈的個人色彩。對于音樂愛好者來說,在這個迫切需要重塑偉大音樂家真實形象的年代,這本書比音樂辭典或者其他傳記生動多了。沒錯,我們是需要辭典上冷冰冰的中立評價,但在這個“嚴肅音樂聽眾明顯減少,大家開始盲目地尋求刺激信息”(諾曼·萊布雷希特語)的年代,也許這類書籍會顯得更有人情味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