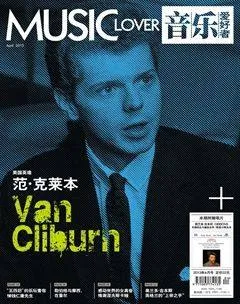大衛?弗雷:法國鋼琴學派的終結者


2013年3月2日,在上海交響樂團的“貝多芬大全2+2”音樂會上,法國鋼琴家大衛·弗雷攜手中國指揮家楊洋,一同上演了貝多芬《第二鋼琴協奏曲》。弗雷似乎并不中意傳統的琴凳,倒是有幾番“老牌”風格地使用起靠椅。演奏時,他坐得略低,弓起身子。觀察其手型,成扁狀,就連碰到作品中一些快速段落時,也伸長了手指彈。他似乎有足夠可靠的技巧支配雙手,觸鍵敏銳……
這些演奏特征和姿勢都能使人聯想起已故傳奇鋼琴家格倫·古爾德。雖然兩人都酷愛巴赫,但藝術風格卻絕然不同,尤其在音色上更是差異巨大。古爾德在音色上求精、求凈,每個音都像彈子落地一樣粒粒可辨;相反,弗雷的音色明顯偏薄,略帶混濁,音符的銜接上有雜質。實際上,不夠飽滿的弱點在貝多芬第二“鋼協”的慢樂章中顯露無疑,與某些鋼琴比賽獲獎的年輕鋼琴家音色并無兩樣。
所以,把弗雷與古爾德拿來相提并論,單從音色來判斷,就已經點了死穴。而與古爾德年輕時相比,就更是相去甚遠、敗下陣來了。更何況,弗雷是法國人、古爾德是加拿大人,兩人接受過的音樂教育也毫無交集。所以,我想更多人是借著古爾德,來突顯對弗雷的崇拜之癮。某些評論依然大夸其談弗雷有“迷幻之音色”真是子虛烏有。
拋開這類一派胡言的“崇拜論”不談,弗雷的確具備了帥氣的外表,猶如大眾之偶像,又娶了美女齊婭拉·穆蒂為妻,大指揮家里卡多·穆蒂成為了他的老丈人,盡顯了風光得意,也迷倒了上海不少現場的女樂迷。但是,如果沒有如此耀眼的外表,在演奏上還能留下多少亮點呢?
從某種意義上講,弗雷應更多繼承了法國鋼琴學派的傳統。但是,如今琴壇已很少有“皈依”傳統學派意義上的年輕鋼琴家了,緣由只是因為他們奔波于世界各地求學,希望集各門派精髓于一生來開拓視野,擁有更多的音樂會曲目量。如今,法國人可以輕而易舉地去演奏斯克里亞賓、普羅科菲耶夫或肖斯塔科維奇,因為他們學到“更多”的演奏法。我們經常在某些年輕鋼琴家的簡歷上,看到一大段其追隨過的老師名字。但是,與多位老師學習并非一定是好事,后任老師極有可能會否認前任老師在演奏上的觀點,這樣對年輕的鋼琴家很不利,甚至會步入無法自我思考的迷茫之中。
正如2010年,波蘭肖邦鋼琴比賽金獎得主阿芙蒂耶娃被稱為俄羅斯鋼琴學派的“叛逃者”一樣,弗雷同樣也是違背自家傳統,一意孤行的鋼琴家。但矛盾在于,他的確繼承了些法國鋼琴學派,老師是雅克·胡米耶(Jacques Rouvier),曾跟隨過簡·胡比歐(Jean Hubeau)、弗拉多·佩勒穆泰(Vlado Perlemuter)學習,可惜代代相傳的“法派”卻一代不如一代,也極少有人像科爾托那樣把畢生的心血傳授給學生了。現在許多學生更多考慮老師是否擁有足夠強大的背景,最好能掌控幾個有影響力的鋼琴比賽。當然,弗雷是頭腦聰明的人,他很清楚如今要穩足于琴壇需要怎么做,怎樣營造爭議,甚至是頭發的長短如何去把控等等。媒體也更關注他獲得了什么大獎,或與哪位明星長得更像。對于年輕鋼琴家,真正去在乎演奏藝術的人越來越少了。
從弗雷近年來的選曲來看,他更偏向于巴赫、莫扎特、貝多芬,卻極少演奏肖邦、舒曼的作品。或許,他慶幸自己是一位不善于“歌唱”浪漫派的鋼琴家,而“歌唱”中所需要賦予的醇美音色,則是其弱項,他更希望在音樂作品中,每一個音符聲音都是獨立存在,而未將他們納為一個整體,甚至脫離了干系。在許多年前,法國學派因講究圓潤通透的音色而盛名,而且完全不會顯露異樣聲音上的棱角。在樂句的處理上也較為委婉,樂句線條調配適中。就連當年備受爭議的桑松·弗朗索瓦(Samson Francois)雖然會作一些奇思妙想的自由速度(Rubato),但依然掌握了無比精湛的發聲技巧。另外,絕大部分老一代法國鋼琴家都能營造一種奇特的共鳴音,大多發生在樂句較長的歌唱中。
但是,這一切都未發生在弗雷身上,沒有那種令人肅然起敬的感染力,也給自古以來法國學派傳承下來的精髓來了一個徹底的否決。當我聽了弗雷的貝多芬“第二”鋼協的現場后,更是發覺他的音樂才能被嚴重高估了。這位被成功淹沒的年輕鋼琴家是時候應該更多利用自己的耳朵,去判別“什么才是真正的音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