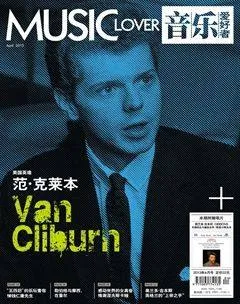“大手筆”的貝多芬

2013年3月3日下午4點,我在擁有一千二百座的天津大劇院音樂廳,臺上是天津交響樂團,被當地人親切地稱呼為“天交”,又有“天驕”之意。這個點對于音樂會的開場有點前不著村后不著店。下午4點一般是拜羅伊特音樂節上長度超過四小時的歌劇的開場時間,而天津的這場音樂會的曲目包括貝多芬和柴科夫斯基的《第五交響曲》,即使加上中場休息,總長不過一個半小時。劇院經理告訴我,這是他們正在采取的全新模式,把音樂會放在雙休日下午比放在晚上更具商業前景。我想也是,即便是像我這樣自封的鐵桿樂迷,要在周末晚上放棄和朋友的燭光聚會而獨自趕赴一場音樂會,尚且需要極大的勇氣和決心,更何況一般人呢?
促使我放棄周日的閑暇,從上海飛到天津,理由只有一個:湯沐海出任天津交響樂團藝術總監后的首場音樂會。3月3日上午,我趕到北京,在國家大劇院聆聽了一場張藝指揮中央芭蕾舞團交響樂團演出的貝多芬《第五交響曲》,這是每周日上午劇院的教育普及項目,因此張藝在音樂會中有著詳細的講解和示范。帶有張藝慣有的極為清晰干練的指揮風格,流淌出的是干凈明快的音樂。這是一場小清新的爽口貝多芬“第五”。
聽完音樂會正好中午十二點。我馬不停蹄地坐高鐵趕到天津。從北京到天津的高鐵只需三十三分鐘,城際聯運變得方便快捷,從北京到天津聽音樂會并當天來回也成為現實。當然,把這一想法變為現實的,并不是高鐵的速度,而是天津音樂市場的崛起。天津交響樂團與湯沐海簽約,變為最新一例。
我之前從未聽過天津交響樂團現場,只在廈門聽過樂團前任總監王均時指揮廈門愛樂樂團的幾場音樂會。對于大部分上海人來說,天津盛產麻花和包子;對于北京人來說,天津盛產相聲。把天津衛和交響樂,把湯沐海和天津衛聯系起來,那都是2013年3月3日才開始萌生的念頭。
音樂廳里的燈漸漸暗下來,人們都在屏住呼吸等待激動人心的一刻。突然有人領起了掌,大家歡欣雀躍地看到大腹便便的湯沐海穿著一身中式西裝而不是小禮服,從臺口慢慢走到中間。我聽過看過無數指揮家的上臺亮相,有國內的、國外的,有男人,也有女人和小孩。一位前輩指揮家告訴過我,指揮家要的就是聲勢(當然是在其他層面的條件都達到一定境界后),手一晃,眼神一給,音樂就自動起來了。
湯沐海是我見過的在舞臺上最有氣場的中國指揮家,他的舉手投足似乎都牽動著大家的心。他掃了一眼臺下,立馬就目不斜視地走到舞臺中間,慢慢地跨上指揮臺。他既不看譜,也不轉身向觀眾問候,不顧掌聲的持續,面對樂團手一比劃,貝多芬《第五交響曲》就在熱重的掌聲中開始了。依靠湯沐海的氣場,音樂打斷了掌聲,把聽眾弄了個猝不及防。
湯沐海的舉手投足無疑也牽動著樂師手里的琴,那雷霆萬鈞的一比劃也把樂團殺了個猝不及防。這是我聽g36JfRsfAUcwHZn6DHDv2w==過的最快的貝多芬交響曲第一樂章,那個正在敲門的命運女神的敲法,就好像是上門查水表似的。飛沙走石的音樂充滿了動感,一些弦樂的細節化成了粗暴的渲染。天津交響樂團在湯沐海手下有了以前俄羅斯樂團的感覺,有序中的凌亂和沉穩中的粗獷。
三個樂章過去后,我已經對這種刻意營造的張力和強大的動態對比開始適應,進入了由湯沐海創造的音響世界。他對速度的隨性恰恰反映了對樂團的絕對掌控力,而自由速度的運用也顯示出了大師才有的自信和決斷。這是一版十分個人化的貝多芬“第五”,從思想上揣摩的話,帶有強烈削發明志式的潛臺詞。從心理上講,我更覺得這是一次釋放,無論是對指揮家還是樂團,有種“久旱逢甘霖”的爽快——或者,用“暴雨”替代“甘霖”可能更加合適。
下半場的柴科夫斯基“第五”失去了上半場的凌厲,但多了一份深邃,這也和音樂風格轉變有關。第二樂章中的圓號獨奏表現優異,弦樂予以了強大的鋪墊。寬廣的音場描繪出濃墨重彩的卷軸畫,充滿動力,鮮活的想像力貫穿始終。同樣讓人心曠神怡的還有出色的單簧管演奏。
兩首重口味的樂曲之后,湯沐海選擇加演了他富有特色的名曲大串燒,以架子鼓開場的音樂輕松活潑,起到很好的調節氣氛的作用。音樂的編配和串聯自然貼切,而湯沐海以氣場和手勢開始音樂后就坐到了樂隊中間,任憑樂團自己演奏。
加演結束后掌聲雷動。我前面是三排領導席,這也是天津大劇院音樂廳的特殊之處,雖然不設包廂,但用座位旁的扶手低調地彰顯主人的身份。領導席上坐著來自全國各地數十家樂團的總經理級別的人物,還有天津本地音樂界的顯赫大腕。他們用力快速地大幅度鼓掌,簡直讓我以為這是一場陳奕迅的演唱會。雷鳴般的掌聲和樂章間不可思議的安靜證明了湯沐海的氣場和由他經過樂團傳達出的音樂的氣勢得到了聽眾的共鳴。在這種氣氛中,樂評人無疑是多余的,樂評人的評論也是畫蛇添足。
但我以為,我捕捉到了湯沐海的內心獨白。他以兩首膾炙人口的命運主題的交響曲,作為他上任后首場音樂會的曲目,充滿了強烈的自傳性色彩。這位卡拉揚曾經的高足如今統領著浙江、河南、天津和上海的四支地方樂團。雖然他的年薪不菲,但中國預算最為龐大的樂團屢屢與他擦肩而過,他在國外的樂團也不再與他續約,他心中的郁郁不得志和東山再起的未酬壯志,都蘊含了對這兩首交響曲排山倒海式的極端詮釋和音樂的無盡釋放中。
而這場音樂會證明,只要有充足的排練時間和雙方全身心的投入,湯沐海的指揮技藝和藝術魅力依舊所向披靡,他的音樂語匯無法復制,他對樂團的掌控和理念依舊技高一籌。湯沐海青年的全盛時期已經過去,但對于這位與共和國同齡的指揮家來說,專心致志下就會有靈光乍現,耳順之年未必不能鍛造他在而立之年時創下的那般天驕神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