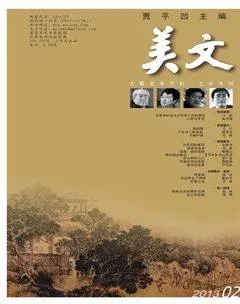不確定性的危險

幾乎每一個中國醫人,都會面對醫學不確定性認知的危險。成功的醫人化解危險的經歷,在中國醫學史上通常會演變為神異的傳奇故事。這樣的故事在17世紀到18世紀期間的明清兩代特別多見,那是因為醫學印刷作品在城市社會盛行。盡管一般說來,這些故事會激起多數閱讀者對于醫學的崇敬,但醫人本人卻深知自己在面對每一種危險狀況時,需要消耗的精力和智能究竟有多少。成功的案例即使到喜悅的成功結束,仍是無法預期之謎,而不成功的痛苦,則使醫人在事后很長時間都會郁積沉埋在內心,直到他們在醫案中書寫出來一吐為快。今天可能很難理解中國醫人的醫學處境,為什么他們甘心在這種不確定性中飽受煎熬和考驗,卻不求改變?是他們能力不夠嗎?還是知道中國醫學的不確定性不可避免,因而使他們在不可知的醫學場域就像在沒有航標的大海上航行,未知前面方向,卻更能獲得冒險的樂趣。
至少有十多年醫學經驗的喻嘉言,已是一個成熟的“傷寒”專家,他在長江中下游一帶的醫學實踐中,依靠對“傷寒”理論的理解和應用,治愈的病人不計其數。即便這樣,所有那些經他診治過的“傷寒”病例,還是讓這位國子監生員出身、年過半百的儒醫,大費周折,煞費苦心。特別與另外一些來自“傷寒”世家的醫師們,圍繞癥候所發生的爭論和沖突,讓他既煩惱又驕傲,既自負又失落。他覺得,僅僅用治療的有效性不能解決問題,只有說明所有那些疾病的事實,才有可能厘清傷寒病的知識立場,以及他在處理“傷寒”的身體所采用的認知模式。因此,“傷寒”解讀在他的《寓意草》中,成為喻嘉言首要的敘述主題。
從《寓意草》第一卷連續性的傷寒病案中選擇六例來說明。第一例黃長人,中年,平時不服藥,病后十天“忽然昏沉,渾身戰栗,手足如冰”;次例金鑒,年歲不詳,“春月病溫,誤治二旬,釀成極重死癥。壯熱不退,譫語無倫,皮膚枯澀,胸膛板結,舌卷唇焦,身倦足冷”;再例徐國禎,“傷寒六七日,身熱目赤,索水到前,復置不飲,異常大躁,將門牖洞啟,身臥地上,更求入井”;四例錢仲昭,“患時氣外感三五日,發熱頭疼,服表汗藥,終止熱不消,口干唇裂,因而下之,遍身紅斑,神昏譫語,食飲不入,大便復秘,小便熱赤,脈見緊小而急。”五例張某,“傷寒壞癥,兩腰僂廢,臥床徹夜痛叫,百治不效。”六例黃曙修、黃起潛父子,“春月同時病溫,乃翁年老而勢輕,曙修年富而勢重。”
六個病例的時間跨度多大,醫案沒有記錄,但可以看作特定的時間過程中構成的“傷寒”系列,作者其實也有意通過他的敘述,建構一種醫學時間,以便從不同的病人和不同的癥候來展開疾病的知識結構。
判斷這些疾病患者時,喻嘉言碰上的問題是疾病的本質與癥候豐富性之間的區分,他與“世醫”的分歧與爭論,以及自我認知的差別與難度,都體現在顯現的疾病事實與隱蔽的疾病本質之間的矛盾對立當中。黃長人的例子,世醫認定為“陰證”,喻嘉言則判別為“陽證”,前者按“傷寒”陰厥成法理解,而“不知傳經之熱邪轉入轉深”,因此后者以“熱深發厥”來斷定疾病的根源。金鑒的傷寒,已經過其他醫師當作單純“陰證”治療,喻嘉言辨析為“春溫證不傳經”,“陰證、陽證,兩下混為一區”,按傳統的“傷寒”認知,這是一種“死證”。他個人缺乏處理這種陰陽混合的疾病經驗,只能按“活法在人,神而明之”的古訓,天機自動,靈活運用。徐國禎與前兩例不同,一位世醫斷定熱證,氣勢洶洶要用“承氣湯”方治療,喻嘉言堅決反對,“陽欲暴脫,外顯假熱,內有真寒,以姜、附投之,尚恐不勝回陽之任,況敢以純陰之藥,重劫其乎?”這種對于疾病身體寒熱關系的把握,并非知識觀點改變,而是他對“陽證”的身體有著變化性的認識。錢仲昭又是一種,此人三五天時間,病情危急,同樣因為被其他醫師誤治。在喻嘉言看來,錢仲昭的身體“陽明胃經表里不清,邪熱在內,如火4b07377eb4a3e8bcf08e6ab9b723e090燎原,津液盡干”,這種“虛熱內熾”表現出來的疾病癥候,需要通過“甘寒”加以調和,才可使元氣再生,化解危險。張某的身體被“傷寒”損壞,亦有其他醫師“百治”,均無效。按喻嘉言的觀察,患者雖不至死,但即使病愈也將成為一個廢人。不過,喻嘉言還是細致審視癥候,斷定病人此時盡管“熱邪深入兩腰”,但還處在“邪正互爭”時期,速治應能“救全”。黃氏父子傷寒,本來由喻嘉言診治,卻因懷疑他的方法是不符合世醫傳統的“偏僻之說”,便另請別的醫人醫治,結果父親服藥后“渾身凍裂而死”,兒子仗著年輕身強,并且先服用過一劑喻嘉言以人參為主的“解表和中”藥,幸免于難,病在床上六十多天,才能爬起身來。有關黃氏父子的病候,喻嘉言一再強調“戴陽之證”,無奈病主不僅在治療期間不相信,事后還要繼續責難,“凡遇戚友家,見余用藥,率多詆訾”。在《寓意草》所有醫學敘事中,這是喻嘉言遭遇到的最為尷尬的事件。
事實上,喻嘉言與世醫在“傷寒”認知上差異,無論怎樣對立,但辯論雙方都沒有解決不確定性造成的難題。世醫靠習慣經驗判斷疾病癥候,喻嘉言則依據他對身體理論的假設來推求疾病真相,以一種不確定性與另一種不確定性競爭,結果還是不確定性,盡管事后證明喻嘉言的判斷與診治比較準確,但他也不會在這種爭論中獲得真實的支持,最多也就如一位不服氣的世醫說的那樣:“此人書多口溜,不能與爭也。”
總之,17、18世紀“傷寒”病的診治,在中國醫學進入現代之前,繼續呈現出一幅困難圖景。或許喻嘉言個人較高的治愈率,為這幅醫學圖景多少增添了一些樂觀氣氛,然而《寓意草》仍然揭示了中國醫學的總體性困難。自建立在自然性疾病經驗與假想基礎上的“傷寒論”產生,進一步加固著中國醫學的身體觀念和知識體系,由那些微妙而復雜的身體因素,以及它們的聯系與組合,所形成的醫學對疾病的描述方式,將《內經》以來的中國醫學進一步推向了非客觀化,因而也阻隔了醫學確定性的探求與發現之路。為什么自有“傷寒”觀念以來,醫學的認知不是變得容易了,而是越來越如此困難,正是因為“傷寒”的身體復雜而不確定的模式,對醫學的認知提出了激烈的挑戰與考驗,以至宋、元、明、清數百年,仍然會視“傷寒”為中國醫學畏途,當然也把它看作檢測醫學能力的最高標準。所以,喻嘉言在《寓意草》中常常悲欣交集、喜怒同在,這種醫學表情在現代臨床醫學那種看透了一切的冷漠目光中是不可能出現的。
相對醫學科學而言,中國醫學的非客觀化和不確定性,是一種缺陷,但不是必須克服的缺陷。疾病的本質到底是什么,離開身體的微妙性和復雜性,將其簡化和消散為完全的“可見之物”,也不一定就能說明真實。而作為彌補,中國醫學對于身體的深思與尊重,或許對現代醫學“非人化”發展還有一種必要的制約。醫學的不確定性確實與醫學危險并存,對于中國醫人如喻嘉言而言,克服危險,靠的是道德勇氣與良知發現,靠的是那種對于人的身體的責任與擔當。《寓意草》里,喻嘉言對他的同行與競爭對手,每有一問:你敢擔承嗎?事關醫學倫理與道德情懷,此問絕非多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