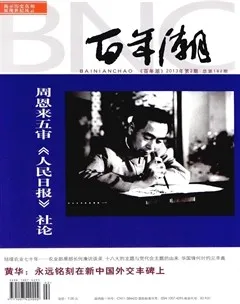韓復榘與蔣介石(下)
據說,會議期間,蔣介石指責我父親丟了山東。我父親毫不客氣地頂撞說:“山東丟失是我的責任,南京丟失又是誰的責任呢?”

下午1點半,軍事會議在開封南關袁家花園舉行,我父親偕孫桐萱等乘車前往出席會議。
開封軍事會議上究竟發生了些什么事情,是人們關注的焦點,有關這方面的文章,連篇累牘,人言言殊。
為盡可能還原開封軍事會議上的情景,我仔細讀了李宗仁、孫桐萱、吳錫祺、張宣武這四位目擊者的文章,綜述如下:
袁家花園的大門朝南,左邊掛著一塊木門牌,上書“中國中學”,院內有一個很大院落和一座大禮堂,可容納數百人,會場就設在禮堂內。與會人員一律在大門外下車,按集團軍整隊進入,集團軍總司令在前面帶隊。所有武裝或非武裝隨從人員一律不準入內,分別被安置在附近招待所內。院內憲兵林立,三步一崗,五步一哨,如臨大敵。與會人員不得攜帶武器進入會場,槍械交副官處統一保管。
參加會議的是第一、第五戰區所轄各部隊團長以上各級指揮官及幕僚長,到會400人左右。坐在第一排的皆為高級將領,從左至右為:蔣作賓、蔣伯誠、俞飛鵬、劉峙、鹿鐘麟、程潛、李宗仁、韓復榘、宋哲元、鄧錫侯、孫震、于學忠、萬福麟等。在高級將領中,除韓復榘、宋哲元、鄧錫侯、孫震四人身著灰布棉軍服外,其余將領皆著黃呢軍裝。韓復榘是高級將領中最后步入會場的。他戴一副茶色眼鏡,身著灰色斜紋布棉軍服,頭戴灰布棉軍帽,下邊打布綁腿,腰扎武裝帶。韓表現得很活躍,與坐在第一排的高級將領一一握手,親熱問候,然后坐在指定的李宗仁與宋哲元之間的空位上。
下午1點半左右,侍從室主任錢大鈞出現在講臺上,首先與在前排就座的高級將領們打個招呼,然后宣布會議開始。蔣介石從講臺右側角門走出來,身著黃呢子軍常服,戴白手套。錢高喊一聲“起立”,全體與會將領立正。錢向蔣報告到會人數。蔣向與會將領脫帽鞠躬;眾將領坐下。蔣摘掉手套,拿起花名冊,拈起一支紅藍鉛筆,開始按戰區、集團軍番號順序一一點名。半個多小時后點名結束,蔣從上衣左邊口袋里掏出一個藍色封面小本子,舉起來說:“你們有誰帶來這本《黨員手冊》?帶著的請站起來,把本子舉起來讓我看看!”全場站起八人。蔣命侍從人員將八人名字記下來。接著,蔣又從上衣右邊口袋里掏出一個紅色封面的小本子,舉起來說:“帶著《步兵操典》的請站起來!”結果,全場只站起一人。蔣又命侍從人員將那人名字記下來。蔣面露慍色,隨即開始訓話,先是反復強調《黨員手冊》與《步兵操典》的重要性,必須隨身攜帶,認真學習,批評眾將不重視戰時教育訓練,不學無術,長此以往,非亡國滅種不可!講到此處,“蔣很憤慨,很暴躁。一面講著,一面頻頻以手背敲打桌面,把桌面擊打得‘砰砰’響”
(張宣武語)。接著,蔣又“鼓勵大家奮勇作戰”(李宗仁語),說:“國際形勢很好,抗戰是有把握的,但是我們要頂得住,大家一定要服從中央和戰區司令長官的指揮,沒有命令,絕對不準擅自后退!要不怕犧牲,如有損失,我一定負責代為補充。”
會議中間休息半小時。據吳錫祺回憶:“中間休息的時候,蔣派人請韓復榘到講臺后邊的休息室談話,劉峙也陪著去了,去后即未再回到會場。”據張宣武回憶,會間休息時,蔣派人傳喚孫桐萱和川軍師長王銘章到講臺后邊的休息室談話,但未提韓復榘,說韓是散會時被扣的;而在孫桐萱的回憶中,根本未說有人在會間休息時被蔣傳喚;李宗仁在回憶錄中也未說有人在會間休息時被蔣傳喚,只說韓是在散會時被蔣傳去談話。如此看來,韓應該不是在會議中間休息時間被扣的,可能是吳錫祺把時間記錯了。
休息過后,天已近黃昏,蔣介石又來到會場接著講下去。蔣介石訓話結束后,由第一戰區司令長官程潛和第五戰區司令長官李宗仁分別報告戰況。晚6點多,程、李報告畢,天已黑透,錢大鈞宣布散會,并通知,晚7點蔣委員長請全體將領吃飯。
當與會人紛紛離去時,發生了戲劇性的一幕。按李宗仁的說法是:“劉峙忽然起立大呼道:‘韓總司令請慢點走,委員長有話要同你講!’韓復榘聞言留下。離會眾人議論紛紛,齊說:‘韓復榘糟了,韓復榘糟了!’當散會時,我走在最后,只見會場內留有委員長的便衣衛士四五人。劉峙便指著衛士對韓復榘說:‘韓總司令,你可以跟他們去。’”按張宣武的說法是:“那位中將侍從官步下講壇,走到韓復榘面前,笑著對韓說:‘請你稍等一會兒再走,委員長約你說幾句話’。”兩種說法大體相近,無非是會散了,別人走了,韓被“留”下來了。
韓復榘從進入休息室,直至被綁架到漢口,其間都發生些什么事,由于沒有目擊者的第一手資料,因此都只是傳聞,但有關蔣介石與韓復榘之間一段精彩對話卻廣為流傳,其中以王一民的說法最有代表性。王曾任山東省政府參議、汽車路局局長,他寫過一篇名為《關于韓復榘統治山東和被捕的見聞》的回憶文章,發表在全國政協《文史資料選輯》第12輯。文中說,蔣質問韓:“‘我問韓主席,你不發一槍,從黃河北岸,一再向后撤退,繼而放棄濟南、泰安,使后方動搖,這個責任,應當是你負擔!’韓復榘是有膽量的,而且他是傲上的老資格。他聽了蔣介石的話,毫不客氣地頂上去說:‘山東丟失是我責任,南京丟失又是誰的責任呢?’韓的話還未說完,蔣正顏厲色地截住韓的話,說道:‘現在我問的是山東,不是問的南京!南京丟失,自有人負責。’韓正想開口反駁,可是劉峙就拉著韓的手,說‘向方,委座正在冒火的時候,你先到我辦公室里休息一下吧。’于是他拉著韓從會議廳邊門(王說這一幕發生在大會議廳,這顯然是不可能的。如確有此事,也應發生在休息室)走了出來。劉峙裝著很親熱的樣子,握著韓的手走到院內,早有準備好的一輛小汽車。劉峙手指著說:‘坐上吧,這是我的車子。’……韓先上了車。劉峙說:‘我還要參加會議去。’說時就把車門關上了。在這個時候,汽車前座上有兩個人爬到后車廂里來,分左右坐在韓的兩旁,出示預先準備好的逮捕令給韓看,并對韓說:‘你已經被逮捕了!’韓起初還以為前座上兩個人是劉峙的隨從副官,看見了逮捕令,至此才知道兩人是軍統特務。”
李宗仁在回憶錄中寫道:“同日(12日)下午(散會后),委員長在其歸德(應是開封)行轅召集一小規模的談話會。出席者僅委員長、程潛、白崇禧和我,共四人而已。大家方坐定,蔣先生便聲色俱厲地說‘韓復榘這次不聽命令,擅自行動,我要嚴辦他!’程潛應聲說:‘韓復榘應該嚴辦!這種將領不辦,我們的仗還能打下去嗎?’白崇禧和我在一旁默坐,未發一言。”
孫桐萱回憶散會后情形:“當天(11日)夜間兩三點鐘,蔣伯誠忽然進來對我們說:‘向方被扣了!’我們三人均大吃一驚。蔣對我說:‘你走吧,蔣先生叫你去。’我同蔣伯誠走到門外,始知軍警已將我們住所包圍,氣勢洶洶地將我們攔住,不許出門。經蔣伯誠給侍從室錢大鈞打電話聯系之后,始得出門。我到袁家花園見了蔣介石,蔣說:‘韓復榘不聽命令,不能再叫他回去指揮隊伍。’我對蔣說:‘他在北伐時期作戰有功,給國家出了很大的力。不過他個性太強,有不周到的地方,請委員長原諒他,無論如何留他的性命,不叫他指揮部隊,叫他休息休息也好,留在鈞座身邊,教他力改前非,以觀后效,或叫他出國。’蔣介石說:‘好,好。考慮考慮,考慮考慮。’接著,他將幾條手諭拿出來交給我,說:‘你當第三集團軍副總司令,曹福林當前敵總指揮,于學忠兼第三集團軍總司令,你聽于學忠指揮。你馬上回曹縣,整頓隊伍繼續抗戰。’蔣同時也召見了于學忠。我退出后,蔣伯誠、何競武(隴海鐵路局局長)同我乘汽車又去見李宗仁、白崇禧。李、白和方振武三人正在閑談,我請求他們在蔣介石面前為韓說情。李、白都很生氣,說韓不服從命令等。我一再要求他們念韓北伐有功,對韓多多包涵。李、白含糊其詞地勉強答應了。這時有個傳令兵告我說,鹿鐘麟幾次來電話找我,要我無論如何務必到他那里見見面。我由李、白處辭出后,對蔣伯誠、何競武I2SAGuPNtPhQxclXWqbF3Q==說:‘鹿鐘麟找我,我去看看他。’蔣、何竭力阻攔,并說:‘你千萬別去,如果你去,于你不利。’當時火車已準備好,蔣伯誠拉我到車站,同上火車,當夜返回曹縣。”
張宣武回憶散會后情形:“晚八時左右,我從宴會廳回到旅社住處。同來住的人差不多都沒在家,于是我也到一家電影院里去看電影。晚九時左右,忽然停電了,據說全城的電燈都滅了,同時聽到外面大街上由北而來逐漸南移的不太稠密的槍聲。街上禁止通行。我在電影院里待了約半小時,等到槍聲停止了,電燈復明了,就急忙回到住處,打聽剛才街上發生的事情。據目擊者說,約有四五十個帶手槍,背大刀的人(韓復榘的手槍隊),順著南門大街由北向南,且戰且走地向南關方向跑去。事先布置在街道兩側的崗哨開槍截擊,但都不敢偎邊,后邊還有約一營人的兵力跑步追趕。究竟是怎么回事,當夜無人摸清底細。12日一早,人們互相奔走相告,紛紛傳說韓復榘于昨晚被捕并已押赴武漢云云。”
韓復榘的手槍隊因拼死抵抗被劉峙部隊消滅;韓的衛隊營被劉部包圍繳械。
12日下午,蔣介石再次召集軍事會議。吳錫祺回憶當時情形說:“蔣又出來講話,隨即宣布:‘山東省主席兼第三集團軍總司令韓復榘違抗命令,擅自撤退,現在已經把他扣交軍事法庭訊辦。’當時到會的人,均為之愕然。宋哲元接著站起來,遲鈍地說:‘韓復榘不聽命令,罪有應得。委員長原諒他是個粗人,沒有知識,請從輕判他。’隨后宋又回過頭來,請大家站起來為韓求情。當時前邊的一些人都站了起來。蔣介石連聲‘嗯,嗯……好,好’,隨即散會。”
孫桐萱說:“據說第二天(12日)蔣繼續開會,不但提出韓的罪狀,還說如果有人作戰不力,向后一跑數百里,均應重辦。宋哲元當時看一眼于學忠,兩人均立起給韓求情,請蔣從寬處理。”
韓復榘被特務帶離會場,由汽車送至火車站,站內一列準備好的專車已升火待發。我父親在眾特務、軍警的簇擁下剛被押上火車,車便轟然開動。一時間,隴海線及平漢線上所有火車一律停駛,讓開線路。搭載著韓的火車先沿隴海線向西疾駛,到鄭州再轉平漢線南下,沿途一刻不停,直達漢口。在車廂里,特務頭目王兆槐一直陪坐在韓身邊。
我父親被扣押后,蔣介石又召見何思源,問:“韓復榘扣留你多少教育經費?”“韓復榘是怎樣賣鴉片煙的?”何直言:“韓復榘從未欠過教育經費,也并不賣鴉片。”

據說,我父親被羈押在武昌平閱路30號軍事委員會軍法執行總監部的一座二層花園小樓里,他住二層,特務住一層,生活上對他尚優待,特務頭目王兆槐每天陪他聊天、下棋,但不準離開小樓,也不準與外界聯系。
由于特務嚴密監守,封鎖消息,我父親從1928年1月11日開封被扣到24日武昌被殺,其間13天時間究竟發生過哪些事情,外間全然不知,至今仍是個謎。
20世紀80年代,時任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北京市委秘書長的王先生告訴我,他在我父親被羈押期間曾陪孫連仲去看望過他一次。王時任孫連仲的秘書長,看望的地點就在武昌父親被羈押的小樓,孫連仲上二樓與他單獨談話,王在樓下等候。半個小時后,孫連仲從樓上下來,他也走下來送客。只聽他很輕松地對孫連仲說:“仿魯(孫字),你放心吧,我頂多就是回家種地去唄,沒什么了不起的。”王見他軍裝很整潔,氣色也很好。至于他和孫在樓上都說了些什么,王當然不知道。
這是迄今為止,我所知道的唯一消息。
我所了解的營救過程大概是這樣的:孫桐萱從開封回到曹縣后,避開蔣伯誠,約省府李樹春、王向榮、張紹堂等省府委員及第三路軍將領曹福林、吳化文、劉書香、張鉞、劉熙眾等開會,研究營救我父親的辦法。與會人員均擔心我父親的安危,心情都很沉重。曹福林埋怨我父親的左右不應該讓他去開會,至于具體如何營救,眾人也無萬全之策。孫桐萱說:“我們跟主席多年,都受過他的培養,要趕快營救,才對得起他。”他主張一面打電報要求軍委會放韓,一面加緊抗戰,爭取立功,并說:“如果不行,即集結兵力在黃河邊,作強烈之抗爭。”
與會者最后一致同意先給軍委會打電報,竭力保韓。張紹堂提議,應立即派人前往漢口,先探聽我父親的情況,再設法營救。眾人一致推舉劉熙眾前往漢口。會后張紹堂擬好電文并拍發。孫桐萱還不放心,又派張鉞攜款六萬元赴漢口活動高層,并囑如款項不夠,可繼續接濟。
孫桐萱召集的會議剛一結束,蔣伯誠即派李文齋(國民黨山東省黨部主任委員)前來打探會議內容,并轉報蔣介石。
劉熙眾到達漢口,住在第三集團軍辦事處。處長王愷如說:被羈押在武昌,吃住均尚優待,只是不準與外人見面,其他情況還不明了。劉說:“我對此間情況全很生疏,只是認識馮先生和鹿先生,其他方面你看怎么樣?”王說:“其他方面全不能幫忙,只能打聽打聽消息,但真實情況也得不到,現在也只有找他們兩位。”
于是,劉熙眾立即去見馮玉祥,先向馮玉祥報告了被扣前后的情形,然后又說我父親種種做法不對,主要是指馮任第六戰區司令長官時與我父親的沖突。劉熙眾最后說:“無論如何,他是先生一手培養的,還得請您想辦法救他。”馮玉祥說:“別說這些了。現在的問題是如何保全他的生命,我這幾天正為這事著急。我覺得應該從你們部隊本身去想辦法,專靠某一兩個人去講情,是沒有多大用的。”
劉熙眾見馮的表現很誠懇,便辭出,再與王愷如一起去見鹿鐘麟(鹿剛從開封回漢口)。鹿鐘麟說,韓向方再回軍隊怕是很難了,現在最重要的問題是先保住他的生命,馮先生的看法是對的。最好由你們部隊將領向蔣委員長表示一下,使他有所顧慮。最主要的是,部隊要團結一致,不要被人分化才有力量。你們自己研究研究吧!我和馮先生自然盡量想辦法,用不著說別的。
劉熙眾和王愷如回到辦事處,都認為無論是馮玉祥還是鹿鐘麟都極為關切,他們的意見都很有道理。父親當團、旅、師長時,都是鹿一手提拔的,第三路的官佐也多是鹿的舊部,如果大家擁戴鹿把第三路軍帶起來,不但鹿高興,馮一定也喜歡。鹿的辦法很多,他到第三路軍不但可以推動馮救父親,而且對第三路全軍也是有利的。劉把這個想法告訴王,王也很同意。
第二天,劉熙眾和王愷如一起去見馮玉祥。劉對馮說:“我們打算由第三路將領出個電報,使蔣有所顧忌。我們還想到第三路軍的隊伍,自韓被扣,群龍無首,孫桐萱不一定能統帥得起來,內部一鬧分裂,即被人分化消滅。這個隊伍是先生一手訓練的,不能看著不管。這個隊伍是第一師的老底子,許多官佐是鹿總監(鹿時任執法總監)的舊部,他如果能去招呼一下,一定不成問題。先生你看怎么樣?鹿總監是否能去?”
馮笑了笑,說:“好,你們的辦法很好!至于瑞伯(鹿鐘麟)去帶這部分隊伍的事,還不是那么簡單。一方面瑞伯是不是愿意去;另一方面是將來如何去,人家是不是讓他去,均是問題。待我問問瑞伯再說吧!”劉看馮的意思是很愿意鹿去的,至于鹿能不能去,關鍵是第三路的將領歡迎不歡迎,蔣介石同意不同意。劉又將準備好的電報稿請馮再過目,作一些修改,意思是抗戰不力,不僅是父親的罪責,第三路將領都有責任,請分別予以應得的處分,今后自當服從命令,效忠委座,帶罪圖功,以贖前愆云云。
劉熙眾向孫桐萱報告漢口之行的經過,孫極滿意。至于那通經馮玉祥修改潤色過的電報,孫意等請各軍、師長過目,再商議定奪。
其實早在劉熙眾回到曹縣之前,馮玉祥已派其孫副官來到曹縣。孫副官見孫桐萱后大哭,說:“我是馮先生派來的,蔣委員長要殺韓主席,你們趕快通電擁護鹿先生當總司令。”孫桐萱說:“你們與曹軍長及各師長先談談,只要他們同意,我就辦。擁護鹿先生我是同意的。”
劉熙眾在漢口與馮玉祥、鹿鐘麟醞釀第三路軍擁鹿之事,自然瞞不過蔣介石的耳目,嗣后有人說:劉漢口之行非但未能救韓,反促韓氏之死。劉亦感慨:“我自己也體會到,蔣之殺韓雖然已是定案,而我們的做法,也的確不夠審慎嚴密。”
赴漢口活動營救的張鉞亦返回曹縣,對孫桐萱說:“見到了何應欽、何成溶等人,他們都表示不敢說話。”
1月19日,蔣介石組織“高等軍法會審”機構,以軍政部長何應欽為審判長,軍委會執法總監鹿鐘麟、武漢行營主任何成溶為審判官,徐業道、賈煥臣為軍法官。
官方說韓案“數度開庭審訊”,但對庭審過程三緘其口,諱莫如深。
有人說:僅22日下午審訊一次,法庭上,我父親在訊問之下,“只昂首微笑,一句也不答復,也不請求寬恕”。會審尷尬收場。此種說法流傳甚廣,雖無可靠佐證,卻也符合他的性格:在危機四伏的政治博弈中落敗,就要認輸,如今人為刀俎,我為魚肉,夫復何言!
不過也有人說:根本就沒審。說這話的不是別人,正是“原告”之一李宗仁。
1938年1月25日,《掃蕩報》發表了中央通訊社的一條消息:山東省政府主席、第五戰區副司令長官、第三集團軍總司令、第三路軍總指揮、陸軍上將韓復榘因“不遵命令,擅自撤退”,并“別有借勢勒派煙土、強索民捐、侵吞公款、收繳民槍等情事”,于1月24日執行槍決。
我父親是1938年1月24日在其被羈押的小樓里遭槍殺的。當時現場發生的一幕,沒有目擊者的報告,有的只是傳聞。不過各種傳聞大抵一致,或許比較接近事實,這里姑從其說。
是日晚7點,兩名特務上樓對我父親說:“何(應欽)部長找你談話,請跟我們走。”父親起身欲走。特務問:“家里有沒有事?你寫信我們可以送到。”我父親說:“我沒有家。”隨即下樓。他走到樓梯中間拐彎處,發現樓下已布滿荷槍實彈的特務和軍警。他對前面領路的特務說:“我的鞋小,有點擠腳,我回去換雙鞋……”遂轉過身去,剛要上樓,背后槍聲大作。他回過頭,只說了聲:“打我的胸……”便倒在血泊中。
幾乎所有的傳聞都確認:我父親身中七槍,不過有說頭部中兩彈,軀體中五彈;有說全部擊中胸部。二夫人紀甘青和五叔為我父親開棺料理遺體時,劉熙眾及第三集團軍第二十二師軍醫處長姜維翰等也在現場,他們都證實父親“身中七槍,都在胸部”。不過,由此又引出一段傳聞,說是蔣介石事先已囑令劊子手不要打韓頭部,因為他是二級上將,又是一省主席云云,是耶非耶,姑妄聽之罷了。
第三集團軍將領及山東省府委員在山東曹縣聽說我父親的噩耗,在驚愕之余都哭了。孫桐萱派劉熙眾到漢口為我父親料理后事。
25日,張鉞、王愷如見馮玉祥,請其幫助探詢我父親遺體之所在,擬前往收殮。馮立即電詢賀耀祖,始知已入殮,停干武昌長春觀。
27日,劉熙眾陪同二夫人紀甘青和五叔來到漢口。劉先去見馮玉祥,馮表示出很難過的樣子,長嘆不已。馮說:“你回來啦,人家這一手真毒,沒想到這么快!你快去看看他的尸體怎么辦,其他的事回頭再談吧。”劉說:“韓主席的家眷也來了,打算領回安葬。”馮說:“在國難期間,他又是這樣死的,可不要鋪張,快去辦吧。”
第二天,紀夫人和五叔在張鉞、王愷如、劉熙眾及谷良民軍長的代表、軍醫處長姜維翰等的陪同下赴武昌長春觀認領遺體。
我父親的棺木停放在長春觀的一間空屋中,棺木前小桌上有用黃裱紙折疊成的一個牌位,上書“故魯主席韓公向方之位”。棺木很大、很考究,通身黑色,前面有朱色木雕文飾。據說棺木是由鹿鐘麟購買的,也有說是何成溶購買的,當然,不管是誰出面買的,估計實際掏腰包的還是蔣介石。
他們打開棺木,檢查遺體,發現我父親身中七槍,都在胸部,血跡已代洗凈,頭面部亦無傷痕。他們一行原先以為收殮得一定很差,故而準備好了更換的壽衣和被褥,看到一切裝殮得很整齊,大家商議,已無再換的必要,就由紀夫人用手巾為我父親凈了面,將準備的壽衣覆蓋在遺體上,另加一幅綢子苫單,蒙蓋全身,再將棺木蓋上,并在棺外做了副棉棺套。
事畢,劉熙眾再去見馮玉祥,報告為我父親認領遺體的情形。馮問:“打算葬在哪里?”劉說:“決定先葬在雞公山,戰事過后,他的家屬還要運回北方安葬。”馮說:“很好。”
吊唁期間,親朋故舊為避嫌,不敢前往,場面自然十分冷清,只有我父親的摯友、時任第二集團軍總司令的孫連仲全副戎裝前來鞠躬致祭,并送來花圈。軍醫處長姜維翰也代表谷良民軍長送來花圈。
由于我父親生前多次前往雞公山,對那里的自然景致情有獨鐘;加之雞公山又在孫連仲的防區之內,便決定暫時將我父親的靈柩安葬在那里的蒼山云海之間,俟戰事結束后再遷回北方。
墓地是由鹿鐘麟和孫連仲一起勘定、購買的,地點在雞公山南崗風景區一處松柏成蔭的山崖下面。我父親的靈柩用火車從武昌運到武勝關,再用汽車拉到雞公山。下葬那天時屆中午,天降大雪,萬籟無聲,在寒山遠樹之間,但見一隊送殯儀仗及一具由數十人抬著的巨大棺木沿山道向墓穴緩緩行進,兩乘藍呢小轎緊隨其后,紙片夾雜著雪片漫天飛舞……
傍晚時分,在一座三尺見方的新土墳前豎起一通簡樸的青石碑,上書“韓公向方之墓”。
全部殯葬活動皆由孫連仲主持。
1954年,我父親的靈柩由其家人遷葬到北京西郊香山腳下的萬安公墓,黑色的大理石墓碑上鐫刻著“韓復榘”三個大字,下邊是“1891-1938”。在那片幽靜的墓園里,與父親長眠在一起的還有谷良民、葛金章、何思源諸先生。蔣介石為什么要殺韓復榘?幾十年來,一直是人們熱議的話題。
要討論這個問題,首先必須明確,韓究竟有沒有犯罪?
在“高等軍法會審”對我父親的判決書中,把“不遵命令,擅自撤退”定為他的主要罪狀,應該說,如此定罪是沒問題的。因為他的確沒有遵照大本營的命令去“死守泰安”。“軍人以服從命令為天職”,這是常識,不遵命令,擅自撤退,就是犯罪,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至于判決書中所謂“勒派煙土、強素民捐、侵吞公款、收繳民槍”等“罪名”,不過是刑名師爺的文字游戲罷了,不足與論。
“撤退”同“進攻”、“防守”一樣,都是一種戰爭形式,本無可厚非。問題的關鍵在于,“撤退”可以,但不能“擅自”。抗戰以來,棄守名城的國軍高級將領不知凡幾,但人家都是“奉命撤退”,何罪之有?更有“奉命”當漢奸的,后來還成了“曲線救國”的英雄呢!那么別人為什么可以“奉命撤退”,韓就必須“奉命死守”呢?為什么劉峙丟了保定、石家莊就不算平漢線北段門戶大開;韓丟了濟南、泰安就是“津浦線北段門戶大開”呢?這應由大本營來判斷,最終解釋權在最高統帥,不是戰地指揮官應該過問的。如果我父親因此就認定是“蔣先生借日人之手消滅異己”,也只能私下發發牢騷而已。
不管蔣介石出于何種動機,在生死存亡的民族戰爭中,蔣以“不遵命令,擅自撤退”的罪名,追究我父親的責任,他應無話可說。
人們之所以指蔣介石殺韓有“消滅異己”、“挾私報復”之嫌,即在他的雙重標準。
我父親于津浦線上失守濟南的同時,第一戰區副司令長官、第二集團軍總司令劉峙于平漢線上連續棄守保定、石家莊,一路跑回鄭州,因此有了“長腿將軍”的雅號,非但未受任何懲處,反而冠冕堂皇地在開封會議上協助軍統特務綁架我父親。
現在普遍認為,我父親的死與他在西安事變中的態度有關。蔣介石都被釋放了,別人紛紛鳴放鞭炮,馳電祝賀,我父親競當著蔣伯誠的面,說張學良做事“虎頭蛇尾”!難怪馮玉祥說起蔣殺韓的一段公案時,感慨道:“很多人私下里說,這是對雙十二事件的報復,看來是頗有道理的。”
梁漱溟于20世紀80年代接受美國人艾愷采訪時,曾就我父親的死因作如下解釋:“韓在無意中得罪了蔣(介石),所以蔣把他槍斃了。怎么得罪蔣呢?就是西安事變。”
梁漱溟在接受汪東林采訪時說:“蔣介石借此殺了韓復榘,是殺一儆百,還是消滅異己,史家評論,都認為是重在后者,我以為是有道理的。”
傅瑞瑗說,社會上“還有一種說法,即蔣介石本不想對韓先生采取如此嚴厲的手段,都是李宗仁施加的壓力”。
1938年夏,國民黨在漢口召開特別代表大會,何思源遇見何應欽,說起我父親被殺的事。何應欽說:韓被殺,主要是因為他不聽命令,擅自撤退,影響軍心。何應欽又說:“韓太剛愎自用,特別是得罪了李宗仁。李宗仁告韓不聽命令,主要是兩個電報:一個是‘全面抗戰,何分彼此’;第二個是‘南京不守,何守泰安’。”何思源認為,“何應欽的話是符合實際情況的”。
二何的談話是兩位國民黨高層之間的私下交流,官腔應該少一些,何應欽又是韓案的審判長,他特別強調父親的兩個電報得罪了李宗仁,是他被殺的主要原因之一。蔣介石在開封扣韓前后都曾與李宗仁、白崇禧磋商,足見李確是參與其謀。
不過,在李宗仁擔任第五戰區司令長官期間,得罪他的遠不止我父親一人。看起來,得罪李是否會送命,也不完全是李說了算。具體到“韓案”上,李狀告韓,既合蔣意,亦泄己忿,可謂公私兩便,同惡共濟也。
外間還有一種傳說,即馮玉祥亦主張殺韓,主要依據是馮在擔任第六戰區司令長官時,曾寫信給蔣介石告韓的狀,又據說馮曾在私下說過一些狠話。
傅瑞瑗在臺北曾與石敬亭是鄰居,經常聚會閑聊,在他的回憶文章里是這樣說的:“還有一種說法,即韓(復榘)的死是馮(玉祥)借刀殺人的結果。馮聽到這種話后,流淚了。馮說:‘我又不是真正的領袖,人家要殺韓向方,我不讓殺,人家能聽我的嗎?韓向方是我一手培植起來的,一個做父兄的,眼看自己的子弟被人一刀為快,我是什么心情?散布這種流言的人真是居心叵測!’”
1938年1月11日,我父親在開封被蔣介石扣留。四天后,即15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改組,取消副委員長制,馮玉祥被免去副委員長職,改任委員,連常委都不是。馮韓之間的關系意味著什么,馮玉祥比誰都清楚。
至于外間所傳父親與劉湘、宋哲元聯合,“密謀倒蔣”,甚至“聯日倒蔣”云云,則純屬惡意抹黑,是軍統局專職或兼職特務散布的謠言。無論是蔣在開封軍事會議上對他的嚴厲斥責還是高等軍法會審關于他的判決書,都沒有這方面的指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