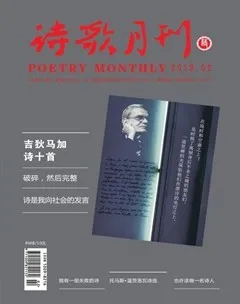黑夜之河(組詩)
露珠
這不是在野外
露珠用它們沿路的淚水
浸濕了我急行的褲管
因此我相信
不是在野外
席山而坐或者
與雨后山間的霧氣相望
我就能從寂靜的
身體中,誘出那位淚水的侍者
這些年,她服侍著我的母親
頭發漸白,服侍著外婆離世
同時,她也催生出我兩個月大的兒子
催生出接下來的生活
如她一般,閃亮而易逝
這段慣性往返上班的小路上
碰到多少露珠,就有
多少滴眼淚。看著它們
像看到無數個不斷在淚水中浮現的自己
被地平線射來的、秘密的陽光
一一抖落
去上海
2006年國慶
再次破曉但仍未到達
我要去的地方
沒想到要去的地方這么遠
火車不知疲倦的咣當聲
像從時光管壁內傳出
經上饒花五元錢
買了一只上饒雞腿香味已久違
太陽即將升起
像行乞者端出的白瓷碗
眼睛第一次被這種日見的光刺痛
車窗外低矮的丘陵被它照亮
仿佛有個聲音告訴我
就要到了
“上海就要到了”確實有人
同時驚奇地叫著
但此刻這個地名變得如此陌生
仿佛來自另外一個星球
我永遠到不了的地方
白晝瞬息變黑夜
心越來越堵——直到黑暗中
的霓虹亮起在黃浦江畔
山巒隱去連著洶涌的大海
呼嘯
大風如期而至
狼群般奔襲在
春天的窗外
我盡量說服自己
到外面走走
有你看的河水
有你曬的太陽
有奔流不息的人群
讓人不易察覺
你已經來到
這生機勃勃的世界
“每個人都可以
爬上一列開往春天的火車”
我盡量不返回愧疚
甚至這個想法
像一排無聲的鐵軌
提前穿過了我的身體
但愿這永恒的車體內同樣載著
我逝去或即將逝去的親人
載著我親愛的
和永遠被愛著的祖國
出了門
我仍提醒自己
別忘了帶上鑰匙
上了車
別忘了給孕婦讓座
返回時別忘了
給自己泡一壺茶
謙卑一回
把窗外那些彌漫的灰塵
請進來歇在茶幾上
我再好好抹一抹
從此心無掛礙
大地深處的聲音
如果我能經常聽見這種聲音
如和尚,聽見木魚
如春天的木匠,聽見秋天的
刨木機;如婦產科護士,聽見
每一次新鮮的啼哭
如果我能經常聽見
當沒有人的時候,你突然
從背后蒙住我的眼睛
說:嗨,我們曾經見過
如果我能經常聽見
——那么,我將一個人
借助寬廣的月明之夜,圍成的一口深井
沖著地心大聲地吼叫
下面,源源不斷傳回來的悶響,仿佛
是我自己身體里,逐漸散失的悲傷
仿佛濃蔭般的青春,正跨過枯水期的尼羅洞
記憶中:沙漠里曾埋伏著整個世界的愛情。
走著山路碰到一群羊
走著山路碰到一群羊
這群羊,并未因我的出現,內部
引發一場小小暴動。像往常一樣
它們跟著頭羊,它們大的,等著小的
有角的,等著沒角的;奔跑的
等著摔倒的。它們聽著,頭羊脖子上
持續晃響搖鈴,仿佛總能聽到
每一位母親的搖籃曲。很快,它們同時
走出了大浪場山谷南面的草場
剩下我一個人,在走
天擦黑的時候,仍是我一個人
趕往已經為外婆搭好的靈堂
走著走著,眼圈莫名濕潤地同頭張望
它們遁跡黑夜的方向
黑夜之河
在我生活的邊界,生長著
一條黑夜之河
黑種的河流
從山上下來,在夜晚
的城鄉結合部,尋找著,遁跡的秘方
它生長著,而非流淌
在它生長的過程中,它的體內
建起一座座秘密的大壩
仿佛它遺失在世上的一座座墳
不斷碼高的水,向上,又不斷
摔下來,向前
星光的掩護下
進行著一場艱辛的眺望運動
每次來到它的岸邊,我都想
站在一座橋上,沖著它,叫幾聲
懇請它,對充滿電量的青春
一次短暫的原諒
但在夜晚,它自顧自地
流淌著,似乎它的生長就是流淌
生活漫長但河面充滿波光
我的愧疚顯影于萬家燈火之下
小如它的流淌
不如它永恒的孤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