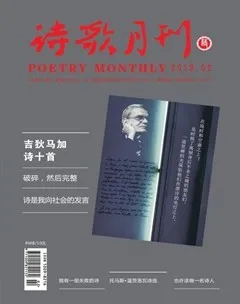在深藍處(外一篇)
從散文(這里指小說)的空間里抵達詩,有怎樣的方式呢?
一種方式是通過宏大的歷史敘事獲得的。比如說,《日瓦格醫生》,它無疑是一首偉大的長詩,帕斯捷爾納克說,他一生所有的詩歌寫作都是為了《日瓦格醫生》而準備的。這是一個純詩人的手段。但我們總是說,這是一部小說;有時候也會說,它是史詩,這樣的說法似乎在接近文學的真相。帕斯捷爾納克作為一位無疑義的偉大詩人,他有能力也有決心處理敘事作品的繁雜,并給我們以距離,在那里,他的小說與他的詩歌一樣給那個特殊的時代作一個腳注,沉郁地低吟著人類的哀歌……
一種方式是通過無限深入地描繪而獲得的。比如說,《追憶似水年華》,普魯斯特這位偉大的歌手在他自己的世界里建造了一切,時間成為他不倦的歌喉。這是一位時間大師的方式。普魯斯特在一篇文論中說道,整個世界需要描寫的素材是“無法確定、難以表達的東西”,人們不可能憑借才智和趣味“憑空制造風景”,需要有一位真正的詩人作為主體憑借某種景物制造一個夢……無疑,《追憶似水年華》中敘述者有一雙善于發現詩意的眼睛、一顆敏感細膩的心靈,一位詩人獨特的情懷……他創造了一種普魯斯特的寫作方式以使散文適應敘事作品的方向過渡。
一種方式是頓悟。比如,喬伊斯的《死者》,結尾是這樣的:“他的靈魂慢慢地睡去,當他聽到雪花穿越宇宙在飄揚,輕輕地,微微地,如同他們的最后結局那樣,飄落在所有生者和死者身上。”在急速中,頓悟把小說瞬間提高到詩的境界里。喬伊斯正以一種迅捷的速度實現詩,而我們知道他一直是一名詩人,詩是他一生追逐的桂冠……我甚至把《尤利西斯》中莫莉的那段有些猥褻有些色情意味的獨白也看成一首博大而無韻的詩……
還有一種是貝克特式,亦即從單調中實現詩的可怕魔術師。貝克特,這位幾乎被認為是20世紀最為乏味的作者,恰恰是一位在單調中實現詩的小說家。貝克特作品中的詩意是作為凌駕于作品其它特性的必然存在。他的作品可以從哲學、心理學、宗教和社會學等方面去闡釋,而且這些闡釋從來就沒有中斷過,但是最重要是把他的作品看成詩,“有關時間、時間的稍縱即逝性、存在的神秘性、變化與穩定的似非而是性、必要性和荒誕性的詩。”(馬丁·艾斯林《荒誕派戲劇》)詩永遠是藝術的最高形式,但并不一定要求它們必須以長短句、韻律和分行的形式來顯示,通過其它形式釋放出詩意也是允許的和必然的。比如,塔科夫斯基的電影作品(塔科夫斯基不止一次地說,我一直視自己為一個詩人,而不是個電影工作者),愛德華·蒙克的繪畫作品,佩索阿的隨筆《惶然錄》,普魯斯特的散文作品(小說《追憶似水年華》)等等。
阿蘭說,小說在本質上應是詩到散文。隨著時間的流逝,小說在到達散文的時刻起,它又要轉向詩了。普魯斯特和貝克特給我們作了精確的示范。
小說作者在很多時候,顯示了寫作者的智力和技巧。然而,真正的藝術不依賴于智力,而更依賴于它趨向詩的動力。普魯斯特說,“我認為作家只有擺脫智力,才能在我們獲得種種印象中將事物真正抓住,也就是說,真正達到事物本身,取得藝術的唯一內容”。小說只有趨向于詩的時候,它才真正獲得生命,它才有了一對能夠飛越塵世的翅膀,它才能在語言、歷史、社會、政治等事物的桎梏下獲得解放……
因而,我想,在寫作的深藍處,小說必然是詩,或者是趨向于詩的。小說美的最終姿態是詩,小說作為藝術的姿態必然是詩。一名小說家只能是詩人,他別無選擇。詩如無可比擬闊大深遠的大海容納著小說的波瀾滔天和異峰突起。
也許該做一名詩人
切·米沃什小心地封存著自己的記憶,并適時地拿出來,為詩歌效力。他清楚地知曉詩歌與童年的不可分割性,“關于詩人不同于其他人,因為他的童年沒有結束,他終生在自己身上保存了某種兒童的東西”。在《詩的見證·生物學課》中,米沃什繼續深入地向這一古老的領域掘進,他闡釋了童年對于詩人日后詩歌氣質的決定性影響。“他(詩人)童年的感知力有著偉大的持久性,他最初那些半孩子氣的詩作已經包含他后來全部作品的某些特征。”我甚至相信,最初的詩作包含著他后來作品的最重要特征,甚至引向詩人的生命本質,即便這些特征尚未顯現、尚無可預期的征兆。
一名詩人的成長其實是極其艱難的抗爭。這種對抗是劇烈而無聲的。在孩童時期,以學校教育為主體的綜合教育體系,通過兩條巨大的絞肉機流水線來摧毀孩子心中的詩。一方面,科學課(物理、化學、生物、數學等)以強大理性和邏輯力量消除了“惡魔和巫師”(在我們的語境里,也許是女鬼和狐仙……)的存在,消除與此相關的被認為是荒誕不經的想像和圖景,原來一切儲存在孩子內心的神秘力量和想像事物都被無可辯駁的事實所摧毀。這將是科學世界觀的勝利,而對于未來詩人而言,無異于大廈傾圮,他的世界必須被隱匿,轉移到不引人注目的拐角。另一方面,屬于社會屬性的廣泛信息越來越多,越來越強大,這些“可靠的信息”將為孩子們將來“參與我們的文明”作好準備。米沃什說,“在學校,我們每天被灌輸,直到我們的觀念與我們同代人的觀念沒有分別,直到我們不敢懷疑某些原理,例如地球圍繞著太陽轉。”
在這樣成長的過程中,未來的詩人奇異的想法總是被日益加強的權威聲音所覆蓋,甚至直到懷疑消退。在這樣的情形下,我們未來的詩人離“詩歌的真實”越來越杳渺。哲學家舍斯托夫總結了這種教育方式帶來的最終結果:“我們每個人都產生一種傾向,就是只有那些對我們整個生命來說似乎是虛假的東西才被當成真理來接受。”而詩歌需要的養分恰恰相反。
在這種情形下,我們未來的詩人只能使用屬于他自己的秘密武器來抵消這種方式帶來的強大影響——他學會了涂鴉,在教科書的邊緣,在他的學校筆記本上,他偷偷地涂劃上幾行幼稚的詩行(也許并不能稱為詩)、一位女同學名字是首字縮寫、一只長得像班主任的烏龜……在這偷偷摸摸的肆意涂鴉中,他無意間消解了上述教育體系對他的禁錮,從而把他的童年保存在遙遠的內心深處,把他的鬼怪儲存在記憶的某個洞穴中。
作為與20世紀有著深度交互的詩人,米沃什虔誠地回到童年,回到自己的幻想時節,在哈佛大學著名的諾頓講座中,不適時宜地宣稱:“對于大多數詩人而言,詩歌是他們的學校筆記本的一種繼續,或者一一這既是實際情況,也是打比方——是寫在筆記本邊緣上的。”
在我們的體制之下,進入大學之后,這些筆記本將發揚光大。我們未來的詩人們可以一展歌喉,在這春天里,在愛情起錨的季節。詩歌是擋不住的,未來詩人必然會寫出他的詩作,必然地宣布“圣神的想象力的藝術”(威廉·布萊克語)的勝利,詩歌必然是孩子的勝利,詩歌必然是青春的勝利。
我回憶起對于大學生活的美好印記,那些戰戰兢兢地在夜晚開始寫詩的日子——就像偷偷從事秘密的非法勾當一樣,但它令我心醉神迷,獲得的是某種罪惡的快感。想想,這是多么美好的事啊!
從你寫下第一行詩起,你就不自覺地學會“在神圣的黑夜里遷徙,浪跡四方”,在大地上“詩意的棲居”……世界是為你而存在的,每一處風景、每一條道路、每一個點都等待著你的巡幸。在這樣的時刻里,你是無比榮耀的王。
無所事事是保存自身的唯一容器。真正的詩人就是無所事事的人。本雅明在評論波德萊爾的時候,就寫了篇名為《游手好閑者》的文章。他這樣說是有道理的。他所說的游手好閑正是無所事事的一種表現方式。我總是告誡我自己,不要在文章中老是固執地提起自己和自己的經歷,那樣未免有自戀之嫌。但是在這里,我還是忍不住地說,我自己喜歡無所事事的時光,我喜歡無所事事的存在,只有在那樣的時刻里,我才品嘗了生命的甜美和作為詩人才擁有的美妙的孤獨。但是,這樣的時刻并不多,我懷戀那些曾經的時刻,我向往在未來我能擁有更多的無所事事的存在。
里爾克在《重力》中寫道:“重力穿透了他。/但是從沉睡者那里,/如同從低垂的云那里,/降下豐厚的重量之雨。”但是,宇宙重力(也許這是不符合科學規律的詞語)對于詩人而言是不存在的,它只對眾多眷戀世俗生活和受其規則約束的人起作用。他爬到高樓的頂端,那些豎立在地球上最高的樓……也許這也不夠……他輕輕地登上神人的山峰:奧林匹亞山和昆侖山,那里的風景才配得上他明亮的眼睛。假如重力在必然存在的,那么它在他身上就會變得輕盈,并且帶給他“豐厚的重量之雨”。
作為詩人,你會跨過那些有形或無形的路障,因為秩序只是針對想被其統治的人們而設置的,于詩人而言,這些根本就不存在。你是一個可以像風一樣飄蕩的人,一個可以像陽光一樣跳躍和閃動的人……最好的他是無形無影的……沒有歷史、沒有身份……沒有過去,也沒有未來……
你的目光是那樣的純凈,閃爍著詩意,要深透重重荊棘、層層迷霧……也許某一天,你要起程,把生命作為旅費,購買一張車票,走上通向四面八方的道路(有詩人說,詩是道路,是的,是這樣的),大地間的悠游卒,將成長為宇宙的流浪者……當然,還有一種可能,你永遠是在路上的,你的腳下一直是無限、神秘、未知的道路……
也許,我們都該做一名詩人,從現在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