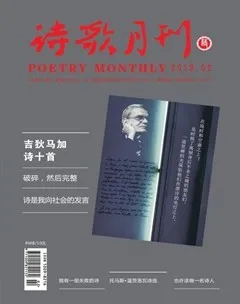托馬斯·溫茨洛瓦詩選
托馬斯·溫茨洛Tomas Venclova(1937-),立陶宛著名詩人,學者,翻譯家。前蘇聯桂冠詩人的叛逆之子,地下詩歌領軍人物,流亡美國。曾與波蘭詩人米沃什和俄羅斯詩人布羅茨基結為好友,“布羅茨基圈”的最后一位在世詩人。1977~1980年在伯克利加州大學執教,1985年在耶魯大學獲文學博士,并留校任教至今。第一本英譯詩集《冬日對話》1997年出版,布羅茨基在序言中大贊其詩中表現出的罕見的勇氣和凝聚的力度,這本詩集奠定了他在歐美文學中的地位。溫茨洛瓦的魅力和影響力遠遠超出了詩歌范圍,除了隨筆、詩歌翻譯和文學評論之外,他的時政批評在歐美具有相當大的感召力。
謝諾梅杰沃,1977年
通過海關的寒意,一排武裝的士兵,
攀上通往硬通貨之天堂的舷梯,
我想起還未向仍留在身后的不多的幾個人揮手致意。
甚至在飛機離地前他們已永久成為影子,
長途電話深處的回聲,被遺忘的小本子里的地址,
而這就是一切是我們時代唯一的奇跡。
我知道他們的聲音會消失而他們的話將化為塵土,
他們相似的臉會在照片的褪色中枯萎,
書架和臺燈將占據他們的位置。
我不知道是我還是他們將置身珀爾塞福涅的牢房。
從座位上我凝視窗外平坦的原野,
我的喪失之身,如本地一位詩人所言。
那里,發電廠一側,被撕裂的太陽很快將掛上天空,
電車嗞嗞作響,將泥漿濺上三月的大街,
格魯吉亞大道附近的池塘開始融化。
在那里,一堵仿佛開了多扇窗戶的戰后的墻邊
一名死者臥倒在地,警察驅趕著人群,
而那時我還不能懂得這意味著什么。
此后我將被賦予足夠的時間來理解
十二年,二十年,也許三十年
在廣闊而黑暗的大陸轉暗的房間。
在那樣的地方在我敲門時鑰匙會吱嘎作響,
在那樣的地方我將體驗一行詩如何迸射火光,
午夜的樹和雪也將因其熠熠生輝。
一片外國的土地被付托給我如一個臨時的身體,
臨近巴倫支海是那些迷失者的濕地
飛機掠過一座看不見的城市。
我不在此地生活已久
如沉默的島
每天我遠遠地漫步
在這空曠河畔的鄰近地帶
沒有人行道,玻璃窗,沒有鎖。
它的路燈幽暗,
房間填滿時光和睡意,
被分配了物體的低語,
在真實與非真實之間,
仿佛一個映象,一個第二自我。
仿佛一個身體,在夢里找到,
或者一條延遲的消息,
被幾重海水清洗,
這就是為何我驚懼于
它的形式,質料,和大小。
誰還留在那一所房子里356122a3348627fecb438b691cabbb62
誰就將繼承一種危險的命運
守護一塊被隨意處置的土地
從塵土到塵土
在現時和空虛之上?
是時候了離別身后不幸之城的朋友們。
一道貧瘠的光保佑他們在漂浮的電燈之上。
夜晚失去了我們而通往奧克斯塔瓦利斯的道路發現了我們
它粗糙的松樹皮,松脂和多松針的天空。
是的,是你的空間如此出乎意料地深厚著、生長著,
是你將我們聚合,將我們從現成的結論帶向遠處。
你收縮我的瞳孔,打開我的視野
在一只手的陰影和一盞隱蔽的油燈下。
假如我這一代命定不能贏得這場比賽,
且讓那些將不久于人世者首先獲得足夠的
日常的面包和不尋常的命運,
日常的鹽和不尋常的水。
讓完美的聲音,沖破一切,找到我,
作為對于謊言的贖罪,作為不幸和自由的開端。
如此奈姆納斯河才會更加幽暗和甜蜜,
如此,虧消之月才會行進和浮動在河口三角洲。
冬日對話
步入這片風景。天仍然很暗。
一條小徑遠遠消失在沙崗那邊。
大陸對抗海洋的戰爭
看不見,但充滿聲音。
一個旅客或天使離去
這輕雪覆蓋的小路,
反射在黑色窗口的海岸
讓我們想起寸草不生的南極。
深海仍涌著泡沫,尚未封凍。
沙子被吹出一英里之外。
大橋在此時而清晰時而模糊
因為嚴冬的洞穴在生長和擴散。
沒有電報,沒有信件,
只有照片。收音機失常。
季節如一支蠟燭,滴下熔蠟,
給這危險的時間封緘。
空氣多么潮濕,巖石多么陡峭,
拂曉的輻照多么強烈!
睜大眼睛,你看到墻壁多么清晰,
還有教堂的高塔,人的身影。
唯有樹林霧中的輪廓突出在
白色背景下。透過樹皮,
即使閉上眼,你也可以看到
它最后的、狹窄的、抵抗的年輪。
“這種注視的習慣令眼睛疲勞,
一個小時后,就不難迷路。”
“預言從不跟我們浪費言辭。”
白霜覆蓋的地軸傾斜,
仿佛在地平線的邊緣,
船舶也變黑和僵直,
在蕭條的海上的天空
木星和火星閃爍。
空虛蔓延到大西洋。
原野光禿如未上鎖的大廳。
二月隱藏在一月的地層之下,
平原縮頭在潮濕的風里。
在海洋之外,群山赤裸自身。
在外表之下,融化著的雪堆
不斷瘦身、變黑。“那是什么?”
“同樣是,河口,海灣和港口。”
在沉重的云織的網下
逼仄的空地像條魚發亮。
“你是否記得星星說過什么?”
“這個世紀沒有征兆地消逝,
這是事實。”“死亡的吸引力
羈絆著人、植物和其它事物,
所以谷物發芽而產品化為灰燼,
所以我認為一切都并未結束。”
“見證者在哪里?我不明白,
誰將真相與謊言區別:
也許世界上就我們兩個。”
“在我看來,似乎只有你。”
“誰是第三個發言者?”你說
“無人聽到過我們這番談論?”
“天堂和冰雪覆蓋的原野聽到了,
聲音有時比我們的心臟活得久長。”
正午使樹木轉黯。
寬闊的日光下,你僅覺察到
一些小東西,替代了那些話的位置
一小時前它們似不存在:
一個厚冰塊落下的碎片,
樹枝的殘骸,脆弱的磚房
在接近路的轉彎處……然后,寂靜
在海的這一邊,在海的另一邊。
紀念一個詩人
我們將再次見面,在彼得堡
——奧西普·曼德爾施塔姆
你是否回到了城市,它的規劃、
副本和骷髏承諾過的地方?
暴風雪帶著它的海軍部快速行動,
它成幾何級數增加的繪畫工作
在壓平一切的工序中衰弱。
當電力切斷,
從冰冷的鬼魂中,陰影誕生,
銹跡覆蓋的機車
潛行在伊茲馬伊洛夫大街。
還是同樣的電車,同樣穿舊的大衣
瀝青路光禿禿托舉著廢紙屑,
來自上個世紀的寒意
淹沒了整個車站。
轟鳴聲,天空
封閉。年代蒼白,
黑暗的城市如濃霧擦肩而過,
各種手勢重新浮現如禮物,但是
從來沒有人能出生兩次。
他走進二月的早晨
走進另一個空間,測量著他
和大雪來臨的時間距離。
母狼凍結的洞穴,
瘋人院,監獄和泥漿在召喚他。
黑色的圣彼得堡是他熟悉的
有一回曾經提及。
標準與和諧不能重生,
木板劈啪作響仿佛傳達著
時間點燃的壁爐的溫暖,
而有一種壁爐之火萬古常新,
光學已完成關于其命運的評估:
精髓在于快樂的可比性,
有時甚至在簡單的會見里,
在可持續性中,具有永恒的形式。
現實沒有鏡子:清晰,干凈。
一座島嶼,植根于水沫四濺的激流,
代表未實現的天堂
誕生于一次現場演講,
仿佛在云層之上,在輪船的煙管之上,
鴿群在一只巨輪周圍盤旋,
不敢從一個平常的轉綠的山頭
認出亞拉臘山。
開船!是我們啟航的時候。
雖然巖石開裂,謊言流布,
見證者留下的唯有藝術
照亮最深的冬夜。
青草帶著它的祝福留在冰層里。
河口在尋找幽黑的海洋。
現在一個簡單、無意識的詞破土而出,
幾乎跟死亡一樣毫無意識。
詩
一個卑下、不誠實的十年
——W.H.奧登
夏季漫過城市。
窗口反射灰塵。
暖暖的葡萄酒滴入
冒氣的高腳杯。
在太陽漸弱的光里,
空氣增加了香氣
稠密如西里爾字母
使狹窄的運河轉暗。
你在這里尋求什么,詩人?
古老的陽臺,剝落的
石膏上被抹去文字,
一個化為塵土的世界,
一道戈爾迪結被解開,
粉筆,走道和林地,
門口的泥漿,樓梯,
垃圾,半掩的門。
手勢,生活和聲音
在這里曾是同一的,
喧囂的人群如今使用
一種被改變的語言。
六月晃動著白光,
盲目的鈣化的大腦
無法理解
失去的時間。
年代變亂著人們的
口音,句法和建筑,
太陽落到柱子上,
青銅在壁龕里微笑。
也許唯有貧窮和饑餓
仍然抵制著年代,
也許唯有恐懼和陰影
是它留給我們青春的全部。
在恐懼中變換著游泳
像一條深海里的魚。
恐懼長存于此,
遠比身體耐久。
和平的圓形的廣場
體味著中午的煙霧。
粉筆,走道和石膏,
剝落的石膏上的文字。
唯有少數幾枚銅錢
保留了生活的變化,
時間將它們留下,通過一家
本地的荒謬銀行清點出來。
旋律和手勢突然停止。
大街朝后街轉過身去。
真奇怪,我們相遇
比預期的早。
不是在耶霍塞哈特河谷,
不是在忘川的岸邊樹林,
甚至不是在真空的宇宙——
開爾文和貝克勒爾
像神一樣統治著這里。
溫暖的酒仍在滴下。
失眠的云浮動
在炎熱、白色的六月。
人群和它的聲音繼續漂浮,
但我們手藝的分量一如昨天
將恐懼集中在一個詞里,
賦予時間意義。
唯有灰塵和聲音顫抖。
而聲音卻不必知道
多少真理已被納入
它的輻射和孤獨中。
獻給一個嬰兒
命運只喚回命運,
死亡喚回死亡。一個孩子的經歷
不同,也許更為簡單:
他長成,重復著創世紀。
在搖籃里仿佛在伯利恒的馬槽,
他感覺到光,很快是黑暗,
他學會區別拱頂和深淵,
大陸緩緩移動脫離海洋的無限
(等同于他和母親)。然后
他識別草,太陽,和月亮,
硬頭鱒以及烏鴉的
隊伍,游蕩在天空。
他以蹣跚的五官,馴服
正午的栗木柱
黑榿木,雪,黑線鱈,馬達
一只夢想的家養的狼
而這狼仍在森林里,保留著
不確定的恐懼。詞語就這樣到來,
還有意識,隨詞語一起
生長,在高處重復著“隨它去”,
將自身嵌入一個奇怪的意思
突然懷疑,黑暗就是我們自身,
雖然光仍存在于我們頭頂。
此后他與這個世界的親緣
超過與生養者之間的關系。
一根秘密的絞線將他束縛于介子,
煤和鉆石,束縛于亞馬遜河,
水星和天使長,
森林和雌鹿。
事物在他面前俯首,另一些
升起,在回聲四起的荒原
在失去的樂園和喇叭之間
他醒來,將宇宙注滿,
它既是沙漏也是沙,
如喬治·赫伯特所言。常常
他似乎接近一個門檻
——詩行交叉,音符共同作用,
存在或許即將企及它的目標。
我們這些此前經歷過創世紀的人,
只能以死亡回答。
我們比他年長我們已經知道
音符會消耗,詩行會磨損,
發音氣室存不住聲音
書寫粉碎在紙上。
只有很少時候,在盲目的希望中
我們偶然遭遇記憶里
熱情的事物。它試圖代表
不朽,但它并不能,并不總
能。讓我們還是感謝它吧。
無論如何,它帶來力量,
在我們步入低谷的時候,暮色
四合,此時最好沉默,
因為我們仍不知道,上帝的臉龐
是否出現在那深邃的所在。
對岸
在椴樹的喧囂下,在石頭堤岸前,
在一條湍急如臺伯河的激流旁,
我和兩位長須年輕人飲著吉爾伯酒。
薄暮中——酒杯的叮當聲,煙霧。
但我不了解他們。我認識他們的父輩。
一代超過另一代。錄音機發出
顫音和噪聲。我的兩位對話者
想要了解我沉思過的問題:
受難和憐憫是否還有意義;如果
不循任何規則,藝術是否會得幸存。
我曾是和他們一樣的人,但神意
賦予我一種奇異的命運:這,當然
不比其他人的更好。我知道惡
從來不會消失,但一個人至少可以努力
消除盲目;而詩,比夢應該更有意義。
在夏天,我常在黎明前醒來,
我感到,沒有畏懼,新的一代
繼承詞典、云、廢墟、鹽
和面包的時刻,正在接近。
而我將被授予的一切不過是自由。
關于朋友的詩
當陌生人甚至不是陌生人
一切尚未被改變
水流流向非存在,
仿佛虛無也有了方向,
當一天在城外結束
收音機嘎嘎吱吱響,風暴臨近,
讓我們再一次將自己藏起
在夏日最后的時刻。
當天空轉暗,經由過道門
消失的,逾期的,后退的人啊
在這個夜晚唯有我們的
房間是唯一的樂土,
他們的影子游蕩在我們的夢里
彼此曾經愛過和遺忘,
他們在一面面鏡子的深處安頓
又從其表面意外地浮現。
就這樣在他們的棺木中重生
長翅膀的女人,看不見的兄弟,
這一代已化為回聲,
書頁,枯草
而那些仍然活著的,聚集在霧里,
在空空的房子和長途跋涉中。
他們的武器是抵抗和沉默,
阿波羅可能拯救他們的希望。
他們參觀了我們的森林。死者
家具記得他們的木頭似的手指。
在他們邁向成熟的時候
他沒有回答俗世的評判。
他們是一個開放和偉大的家族
他們的子女享有一個共同的姓名。
代替他們的聲音,空虛
填滿了我們空置的一切。
我不相信壞運氣我相信
朋友,為了他們我等分
世界和眼睛之間的距離,
脆弱而空幻的永恒。
所有的面孔都將消失在光里。
燈盞燃盡,真相大白,
但他們的腳步與我共存
如同在空間里的平行線。
又是秋天,充實而慷慨。
在由少數靈魂贏得的城市
在異國的有軌電車和老房子上
這是九月最初的壯麗時間。
大型駁船隱隱出現在水域,
早晨的每根神經緊張著,
第一片擊中地面的樹葉
棱角分明,像一枚盾形紋章。
詩
傍晚帶著寒意抵達:
在拱門牌樓之外
出現或許十個車站
和數個九月的公園
住宅區或生活圈
游移的一百瓦的燈光
落在盲目的磚房上,
猶如進入迷宮的護衛隊。
阿里阿德涅和彌諾斯規則
這時仍然管用:
由于幾個小時的大霧
沒有一架飛機起飛。
每天列車都擁擠不堪
多少空間,多少空氣和不幸!
所以返家的囚犯
有時也會想念監獄的看守。
仿佛空間償還的債務
打開了幾處熟悉的地方。
我重復道:“紀念碑,島嶼,
公共汽車,大學。”
我說:“明天我將離開,
我將離開,至少將盡我所能。”
沿著生活世界的邊緣
我的靈魂匆匆走進黑暗。
舊址在挨近,
書信改變了形式和意義。
我聽到聲音變弱,
無法找到我們兩個
即使在這空的上鎖的房間
那些油畫也認不出我,
不是在夢里,不是在天國,
不是在但丁的第二圈。
時間這樣停止;更確切地說,
它這樣漸漸被打破,
就像每年,你聽到
更遙遠的電話里的鈴聲。
一天又一天,記憶
如指南針改變了直徑,
直到過去成為簡單的一擊
在起初偽裝的復雜之后。
我不知道你聽到看到了什么
在從現實碎裂出的現實里。
冥河平鋪的河岸
經受了無情的漲潮。
所有輕微的事物都是分開的,
沒有我們世界照樣存在,
而且,說實話,存在著
寂靜和九個繆斯。
它的首都是輪流的,
冰雪的游戲令我們厭倦,
大霧從不出賣什么,
感謝上帝,仍然有字典存在。
在這樣的王國朋友的手
從不急于為幫助誰伸出,
空虛或最高的權力
給天使送去節奏和語言。
我甚至不會要求一個短暫的遺忘,
或死亡,或罪的赦免,
只是留下最初的皮
在石頭和冰冷的夜晚上。
告訴福丁布拉斯
時間,被拒絕的聲音和手勢,
終于免除未知的遺產之重,
他們在臺階下將禁錮舒服地裹好
再也不來看這最后的一幕,
丹麥,丹麥已不復存在。
愿他們安息。白色的島嶼,
巖鹽補足了他們的血,
雪暴從康諾特。海岸升起,
森林裹進水汽和草木叢生的果園,
丹麥,丹麥已不復存在。
永恒拒絕;永恒保護他們,
夏天守衛著沙灘,彩色
玻璃,巖石的耐心,
孤立的田野,被詛咒的柳樹。
丹麥,丹麥已不復存在。
詩
九月初以來我們就受制于宇宙的引力。
閉上眼,你會感到樹葉輕拂臉上,
擦在百葉窗上,無意地碰到一片云彩,
屋瓦間的枝條,躲開了我們的雙手。
大樹使白晝枯竭。天空白得刺目。
話說了一半,沒入退潮的河谷。
一切都在我心中,我知道疲倦的阿特柔斯。
為何歡欣于城堡的靜默和熱氣騰騰的水域。
你會邁過這道門檻么?命運,水堰,礫石,
破舊的教堂,三角形的泥沼。
時間匆忙走向腐質物和沃土,
城市在打轉,風聲此起彼伏。
你會贏得還是失去我,迄今無人知道。
休耕地侵蝕,星座被刪減。
我吸引著惡運,像一塊磁鐵,
像一塊磁鐵,惡運吸引著我。
R.K.
我所知道的全部就是,它已過去(或正在過去)
這個黑暗的世紀,其程度難以置信,
也許它只是,不比少數幾個世紀更黑。
黑暗是一貫的。它把人的身體變成數字,
將人的靈魂碎成鋸末和虛無,
所以它看起來贏了。懸崖的邊緣
假裝成希望,我愿意說,的確是某種成功。
欺騙的邪惡設計曾被冶煉爐忠實地執行,
而下一刻是石質的星下的
堅冰。令人窒息的貨運列車
吃力地駛向虛無,向西和向北。
但一切都是暫時的。帝國的紀念碑
矗立在堅韌的薊和芒刺之間的泥漿中。
擴音器安靜下來,花崗巖被風化。
我們出生在那片土地。現在,我們將它留在身后,
我們甚至不敢轉身,像俄耳甫斯。
我們隨身擁有的是什么?反諷,耐心,
以及不多的勇氣。通常只有一種不確定的感受
認為你做的遠遠少于你應該做的
(一種歉疚或有罪的下沉的感覺,你的孩子
也不會原諒即使上帝原諒了你。)
這是我們所有的選擇。即使如此我們知道
如何接受苦澀的真理仿佛它是一件禮物。
我們并不崇拜死亡。在車轍和水泥路面之上
我們了望天使。我們熱愛她們。在圖書館里
我們點燃燈。我們稱惡為惡
稱善為善,我們心知將它們分開是多么困難。
我們舉燈走進黑暗之中,也許這樣就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