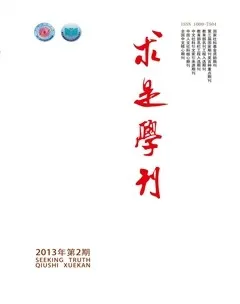論馮舒、馮班對李商隱詩歌藝術(shù)的繼承
摘 要:馮舒、馮班以李商隱、溫庭筠為宗,上導(dǎo)魏晉六朝,下及宋代“西昆”。二馮不僅以文本批評推廣晚唐詩歌理論,且詩歌創(chuàng)作中重視用典、追求比興、文字華美等特點(diǎn)均與李商隱、西昆派一脈相承。二馮詩歌中既有對字詞的錘煉、聲律的修整、典故的繁用、結(jié)構(gòu)的巧妙布置,又有很深沉的人生感慨,并能將這種人生感慨和詩歌技巧巧妙融合。雖然表達(dá)的是敏感的政治美刺主題,卻能寫得蘊(yùn)藉含蓄、綺艷瑰麗,充分體現(xiàn)了溫、李范式和綺艷風(fēng)采。
關(guān)鍵詞:馮舒;馮班;李商隱;西昆
作者簡介:周小艷,女,河北大學(xué)文學(xué)院中國古代文學(xué)專業(yè)博士研究生,從事古代文學(xué)批評史研究;周杰,女,河北大學(xué)文學(xué)院中國古代文學(xué)專業(yè)博士研究生,從事唐宋文學(xué)研究。
中圖分類號:I207.2 文獻(xiàn)標(biāo)識碼:A 文章編號:1000-7504(2013)02-0141-06
馮舒,字巳蒼,晚號癸巳老人,明末諸生。馮班,字定遠(yuǎn),號鈍吟、鈍吟老人,自號“二癡”。兄弟二人為江蘇常熟人,師從錢謙益,為“虞山詩派”的中堅(jiān)人物,號稱“二馮”或“海虞二馮”。
二馮詩學(xué)是在對明代思潮的反思中形成的。明七子派“文必秦漢,詩必盛唐”的主張強(qiáng)調(diào)了形式風(fēng)格的古典性,但將詩歌引至死擬古人的狹小境地,犧牲了情感的真實(shí)性;公安派、竟陵派強(qiáng)調(diào)情感的真實(shí)性,但脫離了詩歌經(jīng)世致用的現(xiàn)實(shí)作用,亦犧牲了形式風(fēng)格的古典性。錢謙益認(rèn)為明七子和竟陵派“學(xué)古而贗”、“師心而妄”[1](P758)的兩種病癥之根在于脫離了詩歌的本質(zhì)特征,背離了儒家經(jīng)典的軌道。所以,錢謙益將詩歌引入“詩言志”傳統(tǒng),從情感上貫通古今,從而將復(fù)古與言情融合。“夫詩者,言其志之所之也。志之所之,盈于情,奮于氣,而擊發(fā)于境風(fēng)識浪奔昏交湊之時(shí)世,于是乎朝廟亦詩,房中亦詩,吉人亦詩,棘人亦詩,燕好亦詩,窮苦亦詩,春哀亦詩,秋悲亦詩,吳詠亦詩,越吟亦詩,勞歌亦詩,相舂亦詩。”[1](P758)詩歌是內(nèi)心情感的真摯流露,只有發(fā)自內(nèi)心之作才為詩,那種一味模仿古人、無病呻吟之作,既無益于個(gè)人情感的宣泄與抒發(fā),亦無益于社會(huì)。所以“有真好色,有真怨悱,而天下始有真詩”[1](P758)。故而錢謙益評價(jià)詩歌以性情為先,只有真情之作才能稱之為詩歌,然后才可以以詩歌之標(biāo)準(zhǔn)衡量之、品評之;否則,一切皆為無根之談。
錢謙益以真情而非形式風(fēng)格作為衡量詩歌的標(biāo)準(zhǔn),從根本上抹殺了各種詩歌題材和詩歌風(fēng)格之間的差異,從性情的差異性上肯定詩歌形式風(fēng)格的差異性。也就是說,各種風(fēng)格特征和各個(gè)時(shí)代之詩歌的地位是平等的,不必強(qiáng)分初、盛、中、晚,亦不必強(qiáng)分唐、宋之優(yōu)劣。這樣就從根本上推翻了明七子“文必秦漢,詩必盛唐”之論,為中晚唐詩、宋詩爭得了與盛唐詩同等之地位。
二馮繼承錢謙益詩論,不遺余力地抨擊七子派和公安派、竟陵派,認(rèn)為“王、李、李、何之論詩,如貴胄子弟倚恃門閥,傲忽自大,時(shí)時(shí)不會(huì)人情;鐘、譚如屠沽家兒,時(shí)有慧黠,異乎雅流”[2]。二馮又繼承了錢謙益之性情論,從古今性情相通的角度融合復(fù)古與性靈。然二馮與錢謙益不同之處在于取法晚唐,以晚唐詩為基礎(chǔ),“建立了以象征性比興為核心,崇尚細(xì)膩功夫與華麗文采的詩學(xué),這種詩學(xué)對晚唐詩歌的審美價(jià)值作了正面的論述與肯定,確立了晚唐詩的地位”[3](P148)。在學(xué)術(shù)界掀起了一場晚唐熱。關(guān)于此點(diǎn)馮班曾自言:“自束發(fā)受書,逮及壯歲,經(jīng)業(yè)之暇,留心聯(lián)絕。于時(shí)好事多綺紈子弟,會(huì)集之間,必有絲竹管弦,紅妝夾坐,刻燭擘箋,尚于綺麗,以溫、李為范式。”[2]
馮班感嘆宋代“江西”以來詩文風(fēng)雅之道的喪失,倡導(dǎo)晚唐詩風(fēng)的復(fù)興。于是,馮班從詩歌發(fā)展觀上建立了其晚唐、“西昆”詩學(xué)的理論支點(diǎn)。從繼承的角度講,“詩妙在有比興,有諷刺。離騷以美人喻君子,國風(fēng)好色而不淫是也”[4](P276)。而古今詩人繼承諷刺比興傳統(tǒng)者,李商隱當(dāng)屬其一,“唐香艷詩必以義山為首,有妝里,意思遠(yuǎn),中間藏得諷刺”[4](P276)。李商隱詩繼承了詩教的比興傳統(tǒng),集萃了先秦漢魏、六朝、唐代詩歌之精華。從變革的角度講,“‘昆體’壯麗,宋之沈、宋也。開國之文必須典重。徐、庾化為沈、宋,溫、李化為楊、劉,去其傾仄,存其整贍,自然一團(tuán)元?dú)鉁喅伞@睢⒍拧W、蘇出而唐、宋漸衰矣,文章之變,可征氣運(yùn)”[4](P55)。徐、庾艷體詩乃詩歌變革之先導(dǎo),為盛世之音的前兆。而晚唐之溫、李,猶若齊、梁之徐、庾,亦是詩歌變革之先行軍,“西昆詩派”可比初唐四杰,為盛世之音的開創(chuàng)者,符合詩歌發(fā)展的規(guī)律。
繼而,二馮從辨析體制的角度徹底摧毀了七子的漢魏盛唐擬古準(zhǔn)則。首先,明確詩與文的分界,“南北朝人以有韻者為文,無韻者為筆,亦通謂之文。唐自中葉以后,多以詩與文對言。余按有韻無韻皆可曰文,緣情之作則曰詩”[2]。保證了詩體的純粹性。其次,在詩體內(nèi)部模糊詩、樂府、歌行的分界,指出詩無定體:“古詩皆樂也。文士為之辭曰詩,樂工協(xié)之于鐘呂為樂。自后世文士或不閑音律,言志之文,乃有不可施于樂者,故詩與樂畫境。文士所造樂府,如陳思王、陸士衡,于時(shí)謂之乖調(diào)。劉彥和以為無詔伶人,故事謝絲管。則是文人樂府,亦有不諧鐘呂,直自為詩者矣。”[2]樂與詩一樣,是生與民具,詩合于樂,則為樂之詞也,而樂府所采之詩即為合樂之詞,所以樂府與詩在合樂的角度并無太多區(qū)別,漢樂消亡前之詩即為樂府,樂府即為詩。“伶工所奏,樂也;詩人所造,詩也。詩乃樂之詞耳,本無定體。”[5]唐人律詩,亦是樂府也。今人不解,往往求詩與樂府之別。破除了樂府與詩之間的隔閡,又重新確立了詩與樂之間的關(guān)系,并通過解構(gòu)樂府詞與樂的關(guān)系,打斷人對音樂的追念;同時(shí)將樂府寫作方式汰存為賦古題和賦新題二種,示人坦易可行之途。
最后,二馮校定《玉臺新詠》和評點(diǎn)《才調(diào)集》、《瀛奎律髓》,“從文本的校勘、輯佚、考訂入手,由文本研究推廣到詩史研究,通過詩史研究和選本評點(diǎn)來表達(dá)自己的詩歌觀念”[6]。并以此教授后學(xué)。馮武《二馮評閱才調(diào)集凡例》曰:“兩先生教后學(xué),皆喜用此書,非謂此外者無可取也。蓋從此而入,則蹈矩循規(guī),擇言擇行,縱有紈绔氣習(xí),然不過失之乎文。若徑從江西派入,則不免草野倨侮,失之乎野,往往生硬拙俗,詰屈槎牙,遺笑天下后世不可救。”[7]從“西昆”與“江西”對舉的角度肯定并推廣晚唐、“西昆”詩風(fēng)。
袁行霈主編的《中國文學(xué)史》評價(jià)西昆體曰:“西昆集中的詩人大多師法李商隱詩的雕潤密麗、音調(diào)鏗鏘。……西昆集中詩體大多為近體,七律即占有十分之六,也體現(xiàn)出步趨李商隱、唐彥謙詩體的傾向。……西昆體詩人學(xué)習(xí)李商隱的藝術(shù)有得有失,其得益之處為對仗工穩(wěn),用事深密,文字華美,呈現(xiàn)出整飭、典麗的藝術(shù)特征。……都是晚唐五代詩風(fēng)的延續(xù)。”[8](P29)這段話亦可以用之于馮舒、馮班。馮舒、馮班不僅以文本批評的方式宣揚(yáng)晚唐詩歌,推廣詩歌理論,且他們詩歌創(chuàng)作中重視用典、追求比興、文字華美等特點(diǎn)均與李商隱、西昆派一脈相承。可以說,馮舒、馮班的詩歌創(chuàng)作是李商隱和西昆詩風(fēng)在清朝的回響,亦是晚唐五代詩風(fēng)的延續(xù)。本文從題材和藝術(shù)表現(xiàn)力兩方面論馮舒、馮班詩歌創(chuàng)作對李商隱詩風(fēng)的繼承。
就題材而言,詠物詩在馮班詩集中占據(jù)很大的比重,所詠之物多是自然界或日常生活中一些纖小的事物,常見的動(dòng)物有“巧語斜飛百草芳,紅閨日暖覺春長”1的燕子,“露洗風(fēng)吹赤玉寒,當(dāng)庭抝頸錦毛攢”的雞,“翦翦身材綠作衣,簾前聲喚為朝饑”的鸚鵡,“一從玄露下青冥,嘒嘒高枝鎮(zhèn)不平”的蟬,“何年變化別青陵,栩栩隨風(fēng)力不勝”的蝴蝶等;常詠的植物有“今日不堪簾外樹,一枝和粉弄?dú)堦枴钡拿坊ǎ皵€紅鋪綠正芳菲,好似文君錦在機(jī)”的薔薇,“風(fēng)吹露濕一枝枝,帶子埀陰是后期”的桃,“濃掃勻鋪綠不休,最宜長路水悠悠”的草,“檀心一點(diǎn)余春在,莫似尋常看白花”的梨花,“何人扇上畫,特遣不宜秋”的石榴,“桃花豐態(tài)海棠名,映石穿階到處生”的秋海棠,等等;日常物品有“一尺清光勢似鉤,鍔邊名姓舊來讎”的小刀,“雙雙桂葉聚,愁態(tài)滿香臺”的愁眉,“龍腦熏多入縷香,輕云一葉照人涼”的美人手巾,“山骨何人琢,床頭作六安”的枕,“螢尾銜光翻覺冷,蠅頭欲墮莫頻挑”的燈,等等。李商隱的詠物詩很少有那些具有巨大力量和崇高悲壯感的事物,亦多選用纖細(xì)微小之事物,如“徒勞恨費(fèi)聲”的寒蟬,“并應(yīng)傷皎潔,頻近雪中來”的蝴蝶,“皎潔終無倦,煎熬亦自求”的燈,“如何肯到清秋日,已帶斜陽又帶蟬”的柳,等等。
且馮班詠物詩的意象多與義山詠物詩有所重合,如蟬、蝴蝶、燕子、鴛鴦、燈、鏡、柳、梅、桃等。李商隱把個(gè)人的身世遭遇及悲劇心態(tài)與所詠之物緊密結(jié)合起來,托物寓懷,并貫穿于他的整個(gè)創(chuàng)作歷程。詩人筆下的物象,如嫩筍、牡丹、秋蟬、錦瑟等,不但能夠展示詩人在不同時(shí)期的心靈軌跡,而且在這些極具悲劇性的物象身上,凝聚著出身卑微的詩人在宦海生涯中特有的感情與心態(tài)。[9]故李商隱的詠物詩在意象色彩的選擇上偏于蕭索,如雙雙對對的鴛鴦,在李商隱的筆下為“云羅滿眼淚潸然”,柳為“如何肯到清秋日”的弱柳,花為“芳心向春盡”的落花,蕭條之氣貫穿筆端,映射出李商隱的不幸遭遇和凄涼身世之感。馮班筆下的物象,梅花亦是“正到暄春恨過時(shí)”的晚梅,樹亦是“蕭條似海槎”的枯樹,燈亦是“輕煤拂落殘書卷”的寒燈,蝴蝶亦是“栩栩隨風(fēng)力不勝”的弱蝶,衰落之意亦見諸筆端。馮班的詠物詩走的亦是詠物托懷的路數(shù),悲鳴無告的寒蟬、難耐風(fēng)雨的弱蝶、飽受摧殘的衰花,都是詩人沉淪世俗、傷友思國心情的凝結(jié)。
李商隱與馮班同生于亂世,同沉淪于宦海,故馮班的詩歌尤其是詠物詩和詠史詩與李商隱具有跨時(shí)代的心靈契合,或者說馮班在生于晚唐的李商隱身上寄寓了生于明清易代的自己的某些寄托。故馮班詩歌的題材以及情感基調(diào)都是延續(xù)李商隱而來。比如,馮班還創(chuàng)作了一類無題詩和戲題詩,顯然也是受李商隱無題詩的影響。此外,馮班的詠史詩如《古城臺》、《夫差廟》、《故陵》等,也能找到李商隱詠史詩的痕跡。
就藝術(shù)表現(xiàn)力而言,馮氏兄弟努力學(xué)習(xí)李商隱,注重比興手法的運(yùn)用和典故的使用,追求辭藻的華美流麗,追求含蓄蘊(yùn)藉的藝術(shù)效果。
首先,李商隱精于用典,常將古人的言論或事跡提煉出來,蘊(yùn)含在詩歌的人物、事件和背景當(dāng)中。由于很多典故已經(jīng)被不同的詩歌內(nèi)容和意境反復(fù)使用,所以典故本身的最初意義慢慢積淀兩層乃至多層的意蘊(yùn)和內(nèi)涵。“恰如其分地用典往往能在非常有限的篇幅里表現(xiàn)豐富而復(fù)雜的內(nèi)容,擴(kuò)大詩歌的內(nèi)涵,使本來難以明言的情意得以順暢地表達(dá),通過古今的對比,引起讀者豐富的聯(lián)想。”[9](P63)如著名的《錦瑟》:
錦瑟無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華年。莊生曉夢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鵑。滄海月明珠有淚,藍(lán)田日暖玉生煙。此情可待成追憶,只是當(dāng)時(shí)已惘然。
中間兩聯(lián)連用了四個(gè)典故:“莊生曉夢迷蝴蝶”化用《莊子·齊物論》莊周夢蝴蝶的故事;“望帝春心托杜鵑”化用蜀王望帝死后魂化為杜鵑,每到暮春啼血不止的故事;“滄海月明珠有淚”化用《博物志》海中鮫人泣淚成珠的故事;“藍(lán)田日暖玉生煙”化用司空圖“詩家美景,如藍(lán)田日暖,良玉生煙,可望而不可置于眉睫之前也”。[10](P1581)首句的“無端”又與尾句的“惘然”之情相互照應(yīng),中間兩聯(lián)滄海、月、明珠、淚、藍(lán)田、日、玉、煙等眾多意象的反復(fù)疊加,又以四個(gè)典故連環(huán)圍繞虛幻悲苦的惘然之情反復(fù)訴說,構(gòu)筑出全詩迷離虛幻的藝術(shù)境界。而馮班亦是用典的高手,如《和錢牧齋宗伯茸城詩次韻四首》其一:
熏風(fēng)長日正悠悠,蘭室新成待莫愁。一尺腰猶紅錦襻,萬絲鬟更玉搔頭。已障畫扇登油壁,好放偏轅促玳牛。爭似秣陵桃葉渡,風(fēng)波迎接隔江舟。
據(jù)姚弼《鈍吟集箋注》(稿本)所指,詩中共用了十五個(gè)典故。熏風(fēng)長日:長日助威棱之氣,熏風(fēng)同長育之恩;蘭室:梁武帝《河中之水歌》“盧家蘭室桂為梁”;莫愁:《初學(xué)記·釋智匠古今樂錄》石城西有女子名莫愁,善歌謠;一尺腰:庾信《昭君詞》“圍腰無一尺”、溫庭筠《張靜婉采蓮歌》“寶月飄煙一尺腰”;錦襻:《賈誼傳注》中師古曰“偏諸若今之織成以為腰襻”;萬金鬟:辛延年《羽林郎》,“一鬟五百萬,兩鬟千萬余”;玉搔頭:《西京雜記》武帝過李夫人就取玉搔頭;畫扇:王獻(xiàn)之《團(tuán)扇歌》“七寶裝畫扇”;油壁:《蘇小小歌》“妾乘油壁車”,《北史·恩偉傳》油壁者,加青油衣于車壁也;偏轅:《世說·汰侈》王愷與石崇競相夸衒,有不及崇處,乃密貨崇帳下都督及馭車人問牛所以駛。馭人曰,牛本不遲,由將車人不及制之耳,急時(shí)聽偏轅則駛矣。玳牛:《藝文類聚》梁吳均贈(zèng)周興嗣詩“朱輪玳瑁牛”;秣陵:《吳志》張纮謂孫権曰“秦始皇改金陵為秣陵”;桃葉渡:楊氏六帖補(bǔ)桃葉渡在秦淮口;風(fēng)波:《桃葉答歌》“桃葉復(fù)桃葉,渡江不待櫓。風(fēng)波了無常,沒命江南渡”;迎接:王獻(xiàn)之《桃葉歌》“桃葉復(fù)桃葉,渡江不用檝。但渡無所苦,我自來迎接”。幾乎無一字無來歷。且用字精妙,僅用正、新成、待、猶、更、障、登、放、促、迎接幾個(gè)字貫穿熏風(fēng)、長日、蘭室、莫愁、腰、錦襻、萬絲鬟、玉搔頭、畫扇、油壁、偏轅、玳牛、秣陵、桃葉、風(fēng)波、江舟眾多的意象。“猶”、“更”兩個(gè)虛詞的使用尤為生妙。
其次,李商隱的詩歌,結(jié)構(gòu)回環(huán)曲折,跌宕起伏,或兩路夾寫、或明暗對比、或回環(huán)照應(yīng),常常出人意料。如上文所引的《錦瑟》一詩,頸聯(lián)一句中既用兩事,而每句內(nèi)又各含兩意:一意,滄海月明而珠偏有淚,藍(lán)田日暖而玉已生煙,下三字與上四字似作反照;一意,唯滄海月明故明珠有淚,唯藍(lán)田日暖故暖玉生煙。兩意都解釋得通,然兩意截然相反。馮班的詩歌亦得義山詩的妙造,如《風(fēng)人體二首》:
擬繡田田葉,尋絲底為荷。城頭無雀網(wǎng),自是欠樓羅。
半夜尋遺風(fēng),誰知暗里環(huán)。夾河飛白鳥,爭奈兩邊鷴。
第一首兩聯(lián)之間繡與絲、葉與荷、城與樓、網(wǎng)與羅之間來回照應(yīng),結(jié)構(gòu)回環(huán)往復(fù)。第二首,每聯(lián)之間夜與暗、白與鷴兩相照應(yīng),結(jié)構(gòu)巧妙。王應(yīng)奎評這兩首詩的結(jié)構(gòu)云:“尚有絲繡雙關(guān),不獨(dú)荷葉而已;尚有城樓雙關(guān),不獨(dú)網(wǎng)羅而已;尚有暗夜雙關(guān),不獨(dú)佩環(huán)而已;又有夾河雙關(guān),不獨(dú)白鷴而已。”[2]馮班巧用雙關(guān)句法,妙作艷體,讓人耳目一新。再看馮舒的《丙戌歲朝二首》其二:
喔喔荒雞到枕邊,魂清無夢未安眠。起看歷本驚新號,忽睹衣冠換昨年。華岳空聞山鬼信,緹群誰上蹇人天。年來天意渾難會(huì),剩有殘生只惘然。1
首聯(lián)寫現(xiàn)實(shí),無夢、無眠;頷聯(lián)寫夢幻,“驚新號”、“換昨年”;頸聯(lián)以典故貫穿歷史;尾聯(lián)回到現(xiàn)實(shí),抒發(fā)感慨。首先,首聯(lián)與頷聯(lián)之間形成真與幻的對比,突出詩人思念故國之心為切;其次,頸聯(lián)與尾聯(lián)之間為歷史與現(xiàn)實(shí)的回環(huán),點(diǎn)明無力回天之感慨;最后,首以現(xiàn)實(shí)開始,尾以現(xiàn)實(shí)作結(jié),然情思卻大有不同,陡然遞進(jìn),方見轉(zhuǎn)折。馮舒此詩的結(jié)構(gòu)在真與幻、歷史與現(xiàn)實(shí)的交織中,圍繞著人生的變換、歷史的興亡來回跳越,既翻出新意,又不離本旨。
最后,李商隱的詩歌往往具有很深沉的人生主題,并將其融入到身邊平常而細(xì)小的事物之中,再配以絢麗的辭藻和回環(huán)曲折的結(jié)構(gòu),形成一種細(xì)小而偉大的巨大魔力,而這一切既來源于詩人的敏銳感知、對語言的把捉能力及對結(jié)構(gòu)的運(yùn)籌帷幄,又在于詩人以麗與傷形成的強(qiáng)烈對比。感傷的主題以感傷的詞語出之,平常易見,然感傷的心緒以明快妖艷的詞語出之,效果加倍。歷代學(xué)李商隱者多著意于他的精美辭藻和獨(dú)特嫻熟的行文技巧,往往忽視他憂國憂時(shí)和自慨身世的兩大人生主題與形式技巧之間的聯(lián)系。而在馮班的詩作中屢屢見到這種情思。平常易見的事物經(jīng)過融入詩人感時(shí)傷世的深刻主題內(nèi)容的熔鑄,就變得不平凡起來。以事、景與人物心情的強(qiáng)烈對比,突出強(qiáng)化感傷的主題色彩,再以艷麗的辭藻和回環(huán)的結(jié)構(gòu)出之,不失直露,而達(dá)到隱晦蘊(yùn)藉的藝術(shù)效果。如李商隱《杜司勛》云:“高樓風(fēng)雨感斯文,短翼差池不及群。刻意傷春復(fù)傷別,人間惟有杜司勛。”以傷春來傷時(shí)、傷別、傷人。“高樓風(fēng)雨”象征著混亂的政局,“短翼差池”象征壯志未遂,而第三句引杜牧之詩句點(diǎn)明題旨,第四句以感嘆杜牧之才華感嘆自身,“惟有”二字,感慨頗深,詩壇寂寞,知音稀少,而又沉淪下僚,均可見于言外。馮班作《春分日有寄》云:
池塘狼藉草紛紛,日帶嫣紅露有文。刻意傷春春又半,可知愁煞杜司勛。
不僅化用義山的詩句,亦用義山詩的詩意,表達(dá)憂國憂時(shí)的主題。全詩看似在漫不經(jīng)心之間信筆書來,描繪一幅美麗的春分景象。然首句中狼藉的池塘和紛紛的亂草卻不是春天應(yīng)有的景象,而是以此不協(xié)調(diào)的景象象征著時(shí)局的動(dòng)蕩。“春又半”、“愁煞”既巧妙化用李商隱的詩句,又不為泥滯,并帶出感傷的主題色彩。再看馮班的《林桂伯墓下》:
馬鬣悠悠宿草新,賢人聞道作明神。昭君恨氣萇弘血,帶露和煙又一春。
首句寫景,言說春去春回,歲月常新;次句寫事,英雄雖已離別,但化為神明常守左右,其精神和魅力永存;三、四兩句用典感懷,連用王昭君被迫遠(yuǎn)嫁異族和萇弘被謗死后一腔精血化為碧玉的兩個(gè)典故,既表達(dá)了對抗清英雄瞿式耜的崇敬與懷念,也表達(dá)了詩人如昭君思念故國之心和如萇弘般對故國忠貞不渝之心。詩人的情思在寫景、寫事、用典中穿梭,結(jié)構(gòu)回環(huán)往復(fù),相互照應(yīng),包羅時(shí)間與空間的巨大跨度,以宿草、明神預(yù)示時(shí)間、空間以及心志的永恒,意味曲致綿長。然而從字面上看,只是淡淡寫來,好像漫不經(jīng)心,哪怕是寫憂國憂時(shí)的巨大人生主題,亦選用馬、草、露、煙等尋常意象,筆觸極其空靈。
馮舒、馮班的詩歌就題材、藝術(shù)技巧和含蓄蘊(yùn)藉等方面都對李商隱的詩作進(jìn)行了學(xué)習(xí)與借鑒,而不像朱庭珍借紀(jì)昀之言所譏:“但取其浮艷尖刻之詞為宗,實(shí)不知其比興深微,用意曲折,運(yùn)筆生動(dòng)沉著,別有安身立命之處。”[11](《筱園詩話》卷一)米彥青在談馮班對李商隱的接受時(shí)說:“在馮班的詩中,對于用詞的雕琢使詩歌有涵量,有深度,故而能以最少的字眼來換取最大的表現(xiàn)力。只是與義山詩相比,盡管文辭、聲律上修整得十分工致,氣度的安詳與意象的渾融則稍有不及。”[12]然而馮班詩作中又有很多詩引人稱道,“就在于詩人能夠貼近歷史來發(fā)揮想象,創(chuàng)造出了一種形象生動(dòng)的史境。詩人把比興、寫景、用典自然地熔裁詩中,雖然表達(dá)的是具有政治色彩的美刺主題,但卻能夠?qū)懙锰N(yùn)藉含蓄,辭采華美,綺艷整麗,充分體現(xiàn)了溫李范式和綺麗風(fēng)采”[12]。所言極是。
由于個(gè)人才力的限制,馮班 “所作雖于義山具體,而堂宇未閎,每傷纖仄”[13](卷十五)。故錢良擇曾曰:“鈍吟詩,是以魏晉風(fēng)骨,運(yùn)李唐才調(diào)者。正如血皴漢玉,寶光溢露,非復(fù)近代器皿,然卻是小小杯犖之屬,而非天球重器也。……獨(dú)精于艷體及詠物,無論長篇大什,非力所能辦。凡一題數(shù)首,及尋常唱酬投贈(zèng)之作,雖極工穩(wěn),皆無過人處。蓋其慘淡經(jīng)營,工良辛苦,固已極錘煉之能事。而力有所止,不能稍溢于尺步之外。殆限于天也。”然他又肯定了馮班學(xué)李商隱之精妙,曰:“定遠(yuǎn)詩謹(jǐn)嚴(yán)典麗,律細(xì)旨深,求之晚唐中亦不可多得。……視李而遜一籌,視溫則殆有過之無不及也。……近人詩都易入眼,鈍吟詩卻不易入眼;近人詩都不耐看,鈍吟詩卻耐看。總之工夫深耳。”[2]既指出了馮班詩歌的不足,又極大地肯定了他學(xué)李商隱的成就。錢良擇所言雖不為錯(cuò),然應(yīng)分而言之,馮班的詩歌當(dāng)分為早期和晚期。其早期詩歌多無太多的人生感慨和時(shí)代主題,較多宴飲游玩之作,或可稱為戲筆,難免“纖仄”。然詩人在這些詩作中鍛煉了對于語言、字句、結(jié)構(gòu)等的把捉能力,可以說馮班早期的詩歌創(chuàng)作是詩人對“西昆派”乃至李商隱詩歌技巧學(xué)習(xí)和熟練的過程。后來,詩人經(jīng)歷了科舉失利的巨大打擊,又經(jīng)歷戰(zhàn)爭的洗禮和亡國的巨大悲慟,對人生和社會(huì)制度以及時(shí)代興亡的感觸更加深刻。詩歌的主題內(nèi)涵亦發(fā)生變化,開始慨嘆自身的懷才不遇和憂國憂時(shí)。而在這兩個(gè)主題的選擇上與李商隱又近了一步。如果說馮班的早期詩歌主要是學(xué)習(xí)李商隱詩的詩歌技巧,與“西昆派”更加接近,而在馮班詩歌創(chuàng)作的后期,他的心境與李商隱更加接近了。所以在馮班的詩歌中既有對字詞的錘煉、聲律的修整、典故的繁用、結(jié)構(gòu)的巧妙布置,又有很深沉的人生感慨,并能將這種人生感慨和詩歌技巧巧妙融合,以創(chuàng)造一種含蓄蘊(yùn)藉的藝術(shù)情思,達(dá)到與李商隱詩歌契合的審美狀態(tài)。
參 考 文 獻(xiàn)
[1] 錢謙益. 牧齋有學(xué)集[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2] 馮班. 鈍吟老人遺稿[M]. 清康熙刻本.
[3] 張健. 清代詩學(xué)研究[M]. 北京: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1999.
[4] 李慶甲. 瀛奎律髓匯評[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5] 蔣寅. 馮班與清代樂府觀念的轉(zhuǎn)向[J]. 文藝研究,2007,(8).
[6] 蔣寅. 虞山二馮詩歌評點(diǎn)略論[J]. 遼東學(xué)院學(xué)報(bào),2008,(6).
[7] 馮武. 二馮評閱才調(diào)集凡例[M]. 清康熙垂云堂刻本.
[8] 袁行霈. 中國文學(xué)史,第二卷[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9] 許琰. 《西昆酬唱集》研究[D]. 西北師范大學(xué)博士學(xué)位論文,2007.
[10] 劉學(xué)鍇,余恕誠. 李商隱詩歌集解[M]. 北京:中華書局,2004.
[11] 郭紹虞編選,富壽蓀校點(diǎn).清詩話續(xù)編[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12] 米彥青. 論二馮對李商隱的接受[J]. 中國韻文學(xué)刊.2006,(3).
[13] 徐世昌. 晚晴簃詩匯[M]. 天津徐世昌退耕堂本,1929.
[責(zé)任編輯 杜桂萍 馬麗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