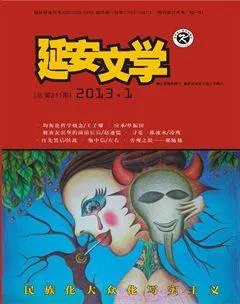迷戀故鄉談論問題:文化及歷史
郝隨穗是這樣的一位作家:他迷戀故鄉,談論問題,抒寫文史,他喜歡把散文當作史詩來寫。
關于他散文寫作的地域性問題,很容易讓人想到沈從文的邊城,莫言的高密,或者福克納的小鎮——一個作家內心無限伸縮的世界。他暢通無阻地在精神和文化的故鄉任意表達。可能是由于虛妄的世界和真實的自我——這種矛盾的焦慮感,帶來的結果是為作家確立一種身份的認可——鄉村知識分子,因而他在遭遇城市日常生活的龐雜和瑣碎之后,開始尋找精神的歸屬感,并試圖還原時代黑白的內容。
我是這么看待這個問題的,作家確立公共的地理意義的書寫坐標,并展開自我的辯論、旁白,并且布道,但這樣處理的結果消解了日益龐雜的細節能力,遮蔽了原鄉的意義:故鄉成了異鄉。這種地域鮮明、個性公共化后的符號化和概念化,構成了讀者的后置的被植入的經驗。而這個被放大的“地方”成了許多所謂鄉村知識分子追憶的來路。
我在故鄉僑居變得才有批判的意義。那些既熟悉又陌生的鄉村經驗,艱難明晰的相關情感,已經變得無可依靠。從這個意義來說,經驗的書寫是靠不住的,充滿疑慮地不斷尋找失去的故鄉,可能會使原本真實的故鄉變得更加模糊,命名可能變得重要起來。虛擬的中國故事里的故鄉成了我們衣食無憂的田園牧歌。
但弒殺故鄉的情結也無處不在,它成了我們這代人身上不可撫平的情感傷口。我們從故鄉到他鄉,從他鄉到異鄉,不斷地從一個地方到達另一個地方,故鄉于是變成了小三。不停遷徙的故鄉和他鄉,使得作家要么迷失自己,要么過于迷戀故鄉的非凡意義——因為我們要為它立言、立碑、立傳,布道者不說家常話。
再回到郝隨穗的散文。我喜歡他寫村里的王老五這樣的小人物們。這些鮮活的中國人的命運歷程,他們在不停輪回。無論地理的故鄉如何變化,人性總刻骨銘心。我想這是故鄉于我們的意義。
談論問題是哲學的書寫。無論中外,經典的文學向來如此。我從哪里來,要到哪里去,只要人類的困頓還在,這樣的宿命永遠存世。詩人屈原《天問》把問題抒寫到極致,無與倫比的想象力和勇敢的藝術超脫,讓后來者高山仰止——他是最早把詩歌當哲學來寫的詩人。作家能夠談史論今,浮想聯翩,這從來就不是什么問題。在物我化的寫作中,個人的重心是對時間的進程作出修正或判斷,但在豐富和殘缺的線裝文明的兩極沖撞中,取舍成了作家的問題。價值的意義是讓我們表達合理的想象,以便切入當下的最日常的問題。
那些遙遠的、不可捉摸的、塵封的歷史或生活史,我們需要一層又一層細心地剝落它。真相通常在背光處,所有的疑難雜癥都在骨子里。我們每走一步,十分吃力,又經常靠不住。那么捷徑又是什么?它是個圓周,不說和少說,便意味著呈現。
我一直對關于文化的和歷史的散文寫作表達退縮的意愿。我覺得戲說和仿材料式的胡說,字正腔圓的理說,假大空的謊說,都具有隱蔽的欺騙性。對于讀者來說,獵奇的心理是人類的共性,越是離奇,越是荒誕——文化不復,歷史無存,這對于散文寫作的談論問題是極大的傷害。文史不分是散文寫作有史以來最大的問題,這樣導致學術規范不嚴謹,散文寫作不鮮活。
文化或歷史應該怎樣被抒寫?把我置于歷史之中,作為旁觀者,又要假若自身是當事者和見證者,這是復雜而困頓的。冷峻而準確地抒情,需要作者一顆強大的不為所動的心。我想說的是,歷史不需要表演,但我們的寫作卻成了表演。
讀了郝隨穗有關文化和歷史的《黃河過客》《帝國童話的質感》等篇章,我想說的是,我們每個人都想站在歷史和文明的面前說話,但說著說著就成了個垂頭喪氣的人。而郝隨穗即使說了很多話,還是一個理直氣壯的人。
欄目責編:楊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