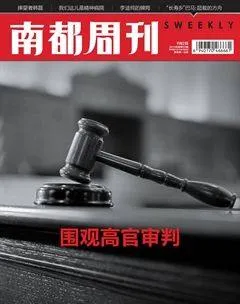楊鍵:現代文明是有毒的
現在和過去
詩人楊鍵常常出現的談話模式是“現在和過去”。過去楊鍵常常在離家不遠的一條小河邊散步,到了秋天,周圍的農田總是美麗的。現在—河邊似乎建了一個板鴨廠,河堤上全是鴨毛,惡臭難聞,再也沒法散步了,美麗的農田也沒了,都蓋了新房。
楊鍵的寫作和自然鄉村的關系很緊密,現在怎么辦?他笑著說靠想象了。《古橋頭》和《墓晚》這兩本詩集里收的都是2003年之前的作品,也是從2003年之后,楊鍵發現自己在寫作中注目的事物正迅速消失。
1993年從馬鞍山鋼鐵廠下崗,之后有過十幾年楊鍵靠300元退休工資生活的時期。現在一周寫一篇專欄的稿費幾乎是他全部的收入,問他夠嗎,他說當然。至于成家之事,在楊鍵看來,現代社會已經完全沒有了夫婦之道,夫婦關系很難相處,尤其現在的家庭都是自私的產物,如同牢獄一般,他是抵制婚姻的,所以沒有家庭之累。至于現代的兩性,楊鍵覺得普遍男性服從女性,所以他愈加不想成家了。
楊鍵用電腦有七八年了,每天他會上上網,看新聞或者查資料。但他的寫作卻還是用筆和紙完成的,他打字速度慢,打完一句,下面想好的句子已經忘掉了。先寫在紙上,再一個字一個字地敲到電腦上,似乎早年很多作家都如此,但現在恐怕只剩楊鍵一個了,不知他的簡約之風是否與此有關。
也是因為朋友越來越少,楊鍵經常自己小喝一點酒,他說寂寞的人都是一個人喝喝酒,和陶淵明一樣,喝酒更多是排遣寂寞。陶淵明曾經是楊鍵最喜歡的詩人,以酒著稱,一個星期的下雨天里會喝上一個星期,喝完還可以寫詩。楊鍵也曾經連喝了十幾瓶白酒,結果是假的,臥床了好幾天。
酒跟中國古老文明的深刻關系已經敗壞了。楊鍵說,過去的酒是真酒,是自然的,促進了文明的發展,現在的假酒相反,反自然,毀壞大腦,是阻礙作用,“現代文明是有毒的,尤其中國的現代文明,嚴重危害我們的現實”。
在韓東的記憶里,楊鍵去過一次KTV,不唱,一言不發。KTV似乎測準著現代人的生活態度,而批判現代文明,每人的側重點都不同,楊鍵覺得現代文明以綜藝化、娛樂化、明星化和拜金為代表,“這是一個欲望至上的時代,是一個沒有靈魂的現場,沒有靈魂喘息的地方。娛樂沒有以我們希望的方式出現”。他提到,在宋代,蘇東坡和王安石才是大明星。這也是他認為時代當然在倒退的表現。但除了大環境,在楊鍵自己的小環境里,他說自己隨著年齡漸長,快樂的對象越來越多,都是普通、簡單的,“比如一個好天氣”。
每個人都有生長期,同時也有著復雜的精神構成,楊鍵身上的“古意”太明顯了,以至于人們常忽略他的另一面。他也經歷過茫然的時期,喜歡過金斯堡的《嚎叫》,在他看來,中國已經到了金斯堡的年代,該出現金斯堡了,該呼喚金斯堡了。會不會是他呢,他說:“我要做索爾仁尼琴,不做金斯堡”。
舊日子的幸福
楊鍵心中最完美的詩人形象是清代的鄭珍。鄭珍的詩作和經歷都不太為人所知:母親死后,他在她的墳邊種滿了梅花和竹子,后來他干脆把家搬到了母親的墳邊,在后半生寫了無數回憶他母親的詩歌。楊鍵的生活方式,也有如當代鄭珍。
他居住在馬鞍山一座已住了35年的老房子里,和母親一起。母親有帕金森癥,一日三餐都由他來照顧。傍晚時分,母親坐在外間看電視節目,他提醒她該吃藥了,然后走進廚房,快速地燒出晚飯來—他燒的菜飯也簡單,一如這個廚房的形象,小、簡陋但潔凈。楊鍵很少出游,給人造成隱居的印象,也是因為有母親走不開。楊鍵說跟母親生活很美妙,他喜歡這種單純的、上下的關系。
這座房子是一樓,有兩間自建的平房,是楊鍵放書和畫畫的地方,在平房和樓房之間,留了個小院子,院子里密匝匝地長著花木。正房里,有著老派生活的熟悉場景:擁擠、簡樸,靠窗放著八仙桌,冰箱和洗衣機上鋪著乳白色的防塵布。此外便是書架,書架上有老子和虛云禪師的畫像。一面墻上掛著古琴,楊鍵已不彈了,只圖它掛在墻上的“幾分古意”。另一面墻上則貼了張“圓超五濁”的紙片。
除了自家院子,房子后面的空地上楊鍵也栽了很多植物。他說之前種過菜,但總是會被拔掉,所以后來改種了果樹。在這一個小小的果園背后,卻是個廢鐵收購站,噪音經常侵襲過來,多次打擾到他的讀書,楊鍵也去交涉過,鄰居卻說“你天天不上班,還指責我的噪音”。所以楊鍵對這三十五年的鄰里關系可以說厭惡,也讓他懷念鄉村生活的宗族感帶來的親切,“現在只能用漠然形容,還不如動物之間的關系”,楊鍵很無奈。

生于1967年,曾當工人,亦研佛教,自1986年起專心習詩,現居安徽馬鞍山。其代表詩作有《一座被廢棄的文廟》、《母羊和母牛》、《在報國寺度過1999年冬至》、《冬日》、《暮晚》、《慚愧》等。
人類生存方式的改變總是令楊鍵思索再三,使用這么多年液化氣了,楊鍵還是用惋惜的口吻說起小時候的松針。撿拾松針和枯枝煮飯,味道帶著自然的清香,當年從桃沖搬家到馬鞍山,他們裝了半卡車松針運來。
這些都令人聯想起詩人柏樺的一句詩“唯有舊日子帶給我們幸福”,楊鍵與偶遇的人的關系也帶著這種舊日子的情感,他會在河堤上與一個乞丐聊很久,也與常遇到的底層商販之間保持長久的素淡溫情。楊鍵認識一個賣菜的,那人過去因為說錯了句話被打成了右派,被放出來時年紀很大了,所以他和他妻子都老了,卻有兩個挺小的小孩,乍看會以為是他們的孫子。楊鍵跟他可以算是老朋友,在馬路上經常見到,然后很親熱地聊一聊家常。楊鍵敬愛他,認為他有著默不出聲的善良,讓人感動的那種。他還認識一個拾破爛的老頭,參加過朝鮮戰爭,現在也沒有退休金,很落魄,全家都拾破爛,女兒、侄子、侄女。楊鍵和他認識幾年,每次見面都坐下聊天,上次見到,老人正在地上燒一堆電線,燒掉外面的膠皮,可以賣銅,“現在不知道他流浪到什么地方去了,他們移動性很大”。
逝去的山水
楊鍵沒法在酒后寫詩,畫水墨是可以的,所以晚上飲完酒,他就去那間自建的小屋里畫畫。在楊鍵看來,酒是神奇的,能刺激大腦,令人達到沒有禁忌的、自由的境地。
楊鍵畫的是抽象山水,他認為這一代人很難親臨山水畫具象山水畫,只能畫抽象,而他自認畫的山水是苦澀的,可以叫苦山水。他寫詩很慢,畫畫卻瞬間完成,因為筆墨展開的感覺也與寫詩不同,所以快樂得多。他最喜歡的山水畫家是開了江南山水秀潤之風的董源,這位奠定了江南文人與山水間關系的畫家,筆下淡墨輕嵐、溫和細膩。八大山人也是他喜歡的,那種樹無葉、景無主、沒有家園的現代性,跟楊鍵的內心很契合。至于那些很工整很美的畫家,楊鍵則不太喜歡。
每年,詩人龐培都會來到馬鞍山看望他一次,聊詩,喝酒。他有一個看待楊鍵詩歌的角度,是從地理上分類出江、河、湖三大類:“隨著水域的不同,詩人的憤慨和柔情也漸由絢爛歸于平淡”。楊鍵自己也認為山水問題是一個重大的問題:“過去的山水是山水,是神性的,如同西方中世紀畫家們畫圣母和基督,我們畫山水也一樣,相當于在不斷地贊嘆、禮拜這種偉大的存在。現在已經修理過了,不那么自然了,變成了資源。中國人和山水的關系在世界文明里都應該好好研究,但我們這幾十年的文明制度,已經不和山水發生關系了”,這樣的山水觀應該也是他詩作和畫作里那種悲愴情感的源頭。


楊鍵最喜歡的詩人是陶淵明,在他看來,弗羅斯特、荷爾德林的詩在陶淵明跟前根本不值一提,“陶淵明是切己的,是道的詩,可以真正幫助人解決一些問題”。楊鍵覺得陶淵明也是關注現實的,著名的《詠荊軻》“登車何時顧,飛蓋入秦庭”,可以說陶淵明在詩歌場域里自稱荊軻,那么在現實政治里他也應該是個猛士。但“最喜歡的詩人是陶淵明”這樣的話楊鍵似乎不愿意多說,他覺得陶淵明太大了,還是應該去發現一些很小的詩人去珍愛。南北朝是他越來越覺得的詩歌黃金時期,“語言和格律還不太成熟,詩歌狀態特別好,向道之心更強烈”。
很多人都認為楊鍵是極端的文化保守主義者,他依然用“道”來辯解:“孔子也是保守主義,他守的也是他的古代,比如周禮,守的是文明之源。歷史上的古文運動,也都是保守主義。其實我們領會錯了保守主義,他們捍衛的是道的存在,道是沒有時間的,超越時空的,是永恒價值的體現。中國幾千年,是憂道不憂貧的幾千年,一直到民國都是如此,現在顛倒了。”
楊鍵的詩歌里絕少有日常感現代感的詞匯,比如冰箱、洗衣機之類,他堅持“這些東西不美,沒有詩意可言”。隨著中國舊有的文明體系里的象征物已經不不復存在,如松梅竹菊,他認為我們的象征體系已經崩潰了,而現代文明里科技的產物時間還不長,還不能夠了解它們,楊鍵總結“所以我們的文明經驗也是非常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