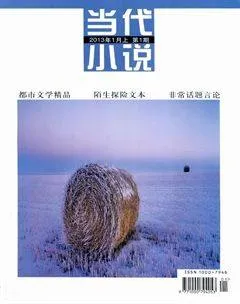小說二題
草手鐲
1988年4月的一天,年輕的柳小惠坐上了張成林的自行車,自行車像個喝醉酒的漢子一樣,歪歪扭扭地駛在了十八盤崎嶇的山路上。這一天,是23歲的柳小惠和28歲的張成林新婚之日,然而除了滿嶺上花白如雪的刺槐花外,卻再也看不見一點新婚的喜氣。
時至今日,我對姐姐柳小惠當初和張成林的那段婚姻仍然百思不得其解。張成林并不是個優秀的青年,無論是從外貌上還是家庭上,都難和柳小惠相般配。柳小惠沒結婚的時候是我們這東山溝里十村八莊出了名的漂亮姑娘,在她剛滿20歲的時候,提親的人便絡繹不絕紛至沓來我們家,其中不乏城里的正式工人和學校里的公辦教師,要知道,在那個時候,一個非農業戶口的分量有多重,而柳小惠只是個連高中都沒上過的農家女。我爸是村里的技術員,但我們家真正說了算的人是我媽。我媽一撥接一撥地接待了來提親的人們,并嚴格地按照她的條件篩選出了她比較滿意的人選不下二十個交給柳小惠。張成林當時也是求親大軍中的一員,他的嬸子曾兩次來到我們家為她的侄子求親,但毫無疑問的是他在第一關就被我媽擋在了門外。我媽這么做是有道理的,張成林是個長相并不出眾的大齡青年,他的家景也遠不能同我們家相比,他又沒有非農業戶口的支撐,綜合他的條件,在求親的隊伍里最多也只能排在中下等,他之所以也敢來我家求親,在我媽看來那純粹是自不量力的異想天開。然而后來事情的發展完全出乎我媽的意料之外,柳小惠對我媽交給她的那些人選看也不看就提出了要嫁給張成林,而張成林的資料我媽并沒有交給柳小惠,這就使我媽感覺到了一絲奇怪。我媽便展現出她少有的溫柔面,慈母般苦口婆心地對柳小惠動之以情曉之以理。然而柳小惠在這件事的態度上卻出乎意料的堅定,任憑我媽磨爛了牙齒她也不為所動,大有非張成林不嫁的態勢。這使我媽很惱火,立馬又恢復了她鐵娘子的作風,她咬牙切齒恨鐵不成鋼地把柳小惠反鎖進房間里,準備以強硬的手段逼其就范。這樣關了兩天,誰也沒有退縮的跡象,局面就有些僵持起來。直到兩天后的中午我媽又打開房門去給柳小惠送飯,一進門覺得有些異常,房間里寂靜無聲,空氣中彌漫著一股刺鼻的腥臭,我媽急忙走進柳小惠睡覺的房間,一眼就看見了柳小惠嘴吐白沫倒在炕上,不知從哪冒出來的一只盛裝“敵敵畏”的瓶子滾落在一邊。我媽尖銳的嚎叫聲引去了我爸他們,幾個人急三火四地把柳小惠送到醫院。幸好發現得早,加上敵敵畏的殺傷力不夠,柳小惠被醫生將胃翻了個后才活了過來。但經過這次事情,柳小惠的名聲就不是那么好聽了,各種流言蜚語甚囂塵上,她的名聲也一落千丈,往日里那些提親的人一下子從我們家門前消失得無影無蹤了。面對迅速冷落的門庭,我媽初時還抱有一絲幻想,但幾天后她就認清了形勢,于是主動出門去尋找當初那些上門提親的人,但條件稍好一點的人家大都避而遠之,而那些當初不入我媽法眼的小子們卻也在猶豫不決的取舍之中。一向要強好勝的我媽終于在數次打擊下頭破血流氣羞交加,大病一場。病中的她指著柳小惠說,滾,你滾!柳小惠就乘勢嫁給了張成林。柳小惠的出嫁也是當年我們十莊八村熱議的話題之一。因為我媽是用一種驅趕的方式把柳小惠嫁出去的,所以柳小惠出嫁那天我們家并沒有一個賓客。不光如此,由于羞于見人,我一向強硬的媽和當技術員的爸像個縮頭烏龜似的蜷縮在屋里任由騎著自行年來迎親的張成林把柳小惠扶上車帶走了。我媽沒有給柳小惠準備什么嫁妝,柳小惠是背著一個花布包袱坐在張成林的自行車上離開家的。那時正是四月初,十八盤嶺上開滿了花白如雪的刺槐花,濃郁的刺槐花香彌漫了整個山谷。而當自行車歪歪扭扭地消失在十八盤后的那片山腳時,一對渴望愛情而又愿為此而抗爭的青年人終于真正地走到一起了。看著他們離去的背影,幾乎所有人都相信,柳小惠和張成林這一對自由戀愛的典范,在經歷了無數的磨難和痛苦之后,他們今后的婚姻生活肯定會和諧甜美,相敬如賓。
然而,婚后的柳小惠過得并不幸福,因此她拼死捍衛自己婚姻的舉動就更加讓人匪夷所思。柳小惠結婚一年多了也沒有再回到我們家一次,雖然她的新家距我們家只有不足十里路。不是她不想回來,是我媽不讓她回來。我媽已經揚言不認這個女兒了,所以當那年八月十五中秋節張成林依俗帶著燒雞和月餅來孝敬丈母娘的時候,被我爸手持一柄鐵锨門神似的擋在門外,我媽沒說多話,只說,快滾!再不走就揍你!張成林倉惶地放下東西扭頭騎上車子飛一般地去了,我媽還不解恨,上前一腳踢飛了那只燒雞,引來了村中兩只惡狗的一場廝殺。這種敵對態勢一直維持了一年半多的時間,在柳小惠結婚后的第二年夏天里出現了轉機。有一天我們村有一個我叫二奶的人回娘家,她的娘家就在張家莊,回來后看見我媽,二奶說,我看見你家惠了。媽說,管她什么樣,死貨,死了才好。二奶說,怪可憐的,還真是死了才好。我媽的臉色就不對了,問二奶,你看見什么了?二奶說,人啦,人瘦了啦。二奶說著伸出兩只手比量了一個不大的圓,腰就這么細,臉也不成樣,臉上還有一塊青……二奶看我媽有聽她說的意思,又說,聽說是張成林打的。這時我媽“喲”的一聲嚎啕起來,她一邊嚎一邊往家里跑,嘴上叫著我爸的名,快,帶上把家什,叫上老三,上張家莊……
張成林所在的張家莊離我們村并不遠,轉過十八盤嶺就到了。我爸叫上我三叔還有大明哥等本家十多個人,坐上柳樹林的拖拉機,浩浩蕩蕩地向張家莊奔去。我媽站在車頭上,一手扶著車欄桿,一手向前有力地揮舞著,她威風凜凜氣勢洶洶,就像電影里的女大王。車人浩浩蕩蕩沖進了張家莊,在張家莊村人目瞪口呆的神色中找到了張成林的家。柳小惠正坐在院子里扒苞米,她瘦瘦的胳膊上筋骨齊露,就像她手里沒有粒子的苞米棒,她的臉上果然有青紫的傷痕,她的眼睛因為臉太小了而顯得格外得大。柳小惠看見沖進來的一幫人,她驚恐萬分不知所措,當她看清沖在最前面的是我媽和我爸時,她竟沒有一絲反應。
我爸看了看柳小惠,一句話沒說就手持鐵锨進了屋,他在屋子里找了兩圈沒有找到張成林,揮起手中的鐵锨將墻上的大鏡子敲了個粉碎,玻璃破碎的聲音刺激著我爸和我媽,他們指揮著隨后跟進來的人說,砸,使勁砸,砸死這個XX的王八蛋!隨后在一陣刺耳的破碎的聲中,張成林和柳小惠的家被搗了個粉碎。
而這時柳小惠就孤單地站在院子中心的一大吊苞米棒前瑟瑟發抖,她的院子外圍攏來許多看熱鬧的村里人。她的院子邊上沒有圍墻,看熱鬧的人圍成一圈相互拉扯著欣賞著房間里的戰斗。并沒有人出來阻止,在張成林和柳小惠的家被搗了個差不多的時候,人群中才推推拉拉走出來幾個年長的老者。他們是張成林的父母和村中的老人,顯然他們已經弄清了來襲者的身份,所以他們并沒有叫囂著理論而是以一種近似文明的方式來協商解決問題。這種以柔克剛的招式給了正怒火中燒的我媽和我爸軟綿綿的一拳,讓他們把準備好的許多惡毒的語言都憋在了心里,差點把自己憋死。他們只好大罵張成林,說張成林你這個XX的王八蛋滾出來。但顯然張成林已得到了信息,自始至終沒有露面。在經過一輪言語交鋒后,我媽把柳小惠拖上了柳樹林的拖拉機,在張家莊的眾目睽睽之下把她帶回了我們家。在拖拉機開動的時候,我媽惡狠狠地給張家莊的老少丟下了一句惡毒的話:早晚弄死XX的張成林。
柳小惠終于回到了闊別快兩年的家,到這時候人間的親情才淋漓盡致地發揮出來。回到家后的柳小惠足不出戶,我媽一邊罵她一邊殺雞燉肉做好吃的給她補養身體,不出幾天,柳小惠的臉上就有了紅潤的光澤。當然,這里面還有一班長的功勞。在柳小惠回家的第二天早上,部隊上的一班長來借我們家的鍤镢,說是要刨菜園種大白菜。一班長所在的連隊就在我們村東邊的山里,連隊里有菜園還有豬場,他們人多工具少,所以勞動時他們常到駐地村民家借用農具,當然他們也會幫助農戶做一些農活,比方說幫助孤寡老人挑水,農忙時節幫忙村民割麥子剝玉米等等,軍民情深,魚水之情。一班長姓姜,是個南方人,但我們只叫他一班長。一班長在部隊上干得不錯,聽說要提排長了,平常日他經常來我家借東西,和我們家人都很熟。一班長進來的時候,柳小惠正坐在院子里發呆,一班長說柳小惠你回來了?柳小惠抬頭發現一班長站在她面前,臉立刻就紅了,呆呆地不說一句話,一班長抬抬手想做個什么動作卻又放下了,說小惠你瘦了。柳小惠聽了這話眼淚一下子就出來了,哭著跑進了房間,把一班長晾在院中,神色極為尷尬。我爸說看這個沒教養的孩子。就把鍤镢遞了過去,一班長笑笑扛上鍤镢走了。傍晚來還鍤镢的時候,一班長帶來了兩盤東西,初時我以為是向日葵盤子,仔細一看,嚇了我一跳,竟然是山上經常見到的馬蜂窩,這兩盤蜂窩上面星羅棋布的巢房內還長滿了白白嫩嫩的胖蜂蛹。我是第一次這么近距離地看這東西,我不相信居然還有人敢去摘馬蜂窩。我看看一班長臉上,果然發現他的額頭上還有臉腮上有幾處鼓鼓的包。我媽看著這些蜂窩說,我的天,你從哪弄來這些東西,沒被馬蜂蜇著吧?你也真敢下手。一班長說,沒事,我在家時養過蜜蜂。又說我媽,把這些蜂蛹蒸了給柳小惠吃,好補身體。以后幾天,一班長又送來了兩次馬蜂窩,這樣過了十多天的樣子,柳小惠的臉上果然恢復了不少的光澤,她的腰身也豐滿起來。
這天柳小惠說在家憋得慌,想出去打豬草,就提著條簍和鐮刀上山了。傍晚回來時她拐著滿滿一簍子青草累得臉紅氣喘,我媽說你身體剛見強就不能少打點?柳小惠微笑著說,以后打豬草的事就交給我吧。這是她回家后臉上第一次有了笑的模樣。我媽說那行,以后打豬草的事就歸你吧,也好讓你弟多寫寫字。柳小惠的弟就是我,那年我十二歲,我是計劃生育新政下的幸運兒。我聽了挺高興,終于可以不打豬草了。
但我還沒高興幾天,一天傍晚,柳小惠回來時把簍子一放就進房間躺下了,她說不舒服,我媽問她哪不舒服,她說哪都不舒服。第二天打豬草的事又歸了我,我挎簍上山的時候看見了一班長,我說一班長又在弄蜂窩啊?一班長說,我給連里打豬草呢,你這是干啥?我說我也打豬草呢。一班長笑了說,我看你不用打了,把我打的裝些回去就行了。我一看,一班長已經打了高高—堆的青草了,估計我裝他一簍子也沒問題。我高興地說那行。我就坐在樹陰下乘涼,一班長還在埋頭割青草,我說一班長,都打這么多了,快風涼風涼吧。一班長聽了就走過來坐下。我問他,一班長聽說你要當排長了,是真的嗎?一班長說,當個屁,本來還指望著,可突然就不從基層提了,都是從軍校下來的,白忙活了這些年。我今年就復員了。我說,什么時候?一班長說就這幾天。我說那你還干個屁。一班長說,站好最后一班崗吧。我說,你不用回去算了,就在這里找個媳婦結婚。一班長說,你小孩伢伢懂啥啊?又說,早知道當不上排長我還真不如在這找個媳婦呢。我說找媳婦和當排長有什么關系?他說,你不懂,部隊上有規定,士兵不能同駐地上的人談戀愛,要是被發現了,就要受處分,更別說提干了。我說,你是不是看好了哪家姑娘,為了提干就不要人家啦?一班長沒回答我,低著頭在青草中撿出了一大把長相別致的毛毛狗草握在手中。我覺得我說的有點不好,就改了話題,那你回家了干什么啊?一班長說,我們家是放蜜蜂的,我回家就放蜜蜂。我說蜜蜂吃什么?一班長說,吃花,最好的就是刺槐花。我說那咱這里滿山是刺槐花,就到咱這里來放吧。一班長說我也這么想,槐花好啊,釀出的蜜甜還有營養。我說那好,明年我就等你來放蜂,我正好嘗嘗蜂蜜什么味。一班長笑起來,到時我弄點蜂王漿給你,保準甜死你。我瞅著他說,你說話可得算數。一班長摸了摸我的頭說,一言為定。說著他把一只用毛毛狗草編的手鐲套在我手上,我看看那只草手鐲,毛茸茸的真可愛,用它撫在臉上,癢癢的真舒服。回家時,一班長把我的簍子里塞滿了青草,我好不容易才扛回去。我媽看了表揚我,我們這小子,真知道干活了。柳小惠站在門旁不陰不陽地看看我打的草,走過來不聲不響地拿起一把丟給了豬圈里的豬。
張成林是在柳小惠回家一個月后來到我們家的。這是他這個當女婿的第一次進我們家門。我爸說,張成林,你坐炕上。張成林說,不用了,我就站地上吧。我爸板著臉說,叫你上炕你就上炕,還吃了你是怎么的?張成林只得上了炕,但他不敢坐實,只用半個腚坐在炕的一角。我爸說,張成林我問你,你為什么要打柳小惠?張成林看看柳小惠,說我沒打。我爸說放你媽個屁,你沒打她還是她自己打的?張成林只得招供,囁嚅地說,我們吵架,吵上火了……還沒說完,我爸一巴掌打在張成林的頭上,這一巴掌的勁力很大,把張成林一下子從炕上打到了地上。張成林有些急了,爬起來梗著脖子說,柳小惠她……柳小惠叫了他一聲,張成林。張成林把脖子低下了看著地,嘴里嘟囔著,柳小惠她……不肯懷孕。聽了張成林這句話,剛才還斗志昂揚的我爸和我媽很意外,氣焰也立刻滅了下去,在我們這里,女子結婚不懷孕和離婚是兩件被人恥笑的事情,不懷孕還不如一只不下蛋的老母雞,而離婚一般就是浪蕩女的表現。我媽說,你們沒去看看?當我媽說這話的時候,氣氛就緩和了。
那天,張成林終究還是重新上了炕,在結婚兩年后第一次在我家享受上了當女婿的待遇,他竟然還意外地享受了一點小酒。在吃飯時,我爸和我媽文武兼備地對張成林進行了教育,教育他夫妻間要恩愛,要體諒,要照顧。我媽說,張成林我問你,你娶了柳小惠知不知足?柳小惠嫁給你屈不屈?你還抬手就打,你對得起她嗎?張成林一邊使勁點頭一邊痛哭流涕下保證,保證以后再不打柳小惠。我媽又批評柳小惠,既然你已經嫁給了張成林就要一心一意地過日子,路是你自己選的你怨不了誰,抓緊的懷個孩子,有了孩子就好了。柳小惠低著頭說,我想離婚。還沒等張成林著急,我爸先急了,他從炕上跳起來指著柳小惠說,你休想,你想讓我們死啊?你這就跟張成林回去。柳小惠說現在不想回去。我爸說你是結婚了的人不回去還能一輩子住在家里?柳小惠一甩臉跑到另一間屋子里去了,我媽也跟了過去。
我爸重新坐到炕上喝生氣酒,張成林在一邊看。張成林酒量小,剛才喝了一點臉就紅得不行了。這時,一班長進來了,不過他今天有點變樣了,他的綠軍裝上已經沒有了領章。我爸招呼他,一班長,這是怎么了?一班長說,我復員了,今天是來告個別。我爸說,怎么復員了,不是要提排長嗎?一班長說,沒戲了,我要復員了。我爸又給一班長介紹張成林,一甩頭卻發現張成林不知道什么時候已經下炕了,我爸一叫他,他才猥猥瑣瑣地湊過來。我爸不滿地看看他,對一班長介紹說,這是……還沒說出什么,一班長就接了過去說,我知道他,叫張成林。說著轉過頭冷冷地對張成林說,是吧?張成林看見一班長和他說話,竟結結巴巴說不出話來了。他的這種卑微的態度讓我爸很有意見,但我爸覺得一班長的態度也有問題,畢竟張成林是被他承認了的女婿。一班長也看出了我爸的表情,就對張成林說,正好這兒有酒,我就借酒敬你一杯吧。張成林趕忙說,我不會喝酒。但一班長卻像沒聽見他的話,拿起兩個大碗,.倒了滿滿兩碗酒,自己端起一碗,說張成林,我現在不是個軍人了,我也當不成排長了,我現在和你一樣了。我們喝一碗吧。說著他也不讓張成林,一飲而盡。張成林兩手抖動著捧起酒碗,神色尷尬地站在那兒,喝也不是,不喝也不是。我爸說,張成林不能喝酒,你看他臉紅的,別讓他喝了。一班長看看張成林沒說話,張成林竟也一仰脖喝了進去。一班長又倒了兩碗,說來張成林,好事成雙,再喝一碗。說著就把酒又一口干了,張成林卻不能喝了,跑到院子里吐起來。柳小惠忽然從里屋走出來,她捧起那碗酒說,姜大成,我陪你喝。我才知道原來一班長叫姜大成。柳小惠說著一口氣把那碗酒喝下去了,42度的老白干一下肚,就把柳小惠嗆了個淚流滿面。我爸說一班長,你看你……我爸沒說完,就閉了嘴,他吃驚地看著一班長,一班長的臉上竟然也淌起了淚。后來我爸跟我媽說,一班長真是個情義人啊,走的時候都哭了。一班長哭了,他沒有再喝酒,他流著淚離開了我們家。在院子里,他看見了還在嘔吐的張成林,一班長伸手在他的肩上用力地拍了一下,就離開我們家走了。
中午的陽光很明媚,太陽穿過十八盤嶺上的樹樹木木直透過來,把柳小惠和張成林的影子都拉短了。他們在前走著,我爸和我媽在后面送。村口那兒正敲鑼打鼓歡送復員老兵,老兵們都被摘了帽徽和領章,正往一輛敞篷軍車上爬,我看見一班長正站在車斗上向這邊張望著。張成林一抬頭也看見了一班長,他腳下一歪踩空了差點跪下,被我爸拉了一下才站住。我爸說小心點,看著道。張成林忙架好自行車,騙腿上去慢慢地向前溜,等著柳小惠坐上去。柳小惠并沒有馬上上去,她跟在車后慢慢走了一段路,沒有回頭,忽然伸出一只手來舉在空中揮了幾下向我們告別,我發現柳小惠的手腕上竟也套著一個毛毛狗草編的手鐲。我剛想說柳小惠,你是不是拿了我的草手鐲?柳小惠已緊走幾步上了張成林的自行車,張成林弓著腰,雙腳猛蹬幾下,自行車逃似的遠去了。而這時,送老兵的軍車也啟動了,我看見一班長也把一只大手伸在空中向我們揮別,他的手腕上居然也套著一只草手鐲,他和許多老兵一樣,臉上也掛滿了淚珠。車子向前走了,我忽然想起一件事來,我追著車子跑了幾步喊,一班長,明年刺槐花開的時候你會來嗎?一班長大聲喊,你等著我,我一定會來的——
他的聲音很宏亮,穿過幾條山谷都聽得到……
在拐彎處
在我20歲的那個夏日里,我和水皮還有大濤三人坐在“美美”燒烤店前喝啤酒。燒烤店的女老板叫高美美,比我大兩歲,人長得風騷,性格又豪爽,所以她的店前總是人最多。那幾天,天氣出奇的酷熱,我和水皮還有大濤三人已經喝了整兩箱了,空瓶子橫七豎八躺了一地,水皮還在大叫:“高妹兒,再來一箱!”
我們總是叫高美美叫高妹兒,每次叫高美美“高妹兒”時,我們都會聽見有人笑,這時我們心里就覺得特別爽。高美美答應著往后走去搬酒。這時我肚子脹得難受,起身歪歪扭扭到后面去上廁所,拐過彎,看見高美美正撅著個屁股在搬酒。高美美穿著個黃色的小短裙,一彎腰露出了兩條雪白的大腿和半個屁股。本來我們是老熟人了,我不該對她有什么想法。但那天我的酒真是喝多了,就走上前去從后面抱住了她。高美美“嗷”的尖叫了一聲,掙扎著要反抗,回頭看見是我,她不反抗了,只是輕輕地扭著身子做樣子,嘴上卻嗲嗲地說:“放開我,放開我……”本來她要是真的不從我可能也就算了,但她這樣說話卻更是給了我莫大的刺激,我就半拖半抱地拉她往另一間屋里走,高美美扭動身子掙扎著配合我,她的大奶子在她的扭動下像兩只歡快的兔子不停地跳著,她的臉紅紅地貼在我的脖子上,嘴巴里、鼻孔里噴出一絲一絲暖暖的熱氣直往我的脖領子里灌,讓我更是激情沖天。我把高美美扔到床上,就要脫她的衣服,這時我腰里的傳呼機響了。在那個時候,通訊工具不是很發達,手機是很少的,傳呼機也不多見,所以有手機的人就在手里提著,有呼機的人就把呼機掛在腰上,這是身份的證明。
高美美說:“有人找你了,快看看又是哪個妹妹吧。”
“去他媽的吧。”我把呼機拿出來摁了一下扔在床上,呼機不響了,我仍去脫高美美的衣服,可能因為是夏天穿得少的緣故,高美美的衣服一下子就被我脫下來了。這時呼機又響了,我不去理睬,又去脫高美美的裙子。高美美一邊裝模作樣地用手去擋一邊伸手拿過呼機看了,笑起來:“哪來個250啊,就這天還東北風啊。”起初我的神經被肚子里的酒精和一副浪樣仰在床上的高美美刺激得云里霧里的,沒聽清她說的什么意思,但嘴里還是順口問了一句:“誰發的?”
高美美又看了看呼機說:“劉大哥。哪個劉大哥呀?”
似乎真的感覺有一股風掠過,我腦袋有些醒了,松開去摸高美美的手,搶過呼機翻看留言:“今天東北風。劉大哥。”兩遍一樣。我的激情一下子蕩去了,酒也清醒了大半,我知道我們一直擔心的事情終于發生了。我推開了纏上來的高美美向外沖去:“我得走了。”
我想我當時沖出門時的速度一定是神速無比的,因為當我最后一個字還在嘴里的時候,我已經站到店前的門口處了,這時我看見水皮和大濤正一人手持一瓶啤酒在“拼刺刀”。我正要喊他倆,突然一聲刺耳的警笛在店前炸開,只見店前停著的幾輛車上同時沖下十多人,誰也沒注意,什么時候店前就來了這么多車。車上沖下來的人直接就把水皮和大濤摔在了地上,有幾個人沖到后院去了,我想那肯定是在找我。我低頭拾起門邊的一把笤帚,裝做做清潔的服務員,幾個人影快速地從我身旁穿過去了。
突發事件讓一九九八年夏天的“美美”燒烤店前的食客們“哄”地就炸了鍋,跑進跑出的人還有滿地亂滾的酒瓶子使場面混亂不堪,我趁機混入亂哄哄的人群中,消失在小巷中了。穿行在小巷中時,我的頭腦異常清醒。我清醒地知道,我們的好日子到頭了,署名“劉大哥”的這條留言無疑已經為我們的幸福+an9sOnx6levfno1NqKNrQ==生活劃上了一個句號。按照我們事先的約定,這條留言只有在最緊急的情況下我們才允許使用的,相當于戰時的明碼電報。
我知道我今后的日子將會是異常艱難的。果然,隨后的日子里我就如同一只被獵人追趕著的兔子,無論走到哪里都發現危機四伏。我給眼鏡打電話時,他還在家里吃飯,在我剛到達眼鏡樓下的那個胡同時,我看見兩個警察架著反手被銬的眼鏡從樓上拖下來扔到了車里,身后追著他快八十歲的奶奶,但警車并沒有等她,尖叫著飛馳而去,刺耳的警笛聲久久不散,把眼鏡奶奶的哭聲都拉遠了。趴在我們家前面公園的那片叢林中的時候,我看見一大群警察堵在我家門口,其中一個警察還不停地用手推搡著我年老的父親,一下又一下,一下又一下。我年邁的父親只是搖頭,一言不發,而我的母親卻在一旁嚎啕大哭,周圍站滿了幸災樂禍看熱鬧的人。
這個城市里已經沒有我的容身之處了。我突然發現,在這個經濟發達、樓房林立、人口眾多的城市里,竟沒有一處屬于我的地方。而就在幾天前,我們還都堅定地認為,我們才是這個城市里的主宰,我們就是這個城市里的主人,我們可以在這座城市里隨心所欲、為所欲為地做一切事情。而現在,我們卻只能如同一條條喪家之犬,東奔西跑,東躲西藏。
在發現我在這個城市里真的無處可去后,我來到了西河子巷的拐子明家。拐子明在巷口處擺了一個小煙攤,他的一條腿不好,走路一瘸一拐的,平時他就坐在板凳上賣香煙。見我到來,拐子明高興得都哭了。他已經聽說了我們的事情,整個夏天,整個海城的空氣都在傳送著我們的事情。但拐子明并沒有因此有絲毫的猶豫和不決,他堅定地把我藏到了他的家中,從此讓我這個喪家之犬有了一點喘息的時間。
拐子明并不是我們的人,有一次幾個地痞來買煙,煙拿了卻不給他錢,拐子明就追著他們要。拐子明腿不好,一瘸一拐地追著他們,幾個壞小子轉著圈子逗他,還把他的煙攤也踢翻了。那天正好我路過,我和拐子明不認識,但看他一瘸一拐地俯著身子去撿散失在地上的煙我就想起了我的三叔,我三叔也是個瘸子,死了兩年了。我攔住了那幾個壞小子,起初那幾個小子還不服,但我一報名號就都老實了,乖乖地賠錢了事。在海城的黑道上,這點名氣我還是有的。從此明就視我為恩人。我看他可憐,也偶爾去看看他。
我不想連累他,可我實在找不到可去的地方了。
此后的日子里,我就如一只見不得陽光的老鼠整日蜷縮在明的小窄屋里,看似無所事事,內心卻備受煎熬。外面稍有風吹草動,就能讓我心驚膽跳半天,我從來沒想到我會如此膽小,我還是原來那個能呼風喚雨、叱咤風云的“東哥”嗎?
在這段日子里,明源源不斷地給我帶來外面的消息,但都是些壞消息。從明嘴里我知道,這次事情的導火索是在衡哥身上。衡哥在政府招待所里為一個女孩子和人打起來了,本來這也不是件什么大事,衡哥和人打架就像撒泡尿一樣隨便,他進出派出所如履家門。但問題在于和他打架這個人是新來市長的兒子,關鍵的又是衡哥把新來市長兒子的“那個東西”給打壞了。在某些方面來說,弄了市長的兒子有時比弄了市長本人還要讓市長難看,更何況還弄壞了市長兒子的“那個東西”,讓市長從此失去了奮斗的動力。新來的市長對海城的治安表達了自己的失望之情。
一場聲勢浩大的行動就開始了。在這次全城性的大拉網中,我往日的弟兄幾乎無一遺漏,而我到現在還能待在這朗朗乾坤,只能說是個奇跡。感謝高美美。現在再提高美美,我對她除了感激再沒有任何一點感覺了。這天,明又帶給我一個壞消息: “衡哥被處決了!”我聽了眼淚立刻就涌了出來,衡哥這么快就被處決了是我沒有想到的。我知道我也到該離開的時候了。我對明說:“明,去給我買一張今晚到K城的火車票吧。”
明很吃驚,說:“你要走?現在外面還是挺嚴的。”我說:“管不了那么多了,再呆下去我會發瘋的,是福是禍由天定吧。”
明望著我,最后還是點點頭,走了。
明走后,我就想衡哥。衡哥是我今生中見到的第一條好漢,在海城這個地方,再不可能有第二個衡哥了。而現在,衡哥卻死了。衡哥,永別了!我又一次流下了眼淚。
傍晚時分,明回來了,遞給我一張火車票,又從腰里拿出一沓錢,說:“東哥,剛才我在朋友家里借了一千塊錢,你拿著路上用吧。”
我很感動,明辛辛苦苦一年,也不過就掙個一兩千塊錢。我說:“明,我這有錢,你掙不多,還是還給人家吧。”
明固執地伸著手,說:“東哥,你一定要拿著,出門在外沒錢怎么行?我在家好辦,大不了出點力。”
“那好,我拿著。”我拍拍明的肩,努力擠出一副笑臉接過了錢。
吃過飯,時候已經不早了,我站起身。明難過起來,說: “東哥,我送你走。”
“不用,別連累了你。”
“我不怕!”明固執地說著就去拿衣服了,我趁機把那一千塊錢又塞到了他的枕頭下,然后邁步走出門去。
到了車站,時間還早一些,我們就在車站不遠處找了一個不被人注意的角落躲了起來。明遞給我一支煙,自己也叼一支,點了火,我們二人就對吸起來,彼此無話。我四下望望,海城的夜晚,幾盞昏暗的街燈照著,人卻不少,然而這蕓蕓眾生中卻只有明一人是我的朋友了。有好幾次,我想對明說聲謝謝,但我終于沒有說出來。有些話,不說,也許比說了更能讓人記住。就這樣又過了一段時間,我看看只有幾分鐘了,把手伸向明,明握著我的手說:“東哥,保重!”我擺擺手,提起行李一步步向檢票口挪去。
車站里的檢查并沒有我想像的那么嚴,年輕的女檢票員冷若冰霜,對擁擠的人群視而不見,眼睛只是盯著伸到眼前的票,嘴里機械地念叨著:“別擠,排好隊。別擠,排好隊。”兩個穿警服的男人遠遠地站著,并沒有過來。我隨著擁擠的人流一起上了車。
在硬臥車廂里,我找到了自己的鋪位,下鋪靠窗,位置不錯。我四下看看,一切正常。等我放好行李后,火車已經徐徐開動了,我就走到車窗前趴在玻璃上往外看。列車正在加速,站臺越來越遠地向后退去,看著車窗外遠遠近近一晃而過的燈火和黑黝黝的樓房,我知道我就要離開海城,離開生我養我的父母,離開我生活了二十多年的土地,去走一條不歸路了,而前方等待我的將又是什么?在這一剎那,我的心竟悵悵然生出了一股說不清的滋味來。
火車全速行駛著,海城已經永遠地離去了。我將留戀的目光收回,扭頭卻覺得有一雙眼睛在盯著我,我猛一抬頭,對面站著的卻是明。
“你怎么上來了?”
“我不放心,等你出了省界我再回去。”
我鼻子一酸,說:“你有票嗎?”
明得意地亮了一下票指指我頭上的鋪位,看來他是早有預謀。明坐在我的鋪位上,我們說話。我說:“明,不要再同我們這種人往來了,沒好處的。”
明說:“同你在一起不是挺好嘛?”我苦笑笑,沒說話。明又說:“東哥,其實你可以不走,投案算了,大不了判幾年,出來還不照樣做人?”
“別說了,明。”我站起身,“有些事你不懂,快睡覺吧。”
明起身往上鋪爬去,但明實在是太矮小了,腿又不好,爬了兩下都沒爬上去。我拉住他,把他按在下鋪,自己一躍身上了上鋪,躺下身去,將毯子整個地蒙到身上,卻不敢真的睡去。我覺得我一直是在半睡半醒中,一閉上眼,腦子里就像是在放電影,一會兒是衡哥,一會兒是警察,馬上又出現了我爸我媽還有高美美,甚至連死去多年的城北大眼狼也出來了。人很多,事也雜,卻又亂糟糟的沒有一點頭緒。無數的人物和鏡頭走馬燈似的晃蕩在我的眼前,我的腦子被膨脹得亂七八糟。睜開眼,頭頂上的燈已經關上了,車廂里只剩下一點昏暗的光亮,火車正快速行駛著,外面的景物被月色斷斷續續地擠進來,斑斑斕斕,光怪陸離的,讓我一時間恍如隔世。就這樣我靜靜地躺在火車硬臥的上鋪上,任思緒自由地飄忽,可能是這幾天實在是怕壞了也累壞了,再加上火車反復不止咣當當、咣當當的聲音,我終于熬不住迷迷糊糊地睡去了。
我醒來的時候,天已大亮了。下床發現明不在,我去洗臉,對著鏡子發現自己這幾天憔悴了許多,模樣也變了許多,心中頗覺傷感,但一想到就要脫離險境了,我又輕松了許多。
回到座位,明已經回來了,他買回了兩瓶啤酒兩只扒雞,我忽然想到下一站我們就要分手了,心中油然而生出一股戀戀不舍之情。我們坐在窗前,一起喝酒吃肉,我說:“明,你回去后可以訂點報紙擺在煙攤旁,夏天你再批點冰棍,一起賣。”
明聽了眼睛一亮,說:“對呀,我怎么就沒想到呢?東哥,還是你有頭腦,等你回來了我們一起開個超市。”
聽明的語氣,好像我這次出走就是一趟輕松平常的旅行,而我,還有以后嗎?海城我還會再回來嗎?想到這些我心里不免有些傷感,就不再說什么了,明也看出了我的心思,也不說話了。就這樣,我們誰也不說話了,誰也不說話。就這樣兩只雞兩瓶酒在我們的無聲無響中落進了我們的肚子里。再過十幾分鐘,我們就要分手了,從此以后,我們將天各一方,也許還能再見,也許就是永別。明終于忍不住了,淚水大顆大顆地掉了下來,我鼻子也有些酸,卻終于忍住了,拍著明的肩說:“別哭了,明,我們還會再見面的。”
明說:“東哥,到了K城不好混你就回來。”
“我有數。”我說:“你也要好自為之,別逞強。有誰欺負你,你不要和他們打,你打不過他們。”
“我知道,東哥,你也保重。”
我忍住淚水,扭頭去看車外,車外是一片一片的田野,莊稼早已收過,而新的莊稼還未上來,于是田野就那么一片片的裸露著,匆匆而過。偶爾閃過一兩個零落的村莊,有渺渺的炊煙若立若飄豎在天空。遠處那些巉峻綿亙的山巒被煙霧籠罩著若隱若現時有時無,顯得既神秘且虛幻。望著窗外,看見有樹一閃而過,有如匆匆的趕路人,我忽然想,我們就如這車外匆匆的樹,一閃就不見了蹤影。衡哥是這樣,海城的那些兄弟是這樣,我又何嘗不是呢?我們急匆匆地趕路,哪里又是我們的終點呢?轉過前面的那道彎,就是K城所在的地界了,那里真會有我的世界嗎?
突然,明抱住了我,哭著說:“東哥,你不要走,我們回去吧,我們回去投案吧。”
我去掰明的手:“別這樣,明,好多人在看,會被人懷疑的。”
明聽話松開手,但語氣卻異常堅定起來:“東哥,外面世途艱險,你一個人在外面人生地不熟的我實在不放心,衡哥死了,我不想你和他一樣,我們還是回去吧,回去投案!”
“明,我不能回去。”我力圖勸說明。我的苦衷他是理解不了的。
“東哥,我不讓你走,你要不回去,我就跳下去!我就去死!”明說著竟然真的沖到車窗前,猛地掀起了車窗。
“不要……”我抱住明,腦子里一片空白。車外是匆匆而過的田野,村莊,還有一閃而過的樹……
我被勞教八年。八年里,明每個月都來看我。明每次來時都背著一大包的東西,碩大的背包壓在明的身上,明瘸得更厲害了。一年后的一次探視,明說:“東哥,我們把巷口的那個超市盤下來了,我給它起名叫‘東明超市’。”又說:“你這個月的工資我幫你存起來了。”
我理解明的心事。我只是失去了八年的自由,而明付出的或將是一輩子。八年的勞役生活是艱苦的,對于這樣的結果,我沒有半點的怪明。我常想:如果沒有明那剎那間的沖動,如今的我又會是什么樣子呢?況且,我不能眼睜睜地看著明從火車上跳下而無動于衷。只是我到現在也沒想明白,火車上那密封的車窗,明怎么一下子就打開了呢?
責任編輯:段玉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