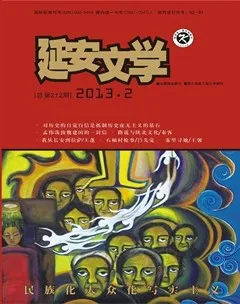解放瓦窯堡的前前后后(連載二)

五、1935年的國內(nèi)外形勢
日本帝國主義侵占東北和熱河后,要求華北特殊化,要求河北省政府從天津遷去保定,要求山東、察哈爾、河北、山西、綏遠(yuǎn)五省脫離南京而特殊化。向全中國遍設(shè)特務(wù)機(jī)關(guān)。向全中國走私傾銷日貨販毒。和德意結(jié)成法西斯侵略軸心,利用美英法的反蘇反共,分向東西進(jìn)攻,走向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的程途。用“善鄰友好,共同防共”作其進(jìn)攻中國的煙幕。
美、英、法帝國主義者,一方面縱容日本侵華,一方面慫恿蔣介石堅(jiān)持內(nèi)戰(zhàn),向英、美、法屈服。英國滋羅斯爵士給蔣介石出主意,濫發(fā)紙幣,實(shí)行“法幣”政策,搜刮內(nèi)戰(zhàn)軍費(fèi),而用海關(guān)關(guān)余豢買蔣介石,企圖保持在南中國長江流域的壟斷權(quán)益。美帝在幫助蔣介石印制“法幣”、使用“法幣”而搜刮中國所有白銀,販運(yùn)紐約,用“麥棉貸款”誘買蔣介石上釣竿,作由經(jīng)濟(jì)侵華轉(zhuǎn)向干涉中國一切、臣服蔣介石于美國統(tǒng)治之下。法、德、意各帝國主義,以少量軍火、用舊或過時(shí)飛機(jī),給蔣介石出賣,煽惑蔣介石,把“反共內(nèi)戰(zhàn)進(jìn)行到底”。
蔣介石為了迎合日本,實(shí)行媚日政策。把集中華中、華北抗日的部隊(duì),調(diào)到鄂豫皖和西北“剿共”。成立“華北軍分會”、“華北政務(wù)整理委員會”,簽訂中日《塘沽協(xié)定》,屈從日本華北特殊化之要求。對日本的各種無理取鬧和要挾,如南京日領(lǐng)事失蹤等,奴顏婢膝,一一聽從。對美、英、法、德、意百般恭順,甚至學(xué)希特勒,留個(gè)鼻胡,表示他對洋大人的忠誠孝順和奉命惟謹(jǐn)。他對江西蘇區(qū),進(jìn)行了飛機(jī)、公路、碉堡配合瓦解的瘋狂“圍剿”,攻奪了紅色首都瑞金,大言不慚地向全世界宣布:“對共產(chǎn)黨只要三分軍事七分政治,就可使中國共產(chǎn)黨在地球絕跡”。對所有侵害了的工農(nóng)兵蘇維埃政權(quán)地區(qū),進(jìn)行了燒殺奸淫、搶劫擄掠的專門制造無人煙地區(qū)的毀滅政策。對全國強(qiáng)迫實(shí)行“法幣”,搜盡各界人民手中的銅幣,引起全國物價(jià)不穩(wěn),金融枯竭。對全國人民實(shí)行著封建奴役的保甲制度。對全國人民施行無理的通行限制,住宅行李的嚴(yán)密搜查、限制。對其軍政公教人員,也實(shí)行五人十人連保連坐的監(jiān)視制度。對全國進(jìn)行奴化思想及統(tǒng)治。在全國各地勒令修建碉堡、公路,“防共”、“剿共”,用全國陸軍、空軍,“追剿”離開江西的主力紅軍。對中國共產(chǎn)黨采取了一面屠殺,一面自首、瓦解的政策。江西蘇區(qū)的革命群眾,為屠殺和自首所苦害者數(shù)百萬人。全國秘密的地下共產(chǎn)黨遭受難以數(shù)計(jì)、難以言喻的破壞,很多的省委被摧毀,很多革命干部被敵人自首誘惑而離開革命,很多革命干部在監(jiān)獄受敵人折磨。蔣介石為了“根絕赤禍”,還發(fā)布了《防止假自首條例》。蔣介石的南京政府,以貪污、腐化、草菅人命、媚外賣國而臭名驚人。
日本帝國主義準(zhǔn)備滅亡中國的《田中奏折》,日文本、中文本、英文本,在各國公開印發(fā),日本的軍事、政治、經(jīng)濟(jì)、文化、特務(wù)活動,依照《田中奏折》原文,逐步向中國推行。全國的抗日救國潮流日益高漲。全國各派系地方軍事實(shí)力分子們,在不滿蔣介石的媚外殘內(nèi)。蔣介石把洛陽、西安、武漢、重慶,作陪都或行都,準(zhǔn)備從日本的侵略進(jìn)攻中,逃開南京,其中對重慶經(jīng)營尤力。西南雜牌軍人,少數(shù)為蔣介石籠絡(luò),與蔣一致經(jīng)營四川,多數(shù)與蔣矛盾對立,怕蔣排擠、分化、吞并,恨蔣侵奪其勢力與地盤。蔣介石為緩和矛盾,把西康建省,把青海建省,并表示東北四省雖失,本土仍大,全國省數(shù)并未減少太多。把從東北撤退入關(guān)的東北軍,分布在華北和鄂豫皖,制止東北軍抗日。向西北提出“開發(fā)西北”的口號,一面轉(zhuǎn)移全國視線,要全國上下,不要努力去收復(fù)東北失去的四省,只要全國都去注意如何“開發(fā)西北”,以求茍延殘喘。一方面企圖把西北地方勢力吞并,據(jù)西北為己有,以屏障其將來在四川之茍安。蔣介石的“開發(fā)西北”,激起西北一些有識人士的反感,認(rèn)為蔣介石把西北當(dāng)“殖民地”,把西北人當(dāng)“奴隸”。以致蔣介石派在軍政界的南方人員,一律被軍政界中的原有人員呼為“蠻子”,談笑之間,“蠻子”一出現(xiàn),人多轉(zhuǎn)移話題或不歡而散。不論軍界政界,南方人員與西北人之間,形成不可逾越或不可化除的思想、言行、情感間的鴻溝。
1927年至1930年,西北的主要武力,為馮玉祥及其屬下。西安政變之后,該部雖然“反共”,但因具體條件不同,在“反共”的殘暴程度,略有差異。初政變后,拘捕了一些革命干部,但黨的各省省委、地委、縣委還未受破壞。只有不準(zhǔn)再作革命活動的禁令,還不像蔣介石那樣,“立即殺無赦”和使用偵探包打聽,搜查追捕的做法。
因?yàn)轳T氏只注意了練兵帶兵,保存兵力,擴(kuò)大兵力,政權(quán)還多在一些封建殘余、立憲思想、改良主義、舊民主主義思想的老官僚政客,或四不像的新官僚政客手內(nèi),既不會搞完全封建政權(quán),也不會搞立憲或舊民主政權(quán)。坐官為了撈本,“三日京兆”,抓得一點(diǎn)本利另作他圖的人,占主要數(shù)量和質(zhì)量。一個(gè)縣同時(shí)來兩個(gè)三個(gè)新縣長接任,使舊縣長不知給誰交才是。幾個(gè)新舊縣長之間,各夸后臺,各搬靠山,爭抗打架,縣政紊亂,笑柄不一而足。省黨部派赴各縣建立縣黨部的人員,縣長不理,紳士不睬,地方人士不與往來,住用辦公皆無處所,生活費(fèi)用毫無著落。弄得省派人員,到各縣向人搖尾乞憐,無人顧念。這種國民黨新“黨棍”,到處不受人垂青,從反面影響了當(dāng)時(shí)在政變后仍立足教育界的許多知識分子共產(chǎn)黨人,雖然對革命動搖,還不敢毅然決然去投奔國民黨或反革命。這種狀態(tài)在西北存在二三年之久,個(gè)別地區(qū)存在達(dá)四五年之久。
改組后的國民黨,既非為馮系,又非蔣系,那系也有,那系也不得人心,不得過問軍政權(quán)力,只是縣長或軍官的尾巴或點(diǎn)綴品。有的官僚政客和軍官們還非常討厭他們,認(rèn)為“黨部”是來給他們做絆腳石或掣肘者。
我們有的同志,利用這種間隙矛盾,做了好多工作。大多數(shù)為教條思想統(tǒng)治的同志,白白放過許多這種有利機(jī)會。
當(dāng)“清澗兵暴”發(fā)生后,蔣介石在西北還毫無爪牙,無從過問。馮玉祥及其部下執(zhí)政陜西者,認(rèn)為系井岳秀部下問題,所以,未從西安派兵赴陜北“剿”或“打”。到起義部隊(duì)轉(zhuǎn)移韓城一帶,才由關(guān)中一些駐在地武裝進(jìn)攻,還不是用全力對付。在陜北,井岳秀一方因幫助烏審?fù)豕珡?fù)辟,被蒙兵將其一團(tuán)擊潰于蒙地,一方防止其部下高子清師也乘機(jī)倒井。所以,清澗以北的兵力未敢稍動,只做防范。延安為中心的兵力,全力進(jìn)攻起義南下的部隊(duì),而且以軍事對軍事為主,對于政制方面毫無新措施。對于共產(chǎn)黨方面,監(jiān)視常漢三和搜捕趙仰普外,也未有其他措施。而西北地方武力,以楊虎城武力最大。從1926年西安解圍后,初有楊虎李虎之爭,繼皆受制受擠于馮系各部,對陜局皆無權(quán)過問。只有于右任及其左右,對陜局有發(fā)言權(quán),也得追隨馮后,拍馮馬屁。而且,有的皆被馮系把他們編調(diào),或在關(guān)中、漢中各地暫駐,或調(diào)出陜西,參加對河南、安徽的戰(zhàn)爭及蔣馮閻間之新軍閥混戰(zhàn)。對陜北,實(shí)仍是井岳秀以“陜北王”割據(jù)獨(dú)霸。
渭華暴動起后,馮系主持陜政部分,以主力對戰(zhàn),在關(guān)中各縣搜查防范配合,比陜北嚴(yán)密殘酷的多。但在暴動武裝失敗后,中共陜西省委才遭重大破壞。在省委遭破壞后,牽連影響關(guān)中各縣黨與團(tuán)才遭破壞。但還不像蔣介石“四一二”后或?qū)Α鞍艘弧薄ⅰ敖鳌钡哪欠N做法,還只是像1925年前京津滬漢軍閥們的那種做法一樣,還是偵探偵知了黨的秘密機(jī)關(guān)所在地,機(jī)關(guān)中秘密人員有點(diǎn)疏忽,露了一點(diǎn)形跡,反革命的鷹犬們,根據(jù)這種蛛絲馬跡,突加包圍搜捕才破壞。由于秘密工作同志的忠實(shí)勇敢和平素的謹(jǐn)防,所以對各縣的株連不太多太重大。因而,省委被敵人破壞后,各縣的損失,還極有限。后來,省委遭破壞,出了叛徒,才使各地黨與團(tuán)的組織受損失重大。
進(jìn)攻渭華暴動的反革命兵力,只是駐關(guān)中的一部分馮系執(zhí)政統(tǒng)治關(guān)中的部隊(duì)。在漢中,在甘肅,在陜北的反動武裝,皆未出動。蔣介石及其部下嫡系,當(dāng)時(shí)因西南、東北、西北皆仍是懸空,其實(shí)力未能到達(dá)。所以,對渭華暴動,根本無從過問。有的還以為是地方實(shí)力和馮系的沖突,有的懷疑共產(chǎn)黨如何在純粹農(nóng)業(yè)地區(qū)能弄起些武裝。而且,蔣介石也并未因?yàn)轳T系執(zhí)政陜西部隊(duì)鎮(zhèn)壓了共產(chǎn)黨而有所獎(jiǎng)勵(lì)或補(bǔ)充。
由于馮系和回民間有過重大沖突,由于蔣介石正在打算削弱分化消滅馮系,所以,蔣介石及其南京政權(quán)對西北一切,只好聽之任之。由于蔣馮閻戰(zhàn)爭已是箭在弦上的形勢,蔣介石也派了些黃埔學(xué)生,到各部隊(duì)中去活動及篡權(quán),也派了一些“黨棍”,向西北各省國民黨黨部中混入,企圖做其軍事政治進(jìn)攻之內(nèi)應(yīng)。蔣介石強(qiáng)調(diào)“服從南京”、“服從中央”、“服從中央黨部”等,懲全國各派系及西北馮系,要把軍權(quán)、政權(quán)、財(cái)權(quán)、黨權(quán),向南京統(tǒng)。
在1929年、1930年,蔣馮閻戰(zhàn)爭爆發(fā)之后,西北、華北,稍有實(shí)力,有一個(gè)旅的軍人,都在招兵買馬,擴(kuò)大實(shí)力。在社會上稍有名望,帶過兵或民團(tuán)的人,活動一下,可以得到團(tuán)長或旅長的番號和委任,大肆活動。在戰(zhàn)爭期間及戰(zhàn)后一個(gè)日期,這種機(jī)會仍多。
投降路線和經(jīng)驗(yàn)主義,使我們未能在此時(shí)放手活動。(陜北當(dāng)時(shí)有數(shù)十名黃埔及各軍校學(xué)生,放手去搞,可以搞好多名堂。)
從1926年起,西北黨內(nèi)有些同志,秘密研究第一國際到第二國際,巴黎公社到十月革命,鴉片戰(zhàn)爭、太平天國、八國聯(lián)軍、辛亥革命,辛亥至1925年國內(nèi)外的各種變化,得到結(jié)論是“西北特殊論”。
西北特殊論的主要內(nèi)容是:
一,西北地廣人稀,民族復(fù)雜。主要人口是漢人,還是農(nóng)業(yè)自然經(jīng)濟(jì)為主,手工業(yè)及前資本主義商業(yè)為副。十萬以上人口的城市,只有西安、三原、南鄭、蘭州。可以走辛亥革命的形式,由省會起義,影響各縣。可以由各縣搞起一支力量,乘機(jī)奪取省會,然后改造各縣各鄉(xiāng)。楊虎城攻守西安和馮玉祥入陜,證明了這一結(jié)論正確,但暴露出馮楊二部皆非絕對受黨領(lǐng)導(dǎo)的部隊(duì)。而黨領(lǐng)導(dǎo)的史可軒、石謙部力量太小,還不能左右西北全局。
二,西北在辛亥之后,雖比滿清有些政治改良,基本未變。縣議會未在各縣普遍設(shè)立,省議會為紳士、政客、官僚所把持,只是軍閥的附庸。所以,實(shí)行國民會議呢?仿效蘇聯(lián)實(shí)行工農(nóng)民主呢?有人主張前者,有人主張后者,有人主張采取二者之優(yōu)乘機(jī)施行。有人主張無產(chǎn)階段專政是基本目的,為達(dá)此目的,可以采用許多過渡橋梁,達(dá)此目的。
三,陜局為西北的中心和關(guān)鍵。誰主陜政,可以由陜帶動和左右甘、寧、青、新。而且,由于交通閉塞,遠(yuǎn)離海口,既不會立即受到帝國主義威脅,又可以脫離上海、北京、南京之政治及經(jīng)濟(jì)的影響而割據(jù)。
四,但西北要搞“上海暴動”,或“首都革命”,或“巴黎公社”,或“進(jìn)攻冬宮”,皆不可能。只能采取中國傳統(tǒng)的農(nóng)民戰(zhàn)爭,加上革命政黨的領(lǐng)導(dǎo),革舊布新,實(shí)行人工培植社會發(fā)展和進(jìn)化,促進(jìn)革命的成熟。
這種西北特殊論,發(fā)展為后來的“爭取革命在一省或數(shù)省首先勝利”。因?yàn)楦鞣N意見、論證、經(jīng)驗(yàn),說明中國領(lǐng)土之大,人口之眾,政治、經(jīng)濟(jì)、文化水平之不平衡,反動統(tǒng)治的軍事力量在各省分布也極不均衡,其控制力之強(qiáng)弱也不相同或一致。這種論調(diào),是駁斥“一夜天變”、“一蹴而成”的盲動主義和幻想一舉而成的小資產(chǎn)階級速勝論和急性病者,也是駁斥那種夸夸其談、不務(wù)實(shí)際、引經(jīng)據(jù)典、玩弄教條、兒戲斗爭、兒戲暴動的教條主義者。
革命營壘中,消極等待,不敢動作,沙鍋搗蒜,挪個(gè)地方,挪個(gè)年月,碰碰運(yùn)氣,隨波逐流……各種思想非常混亂。“不造反,難安然”的路線,好多人不愿意接受。
1929年到1931年的反革命對付革命,在西北地區(qū),還是“各掃門前雪”、“各自為政”、“逆來順應(yīng)”的地方性部分做法。革命力量是此起彼露,反革命“追剿”此緊彼松,還不是全省或數(shù)省的聯(lián)合行動。
1931至1933年,各省推行保甲、軍警、民團(tuán),還不一致。蔣系勢力滲入西北,只顧抓省級軍政黨的重要人員任免權(quán),還不能把南京所決定的一切,貫徹到各縣政府。
由于蔣馮閻戰(zhàn)爭中馮閻失敗,馮氏及其直屬系統(tǒng)的軍政要員及部隊(duì),全部離開陜甘及西北,而被分散在皖豫魯華北各省。蔣介石當(dāng)時(shí)兵力有限,無兵開入陜西,不得不利用與允許楊虎城率部由安徽返回陜西。蔣系只好在省政府及省黨部兩方面派些人來,抓黨權(quán)、政權(quán)、財(cái)權(quán),企圖控制與“中央化”。
楊虎城及其部屬,一些改良主義的政客、官僚和新舊知識分子,依附楊虎城,利用西北普遍種大煙籌款,經(jīng)過上海,由國外購買軍火,一方興建華陰兵工廠,修造武器,謀擴(kuò)充兵力,推行“大西北主義”,打算割據(jù)西北,觀望全國形勢,可能于有利情況下,出兵潼關(guān),逐鹿中原,問鼎國政。向國外派遣省公費(fèi)學(xué)生,給國內(nèi)國立或某些私立大學(xué)貧寒學(xué)生獎(jiǎng)學(xué)金,收買人心,延攬人才,企圖形成一個(gè)堅(jiān)強(qiáng)的西北地方實(shí)力集團(tuán)。
蔣介石為瓦解和“中央化”,不使西北地方實(shí)力派形成,強(qiáng)調(diào)嚴(yán)禁種煙,扼絕地方勢力之財(cái)源。黨務(wù)經(jīng)費(fèi)由南京“中央黨部”發(fā)給,政務(wù)經(jīng)費(fèi)由南京“國民政府”補(bǔ)助,軍費(fèi)從軍隊(duì)由軍委會統(tǒng)一整編,統(tǒng)一補(bǔ)給。一方給西北派遣黨政財(cái)軍各色人員,安插到黨政及軍隊(duì)中,一方把建制及人員任免權(quán)收到南京。
在“九一八”事變后,為安置東北入關(guān)黨政軍人員,轉(zhuǎn)移全國視線,提出“開發(fā)西北”,“建設(shè)西安為陪都”,設(shè)立“西京建設(shè)委員會”,各派系的黨棍政客,向西北黨政教界羼鉆爭奪。
到1933年左右,為了“剿共”,為了控制縣以下政權(quán),為了篡奪省政府權(quán)力和機(jī)構(gòu),蔣介石把在南方湘鄂贛皖“剿共”行之有效的“專員”、“專員公署”推行于西北。自1926年被取消而銷聲匿跡的“道尹”及“道尹公署”,改變?yōu)椤皩T”及“專員公署”而出現(xiàn)。他在陜西開始只先設(shè)一個(gè)榆林專員公署,對付陜北。以后,才每十縣或數(shù)縣設(shè)一個(gè),為省的代表機(jī)構(gòu)。對禁絕大煙、編保甲、筑碉堡、聯(lián)結(jié)民團(tuán)、保安隊(duì)和反革命主力部隊(duì)之間的協(xié)同“剿共”,起了極重大的作用。西北沿清末而來的縣政拖延、因循、腐化、頹廢惡習(xí),在革命戰(zhàn)爭面前,表現(xiàn)了昏聵無能,混亂軟弱,極易為革命風(fēng)浪把他們?nèi)缜镲L(fēng)振落葉一掃而光。但,反革命專員制和專員公署,卻成為革命的頑敵和勁敵。它具有“便宜行事”、“隨機(jī)應(yīng)變”的權(quán)力。蔣介石所以堅(jiān)持這種制度至1949年快20年,不是沒有原因的。反革命罪行和血債,也在這種機(jī)構(gòu)和人員身上最多最大。
西北的革命武裝斗爭,從1927年的“清澗兵變”起,一直在向著推翻蔣介石在全國統(tǒng)治的目標(biāo)戰(zhàn)斗著。在政治和軍事戰(zhàn)斗口號方面,始終只提推翻蔣介石國民黨的反革命統(tǒng)治,而沒有明白提“打倒井岳秀”或“打倒馮玉祥”或“打倒楊虎城”的口號。在實(shí)際戰(zhàn)斗行為中,相與直接肉搏拼生死作戰(zhàn)的,卻為井系馮系楊系部屬,而一直從1927年到1933年快10年間,還沒有和蔣介石的嫡系主力接火,但從1932年以后,西北紅軍逐漸壯大。
到1933年,蔣介石在南方“圍剿”有所進(jìn)展,尤其從1934年,南方紅軍長征,蔣介石所謂“收復(fù)江西”之后,因鎮(zhèn)壓察哈爾抗日同盟軍,將其嫡系部隊(duì)駐在以北平為中心的華北,同日本訂了“何梅協(xié)議”。西北紅軍聲勢壯大起來了,長江以北的河南也為蔣系控制,馮系閻系及東北軍西北軍也已大多受制于蔣氏。所以,蔣介石在全國建立了兩個(gè)“剿共”指揮中心:一個(gè)是“南昌行營”,進(jìn)行尾追長征中的南方主力紅軍,“圍剿”鄂豫皖和川陜紅軍,搶劫、擄掠、搜捕“收復(fù)了的江西”蘇區(qū),搜捕破壞南方各大城市殘存的秘密共產(chǎn)黨和閩贛各地散存的紅軍和赤色游擊隊(duì)。一個(gè)是“北平軍分會”,進(jìn)行調(diào)遣華北雜牌軍隊(duì)入陜,協(xié)同西北地方軍“剿共”;督促閻錫山沿黃河修筑二千多里碉堡線,阻止紅軍東渡抗日;派組以毛侃為首的北平軍分會駐綏德參謀團(tuán),聯(lián)絡(luò)晉綏寧甘陜五省地方兵力,協(xié)同84師,“圍剿”西北在陜甘交界及陜北為中心的紅軍和蘇維埃區(qū)域。在華北各大城市,實(shí)行極嚴(yán)密的搜查制度,沒有擔(dān)保,行旅不能入店投宿;沒有鋪保和家眷的人,不能租房住。一切關(guān)卡渡口,嚴(yán)密控制和搜查,商旅皆難通行。學(xué)生也受搜查監(jiān)視。連國民黨自己的黨政軍機(jī)關(guān)中的大小職員,因無黨派人占大家多數(shù),也得五人或十人互相連保,才能任職。動員東北軍、晉軍、綏軍、寧軍、陜軍及蔣系嫡系主力與空軍,向西北大規(guī)模進(jìn)軍。制止華北的抗日宣傳與活動。
從1934年起,西北的革命與反革命,完全以新的形態(tài)和陣營出現(xiàn),而對戰(zhàn)。過去,雖曾你死我活,作生死戰(zhàn)爭,參與的人,雙方皆屬地方對地方,部分對部分。從1934年起,首先一個(gè)特點(diǎn)是蔣介石以全力媚日,瓦解與鎮(zhèn)壓華北的察哈爾抗日同盟軍,唯恐其與土地革命的紅軍聯(lián)結(jié)起來;布置以全力“消滅”西北的紅軍、共產(chǎn)黨,惟恐其與南方長征的紅軍會合起來,同北方的抗日同盟軍聯(lián)合起來。
第二個(gè)特點(diǎn)是日本從侵占東北、熱河,蠶食華北察北,冀東又制造出“防共自治”的“中日緩沖地帶”,推行華北五省“偽滿化”。《田中奏折》,不只是進(jìn)兵計(jì)劃或密謀,而是滅亡中國的日寇的行動綱領(lǐng)在逐步謀實(shí)現(xiàn)中。抗日將成中國民族革命的主題,中國革命面臨由社會革命轉(zhuǎn)向民族解放的關(guān)頭。
第三個(gè)特點(diǎn)是蔣介石督戰(zhàn),何應(yīng)欽指揮,毛侃作聯(lián)系,84師作先鋒,全力“消滅”西北和全國的共產(chǎn)黨、紅軍、革命根據(jù)地。而是以“消滅”西北的革命勢力為主要的反革命具體目標(biāo)。
第四個(gè)特點(diǎn)是西北的地方勢力,地主武裝民團(tuán)、貪官污吏、土豪劣紳、地主惡霸的統(tǒng)一行動,一致動員,才真正開始了。過去,這個(gè)官紳被斗,其他官紳不動;甲區(qū)或甲縣民團(tuán)作戰(zhàn),乙區(qū)或乙縣者既不相援,也不過向。此時(shí),一反數(shù)十年積習(xí),一切地主反革命利益的代表人物或一切反革命分子,都在竭謀盡力,進(jìn)行“防共”“反共”和反人民。
而革命陣營內(nèi)部,也由陜北黨與團(tuán)特委畢維周、王兆卿等被屠殺破壞后,經(jīng)過華北北方局的幫助,重新恢復(fù)起來,陸續(xù)派回許多干部,加強(qiáng)與充實(shí)黨的領(lǐng)導(dǎo)與工作。黨的領(lǐng)導(dǎo)重新建立與恢復(fù)了。接著,參加察變失敗的干部、西北軍事領(lǐng)導(dǎo)之一的謝子長重返西北。西北的“分土地”、建立“貧農(nóng)會”、“擴(kuò)紅”、建立“紅軍”、“游擊隊(duì)”運(yùn)動大規(guī)模開展起來。陜西省蘇維埃代表大會于1934年底舉行。西北原有的紅軍游擊隊(duì),經(jīng)過戰(zhàn)斗,洗煉,建立了紅26軍的統(tǒng)一番號,建立了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的統(tǒng)一作戰(zhàn)領(lǐng)導(dǎo)機(jī)構(gòu),由地方黨力量不夠雄厚的陜甘交界,轉(zhuǎn)移到全國僅存的地方黨力量和群眾基礎(chǔ)最雄厚的陜北。
革命與反革命的最殘酷最激烈的戰(zhàn)斗,在1934年,開始遍地展開。
黨的陜北特委,從1931年白明善犧牲,許多人先后被捕,在陜北的特委常委、執(zhí)委呈現(xiàn)渙散、凌亂、不振氣象,旋改組。由畢維周、王兆卿等同志負(fù)責(zé)后,初由于1931年之新的盲動冒險(xiǎn)路線,把黨與團(tuán)合并,組成行動委員會,由畢任書記,取消過去的組織形式。由于行動變化猛驟,使許多人失去關(guān)系,也造成黨與團(tuán)內(nèi)的一時(shí)混亂。由于在華北和西安的一些人努力幫助,旋又糾正了總路線的盲動冒險(xiǎn),改變了行動委員會的組織,仍然恢復(fù)了黨的陜北特委和團(tuán)的陜北特委,而且是黨領(lǐng)導(dǎo)團(tuán),團(tuán)是黨的助手,領(lǐng)導(dǎo)青年參加戰(zhàn)斗。仍由畢維周任黨特委書記,王兆卿等為委員。魯學(xué)增、趙景隆等為團(tuán)特委委員。黨與團(tuán)特委在一塊組織機(jī)關(guān),過生活。因工作和職務(wù)關(guān)系到華北的和在西安的,或另任工作(如劉瀾濤是陜北黨特委之一,到華北后,另分工作。李馥華是特委巡視員,也另做北方工作。只有趙通儒仍按1930年棗樹坪會議執(zhí)行任務(wù)與保持關(guān)系。焦維熾等在西安……),或仍與陜北黨與團(tuán)工作保持密切關(guān)系。
在1932年前后,陜北黨與團(tuán)特委遭受敵人摧殘和破壞,畢維周、王兆卿等五人殉難。黨與團(tuán)的主要領(lǐng)導(dǎo)機(jī)關(guān)受此慘痛損失,也造成一時(shí)混亂。由于北方局派人,魯學(xué)增、安芳洪夫婦奔走于華北陜北之間,還有些人奔走于西安陜北之間和陜北與北方局之間,陜北黨與團(tuán)特委,在馬明芳、崔田民、馬文瑞、魯學(xué)增、安芳洪等的在陜北支持和向外聯(lián)結(jié),以及久在華北、西安同志們的策劃(每次陜西、西北、陜北黨遭破壞后,喬國楨和趙仰普,以及當(dāng)時(shí)尚未叛變的楊應(yīng)舉,苦心盡力,謀恢復(fù)與重建工作……)配合,先后楊璞(1934年冬被捕,1935年春才自首,自首后參加敵肅反工作,才進(jìn)行勸解別人自首的反革命活動)、郭洪濤、王達(dá)成、彭飛等到陜北。郭洪濤回陜北,對當(dāng)時(shí)盲目提倡“成份論”造成的工作慌亂和開始進(jìn)行分配土地、建立蘇維埃政權(quán),同謝子長的返回陜北廣泛開展游擊戰(zhàn)爭,起了極重大的作用。
渭華暴動失敗后,在陜西及陜甘,有過許多大大小小的武裝起義和戰(zhàn)斗,有過武字區(qū)及南梁堡的割據(jù)和大小塊根據(jù)地的試建與堅(jiān)持,但還未進(jìn)行過黨的代表會和蘇維埃代表會,而且也未形成堅(jiān)固的黨的領(lǐng)導(dǎo)。只是一些高級干部,一方面團(tuán)結(jié)一致,一方面又為分歧的意見各執(zhí)一是,牢牢領(lǐng)導(dǎo)與創(chuàng)建武裝部隊(duì),團(tuán)結(jié)在部隊(duì)為中心的活動。
陜北黨,自1927年至1930年,經(jīng)過數(shù)次代表大會、擴(kuò)大會,又與北方局和陜西省委、上海中央、南方江西蘇區(qū)中央,取得和保持著緊密聯(lián)系,雖屢遭破壞,下層從支部、區(qū)委、縣委到特委,各種系統(tǒng)、關(guān)系,始終保持著。尤其陜北黨特委的軍委,雖然有了楊國棟的由消極到不干到離開,但軍委本身并未削弱,因劉志丹、謝子長堅(jiān)持建軍擴(kuò)軍,趙仰普同北方局保持華北與西北間的關(guān)系,由陜北黨特委軍委,經(jīng)北方局及中央批準(zhǔn)而擴(kuò)大成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鑒于陜西省領(lǐng)導(dǎo)之不能隨機(jī)應(yīng)變,給根據(jù)地黨的統(tǒng)一領(lǐng)導(dǎo),建立了由中央批準(zhǔn)的西北工作委員會。以至后來1935年北方局又有朱理治等的中央代表團(tuán)、張慶孚的中央代表等相繼出現(xiàn)。這些機(jī)構(gòu),限于當(dāng)時(shí)戰(zhàn)爭環(huán)境,人員未充實(shí),制度未完善,機(jī)構(gòu)不整齊,那是另一回事。而且于開始分土地后,召開了陜北蘇維埃代表大會于1934年冬,陜北黨與團(tuán)是起了重要作用的,對培養(yǎng)黨政民地方工作干部,對陜北土地革命開始在綏米佳吳分土地,是起了推動作用的。洪濤在當(dāng)時(shí)及稍后的一些偏差、錯(cuò)誤、毛病,別人也不是沒有,而且有的比洪濤有過之無不及。前后事證,不難徹查。
在西北革命與反革命戰(zhàn)爭急驟直變、慘酷劇烈形勢下,有些人被嚇的不敢革命,有些人逃避革命,有些人叛背革命。但在參加了革命的人們之中,也有不少人被反革命“圍剿”嚇得倉皇失措,手忙足亂,或一味逃奔,或一味應(yīng)付,或遷怒于群眾,或怨天尤人,過分地從內(nèi)部搞鎮(zhèn)反。
蔣介石在“圍剿”江西戰(zhàn)爭中,沒有使用海軍,因中國海軍有個(gè)傳統(tǒng),不參加內(nèi)戰(zhàn)。他使用了新建立的空軍和嫡系,他瓦解了福建人民政府的抗日反蔣。對西北,從1925年北伐到1934年的十年間,一直未使用過嫡系武力。蔣馮閻戰(zhàn)爭,雖然蔣介石勝利,還未有一兵一卒入西安。
由于回民實(shí)力和陜西地方實(shí)力,乘馮玉祥在魯豫冀間之失敗(山東韓復(fù)榘為蔣收買,河南戰(zhàn)敗,河北為奉軍接去)而取得寧甘陜。連蔣介石本人,也在1935年前不敢到西安一行。
1934年一年的竭力經(jīng)營,才把84師、晉軍、東北軍驅(qū)在前鋒,而以嫡系之黃杰、關(guān)麟征、杜聿明部殿后,胡宗南等準(zhǔn)備入陜。到1935年,蔣介石在西安建立了“西安行營”,把憲兵第三團(tuán)蔣孝先(雙一二打死)全部開入,駐于西安,飛機(jī)場修好,鐵路修好,公路修到甘肅,碉堡從蘭州、寧夏、山西、陜北,沿長城和黃河,修到潼關(guān),才屢屢親到西安,督促監(jiān)視張學(xué)良、楊虎城進(jìn)行內(nèi)戰(zhàn),隨帶朱紹良、胡宗南等駐西安,造成和東北軍、西北軍的矛盾,促成“雙一二”事變前張楊的危急,也造成中國革命在西北的千鈞一發(fā)形勢和極端困難。
六、1935年5月,吳家坪戰(zhàn)役和玉家灣祝捷大會,造成的瓦窯堡城內(nèi)外的敵我雙方具體形勢和條件
玉家灣祝捷大會前,吳家坪、吳家寨、馬家坪三個(gè)戰(zhàn)役,扭轉(zhuǎn)了西北革命根據(jù)地、西北紅軍和西北黨對西北革命的整個(gè)形勢,也改變了西北革命對全國革命的比重。
在這三個(gè)戰(zhàn)役之前,從1924年到1934年,黨領(lǐng)導(dǎo)西北人民和革命武裝,經(jīng)過十年的漫長歲月,經(jīng)過成功和失敗,經(jīng)過渙散和恢復(fù),經(jīng)過敵人的摧殘、破壞、屠殺、拘捕、囚禁和瓦解,經(jīng)過大大小小許多戰(zhàn)斗,成千成萬的黨團(tuán)員和革命戰(zhàn)士、革命人民,為戰(zhàn)爭而犧牲流血,捐付了生命、家庭財(cái)產(chǎn),許多人員負(fù)傷殘疾。但西北的任何成功或失敗,不論在敵人的心目中,或革命的營壘中,人們評價(jià)起來,總認(rèn)為西北革命還只是西北一隅的局部問題,甚至還被目為是陜北的局部問題,無關(guān)大局,無足輕重。
從1934年起,反革命方面首先認(rèn)為,陜北革命,不容忽視,不亞于江西。一旦和華北接連,和江西出征結(jié)合,所謂“禍延全國,勢難可遏”。蔣介石與何應(yīng)欽把對“圍剿”西北革命,看得比對付日本進(jìn)攻華北還重要。因而,動員修碉堡,修公路,修隴海路到西安和銅川,給運(yùn)輸重兵及軍糧軍械開路。從西安關(guān)中調(diào)42師到陜北,從華北調(diào)84師到陜北,組織晉綏寧甘陜五省聯(lián)合“圍剿”的指揮部——華北軍分會和參謀團(tuán)。把五省地方實(shí)力軍人,各任命為綏靖主任,設(shè)綏靖公署,指揮原有部隊(duì),均受節(jié)制于蔣介石自己的“委員長西安行營”。調(diào)東北軍入陜,設(shè)“全國剿共副總司令部”于西安。蔣介石的“委員長西安行營”,和南昌廬山的“全國剿共總司令部”、“南昌行營”一模一樣,駕凌一切,專橫獨(dú)裁,生殺予奪,唯心所欲。
革命陣營,土地革命,如火如荼,遍地開展,游擊隊(duì)風(fēng)起云涌。紅26軍北上陜北,紅84師和紅27軍誕生于陜北,但只能打開些民團(tuán)盤據(jù)的山寨,消滅反革命的小股武裝。
1935年5月上旬,上午9時(shí),瓦窯堡84師一個(gè)營出動,向東三十里楊家園“會哨”。行至吳家坪,才10時(shí)左右。賀晉年帶一個(gè)班戰(zhàn)士和武裝,四匹馬,在吳家寨大路邊破廟中埋伏。紅軍主力部隊(duì)原計(jì)劃進(jìn)攻駐楊家園敵人那個(gè)營,未果,全部埋伏在吳家寨山上、山下的村莊溝渠,近者距大路二三里,遠(yuǎn)者約五里,和賀晉年等保持密切聯(lián)系。
趙仰普在敵84師由瓦窯堡出城前,每日給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西北工作委員會、陜北特委、陜北省蘇維埃政府劉志丹、郭洪濤、馬明方等有秘密報(bào)告,說明敵必東往,自己在內(nèi),將設(shè)法利用空隙,返回蘇區(qū)。
敵主力行至吳家坪,最前邊以一個(gè)排作尖兵。行至斷橋河邊溝渠,正在下坡,距賀晉年、郭立本埋伏之廟不過五六十步遠(yuǎn)近。賀等開槍,敵還槍,后退,報(bào)告前邊遭遇,請示進(jìn)退。趙在敵政訓(xùn)員徐克鉅(等于紅軍中的政治委員,特務(wù))、營副(未來營長,營長在城內(nèi))、三個(gè)連長、86師軍需一塊同行,受軟禁與監(jiān)視,牽一毛驢,未被綁。
槍聲一響,敵營副已布置三個(gè)連頑抗,只輕機(jī)槍已在大路上架起二十余挺。敵政訓(xùn)員徐克鉅聞槍聲驚懼,面色如土,掏出手槍向趙,欲射趙,又欲督戰(zhàn)部隊(duì),正在猶豫不決。尖兵跑回向徐及營副、連長等請求進(jìn)退命令。趙見吳家坪村子邊山頭牧羊人趕羊逃奔,塵土飛揚(yáng),乘機(jī)主動地、不待敵人開口,提出:“已被紅軍包圍。趕快向后退卻,找到有利地形,再作布置。”敵人指揮軍政人員,聽趙說詞,還定不了主意。趙把86師軍需拉上馬去,踢其馬向后奔逃。趙等前邊二連士兵,后邊一連士兵。趙踢馬并說86師軍需:“你何必受此危險(xiǎn)?”這馬和人向后一逃,沖慌了后邊一連,全部向后隨馬而逃。
趙乘此機(jī)會,促徐逃走,因徐一走,全部可退。趙又向徐說:“上馬進(jìn)退皆便”,邊說邊拉徐上馬。趙謀奪徐手槍,私計(jì)奪到手,還有兩連士兵包圍,如何逃出?決計(jì)促成敵人全部逃退比較最好。何況一奪之際,二人扭住,前后三連敵士兵,身邊敵有五名助手,如何能得手呢?
趙拉徐上馬時(shí),發(fā)覺徐已被嚇到手戰(zhàn)腿軟。趙又邊說邊動手,把徐馬上的“捎連”拉下來,說:“要這些累贅干啥!”內(nèi)一狐皮大衣、反共文件及自首分子們的表格文件和趙寫的簡歷。趙用腳踢其馬狂奔。敵士兵更被徐及其馬帶動,沖動,不顧一切向后跑。
敵營副同三位連長還計(jì)議如何作戰(zhàn),趙向營副說:“出城時(shí)沒有作戰(zhàn)命令,安全回去比什么也好!團(tuán)政訓(xùn)員已走了!”敵營副立即跨馬,向后沒命般打馬奔逃,既來不及命令進(jìn)退,也來不及向三個(gè)連長說如何對待趙。
趙見大勢向后逃已定,立即動手把毛驢馱的“被包”拉下來,大踢毛驢,使毛驢狂奔。士兵們討厭毛驢沖闖,也打毛驢。毛驢在四面被擊下,越奔越狂,又是叫驢,連叫帶奔,分外驚人。兵打驢踢人,亂成一堆向后跑。三個(gè)連長見團(tuán)政訓(xùn)員和營附奔逃,也撒腿狂奔,只嫌跑的慢,只嫌他娘生少了腿。
趙在當(dāng)時(shí)計(jì)劃,至少自己要受兩粒流彈的光顧,但,還一一安全如計(jì)劃而勝利。身后士兵催趙“快跑!”趙亦隨口催士兵們“快跑!”但若一直跑回城內(nèi),又將如何得出?
趙發(fā)現(xiàn)跑的士兵有跌倒者。趙趕快向敵士兵學(xué)習(xí),連連跌倒,慢慢往起爬,裝作跌痛跌疼模樣,邊爬邊跌,邊看邊算,邊立高處向后看追者遠(yuǎn)近。數(shù)的敵士兵自己身后,還有十多人,而是槍扛著,毫無戰(zhàn)斗準(zhǔn)備。于是趙在一些灌木叢旁蹲下,企圖趁敵慌亂,向蘇區(qū)奔。
忽聽后邊馬蹄響。趙一再計(jì)算:敵人的三匹馬,自己的一匹毛驢,已經(jīng)向后跑出四五里遠(yuǎn)了,哪里來的馬蹄聲?屢屢向后看,晴朗的初夏,為逃奔帶起的塵土籠罩的一片模糊。只見敵士兵,有跌倒路旁者。從槍聲第一聲響起,一共聽到還不及十響。再三思維判定,必然真有紅軍追來。因?yàn)榫鄺罴覉@還有十里,出城時(shí)敵團(tuán)長送出城門,也未說中途或楊家園有敵軍接應(yīng)。趙于戰(zhàn)斗日前已知紅軍在玉家灣一帶舉行紀(jì)念“五一”國際勞動節(jié)大會。自己有秘密報(bào)告連日轉(zhuǎn)去,至少必然偵察部隊(duì)或游擊隊(duì)在這條路上,吳家寨、楊家園或湫峪溝和自己聯(lián)系或接迎,自己逃奔蘇區(qū)。因?yàn)檫@種計(jì)劃,在自己未入瓦窯堡時(shí),已與劉志丹、郭洪濤等當(dāng)面會議決定。既入瓦窯堡后,也已不只一次秘密報(bào)告中請求過,而且把自己的衣物特征,種種暗號,互相約定。自己上路,完全按約定的衣帽鞋襪用品穿戴,防止被敵打死傷后,還要入蘇區(qū),防止在自己負(fù)傷昏迷、不會說話或來不及說話時(shí),仍能辨認(rèn)不誤。也還有過遺囑等,防止戰(zhàn)斗中死亡。
在雙方槍聲響后,賀晉年率郭立本等四人,發(fā)現(xiàn)敵人聞槍后退,未計(jì)敵人多少,也未計(jì)敵人有無布置或埋伏,四人四馬猛追后退之?dāng)场城吧诓奖婒T兵猛追,只顧狂奔后逃,未敢抵抗。從橋邊跑到吳家坪沒二里,見敵全部皆向后逃,未行頑抗。
郭立本追到大路上,由馬上看到趙的衣帽眼鏡,向賀晉年同志建議說:“趙通儒在內(nèi)!”賀問:“你怎知道?”郭說:“那位大個(gè)子,戴眼鏡的。一個(gè)街上長大,他的眼鏡再沒第二人有!”郭連1934年農(nóng)歷正月曾一同鬧秧歌也來不及說。賀聽郭言,立即下令:“追!追!追!”多連一個(gè)字也不說,四人鞭馬猛追。
在灌木叢邊,趙抬頭看賀等四人皆從馬上躍下,一位小戰(zhàn)士將趙眼鏡摘去,給自己戴上。賀司令員見趙握手說:“趕快回!不用別處接了!”趙向賀說:“拼命追二里,全部交槍!”賀等聞言,翻身上馬,向前猛追,不顧后邊有無援軍繼來。趙忙對小戰(zhàn)士說:“不敢戴,近視鏡,戴上眼看不清!”小同志邊將眼鏡裝入衣袋,邊拍馬隨賀郭追去。
趙見四人四馬追敵,萬一敵人稍加抗阻,如何得了?忙立起身來,向后大喊:“交開槍了!快去收槍!”大喊大跑,找人催隨賀郭。時(shí)才上午10時(shí)多還未到11時(shí)。
趙至吳家堡(大路邊),沿途數(shù)得敵軍陣亡士兵不到十人,賀等只從尸身拉去子彈,來不及解拾全部武器。在趙大喊大叫聲中,有二百多戰(zhàn)士、農(nóng)民,拿大刀長矛,或只拿根麻繩,很多都是空手,許多農(nóng)民是一邊丟下手中的簸箕筐擔(dān),一邊向前跑去追隨賀等。頭前幾位收到路旁尸體上的步槍和手榴彈,后邊聽到更歡呼,蜂擁前奔。
賀晉年在馬也未下,拉開機(jī)槍,在馬上向前邊逃奔之?dāng)尺B住掃射幾下。敵人從吳家寨、吳家堡、吳家坪,有的跑了三四里,有的跑了五六里,掙命逃奔,跑的上氣不接下氣,誰也不顧誰。趕到中灣河灘,人人跑的力竭聲嘶,汗喘不上,神魂不清。賀郭等人的馬蹄聲,機(jī)槍聲,后邊群眾和戰(zhàn)士的追跑聲,喊叫聲,震天動地。敵人多數(shù)排長以上的二十多人,奔向瓦窯堡。余全部在中灣被賀等追上,圍住交槍。我無傷亡,敵共死傷不及二十人。
趙從灌木林旁到吳家堡,約二里,已跑得口干舌焦,連說話也不流利。該村農(nóng)民三四十人包圍住趙,問長問短,拿來給紅軍備下的干糧要趙吃。趙見盛情難卻,邊說:“趕快去收槍!問我干啥?”青壯年聞聲奔赴前線。老頭老婦拿來三個(gè)大木勺,滿盛綠豆湯,給趙。趙接著,一飲而盡,一氣三五分鐘喝了有五、六斤,才解渴,才說話清楚。一邊派人向山頭喊叫主力部隊(duì)進(jìn)軍援賀,一邊寫信派人送,一邊遇一號兵,催號兵吹號,調(diào)部隊(duì)前進(jìn)。到十分鐘,派五六批人帶口信及紙面信,送劉志丹。兩個(gè)戰(zhàn)士拉一沒鞍子馬和三個(gè)農(nóng)民,扶趙騎上,由大路口,向吳家寨子村后走。
趙在馬上,看到志丹和郭寶珊等帶部隊(duì)從山上向大路奔沖。而楊家園所駐敵人一個(gè)營,已聞槍聲,跑步前來。敵人從東面打來的飛彈,在趙頭上飛過,馬蹄邊颼颼落下。隨趙的戰(zhàn)士和農(nóng)民向趙說,楊家園敵軍昨晚被圍未攻,今晨紅軍撤在山上,他們卻出來送槍。時(shí)上午十一時(shí)多。賀等此時(shí)在距吳家寨西距瓦窯堡十二三里之中灣,忙于收槍。
趙與戰(zhàn)士農(nóng)民行至魏家岔休息等候。聽到溝口雙方激戰(zhàn),槍似炒豆一般“碰!碰乒乓”,響徹云霄,手?jǐn)S彈的爆炸聲動山岳。
下午三時(shí)后,全部戰(zhàn)斗結(jié)束。吳岱峰、吳志淵、劉志丹與趙相會于魏家岔。在會見前,趙用農(nóng)民的杏仁油,給一個(gè)被炸彈炸傷的紅軍戰(zhàn)士醫(yī)治傷殘。
從上午10時(shí),至下午3時(shí),五小時(shí)內(nèi),連勝兩役,得步槍千余支,輕機(jī)槍近百挺,最多有一人收槍17支者。第一役為只有收入、極少消耗的完滿完全勝仗。第二役因敵人也是主動奔來戰(zhàn)斗,雙方對戰(zhàn)達(dá)三小時(shí)之久,我方因得到第一役的勝利支援,終獲全勝。傷亡頗不少,為少數(shù)犧牲換得極大勝利。次日,又用二三小時(shí)戰(zhàn)斗,殲滅從綏德來的一個(gè)全營和由楊家園逃去之一個(gè)全排。
兩日,三役,打死敵營長二,連長四五,排長數(shù)名,士兵百余名。俘敵連長二,排長數(shù)名,士兵近千名。自愿參加紅軍者數(shù)百人。得迫擊炮一,機(jī)槍百余挺,步槍近二千支。兩團(tuán)人的夏衣和醫(yī)藥。兩團(tuán)人兩個(gè)月的軍餉。
這三個(gè)仗,是1927年“清澗起義”至1935年初,九年間黨在西北領(lǐng)導(dǎo)的革命戰(zhàn)爭的最大勝仗。這三仗的收獲,給解放延長、靖邊,攻橫山,慕家塬一帶消滅晉軍,會合紅25軍,迎接中央和毛主席及長征到西北的全國紅軍主力,弄下會師的場會和見面禮。這三仗的收獲,壯大了西北紅軍,擴(kuò)大了西北蘇區(qū),鍛煉了全體蘇區(qū)勞動人民,不分男女老幼,和紅軍主力部隊(duì)、游擊隊(duì)配合,一致作戰(zhàn),伏擊、襲擊、包圍,殲滅強(qiáng)大的反革命整營整團(tuán)整旅整師至數(shù)師主力部隊(duì)。前此,紅軍主力和游擊隊(duì)也互相配合不妥當(dāng),打硬仗,打大仗,主要是主力部隊(duì)的事,各方面只能在戰(zhàn)后或戰(zhàn)爭中擔(dān)抬傷兵、通風(fēng)報(bào)信而已,有的根本只能在打了勝仗來看熱鬧,打了敗仗一齊逃奔,有的連封鎖消息的任務(wù)也完成不了。這三個(gè)勝仗的政治作用和影響,無論在蘇區(qū)內(nèi)外、國內(nèi)外,都是極重要和極大的。過去,知道陜北的人很少,陜北的人和事,在西安都不引人注意。這三仗之后,美日英法帝國主義大起慌恐,蔣介石的賣國“剿共”軍事、政治、財(cái)政賭注,完全從對付江西,轉(zhuǎn)而對付“陜北”了。接受日寇條件,接受美英法的軍火和不平等條件,向美帝的“麥棉借款”修隴海路,修碉堡,修公路運(yùn)兵,調(diào)兵遣將,一言一動,無不是為了爭取“剿共”在“陜北”的勝利。
5月9日,為了紀(jì)念“五九”“廿一條”國恥紀(jì)念,為了慶祝三個(gè)勝仗的大捷,為了抗日救國,為了部署西北革命的新布置,在玉家灣舉行了全體紅軍將士及一些黨政干部和近萬人的革命工農(nóng)群眾大會。
大會由小劉(張達(dá)志同志的代名)宣布:西北工作委員會和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任命劉志丹為前敵總指揮,任命高崗為總政委。接著是劉志丹總結(jié)三個(gè)勝仗對反帝抗日和土地革命的意義,及用更大的勝利粉碎“圍剿”。
在劉講話之后,是趙仰普報(bào)告:國際間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由德意日法西斯軸心,分頭由歐洲德意的“爭取生存空間”,和日本在中國推行《田中奏折》侵占華北、滅亡中國開始。全世界在形成法西斯侵略陣營和反法西斯陣營的過程中,美英法在暗助德意日軸心而搖擺中。蘇聯(lián)將是反法西斯戰(zhàn)爭的領(lǐng)導(dǎo)者和組織者。中國革命,中日戰(zhàn)爭,將是全世界反法西斯戰(zhàn)爭的有機(jī)組成部分。日本滅亡中國,占去東北四省,又要華北“特殊化”,浪人橫行,走私,設(shè)特務(wù)機(jī)關(guān),藏本事件,推行《田中奏折》。蔣介石媚日“剿共”,賣國殃民。“兩個(gè)中國的對比”:蔣介石中國的賣國媚日,內(nèi)戰(zhàn),貪污,腐化,無能;中國共產(chǎn)黨領(lǐng)導(dǎo)的蘇維埃中國,抗日,反帝,反封建,反買辦官僚,工農(nóng)人民民主中國的一切愛國愛民,為國為民,互相針鋒相對,勢不兩立。蔣介石的上下不一,官兵不一,軍民不一,黨政軍不一,是他必然崩潰的致命癥結(jié)。國內(nèi)陸海空軍的特點(diǎn)性能。各派系陸軍的編制、裝備、素養(yǎng)、作風(fēng)、習(xí)慣、戰(zhàn)斗力,其互相矛盾、吞并、雇傭兵,樹倒猢猻散規(guī)律,都不是志愿的工農(nóng)子弟兵和紅軍的敵手,各有弱點(diǎn),各不值擊。抗日,團(tuán)結(jié)全國,團(tuán)結(jié)各階層,建立人民民主政權(quán)和新中國,走向社會主義和共產(chǎn)主義中國。
再無人講說什么。
劉志丹宣布:獎(jiǎng)給戰(zhàn)斗英雄、收槍最多的郭立本狐皮大衣一件(俘得徐克鉅的大衣)。全軍發(fā)給夏衣,每人一套。少先隊(duì)用短半褲區(qū)別。愿參加紅軍的白軍士兵俘虜向左邊集合,得數(shù)百人,與紅軍戰(zhàn)士一樣發(fā)給新夏衣。
趙仰普處理不愿當(dāng)紅軍愿出蘇區(qū)的白軍俘虜排長、連長和士兵,一律每人給三元路費(fèi),無條件釋放。馮醫(yī)官老婆首先無條件釋放。李團(tuán)長和營長的女人,待談明“共同抗日”之后仍釋放,絕不為難。小商人貨物全部物歸原主。大商人及豪紳、地主、反革命商人的貨物,全部沒收。沒收貨物的腳戶及其應(yīng)得腳費(fèi),按原訂腳費(fèi)由國民經(jīng)濟(jì)委員會照數(shù)發(fā)給。不沒收的貨物由原貨主與原腳戶按原議腳價(jià)付給。俘得醫(yī)藥及醫(yī)務(wù)人員,開辦紅軍醫(yī)院。醫(yī)生、護(hù)士按原薪,現(xiàn)給三個(gè)月薪金,托馮醫(yī)官老婆、馮醫(yī)官及出蘇區(qū)之友人捎回其原籍家中。按原級升一級任用。待遇按原薪支給(黨政軍任何人無薪餉。只對醫(yī)生、護(hù)士按其原薪支給,以示優(yōu)待,而且給申明,以后條件好,還可給加薪)。沒收得一切非武器物資,全交國民經(jīng)濟(jì)委員會與黨政軍領(lǐng)導(dǎo)機(jī)關(guān)議處。傷員一律送醫(yī)院治療,并給傷病員規(guī)定飲食、蔬菜供給標(biāo)準(zhǔn)(過去沒有)和養(yǎng)傷費(fèi)(按傷輕重給)。開辦了第一所醫(yī)院,改變了俘虜政策(過去所俘排長以上,一律槍斃)。實(shí)行了工商業(yè)政策、金融政策、優(yōu)待醫(yī)生等科學(xué)技術(shù)人員政策。(延長解放,俘獲無線電臺及石油科技員,皆援醫(yī)生之例而友待。)肯定不殺婦女及女俘。(有許多人主張把女俘殺掉,或婚配給紅軍戰(zhàn)士,經(jīng)苦苦說服)。
玉家灣祝捷大會,對蘇區(qū)的黨政軍民,起了全體總動員的作用,也改變與確定了許多重要政策法令。對國民黨區(qū)域,起了很大的推動抗日救國宣傳活動的作用,士兵軍官女俘們回去,粉碎了蔣介石國民黨對蘇區(qū),對紅軍,對黨的許多造謠誣蔑。紅軍共產(chǎn)黨的抗日主張,由幾百張活口生動地傳說著。
玉家灣祝捷大會后,敵人知道陜北紅軍不是像過去,包圍住國民黨井岳秀部一個(gè)連還不一定能消滅的樣子了。而是包圍住84師一個(gè)營,有西北最好裝備的武器,用不了二三小時(shí),即可全勝。也不是像過去,在某村一接火,勝利后立即他往,失利后更不知何往來了。而是可以上午剛打了仗,下午仍可打仗,今天所戰(zhàn)皆捷,每戰(zhàn)必勝,愈戰(zhàn)愈強(qiáng)的,不可想象的武裝力量。從古至今,不論中國或外國,一役之戰(zhàn)縱使勝利,上下無不疲累不堪。陜北紅軍,亦皆人生父母所養(yǎng),既無三頭六臂,何來如此精力?有的俘虜?shù)絿顸h區(qū)域說:“紅軍找了十石綠豆煮湯喝,水帶點(diǎn)黃色,一碗中見不到三粒綠豆。人數(shù)之多,由此可見,如何能不被俘呢?”
其實(shí),我們紅軍在當(dāng)時(shí)并沒那樣多。我們所有黨政軍人員,參加戰(zhàn)斗的人,還沒三千名,連老百姓在內(nèi),也沒有一萬人。我們只是二千多人,千多不完全管用的武器,每槍不到三十粒子彈。有很多徒手,有很多人只拿一把清朝時(shí)代的大刀,有的拿一枚手?jǐn)S彈,有的還拿農(nóng)器,有的只拿自己的一條布腰帶當(dāng)繩子用。陜北紅軍的聲威,把國內(nèi)外的反動分子都震昏了,都被嚇的手忙腳亂。在玉家灣西五十里的安定縣駐軍,感到元朝修建下的古老城墻不可靠,逃入瓦窯堡去了。在東五十里的折家坪國民黨駐軍,逃到清澗縣城內(nèi)去了。遠(yuǎn)在距八十里的南面永坪的國民黨軍,也因無險(xiǎn)可守,逃入瓦窯堡去了。連遠(yuǎn)在百里外的延川城內(nèi)國民黨駐軍,也嫌城不可待,逃入清澗城了。
過去是每三十里或五十里相為犄角的“圍剿”網(wǎng),在玉家灣祝捷大會后,成為:清澗駐敵一個(gè)旅部,兩個(gè)團(tuán)部,七個(gè)營;延長駐敵一個(gè)騎兵連,百名左右民團(tuán);延安駐敵一營;瓦窯堡駐敵一個(gè)團(tuán)部,三個(gè)營,十個(gè)連,延川、安塞民團(tuán),各縣逃亡地主組成的劉壽卿二三百人一支反共游擊隊(duì);靖邊駐敵86師一個(gè)營。除以上這些主要據(jù)點(diǎn)和幾個(gè)民團(tuán)小據(jù)點(diǎn)外,縱橫千里,七縣多境內(nèi)的鄉(xiāng)村,全成革命根據(jù)地。革命人民,從忽此忽彼、不定量、不定地區(qū)而陡然成為五十多萬人口,革命力量驟增,勝利猛烈。反革命也在大加驚惶之后,一方集中力量,一方大修強(qiáng)固工事,一方動員晉軍過河“圍剿”,一方準(zhǔn)備空軍配合陸軍。
大勝之后,革命又面臨了更加艱難的戰(zhàn)斗任務(wù)。革命形勢,要求我們迅速培養(yǎng)大量干部,要求我們迎擊強(qiáng)大的由山西過河的敵軍及關(guān)中北上的強(qiáng)大敵軍,要求我們在山西、綏遠(yuǎn)南部、寧陜交界、陜甘交界、關(guān)中地區(qū)迂回作戰(zhàn),殲滅強(qiáng)大敵人。
瓦窯堡,應(yīng)該解放,成為根據(jù)地的心臟。
欄目責(zé)編:魏建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