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沈從文的幾個片段
程耀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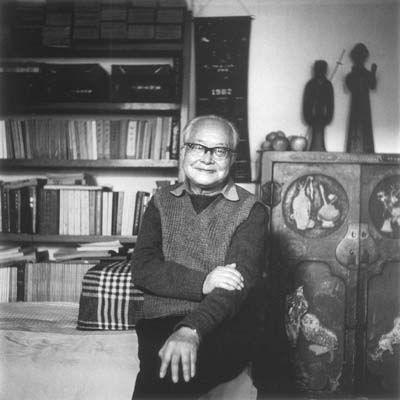
1
2006年,在故宮看見沈從文捐獻的文物時,我不知道自己為什么要長久地站立;在歷史博物館,我曾幼稚地詢問一個講解員,哪里是沈從文曾經站立的地方?那講解員說來過這里的名人實在太多,她也不清楚。在去昌平的路上,看見達子營的路牌、奔馳的大巴、高遠的藍天,想起沈從文初到北京時的那句話:“北京的天藍得使我想下跪。”北京之于沈從文,有過太多的輝煌、失落和苦難。
我要說的是巴金的回憶文字。在這些文字中,有大量的信息,使我們更多地去了解沈從文。“照我思索,能理解我;照我思索,可認識人。”這是沈從文一生的經驗,我們了解了,未必是壞事。
2
沈從文去世后,巴金并沒有參加他的葬禮。因為那時候的巴金身在醫院,只好委托恰在北京出差的女兒李小林送去花圈。但此時的巴金并沒有忘卻他的好友,他不時地想從北京和上海的報紙上知道關于沈從文葬禮的消息。但是,巴金失望了。新華社因巴金女兒送花圈,發了一則簡短的消息——沈從文告別親友和讀者。之后,只字未提沈從文的葬禮。
沒有達官顯貴,來告別的只是些親朋好友。廳里播放著死者生前喜愛的樂曲。沈老躺在那里,十分平靜,仿佛在沉睡,四周幾籃鮮花、幾盆綠樹。每個人手中拿著一枝月季,走到沈老跟前,行了禮,將鮮花放在他身邊。沒有哭泣,沒有呼喚,也沒有噪音驚動他。
這是李小林描述給巴金的當時的場景。
在我掌握的有限的材料中,沈從文去世的消息除大陸以外,全球幾乎所有的華人報紙都作了報道。大致內容是:沈從文的逝去,是中國文壇的巨大損失。
就這樣一位偉大的作家,從湘西的一條船上開始了自己的人生,開始是悄寂的,如同他的作品,清風一樣拂過中國文壇;就這樣一位偉大的作家,依舊在悄寂中終結了他的人生,沒有評價,沒有定論,沒有熙攘和嘈雜。
3
首屆文代會在欣欣向榮的北京開幕。許多只聞其名未見其人的作家、詩人、評論家在這次大會上相互見面,相互擁抱,訴說往事,共話未來。然而,滿懷希望的沈從文卻被拒之門外,他不是文代會的代表。當巴金、李健吾、趙家璧等人前去看望他的時候,他的臉上依然露著微笑,并且打聽文藝界一些熟人的近況,關心每個熟人。此時的沈從文,表面看上去是樂觀的,其實,他的內心承受著多大的痛苦和壓力,恐怕只有他自己知道。巴金是這樣說的:“他在圍城里,已經感到了孤寂,對形勢和政策也不理解,只希望有一兩個文藝界熟人見見他,同他談談。他當時戰戰兢兢,如履薄冰,仿佛就要掉進水里,多么需要有人來拉他一把。可是他的期望落空了。”
這個時候,誰愿意去拉他?想拉他的人,在當時說不起話,也不敢說話。幾個熟人,當然是有的,恐怕都站在了他的對立面。
我在閱讀《沈從文傳》和黃永玉寫的《比我老的老頭》時,也讀到了關于沈從文淡出中國文壇的一些描述。首屆文代會被拒之門外、弟弟被正法、一些熟人遠離,等等,這些事件的發生,是不是沈從文淡出文壇的真正原因,誰也說不清楚。然而,在我看來,沈從文就此擱筆,轉入文物和中國服飾研究,他的《中國古代服飾研究》《戰國漆器》不僅奠定了他在文物界的地位,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拯救了他的生命。那個時候,為了命運,為了表現,為了一個新的活法,如果他繼續寫下去,在以后的時間里,會發生什么?老舍、傅雷的結局會不會在他的身上出現?
并非塞翁失馬、因禍得福,而是沈從文實在太聰明了。
4
在巴金的回憶文章中,有這樣一段描述。描述的內容來自沈從文寫給巴金的信件。“因住處只有一張桌子,目前為我趕校那兩份選集,上午三點她即起床,六點出門上街取牛奶,把桌子留給我工作。下午我睡,桌子再讓她使用到六點,她做飯,再讓我使用書桌。這樣下去,那能支持多久!”這里的她,自然是張兆和了。一張小桌,夫妻二人,錯時使用。
我是躺在床上讀這篇回憶文章的。讀到這里的時候,我感覺到自己頭下的枕頭有些潮濕。這封信是1980年2月,沈從文寫給巴金的。那年,我已經上小學,在西海固那個閉塞的小村莊里,我已經有了供自己做作業的木質書桌。然而,在北京,一位偉大的作家,為一張用來寫字的書桌向友人傷感地訴說。
很明顯,這是兩個作家之間的筆談,是來自肺腑的真言。此時的沈從文買不起一張書桌嗎?書桌是有的,只是沒有擺放書桌的地方。僅僅一封書信,從書信的背面,我能聆聽到沈從文的聲音、呻吟和申訴。而巴金將這封書信中的一個細節呈現給世人,他想要表達或傳遞什么信息?閱讀此文字的人都很明晰。
關于書桌之事,巴金在文章中又發表了一點自己的感慨:“這事實應當大書、特書,讓人們知道中國一位大作家、一位高級知識分子就是在這種條件下工作的。”這樣的語言,只有巴金,而且只能是巴金這樣的人才敢說出口,其他人呢?
在我閱讀到的關于沈從文的文字中,沈從文的住房得到胡耀邦同志的關照和批示,給他解決了大房子,配了車、配了助手。關于此事,巴金是這樣寫的:“這個問題要是能早解決,那有多好!可惜來得遲了。不過有人說,遲來總比不來好。”
來了,一切都來了。當一切優越的條件向沈從文走來的時候,死亡并沒有垂青這位偉大的中國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