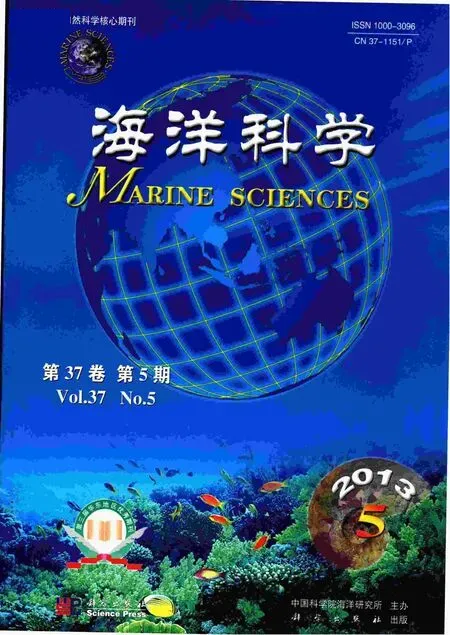灌河口海域表層沉積物中重金屬的污染變化及潛在生態危害
宋曉娟, 賀心然 , 陳斌林, 曹廣林, 曹 雷, 馬玉琴
(1. 河海大學 環境學院, 江蘇 南京 210098; 2. 連云港市環境監測中心站, 江蘇 連云港 222001; 3. 連云港市環境保護局, 江蘇 連云港 222001; 4. 連云港市環境保護科學研究所, 江蘇 連云港 222001)
重金屬是具有潛在危害的重要污染物, 它不能被微生物分解, 可在生物體內富集, 并通過食物鏈危害人類健康。研究表明, 通過各種途徑進入水環境中的重金屬, 絕大部分迅速轉移到懸浮物和沉積物中[1-2], 因此, 無論是追蹤重金屬的污染源, 還是了解金屬污染物的擴散, 主要依賴于對沉積物的研究。河口海域是陸地與海洋的交接地帶, 具有多種環境功能和生態價值, 同時也是受人類活動影響較明顯的地帶。研究河口沉積物中重金屬的污染狀況, 可深入了解污染物在不同介質中的分布特征和遷移轉化, 明確污染來源, 對河口海域的良性發展具有重要意義[3-5]。
灌河地處海州灣南部, 在江蘇省燕尾港注入南黃海, 灌河口具有優良的建港條件, 對鄰近地區的經濟發展起到重要作用[6-7]。近幾年, 隨著江蘇沿海大開發政策的落實, 臨海工業獲得了飛速發展, 該海域沿岸新建了多個工業園區。經濟的迅速發展, 必將對生態環境構成嚴重威脅[8], 該海域的環境污染也日益受到關注[9-12]。為及時跟蹤重金屬的污染狀況, 本研究對灌河口海域及其入海河段以及鄰近的埒子河口海域表層沉積物進行了采集, 分析了重金屬含量, 并進行生態風險評估, 確定可能存在生態危害的區域, 為灌河口海域及沿岸的污染治理、環境管理以及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提供基礎數據和決策依據。
1 材料與方法
1.1 樣品采集
2011年4月在灌河口海域布設13個站位(H01-13), 為便于比較分析, 同時對其入海河段和鄰近的埒子河口海域進行了采樣分析。用抓斗式采樣器采集了表層沉積物樣品(0~20 cm)。樣品編號后放入預處理的聚乙烯袋中, 密封運回實驗室, 陰暗處0~4℃保存。
1.2 樣品分析
樣品在潔凈室內冷凍干燥(FDS5512型冷凍干燥機, ILSHIN公司)后研磨過60目篩, 采用標準方法測定。Cu、Pb、Zn、Cd和Cr用鹽酸-硝酸-高氯酸消解, 采用電感耦合等離子體質譜(ICP-MS, 美國ThermoFisher X Series Ⅱ 型)測定[13]。Hg和As用濃鹽酸、濃硝酸(3+1)混合溶液水浴消解, 采用原子熒光光譜(9230型AFS, 北京吉天儀器公司)測定[14]。

圖1 采樣位置圖 Fig. 1 Map of sampling sites
1.3 質量控制
聚乙烯袋預先用硝酸溶液(1+2)浸泡2~3 d, 用超純水淋洗干凈、晾干[15]備用。采樣和分析過程中所用采樣器及玻璃器皿均用硝酸溶液浸泡, 并用超純水沖洗干凈后低溫烘干。實驗所用試劑均為優級純, 實驗用水為超純水。分析過程中采用平行樣、密碼樣和標樣監控精密度和準確度, 相對誤差分別小于10%、10%和5%。
1.4 生態風險評價方法
1.4.1 H?kanson潛在生態危害指數法[2]:

式中:Ci是單個重金屬的污染系數;C是表層沉積物重金屬濃度值;Cn為背景值。Ei是重金屬的潛在生態危害系數;Ti是重金屬的毒性響應系數。RI是多種重金屬的潛在生態危害指數。Hg、Cr、Cu、Zn、Pb、Cd和As的Ti值[16]分別為: 40、2、5、1、5、30、10; 為便于同其他海域的研究結果相比較, 本研究仍采用未受污染(即工業化前與現代文明前)沉積物中重金屬含量為背景值[2], 分別為: 0.25、90、50、175、70、1.0和15 mg/kg。Ei、RI與污染程度的關系如表1所示[2]。
1.4.2 沉積物質量基準法(Sediment Quality Guidelines, SQGs)
SQGs的基礎是沉積物的生物效應數據庫(biological effect database for sediments, BEDS), BEDS通過現場研究、毒性測試和平衡分配模型建立沉積物中目標污染物與生物效應的定量關系。SQGs已被證明是評估淡水、港灣和海洋沉積物質量的有用工具, 常用的評價形式為: 當沉積物中某種重金屬的濃度低于效應范圍低值(ERL), 表明生物毒性效應很少發生; 高于效應范圍中值(ERM)時, 表明生物毒性效應將頻繁發生; 如果介于二者之間, 生物毒性效應會偶爾發生[17-19]。

表1 Ei、RI與污染程度的關系 Tab. 1 The potential ecological risk factors (Ei) and potential ecological risk indexes (RI) for different pollution levels
1.4.3 加拿大沉積物質量標準法
本研究采用加拿大魁北克省2006年頒布的沉積物質量標準[20]對表層沉積物的重金屬污染開展評價, 該標準包含5個閾值, 分別為生物毒性影響的罕見效應濃度值(the rare effect level, REL)、臨界效應濃度值(the threshold effect level, TEL)、偶然效應濃度值(the occasional effect level, OEL)、可能效應濃度值(the probable effect level, PEL)和頻繁效應濃度值(the frequent effect level, FEL), 7種重金屬的上述5個閾值見表2。
2 結果與討論
2.1 表層沉積物中重金屬濃度及分布
28個站位分析統計數據詳見表3。灌河口海域表層沉積物不同重金屬濃度由高至低依次為:Zn>Cr>Cu>Pb>As>Cd>Hg。其中Zn和Cd的濃度明顯高于其入海河段, Hg、Cu、Pb和As的濃度略高于入海河段, 但Cr相反在入海河段略高。當污染物通過河流徑流進入河口區域后, 由于水流平面擴散和海水頂托作用, 流速迅速減慢, 大量泥沙迅速沉積, 重金屬被沉積物吸附后也隨之沉積[21], 因此河口海域重金屬等污染物的濃度一般要高于其入海河段。從變異系數看, 灌河口海域Cd的變異系數較大, 說明Cd受外界污染和人為擾動的影響可能性較大。埒子河口海域重金屬Cr的濃度是灌河口海域的3.5倍, 是夏曾祿等[22]1987年調查江蘇沿海濱海土壤背景值的4倍, 其余6種重金屬的濃度都明顯低于灌河口海域及其入海河段。埒子河口海域沿岸目前尚無較大的污染源, 監測數據也表明該海域表層沉積物重金屬污染程度總體低于灌河口海域, 但Cr的污染來源尚需查明。

表3 表層沉積物重金屬的分析統計數據 Tab. 3 Statistical characteristics of heavy metal concentrations in surface sediments from different areas
灌河口海域表層沉積物Hg的濃度變化不大, 分布規律不明顯。Cr等其余六種重金屬的分布特征基本一致, 高濃度值均出現在H07、H05和H04等站位, 并以此為中心向四周逐漸降低。張東生等[23]研究指出, 灌河口門處有沙咀, 根基在口門左岸, 并向西北延伸, 而沙咀形成的重要原因是泥沙自東南向西北的不斷輸運。因此, 重金屬吸附在易沉降的顆粒中排放入海后, 也會受到東南向西北潮流的影響, 在H07、H05和H04等站位沉降較多, 并隨潮流的擴散向四周逐漸降低。其中, Cr和Cd的分布特征如圖2所示。
黃家祥等[10]2005年對灌河口海域表層沉積物重金屬的累積特征進行了研究, 陳斌林等[11]2005年也對連云港近岸海域5種重金屬的污染進行了評價, 陳秀開等[12]2008年對海洲灣近海沉積物6種重金屬的分布特征進行了分析, 結果表明(表4): 2005~2008年間, 灌河口海域表層沉積物重金屬濃度變化不大, 但本次調查重金屬的濃度均有升高, 特別是Hg、Zn和Cd的濃度升高明顯; 與國內其他幾個海域(表4)比較可知, 灌河口海域表層沉積物中Cu和Pb的濃度處于中等水平, 低于長江口、廈門灣和珠江獅子洋等海域, 高于小窯灣、渤海灣、膠州灣、欽州灣等海域。其余五種重金屬的濃度都相對較高: Zn的濃度在表4所列海域中處于最高水平, Hg的濃度僅低于珠江獅子洋海域; Cr、Cd和As的濃度也僅低于約兩個海域, 而高于其余大部分海域的濃度。

圖2 灌河口海域表層沉積物Cr和Cd的濃度分布 Fig. 2 Spatial distributions of Cr and Cd in surface sediments from Guan River Estuary

表4 國內部分海域表層沉積物重金屬含量及海洋沉積物質量標準[24] Tab. 4 Concentrations of heavy metals in surface sediments from different estuaries in China and the standard levels
與夏曾祿等[22]1987年調查的背景值相比較, Hg、Zn、Cu、As等4種重金屬的濃度均上升1倍以上, 其中Hg的富集系數已高達3.44, 說明可能存在新的污染來源。通過綜合比較說明: 2008年以來, 由于灌河沿岸經濟的高速發展, 特別是化工園區的排污, 該海域以Zn、Hg、Cu和As等為主的重金屬污染不斷加重。
2.2 重金屬污染評價
2.2.1 海洋沉積物質量標準評價法
按照江蘇省海域功能區劃, 灌河口和埒子河口海域執行國家《海洋沉積物質量》[24]二類標準(表4)。評價表明: 灌河口海域表層沉積物中Cu、Pb、Hg、Cr和As的濃度均低于二類標準限值, 但Zn和Cd分別在H05和H04超過了二類標準限值, 導致灌河口海域沉積物質量不能滿足標準的要求。埒子河口海域Cr的濃度較高, 9個站位中僅有3個符合二類標準, 最高濃度出現在H16, 劣于三類標準限值, 其余重金屬的濃度均低于二類標準限值, 由于Cr的污染嚴重導致該海域沉積物質量不能滿足標準的要求。
2.2.2 潛在生態危害指數法
重金屬的潛在生態危害系數(Ei)和潛在生態危害指數(RI)的計算結果見表5。所有站位不同重金屬的Ei值均低于40, 表明表層沉積物中的7種重金屬均處于“輕微”生態危害水平。灌河口海域不同重金屬Ei平均值由高至低順序為: Hg>As>Cd>Cu> Pb>Cr>Zn, Hg和As的Ei平均值分別為17.85和11.88, 是該海域的主要潛在生態風險因子。灌河入海河段重金屬Ei值排序與灌河口海域一致, 除Cr的Ei略高于灌河口海域, 其余六種重金屬的Ei均低于灌河口海域。埒子河口海域重金屬Ei值順序為: As >Hg>Cr >Cu>Cd> Pb>Zn。Cr的Ei值明顯高于灌河口海域及其入海河段, 其余六種重金屬均低于灌河口海域及其入海河段。As和Hg的Ei值在埒子河口海域最高, 分別為7.21和5.87, 但均低于灌河口海域。從RI值可知, 兩個海域和入海河段中表層沉積物重金屬均屬于 “輕微”生態危害水平,RI值排序為: 灌河口海域>灌河入海河段>埒子河口海域。

表5 各海域表層沉積物重金屬的Ei和RI值 Tab. 5 Potential ecological risk factors and risk indices of heavy metals in surface sediments from different areas
雖然國內其他典型海域(表5)表層沉積物中重金屬也均處于“輕微”生態危害水平, 但不同的重金屬潛在生態危害系數有所不同。灌河口海域Zn的Ei值明顯高于比較地四個海域, Hg的Ei值也較高, 僅低于珠江獅子洋海域, 生態風險水平相對較高, 其余重金屬的Ei值在不同海域地或高或低, 處于中等風險水平。
2.2.3 沉積物質量基準法
表6列出7種重金屬生態風險評價指標和本次監測評價結果。28個站位中均有不同種類的重金屬的濃度大于ERL, 表明各站位均存在潛在的生物毒性效應。其中灌河口海域: Zn在H05的濃度超過了ERM, 表明該站位Zn的生物毒性效應會頻繁發生; Zn在H04等4個站位、As在全部13個站位、Cu在H07等7個站位、Cr在H07等4個站位以及Cd在H04站位的濃度均介于ERL和ERM之間, 即在不同的站位其相應重金屬的生物毒性效應會偶爾發生; Pb和Hg 在13個站位的濃度均低于ERL, 表明該海域目前以Pb和Hg為主的生物毒性效應很少發生。灌河入海河段: As在全部6個站位、Cr在R02站位的濃度均在ERL和ERM之間, 表明灌河入海河段以As為主的生物毒性效應會偶爾發生; 在R02站位以Cr為主的生物毒性效應會偶爾發生。埒子河口海域: 首先是重金屬Cr, 在H16站位的濃度大于ERM, 表明在H16站位以Cr為主生物毒性效會頻繁發生, 其余8個站位的濃度介于ERL和ERM之間, 其生物毒性效應會偶爾發生; 其次是重金屬As, 除H22外8個站位的濃度介于ERL和ERM之間, 表明埒子河口海域以As為主的生物毒性效會偶爾發生; 另外, Cu在H20站位的生物毒性效應會偶爾發生。
2.2.4 加拿大沉積物質量標準法
根據加拿大沉積物質量標準[20]設定的5個閾值對灌河口等海域表層沉積物中的重金屬污染進行評價, 把7種重金屬中至少有一種是超過低值標準的站位編號列于表7中, 從而將各站位的污染程度區分在各閾值之間。結果表明在灌河口海域, H01等7個站位(54%)的重金屬濃度介于TEL和OEL之間, 即這7個站位所在區域對生物產生不良影響的概率較低; H03等4個站位的重金屬濃度介于OEL和PEL之間, 其中Zn、Cu和As對生物產生不良影響的概率較高。H04和H05則由于Zn的污染較重, 以Zn為主的不良生物效應可能發生甚至頻繁發生, 因此需開展Zn的污染來源調查和底質生態修復研究工作。在灌河入海河段, R01等5個站位(83%)的重金屬濃度介于TEL和OEL之間, 即這5個站位所在區域對生物產生不良影響的概率較低; R06站位As的不良生物影響會偶然發生。在埒子河口海域, 僅H22一個站位的重金屬濃度介于TEL和OEL之間; 其余站位均由于Cr的污染較重, 在不同的站位生物毒性效應會偶然發生、甚至頻繁發生, 說明埒子河口海域需要開展Cr的底質生態修復研究工作。

表6 表層沉積物中重金屬的質量基準評價表 (mg/kg) Tab. 6 Quality assessment guidelines to heavy metals in different sites (mg/kg)

表7 各海域表層沉積物重金屬的污染程度分析 Tab. 7 Analysis of pollution degree of heavy metals in surface sediments of different areas
由4種評價方法可見: 按國家《海洋沉積物質量》[24]二類標準限值, 灌河口海域個別站位Zn和Cd超標, 埒子河口海域Cr約70%的站位超標。但該方法是依據功能區劃而進行的評價, 是為環境管理需求服務的, 功能區劃調整后標準限值隨之改變, 和重金屬的潛在生態危害不是直接相關的。其他三種方法側重對生物的潛在生態危害進行評價。H?kanson生態危害指數法表明, 灌河口海域表層沉積物重金屬總體均處于“輕微”生態危害水平, 但該評價方法得出的結論與選用何種背景值為參考直接相關。加拿大沉積物質量標準法與SQGs法評價結論基本一致, 但略嚴于SQGs法。這是因為加拿大沉積物質量標準法是在SQGs法客觀評價的基礎上, 同時考慮了自然條件、經濟狀況、技術水平、社會發展、生態保護需求等多方面的因素, 進行綜合決策并服務于環境管理的科學評價方法。
3 小結
⑴ 灌河口海域表層沉積物Zn、Cr、Cu、Pb、As、Cd和Hg的平均濃度依次為: 161、70.1、34.4、29.7、17.8、0.32和0.11 mg/kg, 其中Zn和Cd的濃度明顯高于其入海河段, Hg、Cu、Pb和As的濃度略高于入海河段。同國內部分海域相比, Zn的濃度最高、Hg處于較高水平, Cr、Cd等5種重金屬處于中等或中等偏上水平。除Hg外其他重金屬的分布均受到灌河口沙咀的影響, 以H07等站位為高濃度中心向四周逐漸降低。Cd在不同站位濃度的變異系數較大, 表明其受外界污染或人為擾動影響的可能性較大。
⑵與背景值相比, 灌河口海域表層沉積物中Hg、Zn、Cu、As等4種重金屬的濃度均有明顯上升, 特別是Hg的濃度上升較高, 富集系數為3.44, 可能存在新的污染源。綜合分析表明: 2008年以來, 以Hg為主的重金屬濃度持續升高, Zn、Hg、Cu和As等的污染不斷加重。埒子河口海域Cr的濃度明顯高于灌河口海域和江蘇沿海濱海土壤背景值, 需查明污染來源。
⑶ 評價表明: 灌河口海域因Zn和Cd超標, 埒子河口海域因Cr超標, 均不能滿足《海洋沉積物質量》[24]的要求; H?kanson生態危害指數法表明, 灌河口海域表層沉積物重金屬均處于“輕微”生態危害水平,Ei值由高到低為: Hg>As>Cd>Cu>Pb>Cr>Zn; SQGs法表明: 灌河口海域依次以As、Cu、Zn和Cr為主的潛在生物毒性效應會偶爾發生, Zn在H05站位的生物毒性效應會頻繁發生; 加拿大沉積物質量標準法表明: Zn、Cu、As對生物產生不良影響的概率較高, 其中Zn的不良生物效應可能發生甚至頻繁發生。埒子河口海域以Cr為主的潛在生物毒性效應顯著, Cr在不同站位的生物毒性效應會偶然發生、甚至頻繁發生。
⑷ 研究表明灌河口海域需開展Zn、Cu、As、Hg的污染來源調查, 及時減少其源排放, 防止污染事件發生。H05等站位需開展Zn污染的底質生態修復研究工作。埒子河口海域需開展Cr的底質生態修復研究工作。
[1] Livete E A. Geochemical monitoring of atmospheric heavy metal pollution: theory application [J]. Advances in Ecological Research, 1988, 18: 65-177.
[2] 陳靜生, 王忠, 劉玉機. 水體金屬污染潛在危害應用沉積學方法評價[J]. 環境科技, 1989, 9(1): 16-25.
[3] 藍先洪. 中國主要河口沉積物的重金屬地球化學研究[J]. 海洋地質動態, 2004, 20(12): 1-4.
[4] 白有成, 高生泉, 金海燕, 等. 長江口及鄰近海域沉積物重金屬潛在生態風險評價[J]. 海洋學研究, 2011, 29(4): 32-42.
[5] 安立會, 鄭丙輝, 張雷, 等. 渤海灣河口沉積物重金屬污染及潛在生態風險評價[J]. 中國環境科學, 2010, 30(5): 666-670.
[6] 祎劉瑋 , 樓飛, 虞志英. 灌河河口河道沖淤演變及航道自然條件分析[J]. 海岸工程, 2006, 25(9): 14-21.
[7] 陳君, 王義剛, 林祥. 江蘇灌河口海域現代沉積特征研究[J]. 資源調查與環境, 2006, 27(1): 39-45.
[8] 馬洪瑞, 陳聚法, 崔毅, 等. 灌河和射陽河水質狀況分析及主要污染物入海量估算[J]. 漁業科學進展, 2010, 31(3): 92-99.
[9] 張憲軍, 藍先洪, 趙廣濤, 等. 蘇北淺灘表層沉積物中重金屬元素Cd、As、Hg、Se分布及污染評價[J]. 海洋地質動態, 2007, 23(2): 9-13.
[10] 黃家祥, 殷勇. 灌河口潮灘重金屬累積特征及其對環境的意義[J]. 環境保護科學, 2007, 33(6): 35-37.
[11] 陳斌林, 賀心然, 王童遠, 等. 連云港近岸海域表層沉積物中重金屬污染及其潛在生態危害[J]. 海洋環境科學, 2008, 27(3): 246-249.
[12] 陳秀開, 田慧娟, 劉吉堂, 等. 海州灣近海海水、沉積物及貝類體內重金屬的含量和分布特征[J]. 檢驗檢疫學刊, 2009, 19(5): 6-11.
[13] 中華人民共和國水利部. SL 394.2-2007 鉛、鎘、釩、磷等34種元素的測定-電感耦合等離子體質譜法[S]. 北京: 中國水利水電出版社, 2007.
[14] 國家環境保護總局. 水和廢水監測分析方法(第四版)[M]. 北京: 中國環境科學出版社, 2002: 308, 364.
[15]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質量監督檢驗檢疫總局, 中國國家標準化管理委員會. GB 17378.3-2007 海洋監測規范-第3部分: 樣品采集、貯存與運輸[S]. 北京: 中國標準出版社, 2008.
[16] H?kanson L. An ecological risk index for aquatic pollution control - A sedimentological approach [J]. Water Research, 1979, 14(8): 975-1001.
[17] Long E R, MacDonald D D, Smith S L, et al. Incidence of adverse biological effects within ranges of chemical concentrations in marine and estuarine sediments [J].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1995, 19(1): 81-97.
[18] Long E R, Field L J, MacDonald D D. Predicting toxicity in marine sediments with numerical sediment quality guidelines [J]. Environmental Toxicology and Chemistry, 1998, 17(4): 714-727.
[19] MacDonald D D, Carr R S, Calder F D, et al. Development and evaluation of sediment quality guidelines for Florida coastal waters [J]. Ecotoxicology, 1996, 5(4): 253-278.
[20] Environment Canada and Ministere du developpement durable, de I’Environment et des Parcs du Quebec. Criteria for the assessment of sediment quality in Quebec and application frameworks: prevention, dredging and remediation [S]. Quebec: Library and Archives Canada Cataloguing in Publication, 2007: 1-39.
[21] 劉志杰, 李培英, 張曉龍, 等. 黃河三角洲濱海濕地表層沉積物重金屬區域分布及生態風險評價[J]. 環境科學, 2012, 33(4): 1182-1188.
[22] 夏曾祿, 李森照, 李延芳. 土壤元素背景值及其研究方法[M]. 北京: 氣象出版社, 1987: 314.
[23] 張東生, 張長寬. 灌河口沙咀成因分析及治理研究[J]. 河海大學學報, 1993, 21(4): 29-37.
[24]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質量監督檢驗檢疫總局. GB 18668-2002 海洋沉積物質量[S]. 北京: 中國標準出版社, 2002.
[25] 孫欽幫, 王陽, 李德鵬, 等. 大連小窯灣海域表層沉積物重金屬潛在生態風險評價[J]. 海洋環境科學, 2012, 31(3): 333-336.
[26] 張珂, 王朝暉, 馮杰, 等. 膠州灣表層沉積物重金屬分布特征及污染評價[J]. 分析測試學報, 2011, 30(12): 1406-1411.
[27] 李磊, 袁騏, 平先隱, 等. 舟山附近海域表層沉積物中重金屬污染及其潛在生態風險評價[J]. 海洋環境科學, 2011, 30(5): 677-680.
[28] 李慶召, 李國新, 羅專溪, 等. 廈門灣海域表層沉積物重金屬和多環芳烴污染特征及生態風險評價[J]. 環境化學, 2009, 28(6): 869-875.
[29] 張際標, 劉加飛, 張才學, 等. 湛江灣表層沉積物重金屬分布及污染評價[J]. 海洋環境科學, 2012, 31(5): 644-648.
[30] 張漢霞, 盧偉華, 李希國, 等. 珠江口獅子洋海域表層沉積物重金屬污染及其生態風險評價[J]. 環境科學與管理, 2011, 36(6): 156-159.
[31] 黎清華, 萬世明, 李安春, 等. 廣西欽州灣-防城港潮間帶表層沉積物重金屬生態風險評價[J]. 海洋科學進展, 2012, 30(1): 141-154.
[32] 董愛國, 翟世奎, 于增慧, 等. 長江口海域表層沉積物重金屬元素的潛在生態風險評價[J]. 海洋科學, 2010, 34(3): 69-75.
[33] 劉建波, 劉潔, 陳春華, 等. 海口灣東部表層沉積物重金屬污染特征及生態風險評價[J]. 安徽農業科學, 2012, 40(17): 9416-94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