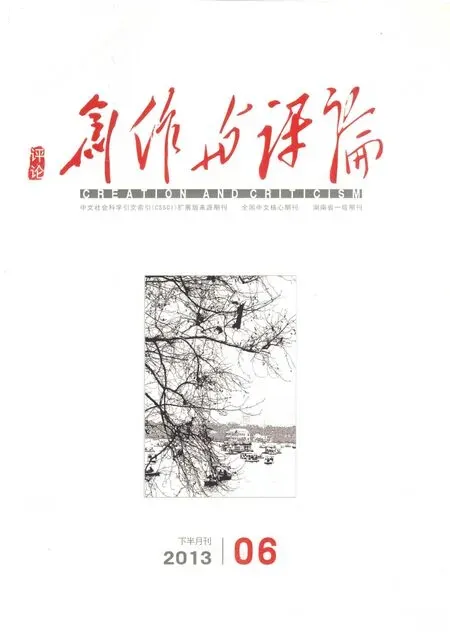歷史『戲說劇』的敘事異變與寓意偏差
○孫麗
電視劇興起之初,歷史劇的創作就占著很大比重。按照歷史劇一直以來的發展模式,演繹帝王將相在時代浮沉中的指點江山和家國情懷,渲染一種莊嚴、權威的背景氛圍,是初期歷史劇創作的普遍追求。20世紀90年代,《戲說乾隆》開啟了“戲說”歷史劇的先河,并在全國范圍內產生了良好的審美接受效應。之后,“戲說劇”就猶如雨后春筍般,紛紛登上了電視大屏幕,迎來了歷史劇的收視熱潮。《宰相劉羅鍋》、《康熙微服私訪記》、《鐵齒銅牙紀曉嵐》、《李衛當官》等等,紅遍全國上下,特別是《還珠格格》更成為“戲說劇”的巔峰之作,造成無人不知“小燕子”的盛大局面。
“戲說劇”之所以被大眾廣泛接受,與它在歷史劇的創作觀念和形式上的大改革有關:歷史知識被娛樂化,人物形象也偏于搞笑與偶像化,滿足大眾的消遣心理成為創作的出發點,這些既成為“戲說劇”受歡迎的主要原因,也是其遭史學家們指責的根源所在。我們既不能單方面地全盤否認這一種戲劇類型的出現,又必須清醒地認識到,“戲說劇”一味的滿足受眾的世俗欲望,對歷史無限度地解構和虛化,在很多方面確有著不良影響。在此文中,筆者將重點討論在消費文化的語境中,“戲說劇”到底存在哪些敘事異變與寓意偏差,而這些變化對于歷史劇的發展和社會的價值觀構建產生了怎樣的影響,力圖對“戲說劇”做出一種較為深入的價值理念探討。
一、消費語境下“戲說劇”的歷史敘事變異
隨著市場體系在國內的進一步健全,西方后現代思潮的涌入,民眾商業觀念的不斷建構,傳統價值觀在社會發展中已經漸行漸遠,取而代之的是消費社會的種種生活方式與價值理念。影視作為消費文化中的一個重頭戲,它的生產觀念與制作方式也不自覺地受到了消費社會的影響。在過去,影視一直被作為一種高雅藝術,知識分子在其中植入他們的社會價值觀以及思想啟蒙性,給受眾以思考和教育。這種對于影視審美性和藝術性的過分推崇,將影視置于一種受人仰視的地位,成為普通大眾不能碰觸的禁忌之所,為精英知識分子所占有。消費時代到來之后,影視從高閣被拉入了日常生活,普通人的酸甜苦辣成為鏡頭關注的焦點,它的娛樂、游戲功能也得到最大限度地放大,而以往一直被推崇的教化功能則被推到了邊緣位置。歷史劇作為影視誕生以來,被廣為詮釋的電視劇種類,在這一時期也發生了變化。新的歷史解讀模式,使歷史劇出現了多種表現題材,“戲說”就是其中頗受爭議的一類型,而其獨特的歷史敘事模式也將其推到了大眾文化研究的熱點位置。新的話語環境,給予歷史闡釋更多的選擇空間,“戲說劇”作為歷史劇史上的一次大變革,呈現出了敘事話語上的諸多異質因素。
1.歷史成為符號化的背景文本
在中國大眾欣賞視野中,歷史厚重感與家國觀念是一個長久不衰的話題。中國人將歷史作為一種映照現實的范本,一個指導現今社會的指南針,以達到“以史為鑒”。歷史被放置在一個權威、神圣的角度被幾千年的文人墨客研讀,它不僅代表著過去,還延續著未來。那些史學名著在時刻敲打著后人,也證明著歷史作為一個源源不斷的藝術源頭,對其的膜拜從未中斷。
但是在不同的文化語境中,歷史是以不同的面貌揭示出來的。傳統的歷史語境中,歷史的真實性與意義深度是最為社會群體看重的問題,挖掘其中深含的“歷史精神”是研究史學的終極目的。中國傳統的歷史劇,也秉承此觀念,保持歷史權威性,對歷史做出本位思考,在最大限度地保持歷史事件與歷史人物原型的基礎上,對其中的意義本質進行提煉,與現實社會形成某種共鳴。但到了消費時代,特別是“戲說”歷史劇的出現,歷史成為了一個被架空的背景文本。感官化的欲望追求,讓歷史成為一個被消費的符號,它本身所代表的時代意義被最大程度地消解,成為一個戲劇空殼。現代式的歷史人物與思維模式在表象化的時代背景中,對觀眾進行著一場脫離歷史的視覺沖擊,歷史與現實的關系越來越模糊。例如目前“戲說劇”中,愛情成為了故事的主線,英雄、才子、佳人盡情地在假象化的歷史表征下,演繹著纏綿悱惻、驚天動地的“歷史故事”。《還珠格格》這部曾經讓萬人空巷的清宮劇,依據的史料竟然是北京西郊一座沒有記載的公主墳,所葬之人是誰,她的生平如何,并不是這部劇要探究的問題,兩個格格與兩位才子間的愛恨情仇成為了戲劇的焦點。清朝的歷史史實被徹底消解,人們追求的是那些情情愛愛之后帶給自己的會心一笑,笑文化代替了史文化。
編劇導演們在歷史的大時空背景下,還加入了一些其他因素,服裝、道具、禮儀與稱呼等成為他們描繪歷史圖景的另一手段。這些表面性的歷史符號,將已經脫離歷史史實的電視劇又哄騙式的帶入了時代語境中,所以我們看到了一群現代思維的歷史人物穿著象征性的古代服飾,演繹著匪夷所思的歷史劇情。而正劇一直棄之不用的稗官野史、民間傳說、神話故事等邊角縫隙的資料,也成為了支撐“戲說劇”內容的基礎,其中的趣味性與娛樂性也被著重強化。這些都成為“歷史的‘大敘事’失效后的補充物”,歷史在這里徹底成為了消費的符號,它的厚重性與啟發性被徹底摒棄。
2.對經典、權威敘事的解構
幾千年來,歷史記錄被作為只有上層文人階級才能碰觸的領域,被視為一項尊貴和神圣的工作。視覺媒體出現后,歷史進入電視劇視野,初期它的權威性與崇高性依然穩固。歷史劇作為弘揚主流價值觀的重要平臺,它擔負著揭示歷史真相,為現實生活提供歷史借鑒的重要責任。精英知識階層是電視劇生成的主要貢獻者,他們充溢著啟蒙的浪漫主義精神和普世的理想主義情懷,這些都無一不附加在歷史劇肩上,所以剝開這些歷史劇的外殼,其中蘊含著豐富的精神性理念與傳統文化精髓。意識形態的建構與借古諷今的現實寓意,使得歷史劇的創作模式有著歷史本身所帶有的厚重、崇高以及權威。
這種權威與經典的敘述模式,將講述歷史的權力緊緊掌握在精英階層手中。精英知識分子的啟蒙立場與烏托邦的激情理想,深深烙印在歷史電視劇創作中,形成高姿態、貴族式的影視說教。這種創作模式造成了此類電視劇類型與普通大眾之間的理解鴻溝,并與他們的觀影趣味形成錯位。“戲說劇”出現后,它們以一種詼諧、風趣、通俗的方式“使宏大、崇高的歷史敘事成為流行的藝術,這恰好彌補了主旋律歷史劇的缺失”①,也昭示著“文學藝術的功能由教化向消遣的轉變”。以往的啟蒙精神、主流價值觀弘揚在這里隱退,得到一種消解與解構,影視藝術從廟堂之上走向大眾生活。歷史上沒有發生的事情,可以隨意被編造和建構;歷史上嚴肅、威嚴的權力與事件,也可以隨意拿來被戲弄、游戲和嘲笑;甚至歷史人物原本的善惡面貌,也會因受眾的口味需要而黑白顛倒。商業化的運作模式使得受眾的歡迎與否成為歷史劇創作的主要依托,娛樂性和瞬時性成為消費語境下歷史劇創作的必然選擇。精英知識分子失去了影視的話語權,嚴肅意識和權威意識也隨之削弱,啟蒙精神和審美主義受到壓制,導演、編劇甚至于受眾群體對于歷史的敬畏之心蕩然無存。
3.面向受眾的價值低位選擇
在消費社會,影視媒體不再作為社會主流價值觀的弘揚者、精英階層話語的傳達者,而將商業價值作為出發點,將受眾作為大眾傳媒過程的重中之重。市場經濟環境下,以往慢節奏的生活氛圍被打破,時代洪流推趕著每個人不斷地向前進發,生活焦慮感和自我缺失感使得人們渴望在閑暇時候能夠放松身心。宏大的歷史敘事,給人思想上沉重的歷史壓迫感和沮喪感,這在消費社會是不被廣泛接受的。而“戲說”這一特殊的歷史劇形式,對歷史進行恣意闡釋,將填充大眾欲望作為首要衡量標準,無疑成為日益激烈的競爭社會中受眾精神的撫慰劑。觀眾的審美期待在“戲說劇”中得到一次完美的展現,歷史的真實內涵被抽空之后,大眾欲望得到大肆揮灑的虛幻空間。
《康熙微服私訪記》中威嚴的皇帝跑到了民間,甚至扮起了叫花子,與平凡女子發生了一幕幕催人淚下的愛情故事,太監、宮女、和尚整天嬉笑怒罵,后宮的妃子為些小事爭風吃醋,整個社會一片和諧安康。俊男靚女間的談情說愛,后宮佳麗間的爭風吃醋,偉人名流們的插科打諢,這些都滿足了受眾暫時的窺探欲望,獲得一種審美快感。虛幻的歷史故事,將受眾從現實痛苦中脫離出來,壓力得到釋放。紅塵社會中的人情淡漠與生存危機,在“戲說劇”中也得到了一次完美的化解:貪官終會得到惡報,明君與清官無處不在,才子佳人歷經磨難也會修成正果。這種種一切,為大眾搭建了一個烏托邦式的理想樂園,救贖式的美好想象鼓勵著人們從疲憊不堪的生活中掙扎出來,繼續前進。
“戲說劇”毫無保留的地將百姓的趣味作為立足點,將對本我欲望的推崇推向極致,表現出了一種“‘低位原則’”。它著力“建構一種基于社會底線原則的審美境界,一次迎合教育水平和精神期待較低的社會群落的需求”②,讓大眾無需太多的知識與思考就與電視劇實現一種共鳴。這種創作理念,不將人類幾千年的歷史價值經驗作為價值主體,影視的文化教育功能和審美功能也最大程度地被弱化,出現了一種“反智主義”傾向。
二、消費語境下“戲說劇”的文化寓意偏差
消費語境下,“戲說劇”的思想啟蒙性和歷史精神追溯感退化,更多地轉為對大眾消費需求的滿足。但另一方面,影視劇與現實政治天然地存在著一種互動、互釋關系,即便是“戲說”這樣的游戲成分較多之作,也不可避免地與社會現實發生著種種寓意糾葛。市場體制開始至今,因為其不可避免的不完善性,在政治、經濟、思想文化領域出現了種種不良現象,受眾在現實碰壁之后,期望視覺媒體能提供一個平臺,抒發個體不快,對問題有所映射和批判。“戲說劇”以其獨特的影視藝術制作,調動各方面的大眾文化策略如清官斷案、明君盛世、宮闈秘史、借古諷今等等,緊緊抓住受眾心理,盡可能多得創造欲望消費符碼。與傳統正劇重點關注那些深的內涵不同,“戲說劇”注重商業利益的出發點,使得它的意識形態傳達試圖在利潤與內涵間找到一個平衡點,迎合受眾心理召喚。從這一方面來說,“戲說劇”因其的審美不純粹性和商業屈從性,在諸多問題上出現了偏離原始意圖的意義悖論,讓作品處在一個尷尬的話語沖突位置。作為當前影響甚大的大眾傳播媒介,對“戲說劇”的寓意分析很有必要。
1.盛世景觀圖寫
無論是《還珠格格》 《神醫喜來樂》,還是《宰相劉羅鍋》 《康熙微服私訪記》等,我們發現,“戲說劇”都將故事背景設置在康乾盛世或其他的歷史輝煌時期,故事人物也多是歷代的明君圣主、清官能吏,并集各種智慧才能、才子氣質和正直品格于一身。他們不僅滿腹抱負、英勇智謀、深藏不露,與貪官污吏斗智斗勇,用權術將其玩弄于股掌之間,在日常生活中,也是幽默風趣、談吐不凡、正直善良,還有不少情愛故事。《康熙微服私訪記》中,高高在上的皇帝,為國為民,私訪民間。他所到之處,首先呈現在我們眼前的是一片繁華景象,即使越深入調查,發現了地方惡霸,殘害百姓,搜刮民脂民膏,但作品著重反映的還是明君懲治貪官,清官得到重用,惡人得到惡報的盛世情懷。《宰相劉羅鍋》講述的是一位正直多謀的清官與和珅這個臭名昭著的貪官之間的斗智斗勇,劉墉不懼和珅在朝中的權勢地位,力挽當時世風日下的局面,而作品也表現了對此種品格的高度認同和贊揚。雖然和珅深得乾隆皇帝寵幸,而他的黨羽也遍及全朝,但劉墉并不依附權貴,而是始終堅持著振興朝綱、憂國憂民的治世情懷,在變幻莫測的時代氛圍中激流勇進。總體來說,“戲說劇”中的時代氛圍清明有序,百姓幸福安康,官吏清廉為民,一派祥和之氣。
除了這些盛世人物的極力渲染之外,劇中還出現了諸多儀式性的盛世場景描寫,這在當前爆火的一系列清朝歷史劇中屢見不鮮。繁華的街市常常是人物活動的主要場所,街旁熙熙攘攘的人群、叫賣的小販、滿目琳瑯的商品和此起彼伏的討價聲,都給我們描寫出了一幅盛世商業圖。而各種民間節日活動和五彩斑斕的彩燈裝飾,也給予民俗文化一個狂歡的舞臺。這些儀式性的表象表演,讓民眾在繁重、無聊的日常生活之外獲得一個釋放不良情緒的空間,帶給身心極大的快樂與滿足,激發起他們對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對目前不滿生活的寬容。
但是盛世圖景的描寫,并沒有達到視覺媒體對于受眾的“盛世”精神傳達與教化,甚至很難說創作者對于盛世內涵有一個深入的思考。“廟會上的演出,是一種對于古人古事的想象性模仿,你也很難斷言它的禮儀、制度、服飾和歷史上的真實沒有一絲半點聯系,但它的目的就是娛樂和狂歡,把時間空間化,而不是喚起觀眾強烈的歷史感受和悲劇意識。”③而劇作家簡單地將大眾對于盛世的幾個特征定義——“國家統一、經濟繁榮、政治穩定、國力強大、文化昌盛”(清史專家戴逸)套在了“戲說劇”上,對于歷史真實境況并沒有進行深入調查研究。當受眾在哄騙性的繁榮情景中清醒過來的時候,會疑惑自己剛剛進入的究竟是一個古代盛世,還是一個當下盛世。大眾文化對于商業經濟毫無顧忌的屈從,導致“戲說劇”在現代國家精神構建和盛世國家想象時,無思考、無責任地簡單將傳統的盛世特征映射在電視劇上,沒有與現實政治生活形成對話,對大眾造成一定的誤導。這種表象與內容的脫節,讓作品的創作意圖與實際傳播效果間出現縫隙,也讓“戲說劇”本身帶有的文化寓意經不起細細推敲而走向變異。
2.帝王形象塑造背后的權力外延
1990年代初,《戲說乾隆》的出現,讓觀眾眼前一亮,不同于以往歷史劇中的帝王形象塑造,劇中的乾隆幽默風趣、風流倜儻,與太監、宮女玩笑嬉戲,毫無威嚴之氣。游訪江南時,與民間女子產生了刻骨銘心的愛情,并卷入了江湖爭斗中,大展皇帝的武打功夫。對比歷史正劇,皇帝皆是高高在上,附著在其身上的沒有“任何倫理褒義色彩,它們只有階級身份,而沒有倫理身份”④,“戲說劇”中將世俗的人情世故給予帝王,讓其與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產生聯系。《還珠格格》中乾隆皇帝也是如此,他是父亦是子,對潑辣冒失的小燕子和身份不被認同的紫薇極盡寬容與照顧,而面對自己的母親對兩位格格的不喜歡,他也盡力從中周旋。身體表演上,皇帝的面部神情更加多樣化,不再不茍言笑,快樂或憤怒皆表于色。這種對帝王形象的重塑,讓我們在好君主的形象背后,還看到了其另一層人性光輝,即“好父親、好丈夫、好兒子”,這滿足了受眾對于皇家生活的窺探心理和對好領袖的政治期盼。
明君圣主的設置,本意是劇作家通過救世主形象的塑造,深化偉人開創盛世、挽救時代危局的傳統歷史觀,迎合主流意識形態,為民眾搭建一個英雄偉業的理想樂園。但是,倫理復歸的背后,僅是電視劇編造的一場幻景,滿足了普通大眾一直以來的英雄崇拜心理,給予受眾一種心理救贖,甚至于到最后,觀眾深深地沉浸其中,把自己想象成那個英雄,而一場戰斗的勝利恰恰也成為了自身的一次成功。但是不能忽視的是,這種英雄崇拜和政治期待的背面,隱藏的卻是創作者意圖抹殺的權力外延。《鐵齒銅牙紀曉嵐》中,乾隆、紀曉嵐與和珅之間雖然組成了“鐵三角”,乾隆對于和珅和紀曉嵐之間的爭斗表面上采取的是睜一只眼閉一只眼的態度,整天嘻嘻哈哈,但是皇帝才是最終清醒的裁判者,和紀二人都必須爭取皇帝的支持,才能取得最后的勝利。《還珠格格》中,無論小燕子多么目無倫理綱常,無視皇家規矩,她最終的婚姻幸福與生死大權仍是牢牢地掌握在乾隆手中。《康熙微服私訪記》中,每到劇情最后,皇帝亮出身份,而貪官嚇得目瞪口呆、以身伏法時,最終借助的還是至高無上的皇權,是權力與權力間的制衡,受眾從中也得到了一種快感。所以一切問題的解決根源仍然依賴明君圣主的權力,在這里我們看到的不是對于封建皇權的某種反思,而是某種好感,強化了大眾對于皇權的某種信任和對人治體制的向往。所以,“戲說劇”對于經典敘事和皇帝形象的解構,因為其對于社會問題簡單的價值思考和利益驅動心理,并沒有出現預期的現實對應與倫理教化寓意,而是表現出了某種價值偏失與寓意偏差。在其制造的假象背后,是對于權力的推崇和對封建皇權的某種認同。
總之,1990年代風行的“戲說劇”,在一方面為歷史劇的創作模式提供了新鮮血液,打破了歷史劇長久以來編寫的固化模式,消除了人們對于權威和經典的畏懼心理。在現代化的商業社會中,對于一切的質疑和創新無疑是有某些益處的。另一方面,“戲說劇”將歷史話語權從精英知識分子手中轉到大眾手里,使得受眾與歷史有了一次平等對話,這也是時代發展的必然趨勢。但是,我們仍然無法忽視“戲說劇”在其消費主義的指導思想下,自身精神價值含量輕薄的現狀,特別是它對于歷史事實的不莊重態度,在影視屏幕上編造了大量的偽命題歷史事件,這對于民族集體的歷史知識普及是十分不利的。對于青少年群體來說更是如此,傳統的歷史價值觀還沒有在腦中形成體系,“戲說劇”展示的歷史圖景在時間上有先入為主的優勢,會讓他們想當然地認為這是真實的歷史。所以視覺文化的泛濫,對于我們中華民族幾千年來的歷史文明和精神內質的傳承,有著十分強大的沖擊力量。“戲說劇”在一味追求商業利益的同時,也應不斷建構起適應全局的倫理價值體系,將精神文化與商業文化合理融合,以適應當下對于歷史劇的更高要求。
注釋:
①南帆:《消費歷史》,《當代作家評論》2001年第2期。
②鄭春鳳:《欲望化時代的文化消費》,《文藝廣角》2005年第5期。
③劉起林:《“戲說歷史”的敘事偏差》,《人民日報》2001年7月28日。
④王昕:《電視戲說劇的戲仿策略與反諷意向》,《當代電影》2006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