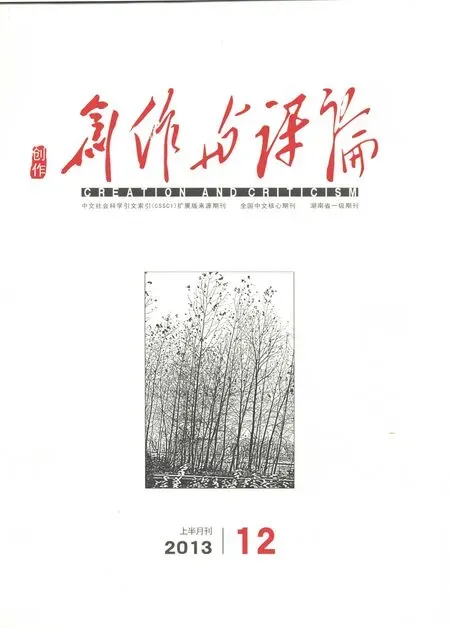理性的選擇與思想的穿越——評譚仲池《東方的太陽》
○ 夏義生
用6000行長詩獻給中國共產黨九十華誕,這就是一個年逾六旬而又滿懷青春激情的共產黨員的理性選擇與浪漫情懷。
《東方的太陽》的寫作,是詩人理性的選擇。詩人在《后記》中引用勃朗寧夫人著名的十四行詩《我是怎樣的愛你》,深情地表達了一個共產黨員對黨的“無限理性和圣潔誠實的至愛”。這種深沉的摯愛,就是詩人譚仲池歷時近一年,三易其稿,完成這部長詩的原動力。作為黨的一名高級領導干部,回首人生道路上的鮮花和荊棘,他深知自己離不開陽光的照耀,他把中國共產黨比作“東方的太陽”、“東方的圣母”,深情地歌唱。他說,“我感謝共產黨,感謝祖國,感謝父母,感謝人民,感謝陽光、空氣……”這種感恩之心,是圣潔至誠的,它構成了詩歌的基調。或許,6000行的長詩還有不完美之處,但自始至終貫穿全詩的詩人的真誠和深情,則是詩歌的藝術魅力之所在。詩人清晰地意識到,“寫這部長詩,或許會有人誤解,這一定是一部充滿溢美之詞的淺薄,充滿概念說教的呆滯,充滿空泛虛脫的蒼白的政治詩歌。”然而,我們從作品中看到,詩人以豐富的藝術經驗和充沛的才情,圓熟地處理了政治概念與藝術形象的沖突。為什么詩人意識到了政治抒情詩的難度而又要迎難而上呢?我們只能說是理性的力量,理性讓他選擇用詩歌去歌吟“東方的太陽”,因為詩人對“東方的圣母”的愛,是用整個心靈和生命,乃至永遠的靈魂眷戀。
《東方的太陽》充滿了思想的力量。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是中國當代政治抒情詩繁盛的時期。賀敬之的《放聲歌唱》、《雷鋒之歌》,郭小川的《致青年公民》、《林區三唱》,還有阮章競、張志民、聞捷、李瑛等都創作過名重一時的政治抒情詩。政治抒情詩往往以其現實性品格和與主流意識形態共鳴的價值追求獲得藝術張力。湖湘文學浪漫主義傳統的先驅之作《離騷》就是一部憂國憂民、抒發詩人屈原政治理想的經典。湖湘文學現實主義傳統的大師柳宗元就是在參與政治改革失敗之后,將政治理想融入文學創作,敘寫底層社會的生活境況,直陳民生之艱難,其“苛政猛于虎”振聾發聵。我國新時期文學自從“躲避崇高”、“零度寫作”之后,文學的思想性漸弱,文學創作難見對社會、人生、人類命運的思考和價值判斷。文學除了給人消遣、休閑,難以給人類和諧發展賦予精神上的力量。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當下文學面對現實的失語,很重要的一個問題就是思想判斷力的問題,是作家精神資源貧乏的問題,是作品思想力貧困的問題。《東方的太陽》在描繪歲月中那些花瓣時,處處閃爍思想的光芒。詩中的“大我”融入了“小我”,在“宏大格局”中可見作者的個性,在“認識歷史”中可見作者的思考。作者以理性節制感性,用思考深化抒情,以使抒情不流于空疏化、淺表化、概念化、口號化。在《東方的太陽》中,我們讀到的不只是黨史、政史、民族史,我們還讀到了作者個人的心靈史。作者對許多歷史人物和政治事件,都有自己獨到的看法和見解,給人無盡的啟迪和遐思。《東方的太陽》是唱給中國共產黨的頌歌,也是謳歌中華民族的史詩。詩人以五千年中華民族文化為基點,從鴉片戰爭以來喪權辱國的歷史中尋找中國共產黨屹立于世界東方的歷史邏輯。詩人用時間這條經線將一個個歷史人物,一個個重大歷史事件串聯起來,將中國共產黨九十年的坎坷歷程,放在世界文明的大格局中來敘述。同時,在敘述歷史中反思歷史,從全球化背景下社會發展的規律來分析中國共產黨的歷史命運。《東方的太陽》在抒寫那些影響中國近現代歷史的巨人時,蘊含了詩人自己對歷史人物的道德評判和歷史評價,在這些獨具慧眼的歷史選擇和判斷中,闡明了歷史的命運、國家的命運、政黨的命運、個人的命運,“是如此的緊密,又是如此的曲折顛簸;是如此的蒼涼,又是如此的波瀾壯闊”。誠如熊召政先生所言,“一位成熟的詩人,往往從感情出發,收獲的卻是思想的光芒。通讀長詩,我感到仲池并不是在唱廉價的頌歌,而是讓自己走進一代又一代東方赤子的心靈,同他們一起拷問、鞭撻、思索與奮進”。
《東方的太陽》不是哲理詩,它是在“愛”和“感恩”的驅動下,愛黨、愛國家、愛民族、愛人民,尤其是愛中華文化;感恩黨……感恩自然和空氣,一切的一切,詩人真情的奔涌,激情的飛翔;它是真情和大愛的抒發,是藝術和政治的融合,是歷史與現在的交流,是心靈與時代的交響,是主體與文化的碰撞,是理想與現實的對話。《東方的太陽》充滿激情,是詩人內心熾烈情感的最直接充分的抒發。作品中反復渲染、鋪陳的句式,形成了簡單、明快、強勁的美學特征。需要指出的是,《東方的太陽》與上世紀五十年代政治抒情詩的一個重要區別,是抒情主體的變化。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政治抒情詩,詩人往往是某一階級、集團的代言人,排斥抒情主體的個人情感與經驗;而在《東方的太陽》中,自始至終貫穿了詩人的個人情感與經驗,如長詩中,面對遵義會議、面對延安、面對胡耀邦,詩人就在詩歌的“現場”。從這個意義上說,《東方的太陽》是一部充滿了作家個體人生經驗和情感的史詩,它反映了作家的理性選擇和思想的睿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