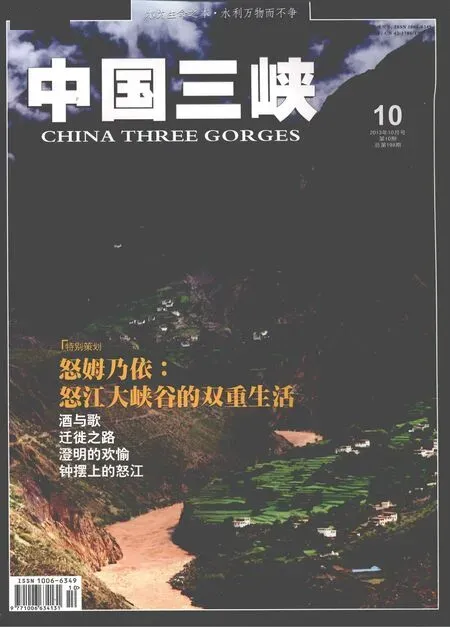酒與歌
圖、文/周 偉 編輯/任 紅
我被貴客般地讓到了一張既短又矮的板凳上,人未坐定,一杯清澈的水酒已經(jīng)遞到我的面前。
在我的周圍是一群皮膚黝黑、穿著雜亂、不修邊幅的男女,唯有對面的一位中年女子與眾不同——她神色傲然地坐在一把老藤椅上,嘴上叼著根一尺長的煙斗,不時吞云吐霧,再把煙嘴在藤椅上敲打敲打,以除卻灰燼,然后抬頭用一種和善的眼神望著我,她的一系列動作中,兩邊耳垂上掛著的銀飾發(fā)出輕微而清脆的聲響。她戴著一頂青灰色的舊布帽,上身紅黑搭配的褂子繡著花邊,模樣與神態(tài)宛然一個山寨里的女大王,莊重中透著些許威嚴(yán)。
這酒看著清澈,但并不十分醇香,端起來就有一股酒糟和玉米的混合味道沖將過來。一口下去,濃烈而溷濁的氣息從口腔剎那間盈滿胸腔直到腹腔。“哦!一拉咻(一口干)——”人群見我一口干盡了他們遞來的第一杯酒,出現(xiàn)愉快而興奮的騷動。“女大王”又給我滿上,身旁的一位中年男子立刻舉著杯笑盈盈地示意要敬我的酒。這時有人嚷道:“喝個同心酒嘛!”我于是被中年男子拉起身,還沒有弄明原委他就一手摟起我的肩膀,把他的臉緊貼著我的臉,另一只手舉著酒杯貼上我倆的嘴唇,慢慢倒下,酒一半進(jìn)了嘴,還有一半則在眾人的推搡中潑在身上。杯中酒盡,人群再次發(fā)出歡快愜意的笑聲。

站在田頭休憩的農(nóng)婦。云南怒江,知洛。2006年4月。
這是云南省怒江州府六庫最熱鬧繁華的地方——向陽橋頭的一個平常的傍晚,是時,我剛剛放下行李迫切地期望在天色暗淡前看一眼已經(jīng)在腦海里翻滾了許久的怒江。我打開隨身的水壺,里面是我從大理帶來的“木瓜酒”,醬紅色的甜酒倒?jié)M了兩個塑料杯,杯子便在人群中傳遞著,人群中洋溢著一片贊美。我則開始和他們聊天,以解開我的疑惑。原來,他們并非閑來無事僅僅在這里喝酒取樂,他們中的幾個是常年在這橋頭擺攤做小買賣的傈僳人,包括那位“女大王”。他們大都是賣酒的——一種用大峽谷中的傳統(tǒng)主食玉米,拌和酒曲發(fā)酵后再經(jīng)蒸餾而得的白酒,怒江人稱之為“杵酒”。傍晚時分,相互熟識的傈僳人便圍攏在這里,賣酒的人也不吝嗇,倒出一杯,讓人隨意去喝,每人喝了一口便自覺傳給下一個,杯就在人群中傳遞著,直到空了,或許另一個賣家會慷慨地再次滿上,然后繼續(xù)……就在這杯酒傳遞當(dāng)中,“女大王”突然從瘦小的胸膛中迸發(fā)出一嗓深沉有力的歌聲:

課間休息的一群小學(xué)生和一個下地干活的男子。云南怒江,知洛。2006年4月。
“依——依賽尼在此谷涅——
霜多忙代付啊,朵——
……”
在“朵——”低低的長音仍然延續(xù)的那一刻,另一個渾厚的男聲突然跳躍八度以鏗鏘的“依——”接續(xù)上來,就這樣一層層不停被延續(xù)與唱和,歌聲忽而低沉委婉,忽而高亢豪邁,跌宕起伏并且?guī)е鴱?qiáng)烈卻不恣肆的顫音,令我的心緊緊跟隨。不需要弄明白那些唱詞,我便依著歌聲在心中展開一幅大峽谷的畫面——時而在谷底,時而在山巔,那長長的低詠就是近在咫尺的怒江之水綿延不絕,那嘹亮的高音猶如雪山背后太陽噴薄而出……曲式具有強(qiáng)烈的敘事性,彷佛一群飽經(jīng)滄桑的老人在垂暮之年向孩子們敘述發(fā)生在大峽谷中的古老故事,那些久遠(yuǎn)的,悲壯的,又是庸常綿延的生活在這豐滿的人聲中如高山峽谷中的涓涓細(xì)流,從容而清澈地流淌,直到匯入蜿蜒起伏的大江,繼而發(fā)出雷鳴般的咆哮。人群在歌聲的激發(fā)下情緒越來越激昂,有幾位男女已經(jīng)情不自禁地站起身來隨著歌聲擺動身體,沉重的跺腳舞步很快成為歌者和諧的伴奏。一位老者顯然已經(jīng)半醉半醒,一邊大幅度地擺動,一邊硬是要拉我起來和他一起舞蹈,就在我猶豫之間,“女大王”站起身用煙斗狠狠地在老人身上敲了幾下,喝叱了一番,然后用生硬的漢語對我說:“他喝醉嘍!”醉酒的老人并不生氣,踉踉蹌蹌退了幾步,便繼續(xù)陶醉于自己的歌聲和舞蹈。這時,峽谷里天色漸暗,沉下高黎貢山的落日發(fā)出最后的余輝,將天空染成鮮艷的紅色,閉上眼睛,這峽谷里彷佛流淌的不是滔滔江水,而只有歌聲……
這場面一下子讓我感受到這個大峽谷的與眾不同,美國作曲家費爾迪·格羅菲(Ferde Grofe)那部氣勢宏大的《大峽谷組曲》在我的心中頓然失色——格羅菲對于大自然極盡所能的描摹和渲染,終究不能超越人類以自己的身體,以千年歷史的積淀而演繹出的樸拙之聲——人的存在,正是科羅拉多與怒江的本質(zhì)區(qū)別,大自然的雄奇與瑰麗終究只是一個巨大的背景。
這便是我在四年以前第一次走進(jìn)怒江,大峽谷為我拉開的序幕。
終于夜幕降臨,人群在歌聲中漸漸散去。我走上向陽橋,這座建于1970年的柔性吊橋和下游不遠(yuǎn)新建的單孔拱橋相比,顯得瘦弱而蒼老。站在橋上,只要一有行人走過,整個橋體就會隨之顫動甚至搖晃。7月的夜晚,峽谷一掃白天烈日下的躁熱,伴隨著江上的水汽,顯得異常清涼。兩岸陡峭的山坡上星星點點的燈光,恍恍惚惚,但這個城市異常狹小,視野的盡頭就完全是黑魆魆的一片,唯有隱約的V形山谷中回蕩著低沉而有力的濤聲。

采柿子。云南怒江,古當(dāng)。2006年12月。
遙望北方,我腦海中清晰可見唐古拉山南麓吉熱格帕峰的腳下,冰雪融化的水滴的相互簇?fù)碇察o地在野草間團(tuán)聚,交融成怒江最初模樣。怒江從一開始就彰顯了它的神秘和獨特——藏族人稱它為“那曲”,意為“黑色的河流”。這條江,夏若洪濤,冬如碧水,站在任何一個點是難以勾勒它宏大旅程的——它在橫斷山脈中突然一個拐彎,撞擊出這個逼窄的峽谷,如刀刻一般,它真的發(fā)“怒”了嗎?否則什么人有如此豐富的想象力將這條大河冠之以“怒”?在西藏八宿、左貢縣向南拐彎的地方海拔都在3000米左右,而抵達(dá)我此刻站立的六庫時,海拔只有820米,落差達(dá)到2000多米。峽谷云南段的300多公里,谷底至兩側(cè)的碧羅雪山、高黎貢山山脊的垂直高差也在3000米左右……此刻,一個由數(shù)字和想象建立起來的峽谷已然呈現(xiàn)在眼前,而傈僳人的酒歌幫我厘清了思緒——我清晰地記得,當(dāng)我正沉迷于傈僳人的歌舞時,圍觀的一位東北商人坐到我的身旁,他善意地提醒我:“離他們遠(yuǎn)一點好,他們出門都帶著砍刀,很危險的!”我當(dāng)時故作驚訝。其實,在我的內(nèi)心里面,已經(jīng)有了自己的答案,從最初所接觸的這些傈僳人的眼神中,從他們的酒歌里,我深深地體會到他們心靈柔軟的質(zhì)感——當(dāng)你用自己的靈魂去觸摸,你能感覺到它粗糙卻柔順,它怦然跳躍卻不恣肆張揚,你甚至能感受到某種舒適的溫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