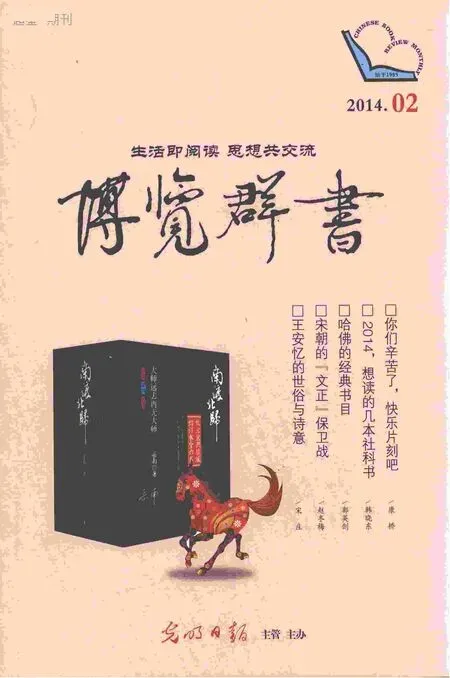斑斕多姿的藝術世界
○曾紀鑫

《落地·沈虹光散文集》,沈虹光著,中國文聯出版社2012年9月版,46.00元。
喜歡讀沈虹光的藝術隨筆。
近年來,在《劇本》、《中國戲劇》、《藝術》等雜志斷斷續續地讀過不少。她所寫的那些人與事,多與湖北文藝界特別是戲劇界有關,我曾以一名編劇的身份,在這個“圈”內呆了十多年,每每讀來,自有一種難得的親切。總希望她能多寫點,多發點,我就可以多看一些,也好沾點靈氣,受點啟發。因此,當我收到她寄贈的散文集《落地》時,心中的欣喜之情可想而知。一冊在手,八十多篇散文隨筆,沈老師近些年創作的新篇舊章,盡收其中。于是,撇開其他俗務,好幾天沉浸于《落地》之中。
一
沈虹光筆下所述,涉及的人與事可謂多矣,有日本戲劇界的同道,有非洲友人,有京城藝術家,更多的則與湖北文藝界相關,從省城武漢到全省各市、縣、鎮乃至僻遠的鄉村藝人;時間跨度拉得也長,長得多達半個多世紀;這些文藝界林林總總的人與事匯在一起,構成了一個五彩繽紛、斑斕多姿的藝術世界。
當然,這個藝術世界是獨特的,有著濃厚的“沈氏風格”。有的篇章是寫自己,更多的則是寫他人,文中不論“主角”,還是“配角”乃至“道具”,作者是其“中介”與“橋梁”,她以自己的親身經歷,將紛繁的人事變遷串在一起,將藝術的時代風云匯于筆端。
沈虹光一生與戲劇、與藝術打交道,透過《感謝戲劇》、《東四八條52號》、《西藏四則》、《搞運動》等篇章,我們看到的,分明是她的一部個人成長史。從一個少不更事的年輕演員到著名編劇、省文化廳副廳長、省文聯主席,一步步走來,委實不易。除了個人天分,更多的是艱辛努力與不懈追求。同時,也是她心路歷程的敘述與袒呈。她是一個典型的性情中人,遇悲則哭,逢喜則笑,內心坦蕩,毫不掩飾。真正的藝術家都葆有一顆童心,都是純粹、本真之人。這,也許正是沈虹光能創作出大量雅俗共賞、傳之久遠的優秀戲劇作品的內在原因之所在吧!
沈虹光敘人寫事,從“我”的視角,以一種平視的目光,不拔高,不委過,娓娓道來,親切真實,平實質樸,體現出一種難得的人文情懷。比如她的話劇《同船過渡》,素材即源于自己一段“團結戶”的經歷。但在現實生活中,她與另一位“團結戶”之間的矛盾,本是幾十年的老同事,直至他去世,也沒能和解。她分析解剖自己的“小”:心中好多次都想和解,并打好了“腹稿”,卻總是“臉皮薄”,礙于面子沒能付諸行動。
沈虹光不僅是一位著名編劇,還是一位優秀的小說家,出版過短篇小說選集《美人兒》。難能可貴的是,她在散文創作時,將戲劇、小說的技巧與元素充分融入其中,縱橫捭闔,游刃有余。于是,這些藝術散文,不僅有人物的刻畫,還有情節的推進、心理的細膩描寫,有的篇章還設置懸念,引導著讀者欲罷不能,迫不及待地往下讀。而每一篇的篇幅都不怎么長,讀著讀著就沒了,心頭不禁生出一種“埋怨”,怎就不多寫一點寫長一些呢?其實,這便是作者深諳創作之道的一種體現,文章不能寫滿,要留下一定的空間,像繪畫那樣講究“留白”,給讀者以回味、思索的余地。對“沈氏風格”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于是,我便慢慢地讀,細細地品,哪怕那些以前看過的熟悉篇章,再讀一遍,又有一番新的感受。作者對藝術的獨特見解,常于短短的幾句話中,就道出其內在而深刻的本質。比如在《不夠滑稽的滑稽戲》中,她對劇本的理解,便深得我心:“有人說劇本的生命在舞臺,可我眼中的好劇本是有獨立的生命的,無需舞臺搬演,泡杯茶蜷在沙發上閱讀就能給人以快感。我相信劇本存在的獨立性。”
品讀中,我對沈虹光的語言藝術,尤為欣賞。沒有那種歐化的轉彎抹角,既豐富凝練,又生動傳神,深諳傳統文字之精髓。比如在《散水聽歌》中寫山鄉聽歌:“當第一個‘鄰居’驀地開口幫腔時,大家都很意外,剛轉眼瞥他,又一‘鄰居’也發出聲音。再后來就像魚兒翻塘一個個地往上躥,‘鄰居’們都跟了上來,爭先恐后似的,有的唱襯詞,有的唱副歌,有的單唱,有的齊吼,都是那種不管不顧一飛沖天的邊音,房子都抬起來了,讓我們知道了什么叫聲震屋瓦。”還如《通向那船的路》中關于書的描寫:“我還擁有了一間書房,我的書們終于也從捆扎中解脫出來,恢復了尊嚴,傲岸地、揚眉吐氣地屹立在書架上了。”再如《感謝戲劇》中對湖北人性格的勾勒:“湖北人偏好沖突,華山一條路,南北兩隊兵,冤家對頭舊恨新仇,唇槍舌劍針尖麥芒,君子動口也動手,猶如一匹激烈奔騰的駿馬,容不得散散漫漫地鋪敘,溫溫吞吞地婉曲。”
就沈虹光亦官亦民的身份而言,我更為看重的,是編劇這一“頭銜”,也就僅以“老師”相稱。毋庸諱言,那為世俗所認可的官員身份——湖北省文化廳副廳長,為這本書許多篇章的創作,其實帶來了不少便利。因職務的重要與工作的需要,便于實地考察,接觸各個不同層面的藝術人才,可以掌握許多鮮為人知的素材。沈虹光因從政而“占有”的資源,是為藝術所用——她這輩子,可謂“徹頭徹尾”地獻給了藝術。
她與導演、演員、作曲家打交道,跟他們交朋友;她深入城鎮、鄉村,前往羅田、麻城、潛江、云夢、遠安、陽新、宜城、來鳳等全省各地進行藝術指導、田野調查;她熟悉不同的劇種、曲調及變腔……她掌握了大量豐富生動的一手材料,可寫的東西實在是太多太多了,但又不得不有所選擇,有所取舍。她從大處著眼,小處著墨:她筆下出現的人物與事件,其實都有著一定的代表性與典型性,而涉及面之廣,幾乎囊括了湖北省的所有戲劇劇種,除京劇與話劇外,還有花鼓戲、楚劇、黃梅戲、采茶戲、漢劇、山二黃、提琴戲、打鑼腔等地方戲曲。毫不夸張地說,散文集《落地》幾乎構成了一部別致的湖北戲劇史。當然,這是一部個人視野里的戲劇史,既有精到簡要的理論勾勒,更多的則是鮮活生動的具體描述。她為這些民間戲劇,正在消逝或風光不再的非物質文化遺產,留下了一份珍貴的記憶與見證。人們將戲劇稱為“夕陽藝術”,太陽西下,透著一股蒼涼與無奈。但是,沈虹光唱出的并非挽歌,我們從她對戲劇的虔誠,對藝術前輩的尊重,對同輩的支持,對晚生的鼓勵中,看到的是盎然的激情、向上的動力與振興的希望。
二
沈虹光認為:“一個劇種不論大小,總有一個或幾個代表性人物,影響大的如豫劇的常香玉、漢劇的陳伯華、黃梅戲的嚴鳳英,聲名遠播越過了本鄉地界,幾乎成為地域的標志。”她還認為,演員就是一個劇種的旗幟,“旗幟所達到的高度就是劇種的高度。”因此,她的筆下,出現了不少追求執著、藝術高超的演員,如荊州花鼓戲的陳新中、何干青,楚劇的李雅樵、劉青珍,漢劇的彩萍、李順娥,話劇的肖惠芳,黃梅戲的張輝,麻城東路花鼓的美玲,京劇的唐愷,竹溪山二黃的周毓成等。
劇種之間的最大區別,便是聲腔。因此,沈虹光常著墨于聲腔的描寫,對荊州花鼓戲作曲家楊禮福贊賞有加,認為“他是花鼓戲的寶”。楊禮福設計了100多出荊州花鼓戲創作唱腔音樂,有幾十臺都是保留劇目。這些花鼓腔,“每一個起伏婉轉都是依著方言的韻律,該上的上,該下的下,自自然然就變成了章程旋律,變成了悅耳動聽的音樂。你不禁會贊嘆語言與音樂之間神秘的關系,就像芭蕾在冰上滑出的繁復花樣,那運行的流暢而美妙,看起來真是莫大的享受。”
在《遠安花鼓的小日子》里,皮影調的精彩表演者是兩位60多歲的普通村民。在歇坐時,沈虹光問及他們的生計,沒想到這兩位姓呂的兄弟是根雕大戶,“產品出售動輒逾萬,唱皮影不圖生計,就圖個高興”。從這些不計功名的民間藝術家身上,作者的思想境界也得到了升華:“我驀地感到自己的俗氣,后悔跟團長說那些得獎的話。山里人自有山里人的樂,服務鄉民鄉里,唱花鼓的唱得高興,聽花鼓的聽得開心,小日子紅紅火火的,有獎沒獎又有什么關系呢?”
一部藝術史,是各行當、各門類無數相關人員共同努力的結果。比如在編寫《中國戲曲志·湖北卷》時,為了精益求精,確定清代著名京劇老生余叔巖的籍貫,兩位編纂人員以“找不到也要找”的精神,不辭勞苦,深入調研,三次前往云霧繚繞的羅田山區,終于尋得一卷民國版的《余氏宗譜》——不僅厘清了余叔巖就是羅田人這一事實真相,還弄清了他的親屬關系、生活經歷及安葬地點等。沈虹光在《三下羅田》中,詳細敘述了尋找的前因后果,讀完全文,我們不禁對這些不計名利、無私奉獻的藝術人員肅然起敬。
關于藝術魅力的評判標準,沈虹光在《天人李雅樵》中寫道:“藝術不論什么形式什么門派,歸根到底要有魅力。魅力是什么?就是讓人看了還想看,聽了還想聽。”于是,她筆下出現的,都是那些創作了讓人想看、想聽而具有藝術魅力的演員、導演、編劇等。
荊州花鼓戲中有一出名叫《王瞎子鬧店》的劇目,觀眾百看不厭。該劇說的是一位算命盲人懲惡揚善、智斗盜賊的故事。劇中沒有多么豐富多么深刻的思想,但有著普通百姓日常生活的世俗,于艱難而無奈的生活中,透著一種難得的機智、詼諧、幽默與樂趣。沈虹光的《王瞎子數數與方言的妙趣》,重點寫了演員何干青對主角盲人的一段表演——數數。從一數到七,七個數字顛來倒去、反反復復地數來數去,演員必須具備高超的口技才行。而從編劇藝術的角度而言,數數表演是一段枝蔓,加工整理時就刪去了。沒有數數這一精彩看點,觀眾的心理期待落了空,他們不買賬了!于是,演員們只好又加回去,此后一直不敢改動。
寫到這里,我不禁想到這部取自書中一篇散文的書名《落地》。希臘神話中有個名叫安泰的巨人,只要離開土地,他就四肢無力,受人所制;而一旦接觸大地,就會變得力大無比,不可戰勝。可見沈虹光老師對藝術的追求,也是真正地“落地”了。
最后,不得不提及書中所配照片,于那些對豐富多彩的民間戲曲,對“文革”、“下放”、“五七”干校等不甚了了的年輕讀者而言,不啻一種生動而難得的“圖解”與“詮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