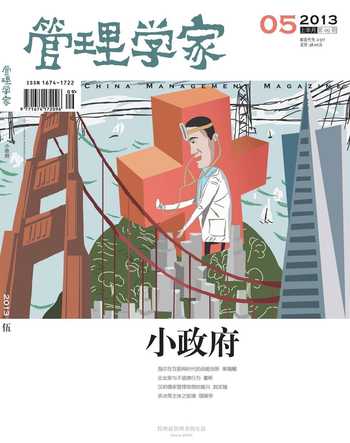《新語》和漢初政治的轉向
陸賈的思想,集中反映在《新語》中。綜觀該書,明顯以儒學為基調。四庫總目提要說:“據其書論之,則大旨皆崇王道,黜霸術,歸本于修身用人。其稱引《老子》者,惟《思務篇》引‘上德不德一語,馀皆以孔氏為宗。所援據多《春秋》、《論語》之文。漢儒自董仲舒外,未有如是之醇正也。流傳既久,其真其贗,存而不論可矣。”對這一提要,余嘉錫有詳細的考辨。但大體來說,提要的定位是恰當的。尤其是對這種流傳已久、影響廣泛的古籍,論證其思想影響要比考證篇章真偽更重要。哪怕是偽作贗品,當它已經被世人當作原作真品用于社會時,它就獲得了新的生命力。《新語》從漢代開始,就產生了重大影響,所以,值得把它作為古代管理思想演變過程中的一個節點來對待。
四庫提要把陸賈作為與董仲舒并列的“醇儒”,說明《新語》的儒學傾向是十分明顯的。但陸賈在儒學基調中滲透了無為和道術思想,所以,今日學術界也有人把陸賈列入漢初新道家。總體上看,陸賈所倡導的,是適應大一統王朝體制,以清靜無為的手段,建立可傳之久遠的理想王朝。《新語》現存十二篇,有些恐怕已經不是當時陸賈所作而是后人羼入,不過基本思想邏輯保持著一致性。
《新語》的主要內容,是從強調道德仁義開始的。陸賈認為,仁義是治國基礎。他以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構建“道基”作為社會治理的框架,這是陸賈不同于先秦儒學的地方,說明他已經有了以儒家為主線,雜采諸子,實現思想大一統的傾向。這正是政治大一統的學術化表現。對自然與社會、歷史與現實的整體觀察,使陸賈為“王道”確立了自然法意義上的正當性。在人類發展歷史上,“先圣”確立了人道,人道展開就是王道。“先圣乃仰觀天文,俯察地理,圖畫乾坤,以定人道,民始開悟,知有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夫婦之別,長幼之序。于是百官立,王道乃生。”此后由“中圣”確立了教化原則,貫徹王道。“中圣乃設辟雍庠序之教,以正上下之儀,明父子之禮,君臣之義。”使強不凌弱,眾不暴寡,棄貪鄙之心,興清潔之行。“后圣”則用五經六藝把教化具體化,建立各種禮樂制度。“后圣乃定五經,明六藝,承天統地,窮事察微,原情立本,以緒人倫,宗諸天地,纂修篇章,垂諸來世,被諸鳥獸,以匡衰亂,天人合策,原道悉備,智者達其心,百工窮其巧,乃調之以管弦絲竹之音,設鐘鼓歌舞之樂,以節奢侈,正風俗,通文雅。”(《道基》)這樣,形成了一個完整的王道演化脈絡,并賦予王道以最重要的仁義內核。“是以君子握道而治,據德而行,席仁而坐,杖義而強,虛無寂寞,通動無量。故制事因短,而動益長,以圓制規,以矩立方。”堅持以仁義為治國準則,就可上承天命,下誅暴虐,忠進讒退,扶正祛邪;不守仁義,國家就會走上秦朝二世而亡的覆滅道路。
道既具有經驗性,又具有先驗性。道在歷史,亦在人心。所以,道既有傳承久遠的歷史佐證,又有“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心理自證。陸賈稱:“道近不必出于久遠,取其致要而有成。《春秋》上不及五帝,下不至三王,述齊桓、晉文之小善,魯之十二公,至今之為政,足以知成敗之效,何必于三王?故古人之所行者,亦與今世同。”(《術事》)一部《春秋》,不需要追溯到五帝三代,僅僅通過魯國的史事記載,遵循天道與人道,陳述人世善與惡,就足以把治道說清楚。“書不必起仲尼之門,藥不必出扁鵲之方,合之者善,可以為法,因世而權行。”由此,陸賈放棄了先秦儒學言必稱三代的舊習,而是立足于當下,明確了自己為漢代新帝國確立治道的使命。追溯歷史教訓,也不必上溯桀紂,有秦二世的例證足矣。由此,陸賈實現了儒學的一個重大轉化,不是“興滅繼絕”,而是面向未來。
作為新興起的大一統帝國,最大的問題是如何在大規模和有效性之間尋求合適的治理準則。先秦時期的國家規模有限,五帝三王的直接治理范圍并不大。而先秦儒學論證仁政王道,基本上沒有考慮過規模問題。像孟子那樣鼓吹“百里而王”,在戰國群雄并起時代已經失去了可操作性,更不要說秦以后的統一王朝。荀子設想的以禮制規范天下,尚未得到實踐證明。要復興儒學,必須直面大一統帝國的廣大范圍。對此,陸賈的方案是:以仁義為價值取向,尋求合適的輔政助手,奉行無為而治的基本策略。輔政者就像君主之杖,“杖圣者帝,杖賢者王,杖仁者霸,杖義者強,杖讒者滅,杖賊者亡。”(《輔政》)秦的教訓,就是以李斯、趙高為杖。
對于如何選擇輔政之杖,陸賈深受道家以柔克剛思想的影響。他稱:“懷剛者久而缺,持柔者久而長,躁疾者為厥速,遲重者為常存,尚勇者為悔近,溫厚者行寬舒,懷急促者必有所虧,柔懦者制剛強,小慧者不可以御大,小辨者不可以說眾,商賈巧為販賣之利,而屈為貞良,邪臣好為詐偽,自媚飾非,而不能為公方,藏其端巧,逃其事功。”(《輔政》)作為君主,在鑒別人才上,應該明白“察察者有所不見,恢恢者何所不容;樸質者近忠,便巧者近亡”。“讒夫似賢,美言似信,聽之者惑,觀之者冥。”(同上)這些論證,明顯把道家與儒家合為一體。
治理國家依賴人才,人才并不缺乏。就像名貴木材,自然生長在山林,就看君主能不能用。即便是窮鄉僻壤的山野之民,身懷不羈之能、德配圣賢之美者也大有人在。“人君莫不知求賢以自助,近賢以自輔;然賢圣或隱于田里,而不預國家之事者,乃觀聽之臣不明于下,則閉塞之譏歸于君;閉塞之譏歸于君,則忠賢之士棄于野;忠賢之士棄于野,則佞臣之黨存于朝;佞臣之黨存于朝,則下不忠于君;下不忠于君,則上不明于下;上不明于下,是故天下所以傾覆也。”(《資質》)要保證王朝的長治久安,就需要君主善于發現和使用人才,進賢良,退奸佞。
在治理策略上,陸賈強調取守異勢,清靜無為。他批評秦政道:“秦始皇設刑罰,為車裂之誅,以斂奸邪,筑長城于戎境,以備胡越,征大吞小,威震天下,將帥橫行,以服外國,蒙恬討亂于外,李斯治法于內,事逾煩天下逾亂,法逾滋而天下逾熾,兵馬益設而敵人逾多。秦非不欲治也,然失之者,乃舉措太眾、刑罰太極故也。”(《無為》)相對于成文法制,陸賈特別強調教化和楷模形成的習慣規范。“是以君子尚寬舒以裦其身,行身中和以致疏遠;民畏其威而從其化,懷其德而歸其境,美其治而不敢違其政。民不罰而畏,不賞而勸,漸漬于道德,而被服于中和之所致也。”(同上)這里陸賈所言,已經是《中庸》的德治主張,遵循儒家倡導的移風易俗途徑。所以,陸賈所說的無為,不同于道家的崇尚自然,而是儒家的君子垂范。陸賈對理想的治理臻境有十分具體的描述,他說:“夫形重者則心煩,事眾者則身勞;心煩者則刑罰縱橫而無所立,身勞者則百端回邪而無所就。是以君子之為治也,塊然若無事,寂然若無聲,官府若無吏,亭落若無民,閭里不訟于巷,老幼不愁于庭,近者無所議,遠者無所聽,郵無夜行之卒,鄉無夜召之征,犬不夜吠,雞不夜鳴,耆老甘味于堂,丁男耕耘于野,在朝者忠于君,在家者孝于親;于是賞善罰惡而潤色之,興辟雍庠序而教誨之,然后賢愚異議,廉鄙異科,長幼異節,上下有差,強弱相扶,大小相懷,尊卑相承,雁行相隨,不言而信,不怒而威,豈待堅甲利兵、深牢刻令、朝夕切切而后行哉?”(《至德》)顯然,他和孟子描繪的仁政場面異曲同工,孟子以“制民之產”來實現仁政,陸賈以無為和教化來實現仁政。
鑒于秦朝建立的皇帝制度,在信息傳遞上有著嚴重的屏蔽和扭曲現象,陸賈提出,統治者必須注意“辨惑”。與荀子主張的“解蔽”相比,荀子側重于認知偏差和技術性信息扭曲,而陸賈側重于社會偏差和權力性信息扭曲。尤其是針對秦朝趙高“指鹿為馬”的教訓,陸賈強調,有媚俗而造成的信息偏差,有媚上而造成的信息偏差,兩者都要防范。否則,視之者謬,論之者誤。儒者要做直言不諱的君子,“夫君子直道而行,知必屈辱而不避也。故行不敢茍合,言不為茍容,雖無功于世,而名足稱也;雖言不用于國家,而舉措之言可法也。”(《辨惑》)對于君主來說,“夫眾口毀譽,浮石沉木。群邪相抑,以直為曲。視之不察,以白為黑。夫曲直之異形,白黑之殊色,乃天下之易見也,然而目繆心惑者,眾邪誤之。”(同上),所以,用人區分正邪,是君主第一要務。由此,陸賈確立了后來為政“親君子,遠小人”的基調。
從思想角度看,陸賈并未對先秦儒學進行深入的理論發掘,他的貢獻主要表現在把道家的無為與儒家的有為、把道家的治術與儒家的權變結合起來,把面向以往的儒學改造為面向未來的儒學,把儒者諷喻朝政的本色轉化為輔佐朝政的間色,進而確立了“治以道德為上,行以仁義為本”的主旨(《本行》),為儒學在漢初的復興開辟了道路。不過,盡管陸賈絕不言利,而且倡導“尊于位而無德者絀,富于財而無義者刑,賤而好德者尊,貧而有義者榮”的政治局面,卻在客觀上為儒者追逐利祿提供了正當途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