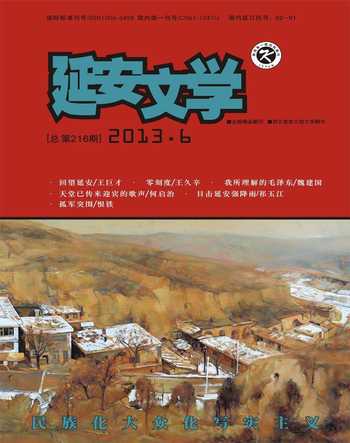在駿馬和茶葉之間
祁建青,青海互助人,土族。中國作協會員,青海省作協副主席。散文隨筆創作獲駿馬獎、全軍優秀文藝作品一等獎等。
這是一場時間空間距離非常之大的經濟互動,物流、人流還有信息流來來往往絡繹不絕。情形之繁盛大體類似于那段絲綢之路貿易:一頭是綢緞錦帛,一頭是香料珠寶,兩類物質以直接的使用價值互通有無。所不同的是,絲綢之路的版本是對過程的強調,是馱載著貨物的商隊成年累月中搖搖晃晃的艱險跋涉,是遙遙無期的東西方兩末端久久的相望。而古湟源丹噶爾的“茶馬互市”,則把這些事體全省略了。它讓兩頭往中間奔忙匯合,把兩大方向的人、事、物聚攏在此,讓人看到貨物運抵如何囤積如山,看到官署商家如何朝九晚五旗幡飄、燈燭明,看到市面街井如何人聲鼎沸摩肩接踵熱鬧非凡。
也就是因為有了馬,這一段大跨度的史實才顯得那么從容又激越。而加之有了茶這直沁肺腑東西,后人的追憶感受便自然而然會伴著茶的余香抽離飄散。
而今,君等來此飲茶思馬,當年那潮水般涌動滿山谷嘶鳴的群馬,任憑想象。
古老的茶和更古老的馬,一個在江南茶山,一個在雪域草原。自帶著暖意和寒氣,遠涉千山萬水,在古老的歷史里相遇。完全可以這樣想象,茶葉像一位南國女兒,駿馬像一位北方漢子,他們被國家做媒,嫁娶給了經濟和軍事兩家。但我還是愿意還原這對有緣千里來相會的冤家,它們的結合,立時令那段時光生出茶之幽香、馬之色澤混合的古風古韻,讓人的心先因茶而寧靜,再因馬而沸騰。
茶與馬,一個植物里的精英,一個動物中的俊杰,以這種方式在此相聚。他們的命運真的傳奇了得。只可惜洞房丹噶爾的花燭夜實在太短,仿佛才拜天地即又各奔東西。茶為馬來、馬為茶去?皆非也。在丹噶爾城堡,它倆永遠互不相識,也永遠不會相互擁有,而只不過是擦肩而過,擦肩而過……
馬首先匆匆走了。負有神命的馬,要義無反顧成全人世上的精英俊杰。是的,馬絕對不能缺席——將士的鐵馬金戈,俠客的鮮衣怒馬,以及還有書生的打馬御街,無馬則一切黯然失色無從談起。極端優秀的馬還要幫助所有的人,官吏或布衣,農民或商賈,遠去人或近來者,男女老幼,皆被馬囊括其中(在沒有火車汽車的那時,情況就是這樣別無選擇)。
馬,就如此重要。茶,也變得非同小可。茶和馬對人、對民族、對國家,那種必不可少,那種舉足輕重,在丹噶爾被一次次衡量并精確記錄下來。
我們的茶馬互市具有顯著軍事含義(比較看,絲綢之路上的商隊則更像一支奉有王命的和平使者)。從草原牧區趕來的一群群馬匹,在此被朝廷購得后運往各地。公馬和騸馬用于補充要地駐軍和裝備邊防兵營,母馬送軍馬場放牧繁殖。記載說,馬價以匹論分上中下三等。最初,上馬一匹換茶120斤,中馬70斤,下馬50斤。這個價顯然為買賣雙方接受。可若按一匹馬需要牧民四、五年飼養的成本計算,此價似乎也低廉了。然而,在同樣辛辛苦苦的茶農那里,幾十上百斤茶卻也不是一個小數目。而這僅是市場價,具體落到牧戶和茶人能有多少?賺利無疑在這之間的官與商手里。
從草山深處下來的成年馬,匹匹品質優良,就是所謂下等馬也差不到哪兒去。馬兒個個機靈,軍旅養馬訓馬正規嚴格,用不多久,這些性烈不羈的馬,便成了矯健有素的軍馬。
文字記載青海年代最早的互市,在隋與吐谷渾時期(地處貴德以北千戶)。如此說,與隋、唐、宋、元、明、清諸帝國同步一路踏來的,有陣容雄壯的青藏駿馬一族。以上這些大名鼎鼎的朝代,無不是靠馬上打江山保江山的。那得多少馬,豈可以數計?而要想搞清為何騎兵那時很發達,為主要作戰兵種和作戰樣式,到丹噶爾來走走看看,可略知一二。
那個冷兵器時代,幾十萬、幾百萬乃至幾千萬以至更多更多馬匹,從這里年復一年代過一代走向四方。既然與國防和戰爭有如此直接的重大聯系,湟源丹噶爾當然久盛不衰,其在西北以至中國歷史上的地位貢獻也就不言自明。是茶和馬所為,在其身后,是從國家到個人的全體經營者利益驅動所為。不,歸根結底,應該說還是茶馬的功勞呀!
在北方邊地,在中原及以外更廣闊的戰場上,高原牧區的駿馬們忠實地在各為其主出力流汗流血。在攻城掠地、封疆守土的無數戰役中,一匹匹良駒神駿乘載著兵卒將帥,也乘載了君王與社稷江山,決定并見證社會史和軍事史上的興亡更替、功過勝負。那年代大小戰事連綿不斷,動輒兵戎相見似乎很容易。若要問有多少馬匹從日月山赤嶺,從湟源丹噶爾走出奔赴疆場,有多少成為馬中英雄烈士,又有多少陣亡后被取革裹尸,實在誰也回答不上。
在丹噶爾,憑吊戰馬,緬懷軍人,乃我真心。
有人妄揣,唐昭陵六駿中有青海驄。還有人說遠征亞歐的元朝,滾滾鐵騎不少來自青藏大草山草原。我想,前一說無法考證只能講有可能,后一說則可以斷定完全可能。戰士和將軍,歷屆史段之蓋世功勛皆有賴駿馬。現在,我們終于明白,在此之前,我是說,在馬成為“駿馬”之前,乃曾依靠或是由輕輕茶葉做著最初的決定和付出。茶葉,貌不驚人,其實英勇。茶馬的結盟,使得平和溫潤的茶葉,成就駿馬的雷霆萬鈞。
茶葉永遠留了下來。馬去無蹤,茶留生香。茶代替了馬,活生生如一位送走了遠征夫君的女人,自己永守在家。大批的茶葉等生活用品,在丹噶爾經赤嶺,經日月山,源源涌入高山草原廣大牧區。茶葉的涌入之早與流量之大同樣也是我們的想象所難以企及的。茶葉的使命,簡約說,又是龍馬精神的另一種風韻體現。應該說茶葉是十分幸運的。它很快迎得人們的接受和肯定。后來,人們對茶葉在情感上由肯定更上升為一種尊重。
從開初至今,煮茶飲茶逐步固定成為牧區牧民(自然也包含城鄉人家)生活的主要風俗,亦是一個特有禮數。祖祖輩輩沏茶、倒茶的身影,請茶、勸茶的眼神和口氣,都顯得喝與不喝茶,是一樁誰也不能忽略和逾越的大事情。和草原牧家相處久了,就知道喝茶從過程到內容,很早很早就已化作一種待客儀式,其中禮遇性規矩和心懷情愿的沉淀遺存,有著很難盡說的恒久和深刻。為什么會這樣?為什么會如此懂茶、愛茶、敬茶?為什么,還須問?
如馬一樣,茶葉也是需求無盡的消耗物。養馬的牧人全家,養活老小早起的第一件事是起火燒茶。早、中、晚及隨時都要喝茶,誰都能意識到,沒水沒茶,生活還如何能維持繼續?說沒茶一天也過不下去,豈是矯情瞎話。在某個清早,一位牧人咽下一口茶,眼前悠然現出自家馬的影子,悟著了自己許多匹馬剛賣了,悟著了,此時之茶乃彼時之馬,這茶馬關系的道理,他很容易就想到。
茶味悠長,茶味濃郁。感情是,唯獨悠長濃郁的茶味,悄然撬動熨帖了駿馬和主人那心之靈犀——那是眼前茶氣漂浮、遠方駿馬騰升的玄奇之極的所謂生命不能承受之輕。
他想那些離他而去的馬了,那是他像自家孩兒一樣看大養大的馬。但他還有馬,很多很多馬,在他一輩子中。馬的繁衍,只要草山雨水年年正常,飼養管理盡心竭力,如自己和子孫的生養活命能力,會愈來愈繁盛的。我們的牧人該干嘛干嘛,馬就這樣源源不斷,生生不竭(你可別誤會,我說的不是現在,我說的是茶馬互市那個時期)。
作為封建朝代官辦的“商貿中心”(權且用一下這個現代用語),湟源的茶馬互市經歷了三個重要階段。先是公元七世紀上葉在哈拉庫圖以西日月山下,設立赤嶺茶馬互市。這正是唐蕃結姻,朝廷與藏區關系密切的時期;隨后到明清時,逐步轉遷至今丹噶爾。顯然,這個地方基于交通和防守的考慮位置最佳;再就是到了上世紀初,其商貿范圍擴大,經營活動達到高峰。經濟的振興終還會催生文化的活躍成熟。就說一個湟源排燈(一種用木作框,蒙鑲以紗或玻璃,繪制各色圖畫,內以燈火映照,成系列地排至街頭巷尾,被稱作原始“燈箱廣告”),所顯擺出的宮廷味兒和商業氣息,那腰包里既有錢財寶物,腹中又不乏詩書文化的因富而貴、因貴而禮的士商群相,幾番讓人再三領教而感慨。
南去拉脊山半路有處地名喚做“騸馬臺”。經貴德過去,再往南百余里,有一繁華小鎮叫“過馬營”。一聽一看,即知都和馬關系最大,正是當年整個青南地區販運馬匹的大通道之一。每年一些時節,有大群的馬經此有計劃輸送過來,到這些地點再進行專門的調理養護。這僅是一條相對固定的路線,而對長時間從青南、藏北奔波來的馬群和馬商們來說,一伺到達了拉脊山事情就好辦了,就可以舒一口氣了。因為,他們和馬群已從充滿艱難險阻的高原群山和茫茫大草原出來了——膘情不錯規模壯觀的馬,可直插日月山而入藥水河谷,也可過湟中沿湟水到達丹噶爾。是的,走到這兒,丹噶爾,已是遙遙在望了。
茶馬互市城從赤嶺移至丹噶爾是一個歷史轉折。像是接通了地脈,占住了好風水,一路興旺起來,人氣財氣就擋也擋不住了。后來在1725年,川陜總督岳鐘琪上奏得允,哆吧(今多巴)市口又西遷并入,使丹噶爾比先前更為壯大。
從經濟角度說丹噶爾是當時的成功范例。這使我們想到,同時期的中原和江南,圍繞物質層面的吃喝用、穿住行,還有文化層面的如戲娛樂、詩書文的生產與消費繁榮多樣不一而足(茶無疑始終是其中重要一種)。科學尤其是技術領域興盛發達,中國最需要出現的商業、制造業甚至金融等經濟活動,也蓬勃看好。不需多說,詩歌、散文、小說、戲劇等曾幾至巔峰。社會有望以一種新機制進行構建組合。那個時候,國家已在萌生由一個封建官僚專制的政治大國,向一個將更多熱情和心思投注于國計民生的經濟大國轉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