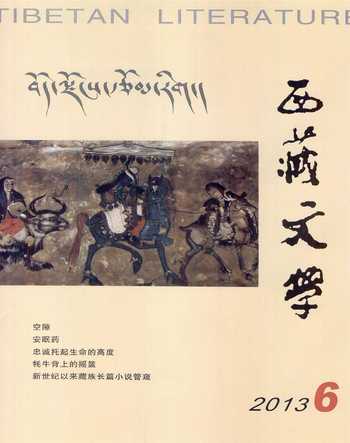朝圣之旅
史映紅
以前,魯迅文學(xué)院在我心中是神圣的,像一名登山者向往珠穆朗瑪峰的高度,像文學(xué)創(chuàng)作者向往諾貝爾文學(xué)獎一樣。我時常虔誠地打開中國作家網(wǎng),或者在百度上直接輸入“魯迅文學(xué)院”字樣,就會出現(xiàn)關(guān)于魯院的簡介、新聞、動態(tài),比如某位作家學(xué)者上課了,學(xué)院組織學(xué)員去某地社會實踐了,某一期開學(xué)了,某一期又畢業(yè)了,開學(xué)與畢業(yè)典禮到會領(lǐng)導(dǎo)是誰,發(fā)言代表是誰等。每每此刻,一種油然而生的羨慕、仰慕之情難于言表,像多次報道貧寒家庭的某個孩子由于種種原因無法上學(xué)卻只能放牛撿柴一樣,那么無可奈何。
說是無奈,一是我覺得自己身處雪域,在喜馬拉雅山脈的一隅服役,那是一塊閉塞落后的地方,寫作寫詩常常不被人理解,作為軍人,我遠(yuǎn)離軍區(qū),更遠(yuǎn)離總部,真不知道部隊關(guān)于扶持文學(xué)創(chuàng)作的門何時開,為誰開?二是作為西藏作家協(xié)會的一員,西藏畢竟是以藏族為主的創(chuàng)作群體,近幾年涌現(xiàn)出了很多優(yōu)秀作家、才華橫溢的青年才俊,加上一些沖擊力很強(qiáng)的藏飄作家,我無論在影響上、水平上、還是社會關(guān)系和人際交往上不占任何優(yōu)勢,一直以為此生那座神圣的殿堂之門永遠(yuǎn)向我關(guān)閉。心里想,即使去不了,有朝一日去北京,也要看一看、摸一摸魯院的大門,甚至在我萬分敬仰的魯迅塑像前、在“魯迅文學(xué)院”的門牌旁照張相,那也是一個特別的經(jīng)歷吧!
命運(yùn)之神有時候也惠顧思想上毫無準(zhǔn)備的人,去年臨近新年的一天,西藏作家協(xié)會辦公室的米瑪卓瑪,這位素未謀面但很謙和的女同志打來電話,說是你上不上明年春季有一期魯迅文學(xué)院的高研班,我因激動而語無倫次地說了好幾個“上”,她又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