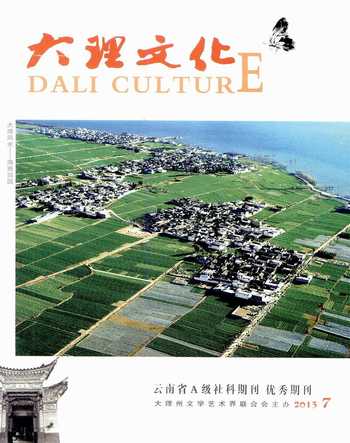蛤蟆塘紀事
楊天健
1
蛤蟆塘是濕地里的一個小湖泊。雨季來的時候,小湖壯得像大水牛,旱季水退,小湖瘦得像蛤蟆,當地人就叫它蛤蟆塘。沿蛤蟆塘往南不到兩里是縣城,我家就住縣城小鎮上。因為離得近,小鎮人常去蛤蟆塘。正因為離得近,小鎮上的許多故事就和蛤蟆塘糾纏在了一塊兒。我家也不例外,我父親和我媽的故事都沒有離開蛤蟆塘。蛤蟆塘成了他們故事里的另一個角兒。
我媽本地人。她命薄,在世時間短,我剛記事不久就撒手人寰。
我父親的老家在得遠,山西太原府往西還走好幾天。
我父親是戰斗英雄,在我認識的人當中,好多人都崇拜他。父親的壽歲也不是很長,和我一起生活了十多年,也撒手離開我,找我媽去了。總體上講,父親沒給我留什么好印象,跟酒囊飯袋沒什么兩樣。至于戰斗英雄形象,影子都沒有。從我記事開始,就見他整天抱一軍用水壺(里頭裝著酒),坐蛤蟆塘邊老柳樹下,老半天不動彈。百無聊賴的樣子。
大概到我讀中學吧。父親開始給我講他的親身經歷了,于是,我知道了父親不同尋常的光榮歷史。他十六歲就參軍,參加的是八路,參軍不久就隨隊伍上前線打日本,以后就一直打仗打仗打仗。一直打到我媽家鄉的小鎮上。
一提起光榮歷史父親就不謙虛,滔滔不絕吹噓他天生就是打仗的料,槍響身先士卒、沖鋒在前。作戰英勇頑強,經歷抗日、解放戰爭大大小小無數戰斗,槍林彈雨中出生入死,屌毛都沒傷著他一根……(我知道,父親還參加過抗美援朝,打美國鬼子終于負傷,但從不見他提起過)每講到精彩地方,父親總邁大步繞圈子,手掌在空中比劃一下又比劃一下,動作干練靈活,精神飽滿極了。
回憶起戰斗歲月(除了抗美援朝),父親總是興沖沖的。多年前的戰斗場面都記得一清二楚,講細節節奏明快、不厭其煩,姿勢加手勢張牙舞爪,胡須眉毛尖上都是得意洋洋……
這時候,我有點相信他是戰斗英雄了。但我不露聲色,保持沉穩,絕不做父親希望我做那種翹首以觀如癡如醉、崇拜他崇拜得五體投地人歡馬叫的粉絲樣。
我問父親,除了打仗。還有嗜好不?
父親見我盯住他的軍用酒壺不放,知道我明知故問,想殺他的威。他不尷尬,也不想遮掩,爽快說,惟一嗜好是喝酒,一喝就高,一高就犯混了。因為這臭毛病,挨處分也是家常便飯。好在老子我戰功底子厚,一次一次處分下來都沒一擼到底,功過相抵總還有連長當,照樣帶百多號人上前線沖鋒打仗。部隊上下都知道我這點破事兒,都知道我也就是能當連長的命,再不叫我名字,都叫我老連長。叫著叫著也習慣了,再叫我名字反倒感覺別扭了。
提起當年,父親的喜笑怒罵里總充滿欣賞和懷念,講缺點都能聽出驕傲和自豪來。一離開回憶,父親百無聊賴,慵懶,對一切都不在乎了。他就在乎一樣東西——酒,酒成了他的命根子。
中學剛畢業,我發現四十多不到五十的父親頭頂禿了,剩在兩鬢的頭發開始花白,一臉虛胖,沒一點紅潤,心事重重,像被拋棄扔到一個被遺忘的角落,已經有很重的暮氣了。
我問他,是不是因為我媽?我知道,我媽死后他一直就這樣。我父親忌諱這個,一直不肯回答。這反過來證明他心里憋著的心事就是我媽,證明我的判斷八九不離十。
有一次我對父親說,我知道的,你愛我媽,你想我媽,在心里思念,舍不下?
父親憋半天不說話,但眼眶濕了,紅了。過了好半天,終于說出一句話,你媽好,是我對不起她,是我把她害了。
父親為什么一直沉浸在一種內疚中不能自拔?是什么事讓他一直不肯寬恕原諒自己,把心事長久放在心坎上,這是一個謎。當時我年紀小,沒有能力揭開它。
長大成人后,通過不少人的只言片語,再通過我的記憶和合理想像,我把那些支離破碎的細節拼湊連接起來,我父親和我媽的故事才由點到面。呈現出一個大概輪廓來。以后,我像學者研究課題一樣,一個片段一個片段補充,豐富,融會貫通,我父親我媽故事的謎底才逐漸從我父親轉業下地方那時候開始,慢慢清晰起來。
2
打完渡江戰役,一路馬不停蹄人不卸鞍、邁著匆匆行軍步伐率部風雨兼程解放大西南的我父親接到上級命令,在云南滇西高原最大湖泊源頭的那個小鎮上停止了行軍,部隊就地駐防。
這時,云南宣布和平解放。
土匪剿滅了,仗打完了,上級號召轉業下地方建設邊疆。
我父親的名字就在那一長串轉業名單上。要分配去的地方,就在他停止住行軍步伐、就地駐扎下來的那個小鎮。
小鎮在西山腳,座落在壩子中央,北邊不遠就是蛤蟆塘,湖光山色秀色可餐。壩子湖河縱橫、稻香焦肥,四季如春,鳥語花香,人稱高原小江南——打著燈籠找都找不到的好地方。可父親死活不干,就是不愿意脫下軍裝,不愿意摘下那支形影不離隨身挎了多年的駁殼槍。
為了繼續挎槍穿軍裝,父親死乞白賴泡蘑菇、千方百計纏首長,首長被他纏怕了,特批他帶走那支形影不離挎了多年的駁殼槍轉業到我媽家鄉的小鎮上。
我父親到小鎮上當縣商業局局長。縣商業局機關在一戶掃地出門的地主家。地主家一進兩院。當街前院是商業局,后院被幾戶翻身解放的城市貧民瓜分了,其中一戶就是我媽家。
都下到地方了,我父親還系皮帶,還打綁腿,還挎駁殼槍,還一身戎裝,鬧得商業局機關一天到晚緊張兮兮,活像軍營一樣。
上班干工作我父親還像打仗,卷衣袖蹭蹭出蹭蹭進,忙活得七竅生煙、四腳不落地,舉手投足仍然是戰爭節奏,破馬張飛的。我父親不能進辦公室坐班,才進辦公室,滿院人就都聽見他打鼾。
人雖下到了地方,骨子里沒變化,我父親儼然還是一個強悍的職業軍人。也難怪,歷經了多年戰火紛飛的戰斗歲月,過慣了飽一頓饑一頓、大家擠一堆睡大房間或是露天睡戰壕的集體生活,艱苦生活,熱鬧生活,冷不丁兒要求他安安靜靜一個人坐辦公室里喝茶,等著別人上門來匯報工作,這簡直就是遭罪,不可以想像的事兒。作為一名下級軍官,我父親習慣實干,習慣服從。他從不挑肥揀瘦,從不討價還價,也從不問為什么?上級指到哪兒打到哪兒。
我父親沒功夫,有功夫也不去琢磨人生觀價值觀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兒?他覺得革命的道理很簡單,參加革命了,自己的生命就是黨的國家的人民的,革命什么時候需要,自己的生命就什么時候拿出來交待,徹底交待了,也就徹底革命了。
全國解放了,進入了和平年代,再沒有槍林彈雨硝煙彌漫,下地方建設邊疆自然就成為南下軍人的必然。我父親很不適應,很孤單,但他仍然像執行戰斗任務一樣,努力強迫自己適應和平、適應地方,努力把自己從職業軍人過渡到地方上。
我父親愛吃,下地方干的頭一件事就抓生活。兵馬未動,糧草先行,打勝仗靠的就是這個,全靠人民群眾的獨輪小車。這不是吹牛,我父親說,陳毅元帥說淮海戰役的勝利是獨輪小車推出來的這句話千真萬確,他親眼所見。所以,抓生活是頭等大事,縣商業局職工食堂的開張也是縣政府各大機關的頭一家。
商業局機關食堂里米飯、掛面、饅頭樣樣俱全,菜還是大雜燴,豬肉粉條白菜蘿卜,有時還有本地不常見的海帶蝦米紅薯粉皮什么的。父親的飲食習慣和當地人不一樣,不吃米飯,愛面食。吃掛面父親不興用筷子夾起來一根一根往嘴里喂,兩筷子叉進大碗里卷,卷好一卷往嘴里塞一卷。吃饅頭更省事,拿筷子穿串兒,從院子食堂這頭走到那頭的辦公室,“戰斗”基本解決。
父親一般不愛開會磨屁股,不興坐班,不習慣批閱文件,喜歡下基層,到辦公室找他十有八九都會撲空的。
在我父親當商業局長的日子里,全縣馬幫運輸有條不紊(剛解放那陣沒公路,交通運輸全靠人背馬馱走茶馬古道),物資供應豐富,老百姓時不時還能買點緊俏軍供,小縣城的商業一派繁榮景象。
打從那時候起,公家人興過星期天。習慣了緊張生活,當時還光棍一條的我父親星期天沒事干。就到蛤蟆塘打獵。
蛤蟆塘天空湛藍湛藍,湖水湛藍湛藍。馱著八哥的馬在湖邊吃草,一大群野鴨在水里游蕩,有幾只悠閑地貼著水面滑翔,像在勾勒高原水鄉的山色湖光……
我父親不在意山色湖光如詩如畫,全部注意力都被水上、天上的野鴨吸引住了。那時的生態環境好,野鴨多,打野生動物不犯法。所以我父親明目張膽肆無忌憚掏出駁殼槍,打開保險,在如詩如畫的山色湖光面前展示他的槍法……
不到半天,我父親拎一大串野鴨回到商業局機關食堂。
后院住戶的孩子很吃驚,一起跑到前院里來看。我父親得意洋洋,吩咐食堂多準備飯菜,由他掏腰包請后院的孩子們吃晚飯。那天,后院的孩子享用到一餐豐盛晚宴,除了大米飯、饅頭、掛面,還有大盆雜燴、大盆的黃燜野鴨。
有個大孩子學我父親蹲在院里吃掛面,一個勁拿筷子在碗里頭卷,但無論怎么卷,掛面就是卷不起來。我父親過去拍拍他的腦袋,說,“憨兵,看好了,我來給你做示范。”
我父親喊了一聲憨兵,滿院子人就再不喊那大孩子的名字了,都喊他憨兵。憨兵十六歲,念小學三年級,同院住的我媽當時也十六,和他同一個班。那時候剛解放,十六七歲讀小學稀松平常,有許多大爺嬸嬸阿姨叔叔為了掃盲認字,都和自家娃娃同念一個班。
在同年齡姑娘堆里,數我媽發育好,該凸的地方凸,該凹的地方凹,出落得一表人材,尤其是那口牙。小鎮到處出熱水,隨便哪個地方捅個窟窿眼兒都會冒溫泉。溫泉含硝,本地人十有八九牙黃,嚴重的黃里帶黑。我媽不一樣,一口牙整齊潔白,笑起來還閃瓷白的光。在平時,我媽就喜歡偷看我父親,看他走路、吃飯、說話,舉手投足一舉一動都看,這已經不是一天兩天的事兒了,從歡迎解放大軍入城的那一天開始,我媽就注意我父親了。
3
按照當下標準。我父親和我媽談戀愛的過程一點都不浪漫,但她們的戀愛過程被蛤蟆塘見證到了,一扯上了蛤蟆塘,事情就變得詩情畫意起來。
每逢星期天,憨兵就跟我父親去蛤蟆塘打野鴨。我媽央求憨兵說情幫忙,也帶她去蛤蟆塘。我父親見我媽張口笑的樣子,爽快答應了。
連片的蘆葦一起一伏,散發出好聞的清香。
湖邊的我媽和憨兵很聽話,遠遠地跟著我父親。父親手起槍響,彈無虛發,我媽和憨兵忙著到處撿野鴨。
湖邊濕地的水不深,一般都不超過膝蓋。水很清幽,陽光在水里忽閃忽閃。
湖邊有棵老柳樹,樹下長半人深水草,踩上去軟軟的。沒草的地方,齊膝的水下盡是爛泥巴。爛泥巴不時冒氣泡,像呼吸,一股沼澤地特有的氣味摻雜在空氣里邊。
一只野鴨落在老柳樹下冒氣泡的地方,我媽急忙跑過去撿。
我父親慌慌地喊:“老柳樹那兒不能去,站住,你給我回來。”
我媽說:“野鴨呢?”
我父親說不要了。
我媽問為什么?
我父親說:“那兒的沼澤是陷阱,我親眼見吃草的馬兒陷下去,一會兒功夫就不見蹤影了。”
一來二去,我媽和我父親戀愛上了。父親像個炸藥包似的,不點便罷,一點就燃,連我媽四年初級小學畢業都等不及,組織上才批準,立馬就和我媽登記結婚了。
聽老鄰居們說,結婚后的我父親和我媽過得很和睦,就像纏一起的豆芽菜——好得扯都扯不開,有些事兒講起來都臉紅,都不好意思給你講。
我父親大我媽十歲,自然把我媽愛得死去活來。一見我媽笑彎了腰,露出那口好看的牙,不管白天黑夜、有人沒人,父親一個沖鋒抱起我媽就進新房……
我媽咯咯笑著叫,“放開我,放開我,討厭,討厭!”接下來就是吱吱咯咯一片床板響。
我父親和我媽的新房在后院。后院和前院一樣是明清建筑,那些雕龍畫鳳的木板格子門窗薄,隔音效果差,放個啞屁隔壁家都聽得見。每月除了有數的那幾天,新房里總傳出吱吱咯咯床板響。
那么多人同住一院,一家連著一家,誰家有點兒動靜聽不見?早晨起來漱口洗臉,穿梭出進,老遠見到我父親老鄰居們就啞然失笑,我媽低頭不好意思,我父親大大咧咧不當一回事兒。久而久之,大家習慣,后院里又都相安無事了。
我父親的生活中有個我媽,很快就適應和平環境,適應地方。我媽的生活中有了我父親,日子過得美滋滋的。心滿意足之余,我媽努力適應我父親的生活習慣,甚至包括一些瑣碎細節。
新麥上市,我媽買剛掃下石磨的新麥面,買許多機器掛面拎回家。除了給父親下機器面,我媽做饅頭、花卷或包子,還特意在面食上頭點紅曲兒,那是當地蓋新房上梁,訂婚迎親辦喜慶事才興點紅的風俗,但我媽不管。面食出鍋,紅紅白白,可愛喜慶極了。知道我父親離不開醋,我媽買大筐當地盛產的青梅,裝進大陶土壇埋進糠皮里用文火燉。一個多月后,燉熟的梅子烏黑閃亮,自此,我家一年四季都散發出一股燉梅的清香。
我父親開心了,感覺日子像過節。他見天喜洋洋唱《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和《我是一個兵》,每首歌只唱開頭兩句,反過來又復回去,跟驢叫沒兩樣。
元宵節后,一個已經當上團長的老部下來家里看望我父親,兩人匆匆說了一陣話,那團長就起身朝他的老連長行軍禮,急忙轉身趕部隊去了。
晚上干活我父親心不在焉(他把和我媽做愛叫成是干活),剛把我媽抱緊了又放開,翻到一邊去數樓板。我媽奇怪,問父親咋個了?
我父親說,“朝鮮那邊的仗打得激烈……朝鮮是兄弟,見死不救行嗎?”
我媽問“朝鮮在哪兒?真是親兄弟嗎?”
父親答非所問,突然說,“你聽,火車叫?日怪,這火車叫喚得跟軍號似的。”
這種幻覺非常奇妙,我父親激動起來了,感覺不再是躺在床上摟老婆,而是登上一趟長長的軍列,身后無數車箱板上是一門門高射炮和一輛輛軍車,跟在他乘坐的悶罐車后面源源不斷、浩浩蕩蕩奔赴戰場……
父親再也躺不住了,渾身的血液如潮水一般涌動起來……
我媽根本攔不住。父親告訴我媽決定第二天一早就走的時候,恨不得連夜就開拔。
天還沒亮透,小鎮還在沉睡,我父親就已經起身了。殘月照著小鎮上的小街,小街青石板路上月光閃閃,小河靜靜流淌到遠方。
不管父親怎么反對,我媽一定要送一送。
月光下,我父親大步流星把身后的我媽甩得很遠,我媽在后頭連喊幾遍他才極不情愿站了下來。我父親一輩子粗枝大葉,但這時候的他多少也感覺到一點離愁別緒了。這種情緒以前沒有,怪怪的,讓他不敢回頭看。出門的時候,我父親假裝不經意看了我媽一眼,就被我媽的目光逮住了。我媽專注看父親的臉、看父親的身子,忽閃著就要滾落淚花的一句話都不講。我父親心慌,受不了,轉身大步朝前趕……
想到這兒,父親連忙回頭,朝著就要趕上來的我媽揮手,壓低嗓門說,“回吧,回去了,別著了涼。”
我媽喊:“一路小心,到了來信,多來信啊!”
“知道了,回吧。”
“一定要保重好,掉一根毫毛,我不饒你。”
“放一百個寬心吧,屌毛都掉不了一根的。走啦走啦……”話沒說完,就逃似地離開了。
日子一天天過去,我媽一天天去郵電局里問訊。次數一多,我媽還未開口,人家郵電局的人倒先笑著搖頭抱歉,仿佛不寄信給我媽的責任不在我父親,是郵電局的錯。我媽不怨我父親,不怨郵電局,她怨戰爭,是戰爭把她忘記了。
父親想讓我媽給他生兒子,我媽爭氣,父親剛走就發現懷上我了。她立刻寫信到朝鮮,但寄出去的一封封信泥牛人海,音訊全無。我媽干著急,她想讓父親第一個知道,他有兒子了。
我媽六神無主、茶飯無思,忘了很多事,單單忘不了去朝鮮當志愿軍行軍打仗的我父親。
是啊,父親是戰斗英雄,解放軍功臣,為幫助朝鮮兄弟,此刻又在冰天雪地里一把炒面一把雪英勇抗擊武裝到牙齒的美帝侵略者……
那時候歌曲里唱,“吃菜要吃白菜心,嫁人要嫁八路軍。”我媽嫁我父親全鎮人羨慕、感激、敬重我媽得很……這些,我媽全知道,內心里頭是幸福的。
那時候年輕的共和國剛誕生,新社會新風尚,新思想,時代精神里洋溢著濃濃的理想主義,大家都不愛錢,不貪圖享受,不羨慕物質生活。一心一意愛黨愛國愛集體崇拜英雄,英雄是楷模,學英雄是時代的主旋律。
我媽和她同時代人一個樣,精神世界就像那清純的蛤蟆塘水,即便和父親一個國外一個國內,即便是三年生活不到一起。三年時間,說長不長,說短不短,這時光足夠心猿意馬的人改弦易張。但我媽專一、忠貞,典型的那時代性格的人,她一直都是我父親的忠實粉絲,海枯石爛堅定不移。
思念我父親了,我媽就到蛤蟆塘。
我媽坐在老柳樹下,靜靜地看天上水里的云,看隨風起舞的蘆葦,看翠鳥一頭扎進水里捕魚的情景……
我媽盡情享受沁人心脾的習習涼風,暢快呼吸潮濕略帶腥味的新鮮空氣。蛤蟆塘的天湛藍,水湛藍,空氣也湛藍,這種湛藍色調使我媽陡然涌起的思念心潮又平復下去,內心得到了安寧。
有時候,我媽會美夢般覺得,我父親就在蘆葦蕩的另一邊打野鴨,她甚至聽到駁殼槍響起的槍吉……
每當這個時候,我媽就輕輕拍拍自己的肚子,對我說,“兒子,你聽,爸爸打到野鴨了。別總是賴在媽媽的肚子里睡懶覺,快快長大出世,到湖邊幫你老爸撿野鴨去。”
4
父親從朝鮮回來的時候,我三歲多了。
分別三年多,久別勝新婚。我媽早早把我哄睡著,麻利沖了個澡靜靜在屋里等。我媽想,父親從槍林彈雨中又闖了一陣,又走過一遭千山萬水才回小鎮,一定非常想她,一定非常想干活。今晚,她要用三年的深深思念,好好慰勞遠道凱旋而歸的英雄男人。
一更天、二更天、一直等到三更,家家燈光全熄了。整個院子黑幽幽的,一直還不見我父親回屋去。我媽沉不住氣了,輕輕推門走到院子里。昏昏的星光下,父親獨個兒蹲在院子里喝酒。
我媽溫柔地說:“都幾點了,還喝,回屋。”
“你先睡,我睡不著。”
“怎么,不想我?不想干活?”
“我,我這幾天,路上,路上辛苦,累病了。”
我媽不相信,摸摸我父親一身的腱子肉,說:“像牛一樣,哪兒病了?”
“病就是病了,噦唆,睡你的覺。”
我媽說了聲“誰管你。”轉身就走。
過了一會兒,我媽拿件軍大衣出來披在我父親身上,我父親還是木然不動。我媽無奈,抹眼淚轉身回屋去了……
第二天早飯,我媽蒸一甑子點了紅曲兒的包子饅頭花卷,燉一鍋父親愛吃的香噴噴雜燴,炒一盤青蔥碧綠青菜,端一盆從蛤蟆塘捕撈來的紅尾巴鯉焦做成的糖醋魚……面對一桌子好菜飯。父親隨便扒拉了幾口就放碗了。
我媽問,咸不咸,對不對口?
我父親只說了聲好,就悶聲不出氣。再也沒聲音了。
我媽8知道,我父親答應的那個好是假的,但又拿不準自己究竟是哪兒做錯了事情?
越緊張就越出錯,我媽做饅頭不是面頭發酵不好,就是堿放多或是放少了。父親好壞都不說,吃飯有心無腸。
有一次我媽忘了買菜,對付煎一盤荷包蛋端上桌去。我父親一見雞蛋就鬼火沖,說我媽存心要臊他這個人。我媽委屈了,眼淚嘩嘩地往下流。她實在弄不懂,怎么也猜不透,男人從朝鮮回來怎么就變成了另外一個人,敏感,挑剔,莫名其妙發火罵人。
酒越喝越多,人越來越混,在單位也一樣,工作丟三落四,動不動罵人,有時還動手摔東西……
父親自己過意不去,堅決辭去了領導職務,但辦公室留起。一到晚上,父親就到辦公室里學習。其實,父親就是和我媽打時間差,等我媽睡熟后,他再回屋睡。
一天晚上,我媽忍不住摸到辦公室,她隔著窗子往里瞧,見我父親正抄口缸仰脖子往嘴里灌酒
我媽沖進屋一把奪過口缸,說:“學習,學習,你就這個樣子學習?”
父親順勢趴在桌上,然后努力抬起頭朝我媽嘟噥一句:“明天,明天不學、學習了。”
那年月沒水電,縣城也沒有路燈,一到夜里小鎮街巷黑黢黢的。剛解放不久迷信還猖狂,生活中還離不開鬼怪狐精黃鼠狼大仙小神子之類……膽小的人天一黑就不敢出門,生怕遇上狐精鬼神仙怪。那時候家家都還窮,一個碗一雙筷都算財產。天一黑,貪小便宜的順手牽羊撈個碗拿雙筷,好吃懶做的索性趁黑夜做起了偷雞摸狗的無本生意,于是。小鎮上就常聽見有人丟失東西。丟失東西的不甘心,第二天扯開嗓子當街罵人。
不在辦公室里學習,就上街巡邏去。值夜班巡邏維護社會治安一樣為人民。人民是靠山,我父親明白這道理,喝酒喝得再迷糊也不會忘記。
上街巡邏了一段時間,偷雞摸狗的知道我父親有駁殼槍,槍法百步穿楊,都金盆洗手改邪歸正。但父親仍然堅持不懈,到了晚上還去街頭巷尾。
夜幕降臨,那些逃學不敢回家的,投親訪友不靠,在小鎮上沒吃沒住的,鄰里爭吵的,兩口子打架賭氣出門的,父親都大包大攬解決他們的問題。他就像片警,調解父子、夫妻、鄰居,甚至解決流離失所、投親不遇……
常抓不懈見了成效,小鎮路不拾遺,夜不閉戶,人人遵紀守法了,連那些成天游蕩在街巷里,一到夜深人靜就爭風吃醋打群架的野狗都收斂了幾分。
小鎮是云嶺高原上的小鎮,父親巡邏的街面海拔高度足足有兩個摞起來的泰山頂。
臘月小年夜,下了一夜的雨夾雪。
一進家門脫下沉重軍大衣,父親像大鳥張開雙臂倒頭便睡,一瞬的功夫就睡沉了。
“睡得跟死豬一樣。”我媽自言自語過去給我父親脫鞋脫衣裳,脫著、脫著手就像觸電,一股熱流迅速傳遍全身,她蹭到他的隱秘地了。猶疑不決了一會兒。我媽又試探了一下,父親真的沉睡得像死豬。她想解開心中的謎,又悄悄把手伸過去……
啊,陰囊空空的?不對,怎么可能?
一條刀疤毛毛蟲似地爬在陰囊上,陰囊真癟了!我媽的心陡然提起,她惱怒、絕望,突然失控大聲尖叫:“啊!朝鮮——你……”
滿院子人被我媽絕望的尖叫嚇醒了。有人看見失控尖叫的我媽沖到門外,被憤怒的我父親揪住頭發往回扯……
我媽在屋里殺豬樣嚎叫,滿院人急得團團轉……
5
我媽猜對了,根源果真就在朝鮮戰場。
抗美援朝上甘嶺一次戰役,打仗從不傷一根毫毛的我父親在戰斗中負傷了,傷口就在好說不好醫的那個隱秘地。
中國人民志愿軍總攻前夜,父親率尖刀連潛伏在敵前沿陣地。拂曉,志愿軍的總攻炮火剛剛延伸,我父親就一馬當先沖向前去……
突然,父親的腳踩到敵人的地雷,地雷爆炸,父親被掀翻在地……
戰役結束,父親被送回國內。傷愈后,父親又在榮軍療養院療養了好一陣,這才磨磨蹭蹭回到了小鎮……
那天以后,我媽一天天消瘦下去。
她頭不梳,衣裳不換,我哭鬧不管,外婆做啥吃啥,咸淡不吭氣。也是從那天起,我媽清晨不留門,自己蒙頭睡,父親叫死不答應。‘
我媽不知道該怎么辦,她麻木不仁了。維系她和我父親的那根看不見的脈管被無情割斷,我媽和我父親由近而遠,由親而疏,他們共同澆灌起來的生活之樹漸漸枯萎。
父親心緒不寧,目光在明顯頹廢下去的我媽身上久久停頓,沉默了好長時間,他才極不情愿地開口,說:“孩子他娘,我們離婚。”
離開軍隊下地方,父親在心底里栽下兩棵樹,一棵是自己,另一棵就是我媽。朝鮮戰爭爆發前。兩棵樹的根上土地肥沃,陽光水分養料充分,兩樹因此枝繁葉茂枝葉相交盤根錯節,彼此幸福擁抱在一起……朝鮮回來,充分必要條件沒有了,兩棵樹再無枝葉相交、盤根錯節,漸行漸遠了。
誰之罪?
自己。我父親想,自己這棵樹已經枯萎,如果還繼續和另一棵樹糾纏在一起,我媽也會枯萎掉的。人不能太自私,不能讓我媽這棵樹跟著枯萎。
我媽抬頭細看,發現我父親皮膚灰暗、臉色憔悴、胡子拉碴,人明顯蒼老下去。她心疼了,眼淚禁不住刷刷往下流,哽咽說:“離婚?以后誰來照顧你?”
“我自己。你另找個人。”
“不,我認命,跟你一輩子。”
“別任性,你熬不住。”
“不,不離,你別逼我,我不離……”我媽咽咽嗚嗚地哭。
“那?那?那你就自己放開手腳,別把自己害得太苦……”
說完這話,我父親怔怔地盯住我媽,我媽也怔怔地盯我父親,倆人像剛認識,互相怔怔地看,再沒有下文。
我父親說到做到,一到晚上就背駁殼槍軍用水壺手電筒,披上軍大衣,很快消失在門外的黑暗里。
我父親像條善解人意的狗,乖乖躲開了我媽,躲進沒人的背街背巷,整夜都不回一次家門。
生活還在繼續。漫漫長夜中,孤燈下,我媽在努力適應。
要不是那天晚上發生的那件事,我媽也許就習慣孤獨了,是憨兵橫插一杠,一下子把她的生活攪亂了。
憨兵一直耍單身。畢竟是同院、同班、青梅竹馬,我媽關心,勸他找一個。憨兵不哼不哈,態度模棱兩可,心里想些什么,我媽不知道。
那天半夜,我媽到前院商業局機關廁所解手,回屋時被憨兵攔住了。我媽小聲叫憨兵走開,回家去睡。憨兵不說話,眼睛把我媽盯得死死的,就是不挪腿。
“三更半夜不睡,半路攔住我不放,你想干什么?”
“干什么?”憨兵一下子被提醒了,他不管不顧,突然用力把我媽緊緊抱住。
“放開,再不放開我就喊了。”憨兵不管我媽小聲警告,依然固執緊抱著,不肯松手。我媽想喊又憋住,莫名其妙產生了憐惜,心突然軟了……
早春二月,郁悶了很長時間的我媽悄悄改變了,她頭不亂衣不臟,居然還穿一件當時很時髦的蘇聯風格墨綠連衣裙,像蛤蟆塘雨后的藕葉生動起來了。我父親注意到我媽的變化,他嘴上不吭氣,心里冰雪融化,為我媽的重新鮮活暗自叫好。
人是奇怪動物,明明設計好了生活軌道,明明知道沿著設計好的軌道生活不會錯,卻偏又不按既定的軌道走,像早春二月的天,說變就變。這一變,事情搞得一團糟。
大寒節令后的第二個夜晚,霜下得雪樣厚,靜靜地把小鎮覆蓋住了。我父親跺了跺已經凍麻的腳,使勁擤了擤鼻子,旋開了軍用水壺蓋,準備再抿一口酒。但酒壺空了。他猶豫了一下,決定回家去拿酒。
正要敲門,黑暗中傳來床板吱吱咯咯一片響,父親熟悉這種響動。他渾身顫抖了一下,按捺下心頭涌起的憤怒,準備悄悄撤退出去……
就在這時。我父親聽見我媽氣喘吁吁地說“討厭,討厭!”接下來又是吱吱咯咯的一片響聲……
父親像突然遭到了電擊,全身血液一起往上涌。他再也忍受不住,暴怒打開駁殼槍保險,一腳踹開了房門……
就在這一瞬間。一個男人慌忙從窗口跳了出去。
槍沒有響,我父親無力垂下手臂。他收起了駁殼槍。那人是憨兵,他看清楚了。
處在極度憤怒中的父親恨不得把我媽撕成碎片,他想都沒想一下,就五花大綁了我媽,送進公安局。這時,天已經蒙蒙亮,小鎮滿街盡是挑水洗菜做小買賣吆喝賣小吃和買早餐的人們。
回家邁進后院,父親才發覺自己處理事情太簡單化:我一臉鼻涕眼淚哭著喊著找我媽,外婆翻白眼癱在院子里。一院鄰居蜂擁過去掐人中……
父親傻眼了,又跑進公安局,趕緊把我媽領了回去。
我父親一大清早制造出來的緋聞就像我媽面食缽頭里的發面頭,迅速在小鎮上發酵了。女人們不管有空還是沒空、都三三兩兩聚一起指指點點……
人們悲悲切切喜氣洋洋,一會兒哀聲嘆氣一會兒笑得彎腰岔氣,連平日見面從不打招呼,彼此之間毫無瓜葛的人們也情不自禁走到了一起。
6
不吃不喝把自己關了一天,夜深人靜的時候,我媽像蛇一樣悄無聲息游出了大門。
我媽死了。
等我父親趕到湖邊的老柳樹下,我媽已經被人打撈上岸,尸體已被好心的蛤蟆塘漁民沖洗干凈。
我媽躺在草地上。草叢想托住她,但無能為力,我媽的身體還是緩緩陷進草叢里。我父親趕緊脫下軍大衣,把我媽裹住,緊緊攬進自己懷里。我父親凝神,屏住呼吸,集中自己的全部意志一聲不吭。用自己的體溫溫暖我媽的身體。過了好一陣,他才捧住我媽的臉,眼睛一動不動和她對視,嘴巴一張一翕對著我媽的耳朵根嘟囔個不停。
陸續趕來的人們手足無措,都站一邊屏氣凝神一眼一眼看我父親。
因為是早上。沒散盡的晨霧在我父親胡須眉毛尖上結成小水珠,晶晶瑩瑩,耀眼霜花似的,人們都以為我父親在淌眼淚。
我父親嘟囔的聲音很孱弱,不像平時咋咋呼呼很大聲音,人們支起耳朵努力聽,但我父親究竟給我媽講了些什么?誰也聽不清。
雨突然下下來,蘆葦蕩噼里啪啦一片響。一股很濃的海腥味和沼澤地的特殊氣味夾雜在空氣里。
我父親一直固執地摟著我媽,不準人們把我媽抬走。他小聲對大家說:“求你們了,別吵,讓她再睡一會兒,行不行?”
我媽沒有死,我媽不會死,我父親想,好好的人怎么會死掉呢?死人我父親見多了,抗日戰場、抗美戰場,多少戰友躺在他的懷抱中犧牲?那傷口,血汩汩地流,那眼睛睜得大大的,嘴張得大大的……我媽她不流血,眼睛閉著,嘴巴閉著,方才跟她講了那么多話都不理,要么是睡得沉,要么是真生氣?我父親從來都沒見我媽真生氣,這回,我媽是真生氣了。
真混,喝了那么多酒,還喝?娘的,怪誰?天太冷,不喝扛不住。
我媽是無辜的,都怪自己,是自己把事情鬧大了。還說要保護,不讓我媽這棵樹枯萎,保護個甚?
我父親在老柳樹下僵坐不動。嘴里依然嘟囔個不停……
…………
事情一晃就過去好幾年。
這天。我父親還在老柳樹下僵坐,姿勢還和幾年前的一個樣,只不過,懷里抱著的不再是我媽,而是他的軍用水壺。
我也跟父親去了蛤蟆塘,在不遠的地方抓蝌蚪,捉蜻蜓。
我父親被人忘記了。陷進無人問津的境地。但他喜歡這樣,喜歡一個人靜靜待在蛤蟆塘里。
一陣雨過后,藍天白云間現出一道彩虹。
肥厚的荷葉上。滾來滾去的水珠被陽光照耀得珍珠水晶般晶瑩剔透,蛤蟆塘呈現出她的另一種美麗。
轉瞬幾年,但父親覺得我媽剛走不久。沒人埋怨他、沒人譴責他,人們在父親面前絕口不提我媽的事情。但我父親知道,我媽就是因他而死,這是揮之不去的事情。
如果在當下,男人除了妻子還另有女人是一件極稀松平常的事情。父親生活在他的時代,除了我媽,心里頭再沒有別的秘密。要說有隱私,父親的隱私也是坦蕩的,愿意說的不愿意說的都是我媽的事情。他就像一個忠實的追隨者,腳踏生活的每一步都以我媽為中心。
父親還來老柳樹下喝酒。有人勸他再找一個伴侶,熱心人甚至替他張羅起相親……礙于人家的好意,父親答應了,但走著、走著,父親就像一匹識途的老馬,突然又朝蛤蟆塘走去。
我父親感覺到累了。
坐到蛤蟆塘的老柳樹下,嗅聞到蘆葦、小草的氣息就想起我媽,那拂在身上的暖風就像我媽柔軟的手,讓我父親不再感覺累,安寧下來了。
有好幾次,我父親聽見我媽說話了,那聲音輕輕的,恍若隔世,猶如在夢里……
聲音越來越近、越來越明的時候,又聽不清了,被蘆葦的沙沙聲淹沒了。每當此時,父親總會不甘心偏著腦袋再聽一陣,但每次都是失望。失望之余,我父親總要莫名其妙流幾滴淚水,越到后來,淚水越渾濁。
父親抿了一口酒,殘酒滲漏到了嘴角外,他伸手拉衣襟去擦嘴,發現衣裳邋遢得不成樣子,只好放棄,順嘴罵一句,“狗雞巴日的美帝國主義。”
這時候,我剛好跑過去,學著父親罵一句,“狗雞巴日的美帝國主義。”
父親裂開嘴笑了,表揚我,“有種,好樣的。”
一只鷹從暮色中掠過,父親突然振奮起來,瞇眼睛扭頭去尋鷹。我眼尖,發現那鷹降落在不遠處的草地上。我說,“爸爸,雞,在那里。”
我父親定眼細看,確實是剛才掠過的那只鷹,猥瑣地蹲在草地上。我父親心里頭想,怪不得兒子說雞呢,真他娘的像雞。嘴上卻對我說,“說甚呢?那是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