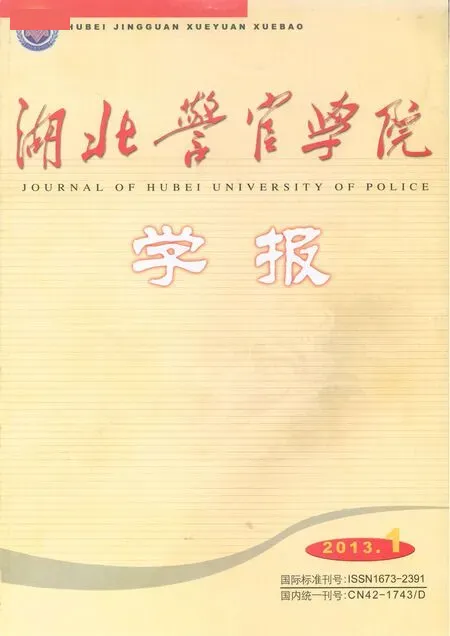交往斷裂:儒家禮法文化的隱含話語解讀
——以《論語》為中心的考察
李遠華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 法學院,湖北 武漢430073)
對儒家思想的研究,是基于文本并結合傳統文化現代化的現實語境的一種多面向闡釋。這就需要我們進一步深入領會與思考作為傳統文化核心的儒家思想的文本的內蘊涵義。正如海德格爾所言:“一切解釋都奠基于領會”。通過進一步理解儒家思想基本命題的能指與所指,明確“命題的展示、述謂與傳達”,從而使傳統文化在這種現象式的顯現中,讓人們看見,并在其規定性中展示出來,打破過去占統治地位的所謂“通行有效”的成見與僵化觀念,對于進一步認識儒家文化向現代化轉化的可能性,孔子與當代中國的關系,以及儒學面向現實、面向未來的可能性作用均有重要意義。①杜維明:《儒家傳統現代轉化的資源》一文,參見《孔子與當代中國》,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8年7月第1版,第11-23頁。本文試圖運用哈貝馬斯交往行為理論,對儒家經典的《論語》文本作分析,以從與我們通常所認識儒家禮法思想的不同的側面,探討文本所展示的不同的結構和意義,剖析儒家思想實際蘊含的深層思想傾向和觀念特征,對儒學的當代詮釋和現代化轉化作出響應。
通過參照交往行為理論的相關方法論原理,可以發現,在儒家禮法思想中存在一個較深層次的問題,即交往的斷裂。這種交往斷裂直接影響著儒家禮法思想的基本結構和主要面向。所謂交往斷裂,是指儒家思想在廣泛的社會關系的層面上有意或者無意地造成了“主體間性”②“主體間性(或主體際性)”為哈貝馬斯交往行為理論的重要概念,是指主體間的相互性、共通性及復數主體的歷時共存性,見龔群:《道德烏托邦的重構——哈貝馬斯交往倫理思想研究》,商務印書館2003年4月第1版,第4-9頁。的向度弱化或者虛化,從而成為一種類似于西方理性特色的主體哲學方法論上的意識形態禁錮,以一種隱蔽的方式弱化人們對社會傳統的批判反省意識。為了更清晰地對文本進行闡釋,我們打算參照哈貝馬斯提出的生活世界的基本結構三分法,即社會秩序、文化傳統、個體人格結構③關于社會秩序、文化傳統與個性結構的生活世界三分法,參見哈貝馬斯:《交往行為理論》,重慶出版社1994年版,第二卷。,從個體、家庭、社會等幾個方面對這種交往斷裂特征展開分析。
一、個體:反話語交往的人格塑造
每個社會個體,除了具有有目的的、有意圖的行為思考能力以及天生的社會性外,還具有一個最重要的特征,那就是語言。“使我們人類超出自然之外的只有一件東西,語言。通過它的結構,自律和責任就都被安置在我們門下了。我們最初的語句毫無疑問地表達了那種普遍的、非強迫性的交感意向,而自律和責任一起構成了我們先天所擁有的唯一觀念。”④這一觀點最初由哈貝馬斯于1965年6月在法蘭克福大學的就職演說中提出,見哈貝馬斯:《交往與社會進化》,重慶出版社1989年3月第1版,英譯本序第11頁。通過對儒家文本的分析,我們發現,除了我們看到的禮法制度對個人的道德意識與人格自我發展的重要影響外,在不同層面還隱含著對傳統人格塑造的反話語交往的偏向。
(一)對理想人格塑造的影響
孔子“追跡三代之禮,序《書傳》。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繆,編次其事。”(見《史記·孔子世家》)其目的就是要紹續三代之德,所謂述而不作,為往圣繼絕學,為當世作則,為后世垂范。孔子所推崇的理想人格目標就是祖述堯舜、章憲周武。孔子的人格最高理想就是體現五帝、三王、湯文武這些古代圣人身上的“仁”的道德本體和終極追求,將“仁標舉為道德人格發展的最高境界”①任建濤:《理想的契合——仁者、智者與自由民主的人格基礎》一文,見陳來、甘陽主編:《孔子與當代中國》,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8年7月北京第1版,第389頁。。在《論語》文本中,我們發現,“仁”與“禮”、“道”、“德”等體現道德追求的詞匯頻繁出現。其中“仁”在十七篇中出現,出現次數為93次。就“仁”來說,孔子在《論語》或者任何其他由其編纂的經典中,均沒有給出“是什么”的本體論式定義。但是,從文本中體現出的概念的外延的廣泛性來看,這種道德理想本體的“仁”,實際上就是遠遠高于一般道德要求的標準,是代表道統的仁人君子們所應該具備的道德品格。這種最高理想人格的塑造乃是依靠對所謂古圣先賢的榜樣的模仿。如,“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見《論語·季氏》)孔子平常引導學生們的,也就是前述包括他自己所體會到的君子理想人格。孔子以后的弟子繼而將孔子尊為“圣之時者”的圣人。這種理想人格的塑造,實際上是單向的,即預先設定一個高不可攀的理想標桿,然后通過君子、中人、小人這樣的鏈條,予以仿效。其道德評價的天平永遠都是偏向于君子、仁人一面,偏向于理想人格的一面,而對于除此之外是否還有一種另外的道德標準,是否還有一種反向的道德交流,是不予理會或者隱形拒斥的。
(二)個體人格發展的路徑偏向性
在孔子思想中的個體人格發展的實現路徑上,他強調“仁”對于“智”的優先性,或者道德人格對于理性人格的優先性。盡管可以將仁與智統一起來闡釋,如牟宗三先生認為的:“道德生命的發展,一方面須要仁,另一方面須要智來輔助與支持。仁且智的生命,好比一個瑩明清澈的水晶體,從任何角度看去都可以窺其全豹,絕無隱曲于其中,絕無半點瑕疵。”但是在孔子學說里,對于仁和智,對于道德人格與理性人格,是具有偏向性的。這就是表現在儒家人格發展中的對于“仁”的修養,對于禮的遵從。在《論語》文本中,“禮”共計出現67次,表現出了其對于道德教化的優先性,而邏輯與理性只能位居其次。孔子自己就是禮樂文化的集大成者,《易》、《詩》、《書》的編撰者,禮樂射御書數的傳承者。他對于弟子的教育,要求“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見《論語·泰伯》)。至于射御書數這些拓展個人體力與智力的技術性教育,孔子似乎偏偏刻意忽視。在《論語》文本中我們也少見孔子教授弟子探討相關問題。相反,孔子還認為不注重德行修養,而一味追求一技之長是不值得稱道的。他將一些具體技藝視為“鄙事”。孔子曰:“太宰知我乎!吾少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見《論語·子罕》)正是這種行孝悌于日用之間,無終食間違仁,將人格道德修養居于理智發展至上的優先性考量,導致了個體人格發展的偏向性,造成了個體人格的發展違背前習慣階段、習慣階段與后習慣階段的次第演進規律。其以人格鍛煉和心性修養為依歸,而個體的認同不依賴于社會交往的獲得,而在于與古圣先賢的道德本體的一致性、單向度的契合。
(三)個體間交往的去語言化特性
從孔子的道德人格理論,我們可以看到,在個人人格的理想塑造與每個人人格心理發展的道德化傾向下,還掩蓋了一種特征,即在孔子觀念體系中的對于個體之間交往的去語言化傾向。人的最重要的交往能力就是語言,這種“陳述被區分了的言語將人類從已被人類觀察到的其他靈長類動物的符號性中介的相互作用中區別了出來”;同時我們還借助語言,構建起賦予對方以可檢驗的有效性要求的“以言行事”意義上的交往社會關系。也就是語言既有描述社會關系的意義陳述功能,也有構建或者結構社會關系的檢驗批判功能。正因為如此,人的自然的或者社會的權利與義務,實際上與語言的表達及言語社會關系具有重要的關聯,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我們的話語實際上就是我們的社會權利義務關系的象征。在對儒家文本的考察中,在對《論語》的字里行間的分析中,我們發現了一種隱含的反話語交往的傾向。
孔子對于言語的態度,大致分為以下幾類:一是認為言語表現對于道德評價有直接的關系。這樣的例子很多,比如“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見《論語·學而》)“君子欲訥于言,而敏于行。”(見《論語·里仁》)“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見《論語·公治長》)以上話語中,孔子將言語作為衡量一個人是否賢德的標準。他認為,作為君子是不應該巧言善辯,不應該向別人展現他們運用語言或者玩弄詞匯的技巧的,應該表現得近乎“木訥”。二是將言語表現與禮儀君子的處事技巧聯系起來。他認為君子應該處處謹言慎行。譬如“子張學干祿。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余,則寡尤;多見闕殆,慎行其余,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見《論語·為政》)“孔子于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其在宗廟、朝廷,便便言,唯謹爾。”(見《論語·鄉黨》)“君子于其言,無所茍而已。”(見《論語·子路》)“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見《論語·憲問》)三是言語的語言表達作用與心靈的體悟相比,更重視心靈體悟。典型的如“子曰:‘予欲無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見《論語·陽貨》)。從以上我們可以看出,孔子認為言語行為,實際上要遵從道德準則的約束,凡是違背禮樂精神的言語行為都給予否定性評價。他認為,日常人們在社會生活中,最好是表現得謹言慎行,這樣才不至于作出違背禮樂的行為。即使一個人木訥不善于言辭,只要在行為上合乎禮儀的原則精神,往往比巧言善辯要更有利于維護道德和禮儀,更接近仁的境界。
(四)個體反思意識的消解
每個人成長到青年時期,個體逐漸意識到傳統的、固有的生活方式,可能被證明為僅僅具有某種慣性的合理性,個體角色的權利義務遵守模式被個體反思意識、自我的同一性取代。行為者在與其他社會主體交合的過程中,通過獨立的判斷看待各種假設有效性要求,并通過論辯或者爭論,理解和運用反思性規范。在孔子的話語結構中,我們往往看到的不是一種反思性規范的正確運用,而是反思性向度被回避,個體的反思意識被消解。
這種消解,在《論語》文本中主要表現在以下方面:一是孔子的言論,往往具有先驗道德命令的性質,或者本身就是道德規范。比如“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見《論語·學而》)“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見《論語·里仁》)而這些道德命令,在孔子看來,是神圣的,是不容置疑的。二是孔子十分贊賞弟子們對他的諄諄教誨細心領會,認真揣摩,在接受的時候表現木訥,在事后私下體會,在與其討論中卻能正確闡發,認真學習。“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以足以發。回也不愚。’”“攻乎異端,斯害也已。”(見《論語·為政》)三是孔子不主張君子在恭行孝弟之外,作更深入的關于人生與社會的反思性思考,忌諱對于人的本性與社會的本體、來自宇宙的本體,這些帶有本體的、抽象的存在做過多的探討。在孔子看來,只有體現行動和包含實際結果的語言才是重要的。而從語言的主動使用和被動使用中抽象出來的命題的意義是毫不相關的。由于中國古代漢語沒有抽象名詞,當我們認為中國古代沒有一個超越性概念時也就是這個意思。(見《論語·子罕》)四是孔子將仁人君子人格神圣化。在孔子的諸多言論中表現對于先賢的不加任何反思的遵從。孔子的弟子在孔子死后,極力維護孔子的圣賢地位:“仲尼,日月也,無得而逾焉。人雖欲自絕,其何傷于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在圣與仁的光輝下,任何對于其錯誤與不足的反思在這種語境中都是不合適的。
二、家族:親屬倫理的單向度義務對交往的阻隔
春秋戰國時期是古代歷史上的長期戰亂時期,道統陵替,禮樂廢弛。然而,這并不意味著中國社會發生了根本的變革。在治與亂之間,并沒有出現類似于西方階級社會的階級革命與社會制度的根本變革。所謂“湯武革命”只是王朝的更迭,并不是社會秩序的推翻與改建。正如梁漱溟先生所說,中國歷史上“只有周期的一治一亂而無革命”。對于家族倫理對言語交往關系的影響,我們從宗法家族制度、祖先崇拜與祭祀、孝道傳統這三個主要方面予以闡釋。
(一)宗法家族制度的影響
孔子生活的時代,商周宗法家族制度沒有完全解體。在宗法社會中,每個人實際上都處于較為嚴密的宗法家族制度的層層包裹之中。正如何懷宏先生所說:“我們在春秋歷史上所見到的重要人物,其后面都有一個家族,個人與家族共衰榮。因而,對于春秋歷史,我們印象最深刻的與其說是一個個的人,不如說是一個個的家族。”宗法家族制度對于個體之間的交往,在以下幾個方面具有阻滯性影響:一是,每個人在宗法家族制度下,首先是一個與其身份與地位不可分割的符號化載體。孔子提倡“正名”,實際上就是要通過“正名”,“將名用于‘實’并和‘實’保持相符”,恢復名所實際代表的周禮所規定的封建宗法等級制度的社會秩序和倫理關系。每個人從出身起,就已經根據他在家族的地位,在九族五服中的身份差異和上下等級,按承載一定特殊的權利義務的秩序分配到他在家族中的坐標之中。二是,家族制度對于家族內部個體之間的交往,不是從每個人出發,而是無條件地服從家長、族長權威。在家族的宗法倫理下,人際關系不具有對話的可能,只有作為權威的家長與族長才有發言權。三是,家族具有的教令子孫、裁處事務的法律上的現實強制力。宗子(或稱為宗族的族長)既是宗族祭祀的主祭人,也是宗族大小事務的最后裁判者。族長實際上等于族的執法者及仲裁者。族長在這方面的權威是至高的,族內的糾紛往往經他一言而決,其效力絕不下于法官。
(二)祖先崇拜與祭祀的影響
梁漱溟先生認為中國古代缺乏類似于西方社會宗教這樣一種意識形態。其最重要的原因在于祖先崇拜這種移情式的信仰轉移,使得“輕浮虛飄的人生,憑空添了千鈞的重量,意味綿綿,維系得十分牢韌!”一方面,祖先崇拜與祭祀從心理上剝奪了個體的統一的人格,將每個人通過這種信仰活動,“牢牢地限制在血緣與私人關系的圈子里,這不僅剝奪了他們渴望追求內在的‘統一的人格’的權利,而且助長了血緣關系的維系和發展。”另一方面,也在信仰意識形態方面將信仰的權力壟斷,“由國家規定的這種‘俗世宗教’,乃是一種對祖靈神力的信仰與崇拜。所有其他的民間宗教信仰,原則上仍停留在一種毫無系統性的、巫術與英雄的專門崇拜并存的階段上。”在祖先崇拜上,斷絕了通過個體與國家的祭祀禮儀所規定的意識形態的對話。每個家族、每個人乃至一個民族的祖先信仰具有前定的一致性。
(三)孝道思想的影響
孔子認為:“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見《論語·學而》)孔子將孝道作為仁人君子的根本準則。但是這種以孝道為根本,以孝道齊家、治國的基本準則,往往造成了對于交往關系的不利影響:首先,孝道重視單方面對于長輩的順從義務。一個人從孝弟的思想出發來考慮,就是“對于四面八方若遠若近的倫理關系,負有若輕若重的義務”。個人首先不是從自我的主體意識出發,而是必須從孝道的義務出發,從對親人長輩的倫理責任出發,從對兄弟姐妹的倫理義務出發,只有這樣才符合家族團體的內在語境。親屬倫理規范的意義在于對單方面的義務與權利的取予,而不是相互性的承認。其次,孝道最重要的是對于父母的意志的順從,特別是父,不再是一個血緣意識上的倫理主體,而更多的是具有精神上的權威的象征。因此作為子孫,他們的任何行為都要符合父母之命,否則就是不孝。這就是說一個人如果慣于標新立異,敢于創新,往往就是違背孝道的,會被認為是不孝順的逆子,甚至有犯上作亂的嫌疑。
三、社會:禮法關系對話語交往的壓制
中國古代社會通常被稱為禮法社會,實際上是說中國古代社會關系的家庭化、倫理化;社會秩序演自禮俗,倚重禮俗,而不在國家法制。其倫理原則和倫理精神滲透到了法律的各個領域,因為古代的社會關系也就是禮法關系。這種禮法關系對交往社會關系的影響,是從多方面體現出來的,特別是在君主與臣民、君子與小人、華夏與蠻夷等幾個方面最具有代表性。
(一)君主與臣民
梁漱溟先生說中國古代雖然只有士農工商職業分途,缺乏階級分野,但從整體來看,實際上存在階級的差別。中國古代,士人無疑是中國的統治階層,君主實際上處于士人階層的頂端,也處于整個社會金字塔的頂端。士人成為君主與民眾的政治上的中介,或者說士人成為政教合一的君主權力的從屬。君主、士人階層為一端,廣大庶民為另一端,形成了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社會結構。孔子說:“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見《論語·季氏》)臣子或者民眾,對君上以服從為義務,至于君主是否有錯,是否應該給予批評和建議,這是次要的。君主與臣民不是一種對話上的相互關系,而是基于權力神圣之下的服從關系。在這種情況下當然不容許有對話存在,更不用說存在相互交往的言語行為。在儒家政治的話語中,作為主體的廣大人民群眾,實際上被作為一種政治客體看待。在統治者與人民之間沒有實際上的對立關系,只有統治者道德上的善與惡、好與壞的差別,根本不存在反思權力作為一種主體間關系的社會基礎的可能性。“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見《論語·學而》)“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所重:民、食、喪、祭。”(見《論語·堯曰》)民眾在君主的意識中,永遠只是行政施行的對象。人民群眾作為一個群體,他們的話語行為無法被包括君主在內的主體發現,基于平等主體的話語交往被埋沒在仁政的話語結構下。
(二)君子與小人
君子在孔子的文本中,有多種蘊含意義和指代。它有的時候指的是最高統治者,有的時候指各級官吏,有的時候指代具有圣人品格的賢者。我們在這里主要指與小人相對而言的道德上具有“仁”品格的儒家理想中的士階層。根據儒家的思想,只有有德的人才有資格居高位,才能夠為政。君子是奉行儒家禮儀的表率,是孝弟忠信的嚴格踐行者,是“代表理性,主持教化”,維護禮樂秩序的“四民”(士農工商)之首。君子在士人活躍的時代里,就是全面達到自我完善的人。就傳統文獻所灌輸給其信徒的那種古典的、永恒的心靈美準則而言,君子們已成為一種“藝術作品”。君子與小人,在《論語》文本中,是孔子經常成對出現的概念。在這些話語中,隱含的實際上是一種對于話語交往關系的掣肘。這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首先,君子與小人在孔子的話語中,地位是不平等的,君子貴而小人賤。我們對《論語》文本中“君子”與“小人”被提及的次數進行了統計①這里的君子,包括文本中使用的“君”、“君子”、“士”等表述;小人包括“民”、“眾”、“人”、“小人”、“臣”、“匹夫”等表述,因此本統計數據具有一定的蓋然性。。“君子”在文本中共出現145次,其中作主語次數為106次,作賓語或者其他成分的為39次;“小人”在文本中出現133次,其中作主語次數為62次,作賓語或者其他成分的為71次。“君子”作主語的次數明顯多于作賓語或者其他成分的次數。“小人”作賓語或者其他句子成分的次數明顯多于作主語的次數。這說明,君子更具有主動性,小人多具有被動性,“唯上智而下愚不移”。其次,君子與小人的言語方式不一樣。君子是靠實實在在的行動取信于民,君子先行其言,而后從之,君子不言而信,思不出其位,小人敏于言而訥于行,言過其行。因此,要從小人提升為君子,就應該在言行方式上予以改變,不應過多地進行言語上的交流,而應該從自身德行上修養,修己以安人。再次,關于君子這種先驗的道德標準從何而來,在孔子看來,就是以傳說中的堯、舜、周公這些古代圣人的道德原則作為先驗來源。對于什么是普遍通行的道德標準,只能由這些先驗規范中推論出來。而實際上,道德作為一種社會現象,既無法從先驗的古代“圣王”德行那里推論出,也無法從任何一個其他的團體或者個人那里發現。一個普遍的、理想的道德規范,只能通過言語交往才能實現。正如哈貝馬斯所說:“進入約定的言說者通常都有這樣一種特定感覺,在這種感覺中,他愿意運用主題化被強調的有效性要求,從事某種人際關系的建立,并因此而選擇某種特定的交往模式。”
(三)華夏與蠻夷
對于跨文化的交往,從《論語》文本中,我們可以看到孔子站在文化中心主義的角度看待異己文化的立場。晚明關于“亡國與王天下”的主題也出現在孔子的思想中。“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見《論語·八佾》)“微管仲,吾其被發左衽矣。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于溝瀆而莫之知也。”(見《論語·憲問》)可以看出,孔子站在中原文化的立場上,以復興周禮為己任,魯就是周禮的直接繼承者,其他的諸侯國都應該以魯國為榜樣,通過倡導禮樂文化,推動禮樂衰微的其他諸侯國文化進步,從而實現“齊一變,至于魯,魯一變,至于道”這樣的目標。對于夷狄,孔子認為他們本身是落后的,是不講禮儀的野蠻部落,應該“尊王攘夷”,決不能讓夷狄落后的文化侵染先進的中原禮樂文化。在野蠻與文明之間,是不存在對話的可能的。因此,孔子的文化觀念從某種程度上否認了野蠻部落作為文明多樣性之一的主體地位。其過于強調禮樂文化的中心地位,不利于文化的交往與對話。
[1][2][3][德]海德格爾.存在與時間[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6:180,181,182.
[4]牟宗三.中國哲學的特質[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27.
[5][6][7][21][德]哈貝馬斯.交往與社會進化[M].重慶:重慶出版社,1989:42,64,70,81-85.
[8][11]張斌峰.人文思維的邏輯——語用學與語用邏輯的維度[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106,78.
[9][15][16][17][19]梁漱溟全集(第二卷)[M].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90:170,174,175,185.
[10]陳來,甘陽.孔子與當代中國[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8:223.
[11]瞿同祖.中國法律與中國社會[M].上海:中華書局,1981:24.
[12]梁漱溟.東西文化及其哲學[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13 6.
[13][14][18][20][德]馬克斯·韋伯.儒教與道教[M].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7:14,168,127,155.
[22][德]哈貝馬斯.作為意識形態的技術與科學[M].上海:學林出版社,1999:1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