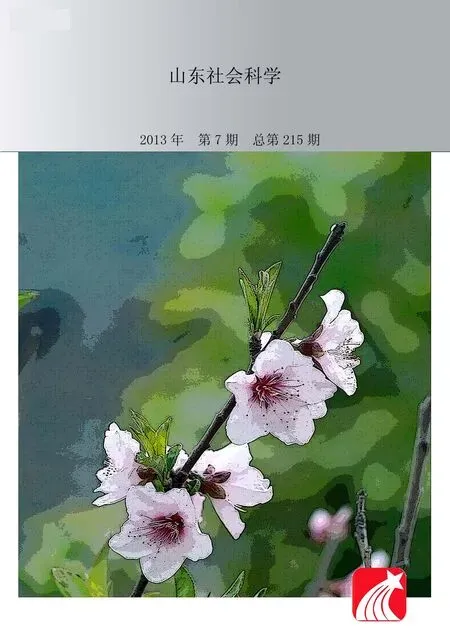芳賀矢一《國民性十論》與周氏兄弟
李冬木
(佛教大學 文學部,日本 京都 603-8301)
一、《國民性十論》的話語背景及其作者
原書日文名稱與中文漢字相同:《國民性十論》。日本明治四十(1907)年十二月,東京富山房出版發行。作者芳賀矢一(Haga Yaichi,1867—1927)。
出版機構“富山房”,由實業家坂本嘉治馬(Sakamoto Kajima,1866—1938)于明治十九(1886)年在東京神田神保町創立,是日本近代,即從“明治”(1868—1912)到“大正”(1912—1926)時代具有代表性的出版社之一,主要以出版國民教育方面的書籍著稱。“(自創立起),爾來五十余年,專心斯業之發展,竭誠盡力刊行于教學有益書籍,出版《大日本地名辭書》、《大言海》、《漢文大系》、《大日本國語辭典》、《日本家庭大百科事匯》、《佛教大辭匯》、《國民百科大辭典》、《富山房大英和辭典》等辭典以及普通圖書、教科書合計三千余點,舉劃時代之事功而廣為國民所知者”。注株式會社冨山房インターナショナル會社概要。參見該公司網站:http://www.fuzambo-intl.com/?main_page=companyinfo.——現今子公司“株式會社富山房國際”引先人之言,雖未免自夸,卻也大抵符合實際。日本國會圖書館現存富山房出版物約950種,僅明治時代出版的就占了630余種,除單行本外,還有各種文庫,如“名著文庫”、“袖珍名著文庫”、“新型袖珍名著文庫”、“世界哲學文庫”、“女子自修文庫”等,各種“全書”,如“普通學全書”、“普通學問答全書”、“言文一致普通學全書”等;而進入“昭和”(1926—1989)以來最著名的是“富山房百科文庫”,從戰前一直出到戰后,共出了100種。就“明治時代”而言,富山房雖不及另一出版巨擘博文館——大橋佐平(Ohashi Sahei,1836—1901)于明治二十(1887)年創立于東京本鄉區弓町,僅明治時代就出版圖書3970種[注]參見拙文《澀江保譯〈支那人氣質〉(上)》,《關西外國語大學研究論集》第67號,1998,第271頁。——卻也完全稱得上出版同業當中的重鎮了。富山房明治出版物中,同期就有不少中譯本,值得關心近代出版的朋友注意。
顧名思義,《國民性十論》是一本討論“國民性”問題的專著。如果說世界上“再沒有哪國國民像日本這樣喜歡討論自己的國民性”,而且討論國民性問題的文章和著作汗牛充棟,不勝枚舉的話,[注]南博『日本人論——明治から今日まで』まえがき(前言),巖波書店,1994年10月。那么《國民性十論》則是在日本近代以來漫長豐富的“國民性”討論史中占有重要地位的一本,歷來受到很高評價,影響至今。[注]參見久松潛一『「日本人論」解題』,富山房百科文庫,1977。近年來的暢銷書、藤原正彥(Fujiwara Masahiko,1943—)的《國家品格》[注]『國家の品格』,新潮社「新潮新書141」,2005年。在內容上也顯然留有前者的痕跡。
“國民性”問題在日本一直是一個與近代民族國家相生相伴的問題。作為一個概念,Nationality從明治時代一開始就被接受,只不過不同時期有不同的叫法。例如在《明六雜志》就被叫做“人民之性質”[注]參見『明六雑誌』第三十號所載中村正直「人民ノ性質ヲ改造スル説」(改造人民之性質說)。明治十二(1879)年出版的『英華和訳辭典』(プロシャイト原作、敬宇中村正直校正、津田仙·柳澤信大·大井鎌吉著)既以「ジンミンノセイシツ,jin-min no seishitsu」即「人民ノ性質」(人民之性質)來注釋英文Nationality(國民性)了。和“國民風氣”,[注]參見『明六雑誌』第三十二號所載西周「國民気風論」(國民風氣論)。其原標題「國民気風」旁邊標注日語片假名「ナシオナルケレクトル」,即英文National Character(國民氣質,國民性)之音讀。在“國粹保存主義”的明治20年代被叫做“國粹”,[注]參見志賀重昂「『日本人』が懐抱する処の旨議を告白す』(告白《日本人》所懷抱之旨義),『日本人』第二號,明治二十一(1888)年四月十八日。明治30年代又是“日本主義”[注]參見高山樗牛「日本主義を賛す」(贊日本主義),『太陽』3巻13號,明治三十七(1897)年六月二十日。的代名詞,“國民性”一詞是在從甲午戰爭到日俄戰爭的10年當中開始被使用并且“定型”。日本兩戰兩勝,成為帝國主義時代國際競爭場中的一員,在引起西方“黃禍論”恐慌的同時,也帶來民族主義(nationalism)的空前高漲,“國民性”一詞便是在這一背景下應運而生。最早以該詞作為文章題目的是文藝評論家綱島梁川(Tsunashima Ryosen,1873—1907)的《國民性與文學》,[注]「國民性と文學」,本文參閱底本為『明治文學全集46·新島襄·植村正久·清沢満之·綱島梁川集』(武田清子、吉田久一編,筑摩書房、1977年10月)。發表在《早稻田文學》明治三十一(1898)年五月號上,該文使用“國民性”一詞達48次,一舉將這一詞匯“定型”。而最早將“國民性”一詞用于書名的則正是10年后出版的這本《國民性十論》。此后,自魯迅留學日本的時代起,“國民性”作為一個詞匯開始進入漢語語境,從而也將這一思想觀念一舉在留日學生當中展現開來。順附一句,作為一個引進的外來詞,“國民性”一詞幾乎不見于迄今為止中國大陸出版的基本辭書(74卷本《中國大百科全書》和12卷本《現代漢語大辭典》這類巨型工具書除外),卻又在研究論文、各類媒體乃至日常生活中普遍使用,其在當今話語中的主要“載體”是“魯迅”。——以上與“國民性思想史”相關的各個要點之詳細情形,請參閱筆者的相關研究。[注]李冬木:《“國民性”一詞在中國》,(日本)佛教大學『文學部論集』第91號,2007年;《“國民性”一詞在日本》,(日本)佛教大學『文學部論集』第92號,2008年。(中國)二文同時刊載于《山東師范大學學報》2013年第4期。
芳賀矢一出生于日本福井縣福井市一個神官家庭,其父任多家神社的“宮司”(神社之最高神官)。在福井、東京讀小學,在宮城讀中學后,18歲入“東京大學預備門”(相當于高中),23歲考入東京帝國大學(現東京大學)國文科,4年后畢業。歷任中學、師范學校和高中教員后,明治三十二(1899)年33歲時被任命為東京帝國大學文科大學助教授(副教授)兼高等師范學校教授。翌年奉命赴德國留學,主攻“文學史研究”,同船者有后來成為日本近代文豪的夏目漱石(Natsume Soseki,1867—1916)。一年半后的1902年——也就是魯迅留學日本的那一年——芳賀矢一學成回國,不久就任東京帝國大學文科大學教授,履職到大正十一(1922)年退休。[注]參見久松潛一編「芳賀矢一年譜」,収入『明治文學全集』44巻,筑摩書房,昭和四十三(1978)年。
芳賀矢一是近代日本“國文學”研究的重要開拓者。如果按現在的理解,近代國民國家離不開作為其“想像的共同體”[注]Benedict Anderson語,參見吳叡人譯:《想象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步》,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5年版。之基礎的“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注]胡適語,參見《建設的文學革命論》,《新青年》四卷四號,1918年4月。的話,那么芳賀矢一對日本語言和文學所作的整理和研究,其“近代意義”也就顯而易見。他是公認的首次將德國“文獻學”(philologie)導入到日本“國文學”研究領域的學者,以“日本文獻學”規定“國學”,并通過確立這一新的方法論,將傳統“國學”轉換生成為一門近代學問。明治三十七(1904)年一月發表在《國學院雜志》上的《何謂國學?》一文集中體現了他的這一開創性思路,不僅為他留學之前的工作找到了一個“激活”點,亦為此后的工作確立了嶄新的學理起點,呈現廣博而深入之大觀。“據《國語與國文學》(十四卷四號【1937年4月——引者注】)特輯《芳賀博士與明治大正之國文學》所載講義題目,關于日本文學史的題目有《日本文學史》、《國文學史(奈良朝平安朝)》、《國文學史(室町時代)》、《國文學思想史》、《以解題為主的國文學史)》、《和歌史》、《日本漢文學史》、《鐮倉室町時代小說史》、《國民傳說史》、《明治文學史》等;作品研究有《源氏物語之研究》、《戰記物語之研究》、《古事記之研究》、《謠曲之研究》、《歷史物語之研究》;文學概論有《文學概論》、《日本詩歌學》、《日本文獻學》、《國學史》、《國學入門》、《國學初步》等;在國語學方面有《國文法概說》、《國語助動詞之研究》、《文法論》、《國語與國民性》等。在‘演習’課上,還講過《古今集》、《大鏡》、《源氏物語》、《古事記》、《風土記》、《神月催馬樂》及其他多種作品,大正六年【1917年——引者注】還講過《歐美的日本文研究》。”[注]久松潛一『解題芳賀矢一』,『明治文學全集』44巻,筑摩書房,昭和四十三(1978)年,第428頁。由此可知芳賀矢一對包括“國語”和“文學”在內的日本近代“國學”推進面之廣。就內容的關聯性而言,《國民性十論》一書不僅集中了上述大跨度研究和教學的問題指向——日本的國民性,也出色地體現出以上述實踐為依托的“順手拈來”的文筆功力。芳賀矢一死后,由其子芳賀檀和弟子們所編輯整理的《芳賀矢一遺著》可示其在研究方面留下的業績:《日本文獻學》、《文法論》、《歷史物語》、《國語與國民性》、《日本漢文學史》。[注]『芳賀矢一遺著』二卷,富山房,1928年。而日本國學院大學1982—1992年出版的《芳賀矢一選集》7卷,應該是包括編輯和校勘在內的現今所存最新的收集和整理。[注]芳賀矢一選集編集委員會編『芳賀矢一選集』,國學院大學,東京,1982-1992。第1巻『國學編』、第2巻『國文學史編』、第3巻『國文學篇』、第4巻『國語·國文典編』、第5巻『日本漢文學史編』、第6巻『國民性·國民文化編』、第7巻『雑編·資料編』。
二、《國民性十論》的寫作特點和內容
《國民性十論》是芳賀矢一的代表作之一,也是他社會影響力最大的一本書。雖然關于日本的國民性,他后來又相繼寫了《日本人》(1912)、《戰爭與國民性》(1916)和《日本精神》(1917),但不論取得的成就還是對后來的影響,都遠不及《國民性十論》。書中的部分內容雖來自他應邀在東京高等師范學校所做的連續講演,卻完整保留了其著稱于當時的富于“雄辯”的以書面語講演[注]小野田翠雨『現代名士の演説振り——速記者の見たる』(現代名士演說風范——速記者所見),『明治文學全集』96巻,筑摩書房,昭和四十二(1967)年,第366-367頁。的文體特點。除此之外,與同時期同類著作相比,該書的寫作和內容特點仍十分明顯。前面提到,在日本近代思想史當中,從“日清戰爭”(即甲午戰爭,1894—1895)到“日俄戰爭”(1904—1905),恰好是日本“民族主義”空前高漲的時期,而這同時也可以看作是“明治日本”的“國民性論”正式確立的時期。日本有學者將這一時期出現的志賀重昂(Shiga Shigetaka,1863—1927)的《日本風景論》(1894)、內村鑒三(Uchimura Kanzo,1861—1930)的《代表的日本人》(1894,1908)、新渡戶稻造(Nitobe Inazo,1862—1933)的《武士道》(1899)和岡倉天心(Okakura Tenshin,1863—1913)的《茶之心》(1906)作為“‘富國強兵——‘日清’‘日俄’高揚期’”的“日本人論”代表作來加以探討。[注]船曳建夫『「日本人論」再考』,講談社,2010年。具體請參照該書第二章,第50-80頁。但作者完全“屏蔽”了同一時期更具代表性《國民性十論》,干脆沒提。就拿這4本書來說,或“地理”,或“代表”人物,或“武士道”,或“茶”,都是分別從不同側面來描述和肯定日本的價值即“國民性”的嘗試,雖然各有成就,卻還并不是關于日本國民性的綜合而系統的描述和闡釋。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這4本書的讀者設定。除了志賀重昴用“漢文調”的日語寫作外,其余3本當初都是以英文寫作并出版的。[注]《代表的日本人》原題Japan and The Japanese,明治二十七(1894)年由日本民友社出版,明治四十一(1908)年再從前書選出部分章節,改題為Representative Men of Japan,由日本覺醒社書店出版,而鈴木俊郎的日譯本很久以后的昭和二十三(1948)年才由巖波書店出版;《武士道》原題Bushido: the soul of Japan,1900年在美國費城出版(許多研究者將出版年寫作“1899”,不確),明治四十一(1908)年才有丁未出版社出版的櫻井鷗村的日譯本;《茶之書》原題THE BOOK OF TEA,1906年在美國紐約出版,昭和四(1929)年才有巖波書店出版的岡村博的日譯本。也就是說,從寫作動機來看,這些書主要還不是寫給普通日本人看的,除第一本面向本國知識分子訴諸“地理優越”外,后面的三本都是寫給外國人看的,目的是尋求與世界的對話,向西方介紹開始走向世界舞臺的“日本人”。
芳賀矢一的《國民性十論》與上述著作的最大不同,不僅在于它是從“國民教育”的立場出發,面向普通日本人來講述本國“國民性”之“來龍去脈”的一個文本,更在于它還是不見比于同類的、從文化史的觀點出發、以豐富的文獻為根據而展開的綜合國民性論。作為經歷“日清”“日俄”兩戰兩勝之后,日本人開始重新“自我認知”和“自我教育”的一本“國民教材”,該書的寫作方法和目的,正如作者自己所說,就是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通過比較的方法和歷史的方法,或宗教,或語言,或美術,或文藝來論述民族的異同,致力于發揮民族特性”,[注]參見《國民性十論·序言》。建立“自知之明”。[注]參見《國民性十論·結語》。
全書分十章討論日本國民性:(一)忠君愛國;(二)崇祖先,重家名;(三)講現實,重實際;(四)愛草木,喜自然;(五)樂天灑脫;(六)淡泊瀟灑;(七)纖麗纖巧;(八)清凈潔白;(九)禮節禮法;(十)溫和寬恕。其雖然并不回避國民“美德”中“隱藏的缺點”,但主要是討論優點,具有明顯的從積極的肯定的方面對日本國民性加以“塑造性”敘述的傾向。第一、二章可視為全書之“綱”,核心觀點是日本自古“萬世一系”,天皇、皇室與國民之關系無類見于屢屢發生“革命”、改朝換代的東西各國,因此“忠君愛國”便是“早在有史以前就已成為浸透我民族腦髓之箴言”,是基于血緣關系的自然情感;“西洋的社會單位是個人,個人相聚而組織為國家”,而在日本“國家是家的集合”,這種集合的最高體現是皇室,“我皇室乃國家之中心”。其余八章,可看做此“綱”所舉之“目”,分別從不同側面來對“日本人”的性格進行描述和闡釋,就內容涉及面之廣和文獻引用數量之多而言,的確可堪稱為前所未有的“國民性論”和一次關于“日本人”自我塑造的成功的嘗試。而這也正是其至今仍具有影響力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我國,日本人“自己寫自己”的書,除新渡戶稻造的《武士道》之外,其他有影響的還并不多見。而關于日本及日本人的論述,從通常引用的情況看,最常見的恐怕是“本尼迪克特”的《菊與刀》,求其次者,或許“賴肖爾”的《日本人》也可算上一本。這兩本書都出自美國人之手,其所呈現的當然是“美國濾鏡”下的“日本”。芳賀矢一的這一本雖然很“古老”,卻或許有助于讀者去豐富自己思考“日本”的材料。
三、關于本書中的“支那”
同日本明治時代的其他出版物一樣,“中國”在書中被稱作“支那”。關于這個問題,特作一下說明: “支那”作為中國的別稱最早見于佛教經典,據說用來表示“秦”字的發音,日本明治維新以后到二戰結束以前普遍以“支那”稱呼中國,因這一稱呼在甲午戰爭后逐漸帶有貶義,招致中國人的強烈反感和批評,日本在二戰結束后已經終止使用,在我國的出版物中也多將舊文獻中的“支那”改為“中國”。事實上,“支那”(不是“中國”)在本書中是作者使用的一個很重要的參照系,由此可感知在一個特定的歷史階段日本知識界對所謂“支那”懷有怎樣的心像。
在日本明治話語,尤其是涉及到“國民性”的話語中,“支那”是一個很復雜的問題,并不是從一開始就像在后來侵華戰爭全面爆發后所看到的那樣,僅僅是一個貶斥和“懲膺”的對象。事實上,在相當長的時間內,“支那”一直是日本“審時度勢”的重要參照。例如《明六雜志》作為“國名和地名”使用“支那”一詞的頻度,比其他任何國名和地名出現得都要多,即使是當時作為主要學習對象國的“英國”和作為本國的“日本”都無法與之相比。[注]參見「『明六雜志』語彙総索引」,高野繁男、日向敏彥監修、編集,大空社,1998年。這是因為“支那”作為“他者”,還并不完全獨立于“日本”之外,而往往是包含在“日本”之內,因此拿西洋各國來比照“支那”也就往往意味著比照自身,對“支那”的反省和批判也正意味著在很大程度上是對自身的反省和批判。這一點可以從西周的《百一新論》對儒教思想的批判中看到,也可以在中村正直(Nakamura Masanao,1832—1891)為“支那”辯護的《支那不可辱論》(1875)[注]「支那不可辱論」,『明六雜志』第三十五號,明治八(1875)年四月。中看到,更可以在福澤諭吉(Fukuzawa Yukichi,1834—1901)《勸學篇》(1872)、《文明論之概略》(1877)中看到,甚至可以在專門主張日本的“國粹”,“以圖民性之發揚”[注]三宅雪嶺『真善美日本人』,生松敬三編『日本人論』,富山房,昭和五十二(1977)年,第17、34頁。該書初版為明治二十四(1891)年政教社版。的三宅雪嶺的《真善美日本人》(1891)中看到——書中以日本人了解“支那文化”遠遠勝過“好學之歐人”為榮,并以“向全世界傳播”“支那文明”為“日本人的任務”。[注]三宅雪嶺『真善美日本人』,生松敬三編『日本人論』,富山房,昭和五十二(1977)年,第17、34頁。該書初版為明治二十四(1891)年政教社版。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后來的所謂“脫亞”[注]語見明治十八(1885)年3月16日『時事新報』社説「脫亜論」,一般認為該社論出自福澤諭吉之手。事實上,“脫亞”作為一種思想早在在此之前福澤諭吉就表述過,在《勸學篇》和《文明論概略》中都可清楚地看到,主要是指擺脫儒教思想的束縛。也正是要將“支那”作為“他者”從自身當中剔除的文化上的結論。在芳賀矢一的《國民性十論》當中,“支那”所扮演的也正是這樣一個無法從自身完全剔除的“他者”的角色,除第十章以“吃人”做比較的材料所顯現的“貶損”傾向外,“支那”在全書中大抵處在與“印度”和“西洋”相同的參照位置上,總體還是在闡述日本從前在引進“支那”和“印度”文化后如何使這兩種文化適合自己的需要。
四、周作人與《國民性十論》
《國民性十論》不僅是魯迅的目睹書,更是周作人的目睹書,該書至少有助于解讀與周氏兄弟相關,卻因年代久遠和異域(中國和日本)相隔而至今懸而未決的若干問題。
到目前為止,在最具代表性的《魯迅年譜》[注]魯迅博物館魯迅研究室編《魯迅年譜》四卷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和《周作人年譜》[注]張菊香、張鐵榮編著《周作人年譜》,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中還查不到“《國民性十論》”這本書,更不要說對周氏兄弟與該書的關系展開研究。就筆者閱讀所限,中國學者最早在關于周作人的論文中談到“芳賀矢一”的,或許是現中國社科院文學研究所趙京華研究員1997年向日本一橋大學提交的博士論文[注]「一橋大學大學院社會學研究科博士論文。論文題目:周作人と日本文化、著者:趙京華(Zhao,JingHua)、論文審査委員:木山英雄、落合一泰、菊田正信、田崎宣義。1997」。筆者所見該論文得自趙京華先生本人。,只可惜尚未見正式出版。
芳賀矢一在當時是知名學者,《朝日新聞》自1892年7月12日至1941年1月10日的相關報道、介紹和廣告等有337條;《讀賣新聞》自1898年12月3日至1937年4月22日相關數亦達186條。“文學博士芳賀矢一新著《國民性十論》”,作為“青年必讀之書、國民必讀之書”[注]《國民性十論》廣告詞,『東京朝日新聞』日刊,明治40(1907)年12月22日。也是當年名副其實的暢銷書,自1907年底初版截止到1911年,在短短四年間就再版過八次。[注]本稿所依據底本為明治四十四(1911)年九月十五日發行第八版。報紙上的廣告更是頻繁出現,而且一直延續到很久以后。[注]《朝日新聞》延續到昭和10(1935)年1月3日;《讀賣新聞》延續到同年1月1日。甚至還有與該書出版相關的“趣聞軼事”,比如《讀賣新聞》就報道說,由于不修邊幅的芳賀矢一先生做新西服“差錢”,西服店老板就讓他用《國民性十論》的稿費來抵償。[注]「芳賀矢一博士の洋服代「國民性十論」原稿料から差し引くユニークな店/東京」(芳賀矢一博士的西服制裝費從〈國民性十論〉的稿費里扣除——東京特色西服店),『読売新聞』1908年6月11日。
在這樣的情形之下,《國民性十論》引起周氏兄弟的注意便是很正常的事。那么兄弟倆是誰先知道并且注意到芳賀矢一的呢?回答應該是乃兄周樹人即魯迅。其根據是,就在《國民性十論》出版引起社會反響并給芳賀矢一帶來巨大名聲時,魯迅已經是在日本有5年半多留學經歷的“老留學生”了,他對于與自己所關心的“國民性”相關的社會動態當然不會視之等閑,此其一;其二,通過北岡正子教授的研究可知,魯迅離開仙臺回到東京后不久就進了“獨逸語專修學校”,從1906年3月初到1909年8月回國,魯迅一直是作為這所學校的學生度過了自己的后一半留學生活,一邊學德語,一邊從事他的“文藝運動”,而在此期間該校特聘芳賀矢一擔任“國語”(即日本語文)教學的兼課教師。[注]參見北岡正子『魯迅救亡の夢のゆくえ——悪魔派詩人論から「狂人日記」まで』「第一章〈文蕓運動〉をたすけたドイツ語——獨逸語専修學校での學習」,関西大學出版部,2006年3月20日。關于芳賀矢一任“國語”兼課教員,請參看該書第29頁,注(30)。從上述兩點來推測,即便還不能馬上斷言魯迅與芳賀矢一有著直接的接觸,也不妨認為“芳賀矢一”應該是魯迅身邊的一個不能無視的存在。不論從社會名聲還是從著作進而是從課堂教學來講,芳賀矢一都不可能不成為魯迅關注的閱讀對象。相比之下,1906年9月才跟隨魯迅到東京的周作人,留學時間短,又不大諳日語,在當時倒不一定對《國民性十論》有怎樣的興趣,而且即便有興趣也未必讀得了,他后來開始認真讀這本書,有很大的可能是受了乃兄的推薦或建議。比如說匆匆拉弟弟回國謀事,尤其預想還要講“日本”,總要有些參考書才好,魯迅應該比當時的周作人更具備判斷《國民性十論》是一本合適參考書的能力,他應該比周作人更清楚該書可做日本文學的入門指南。而從周作人后來的實踐來看,其所體現的也正是這一思路。當然,這是后話。
不過,關于這本書最早留下文字記錄的卻是周作人。據《周作人日記》,他購得《國民性十論》是1912年10月5日[注]《周作人日記(影印本)》(上),大象出版社1996年版,第418、501-502頁。,大約一年半后的1914年5月14日有購入相關參考資料和同月17日“閱國民性十論”的記錄,而大約又過了一年四個多月之后的1915年9月“廿二日”,亦有“晚,閱《國民性十論》”的記錄。[注]《周作人日記(影印本)》(上),大象出版社,1996年版,第580、740-741頁。而周作人與該書的關系,恐怕在其1918年3月26日的日記中最能體現出來:“廿六日……得廿二日喬風寄日本文學史國民性十論各一本”[注]《周作人日記(影印本)》(上),大象出版社,1996年版,第580、740-741頁。——周作人前一年,即1917年因魯迅的介紹進北京大學工作,同年4月1日由紹興抵北京,與魯迅同住紹興會館補樹書屋[注]前出《周作人年譜(1885-1967)》,第121、131頁。——由此可知《日本文學史》和《國民性十論》這兩本有關日本文學和國民性的書是跟著周作人走的。不僅如此,1918年4月19日,周作人在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小說研究會上做了可堪稱為他的“日本研究小店”[注]《〈過去的工作〉跋》(1945),鐘叔河編《知堂序跋》,岳麓書社1987年版,第176頁。掛牌開張的著名講演,即《日本近三十年小說之發達》(4月17日寫作,5月20日至6月1日在雜志上連載[注]前出《周作人年譜(1885-1967)》,第121、131頁。),其中就有與《國民性十論》觀點上的明確關聯(后述)。與此同時,魯迅也在周作人收到《國民性十論》的翌月即1918年4月開始動筆寫《狂人日記》,并將其發表在5月出版發行的《新青年》四卷五號上,其在主題意像上出現接下來所要談的與前者的關聯,殆并非偶然吧。
筆者曾在另一篇文章里談過,截止到1923年他們兄弟失和以前的這一段,周氏兄弟所閱、所購、所藏之書均不妨視為他們相互之間潛在的“目睹書目”。[注]拙文《魯迅與日本書》,《讀書》2011年9期。兄弟之間共享一書,或誰看誰的書都很正常。《國民性十論》恐怕就是其中最好的一例。這本書對周氏兄弟兩個人的影響都很大。魯迅曾經說過,“從小說來看民族性,也就是一個好題目”。[注]《華蓋集續編·馬上支日記》,《魯迅全集》第3卷,第333頁。如果說這里的“小說”可以置換為一般所指“文學”或“文藝”的話,那么《國民性十論》所提供的便是一個近乎完美的范本。前面提到,在這部書中,芳賀矢一充分發揮了他作為“國文學”學者的本領,也顯示了作為“文獻學”學者的功底,用以論證的例證材料多達數百條,主要取自日本神話傳說、和歌、俳句、狂言、物語以及日語語言方面,再輔以史記、佛經、禪語、筆記等類,以此推出“由文化史的觀點而展開來的前所未見的翔實的國民性論”。[注]南博『日本人論——明治から今日まで』,巖波書店,1994年10月,第46頁。這一點應該看做是對周氏兄弟的共同影響。
尤其是對周作人。在周作人收藏的一千四百多種日本書[注]拙文《魯迅與日本書》,《讀書》2011年9期。當中,芳賀矢一的《國民性十論》對他的“日本研究”來說,無疑非常重要。事實上,這本書是他關于日本文學史、文化史、民俗史乃至“國民性”的重要入門書之一,此后他對日本文學研究、論述和翻譯也多有該書留下的“指南”痕跡。周作人在多篇文章中都援引或提到芳賀矢一,如《游日本雜感》(1919)、《日本的詩歌》(1921)、《關于〈狂言十番〉》(1926)、《〈狂言十番〉附記》(1926)、《日本管窺》(1935)、《元元唱和集》(1940)、《〈日本狂言選〉后記》(1955)等。而且也不斷地購入芳賀矢一的書,繼1912年《國民性十論》之后,目前已知購入的還有《新式辭典》(1922—購入年,下同)、《國文學史十講》(1923)、《日本趣味十種》(1925)、《謠曲五十番》(1926)、《狂言五十番》(1926)、《月雪花》(1933)、《芳賀矢一遺著》(富山房,1928出版,購入年不詳)。[注]在《元元唱和集》(《中國文藝》3卷2期,1940年10月)中有言“據芳賀矢一《日本漢文學史》”。《日本漢文學史》非單行本,收入《芳賀矢一遺著》,1928年由富山房出版。總體而言,在由“文學”而“國民性”的大前提下,周作人所受影響主要在日本文學和文化的研究方面,包括通過“學術與藝文”[注]參見《親日派》(1920),鐘叔河編:《周作人文類編7·日本管窺》,湖南文藝出版社1998年版,第619-621頁。《日本管窺之三》(1936),出處同前,第37-46頁。看取日本國民性的視角。這里不妨試舉幾例。
周作人自稱他的“談日本的事情”始于1918年5月發表的《日本近三十年小說之發達》。該文在五四時期亦屬名篇,核心觀點是闡述日本文化和文學的“創造的模擬”或“模仿”,而這一觀點不僅是基于對芳賀矢一所言“模仿這個詞有語病。模仿當中沒有精神存在,就好像猴子學人”(第三章“講現實,重實際”)的理解,也是一種具體展開。
又如,從1925年開始翻譯《〈古事記〉中的戀愛故事》,[注]載《語絲》第9期。到1926年《漢譯〈古事記〉神代卷》,[注]載《語絲》第67期。再到1963年出版《古事記》全譯本,[注]日本安萬侶著,周啟明譯,人民文學出版社1963年版。可以說《古事記》的翻譯是在周作人生涯中持續近40年的大工程,但看重其作為“神話傳說”的文學價值,而不看重其作為史書價值的觀點卻始終未變,雖然周作人在這中間又援引過很多日本學者的觀點,但看重“神話”而不看重“歷史”的基本觀點,最早還是來自芳賀矢一:“試觀日本神話。我不稱之為上代的歷史,而不恤稱之為神話。”(第一章“忠君愛國”)
再如,翻譯日本狂言也是可與翻譯《古事記》相匹敵的大工程,從1926年譯《狂言十番》[注]周作人譯:《狂言十番》,北新書局1926年版。到1955年《日本狂言選》,[注]周啟明譯:《日本狂言選》,人民文學出版社1955年版。前后也經歷了近30年,總共譯出24篇,皆可謂日本狂言之代表作,由中可“見日本狂言之一斑”。[注]周啟明:《〈日本狂言選〉后記》,鐘叔河編:《周作人文類編7·日本管窺》,第365頁。這24篇當中有15篇譯自芳賀矢一的校本,占了大半:《狂言十番》譯自后者校本《狂言二十番》6篇,《日本狂言選》譯自后者校本《狂言五十番》9篇。而最早與“芳賀矢一”及其校本相遇還是周作人在東京為“學日本語”而尋找“教科書”的時代:
那時富山房書房出版的“袖珍名著文庫”里,有一本芳賀矢一編的《狂言二十番》,和宮崎三昧編的《落語選》,再加上三教書院的“袖珍文庫”里的《俳風柳樽》初二編共十二卷,這四冊小書講價錢一總還不到一元日金,但作為我的教科書卻已經盡夠了。[注]周作人:《知堂回想錄》(上),“八七 學日本語續”,止庵校訂,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74頁。
作為文學“教科書”,芳賀矢一顯然給周作人留下了比其他人更多的“啟蒙”痕跡。這與芳賀矢一在當時的“出版量”以及廉價易求的“文庫本”直接有關。日本國會圖書館現藏署名“芳賀矢一”出版物42種,由富山房出版的有24種,屬富山房文庫版的有7種:《狂言二十番》(袖珍名著文庫第7,明治三十六〔1903〕年)、《謠曲二十番》(同名文庫第14,出版年同前)、《平治物語》(同名文庫第41,明治四十四〔1911〕年)、《保元物語》(名著文庫,卷40,出版年同前)、《川柳選》(同名文庫,卷50,大正元(1912)年)、《狂言五十番》(新型袖珍名著文庫,第9,大正十五〔1926〕年)、《謠曲五十番》(同名文庫,第8,出版年同前)。這些書與周作人的關系還有很大的探討空間。而尤為重要的是,芳賀矢一把他對各種體裁的日本文學作品的校訂和研究成果,以一種堪稱“綜合”的形式體現在了《國民性十論》當中。對周作人來說,這就構成了一個相對完整的“大綱”式教本——雖然“有了教本,這參考書卻是不得了”[注]周作人:《知堂回想錄》(上),“八七 學日本語續”,止庵校訂,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74頁。——為消化“教本”讓他沒少花功夫。
此外,周作人在對日本詩歌的介紹當中,芳賀矢一留下的影響也十分明顯。由于篇幅所限,這里不做具體展開,只要拿周作人在《日本的詩歌》(1921)、《一茶的詩》(1921)、《日本的小詩》(1923)、《日本的諷刺詩》(1923)等篇中對日本詩歌特點、體裁及發展流變的敘述與本書的內容對照比較,便可一目了然。
當然,對《國民性十論》的觀點,周作人也并非全盤接受,至少就關于日本“國民性”的意義而言,周作人所作取舍十分明顯。總體來看,周作人對書中闡述的“忠君愛國”和“武士道”這兩條頗不以為然(《游日本雜感》1919、《日本的人情美》1925、《日本管窺》1935)。雖然周作人認為確認“萬世一系”這一事實本身對于了解日本的“重要性”,而且像芳賀矢一那樣介紹過臣民中很少有人“覬覦皇位”的例子(《日本管窺》),雖然周作人在把對日本文化的解釋由“學術與藝文”擴大到“武士文化”時,也像芳賀矢——樣舉了武士對待戰死的武士頭顱的例子,以示“武士之情”(《日本管窺之三》1936),但對這兩點都有前提限制,關于前者,認為“忠孝”非日本所固有,關于后者,意在強調“武士之情”當中的“忠恕”成分。而他對《國民性十論》所做評價是“除幾篇頌揚武士道精神的以外,所說幾種國民性的優點,如愛草木喜自然,淡泊瀟灑,纖麗纖巧等,都很確當。這是國民性的背景,是秀麗的山水景色,種種優美的藝術制作,便是國民性的表現。我想所謂東方文明的里面,只這美術是永久的永久的榮光,印度中國日本無不如此”。[注]周作人:《游日本雜感》,《新青年》6卷6號,1919年11月刊。鐘叔河編:《周作人文類編7·日本管窺》,第7頁。
還應該指出的是,越到后來,周作人也就越感到“日本”帶給他的問題,而“芳賀矢一”自然也包括在其中。例如,1935年周作人指出:“日本在他的西鄰有個支那是他的大大方便的事,在本國文化里發現一點不愜意的分子都可以推給支那,便是研究民俗學的學者如佐藤隆三在他新著《貍考》中也說日本童話《滴沰山》(Kachikachi yama)里貍與兔的行為殘酷非日本民族所有,必定是從支那傳來的。這種說法我是不想學,也并不想辯駁,雖然這些資料并不是沒有。”[注]知堂:《日本管窺》,《國文周報》12卷18期,1935年5月,鐘叔河編:《周作人文類編7·日本管窺》,第26頁。其實這個例子周作人早就知道,因為芳賀矢一在《國民性十論》第十章“溫和寬恕”里講過,“這恐怕不是日本固有的神話”,而是“和支那一帶的傳說交織轉化而來的”,由此可知,周作人從當初就是“不想學”的。
到了寫《日本管窺之四》的1937年,年輕時由芳賀矢一所獲得通過文藝或文化來觀察日本“國民性”的想法已經徹底發生動搖,現實中的“日本”令周作人對這種方法的有效性產生懷疑:“我們平時喜談日本文化,雖然懂得少數賢哲的精神所寄,但于了解整個國民上我可以說沒有多大用處”,“日本國民性終于是謎似的不可懂”。[注]原載《國文周報》14卷25期,1937年6月,署名知堂,鐘叔河編:《周作人文類編7·日本管窺》,第56頁。這意味著他的“日本研究小店的關門卸招牌”。[注]《〈過去的工作〉跋》(1945),鐘叔河編:《知堂序跋》,岳麓書社1987版,第176頁。——就周作人對日本文化的觀察而言,或許正可謂自“芳賀矢一”始,至“芳賀矢一”終吧。
五、魯迅與《國民性十論》
筆者曾撰文探討魯迅《狂人日記》“吃人”這一主題意象的生成問題,認為其與日本明治時代“食人”言說密切相關,是從這一言說當中獲得的一個“母題”。為確證這一觀點,筆者主要著手兩項工作,一項是對明治時代以來的“食人”言說展開全面調查和梳理,另一項是在該言說整體當中找到與魯迅的具體“接點”,在這一過程中,芳賀矢一和他的《國民性十論》“浮出水面”,因此,“魯迅與《國民性十論》”這一題目也就自然包括在了上述研究課題中。論文題目為《明治時代“食人”言說與魯迅的〈狂人日記〉》,發表在《文學評論》2012年1期(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上,詳細內容請讀者參閱這篇文章,這里只述大略。
與周作人相比,魯迅對《國民性十論》的參考,主要體現在他對中國“國民性”問題的思考方面。具體而言,魯迅由芳賀矢一對日本國民性的闡釋而關注中國的國民性,尤其是對中國歷史上“吃人”事實的注意。
在魯迅文本中沒有留下有關“芳賀矢一”的記載,不過,不提不記不等于沒讀沒受影響。事實上,在“魯迅目睹書”當中,他少提甚至不提卻又受到很深影響的例子的確不在少數。[注]請參閱拙文《魯迅與日本書》,以及筆者關于《支那人氣質》和“丘淺次郎”研究的相關論文。芳賀矢一的《國民性十論》也屬于這種情況,只不過問題集中在關于“食人”事實的告知上。具體請參閱第十章“溫和寬恕”,芳賀矢一在該章中舉了12個中國舊文獻中記載的“吃人”的事例,其中《資治通鑒》4例,《輟耕錄》8例。筆者以為,正是這些事例將中國歷史上“吃人”的事實暗示給了魯迅。其推查過程如下:
《狂人日記》發表后,魯迅在1918年8月20日致許壽裳的信中說:“偶閱《通鑒》,乃悟中國人尚是食人民族,因成此篇。此種發見,關系亦甚大,而知者尚寥寥也。”這就是說,雖然史書上多有“食人”事實的記載,但在《狂人日記》發表的當時,還很少有人意識到那些事實,也更少有人由此而意識到“中國人尚是食人民族”;魯迅是“知者尚寥寥”當中的“知者”,他告訴許壽裳自己是“偶閱《通鑒》”而“乃悟”的。按照這一說法,《資治通鑒》對于“食人”事實的告知便構成了《狂人日記》“吃人”意象生成的直接契機,對作品的主題萌發有著關鍵性影響。
魯迅讀的到底是哪一種版本的《資治通鑒》,還有待進一步探討。不過,在魯迅藏書目錄中未見《資治通鑒》。[注]參閱《魯迅手跡和藏書目錄》(內部資料),北京魯迅博物館編,1957年;《魯迅目睹書目——日本書之部》,中島長文編刊,宇治市木幡御藏山,私版300部,1986年。《魯迅全集》中提到的“《資治通鑒》”,都是作為書名,而并沒涉及到其中任何一個具體的“食人”記載,因此,單憑魯迅文本,目前還并不能了解到究竟是“偶閱”到的哪些“食人”事實令他“乃悟”。
不排除魯迅確實直接“偶閱”《資治通鑒》文本這一可能性,也還可以做這樣的推斷:即魯迅當時“偶閱”到的還有可能是《國民性十論》所提到的4個例子而并非《資治通鑒》本身,或者還不妨進一步說,由《國民性十論》當中的“《資治通鑒》”而過度到閱讀《資治通鑒》原本也并非沒有可能。但正如上面所說,在魯迅文本中還找不到他實際閱讀《資治通鑒》的證據。
另外,芳賀矢一援引8個例子的另一文獻、陶宗儀的《輟耕錄》,在魯迅文本中也有兩次被提到,[注]《中國小說史略:第十六篇明之神魔小說(上)》,《魯迅全集》第9卷,第57頁。《古籍序跋集:第三分》,第10卷,第94頁。只不過都是作為文學史料,而不是作為“食人”史料引用的。除了“從日本堀口大學的《腓立普短篇集》里”翻譯過查理路易·腓立普(Charles-Louisphilippe,1874—1909)《食人人種的話》[注]參見《〈食人人種的話〉譯者附記》,《譯文序跋集》,《魯迅全集》第10卷。和作為“神魔小說”資料的文學作品“食人”例子外,魯迅在文章中只舉過一個具體的歷史上“吃人”的例子,那就是在《抄靶子》當中所提到的“兩腳羊”:“黃巢造反,以人為糧,但若說他吃人,是不對的,他所吃的物事,叫作‘兩腳羊’。”1981年版《魯迅全集》注釋(2005年版注釋內容相同)對此作出訂正,說這不是黃巢事跡,并指出材源:“魯迅引用此語,當出自南宋莊季裕《雞肋編》”。[注]收入《準風月談》,《魯迅全集》第5卷,第205頁。這一訂正和指出原始材源都是正確的,但有一點需要補充,那就是元末明初的陶宗儀在《輟耕錄》中照抄了《雞肋編》中的這個例子,這讓芳賀矢一也在讀《輟耕錄》時看到并且引用到書中:“宋代金狄之亂時,盜賊官兵居民交交相食,當時隱語把老瘦男子叫‘饒把火’,把婦女孩子叫‘不慕羊’,小兒則稱做‘和骨爛’,一般又叫‘兩腳羊’,實可謂驚人之至。”私以為,魯迅關于“兩腳羊”的模糊記憶,不一定直接來自《雞肋編》或《輟耕錄》,而更有可能是芳賀矢一的這一文本給他留下的。
截止到魯迅發表小說《狂人日記》為止,中國近代并無關于“吃人”的研究史,吳虞在讀了《狂人日記》后才開始做他那著名的“吃人”考證,也只列出8例。[注]參見《吃人與禮教》,《新青年》六卷六號,1919年11月1日。調查結果表明,“食人”這一話題和研究是在明治維新以后的日本展開的。《國民性十論》的重點并不在于此,卻因其第十章內容而與明治思想史當中的“食人”言說構成關聯,其之于魯迅的意義,是促成魯迅在“異域”的維度上重新審視母國,并且獲得一種對既往閱讀、記憶以及身邊正在發生的現實故事的“激活”,也就是魯迅所說的一個“悟”。
總之,即使只把話題限定在“周氏兄弟”的范圍,也可略知《國民性十論》對于中國五四以后的思想和文學有著不小的意義。
2012年3月15日于大阪千里
【附識】
本文是為即將在商務印書館出版的芳賀矢一《國民性十論》中譯本所做的導讀(略有改動),翻譯此書的直接動機,緣于在檢證魯迅思考“國民性”問題時所閱文獻過程中的一個偶然發現:芳賀矢一著《國民性十論》不僅是魯迅的目睹書,更是周作人的目睹書,于是,“《國民性十論》與周氏兄弟”便作為一個問題浮出。對其檢證的結論之一,便是作為一個譯本,該書至少有助于解讀與周氏兄弟相關,卻因年代久遠和異域(中國和日本)相隔而至今懸而未決的若干問題。這是我們為商務印書館“日本學術文庫”提供這一中譯本的緣由所在。
相信讀者在閱讀中還會有更多的發現和新的解讀。通過調查和翻譯,檢證并確認兩者關系的存在,不論對周氏兄弟的研究來說,還是對整個中國現代文學的研究來說,都是一個發現,因為截止到2012年1月筆者發表《明治時代的“食人”言說與魯迅的〈狂人日記〉》(《文學評論》同年1期)為止,“芳賀矢一”和“《國民性十論》”作為兩個固有名詞還幾乎不為上述研究界所知,更不要說引起注意。論文發表后,引發了各種不同意見,如果把反對的意見做一個歸納,那么大致都指向一點,即否定《國民性十論》與周氏兄弟存在關系。對此值得反思的是論文本身恐有言不達意之處,或許應做出更充分的論證才好,從這個意義上講,本篇導讀乃至整個中譯本便都是不可或缺的補充了。這樣,此后的反對意見才或許可信,因為至少不會再像現在這樣,連原書都沒看,更不自己動手去找證或反證的資料,就能斷言“事實上,沒有證據能夠證明”……“存在哪怕是絲毫的關系”,或“不能成立”之類。
——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