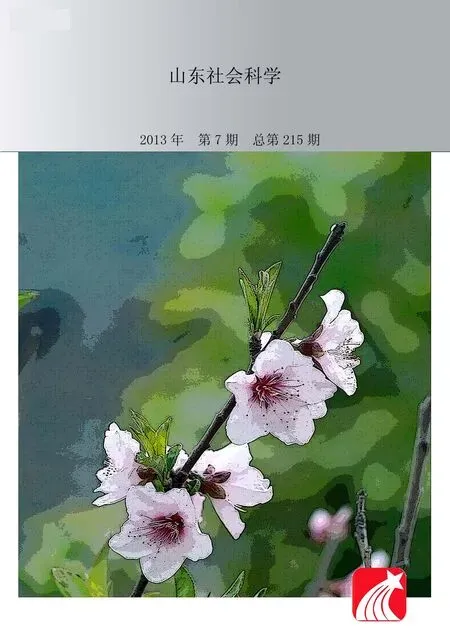從“立腳點”重思新唯物主義“新”在何處
——《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第10條的考辨
單提平
(山東大學 哲學與社會發展學院,山東 濟南 250100)
面對馬克思的《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阿爾都塞曾經這樣感嘆道:“《提綱》的各條,猶如短暫的火花,讓走近它們的每一位哲學家都眼前一亮。然而,眾所周知,火花只是眩目一瞬,卻不能照明通途:在漆黑的夜晚,要想給劃過的閃電定位,是何其困難之事。總有一天,我們不得不表明,這十一條看似透明的提綱真的就是一團謎。”①Louis Althusser,For Marx,Trans.by Ben Brewster,Verso,London,New York,1990,p.36.也許,阿爾都塞有些夸大其詞了,但時至今日,《提綱》依然激發著學者們的探究熱情和想象空間則是不爭的事實。隨著時間的推移,人們逐漸發現它是馬克思哲學中最簡短卻又最難讀的文本,圍繞這一文本衍生出各種解讀模式和路向,攪動起思想界一次又一次的波瀾。《提綱》第10 條申說了新舊唯物主義立腳點的差異,不啻找到撬動社會變革的“阿基米德點”。本文僅就此條展開追問和考辨,重思馬克思的“新唯物主義”之“新”。
一、《提綱》第10 條的辨識修訂及解釋分歧
眾所周知,馬克思生前并未發表《提綱》,是恩格斯在1888年重新發表《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時,翻檢出《提綱》,作了辨識,修訂發表出來的。由于馬克思《提綱》原文的思辨性,加之辨識修訂版本與馬克思原文文字上的差異,導致后人在理解上衍生出極大的分歧。
為方便說明,這里先引用馬克思在1845年寫作的《提綱》第10 條原文及中文權威譯文:“Der Standpunkt des alten Materialismus ist die 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der Standpunkt des neuen die menschliche Gesellschaft oder die gesellschaftliche Menschheit.”②MEGA1,Band 5,Berlin,1932,S.535.(舊唯物主義的立腳點是市民社會,新唯物主義的立腳點則是人類社會或社會的人類。③《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 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02頁。
恩格斯的辨識和修訂主要體現在三個詞上:第一,bürgerliche 化為斜體并加引號,表示強調;第二,menschliche 化為斜體,表示強調;第三,gesellschaftliche 辨識為或者說修訂為vergesellschaftete。這樣,譯成中文就是:舊唯物主義的立腳點是“市民”社會;新唯物主義的立腳點則是人類社會或社會化的人類。④《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 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06頁。
可以看出,恩格斯的改動已經打上了他對馬克思的理解的印記,既提醒讀者需要注意的重心,又對馬克思原文費解之處作了自己的辨識和處理。長期以來,人們站在馬克思恩格斯一致論的立場,認為恩格斯修訂本更完善,因而基本上是依據恩格斯修訂版本解讀馬克思的思想,并沒有意識到這里有什么問題。但問題在于,人們的解讀特別是對新唯物主義立腳點的解讀出現了兩種方向上涇渭分明的理解。
其一,把新唯物主義立腳點解讀為未來的社會主義社會或共產主義社會,并強調社會化的人類是無產階級。如果細分,又可以分為兩種情況,第一情況是國內學界主要依據前蘇聯學者的理解,從政治立場上,把市民社會解讀為資產階級社會,與之相對應,人類社會就是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社會。①[蘇聯]弗·然·克列:《關于馬克思的著作〈費爾巴哈論提綱〉》,《教學與研究》1955年第3期;樂燕平:《怎樣讀〈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前線》1962年第18期。這種解讀方式在上世紀90年代前占據了主流。另一種情況是受西方馬克思主義人道主義思潮影響的解讀,雖仍然把它解讀為未來社會,但卻把市民社會解讀為人性異化的社會,而把人類社會解讀為人性復歸的未來社會。值得說明的是,朱光潛先生重譯的《提綱》譯文對后一種理解也有較強的學理支持。他認為:“‘社會化的人類’,依原文die gesellschaftliche Menschheit,沒有‘化’的意思,應譯為‘社會性的人類’,前一詞‘人類社會’原文是die menschliche Gesellschaft,亦可譯為‘人性的社會’。”②朱光潛:《對〈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譯文的商榷》,《社會科學戰線》1980年第3期,第40-41頁。當然,立足人性這一角度,西方馬克思主義的影響更不容忽視,特別是[德]恩斯特·布洛赫在《希望的原理》中對此的解讀,參見The Principle of Hope,I ,Trans.by Neville Plaice,Stephen Plaice and Paul Knight,The MIT Press,Cambridge,Massachusetts,1986,p.286.這就從價值判斷上為理解新唯物主義的立腳點提供了重要參考依據。有學者提出:“作為新唯物主義立足點的社會,既不是異化的物性社會,也不是生存斗爭的獸性社會,而是一個沒有階級剝削和統治的、真正符合人性的社會。”③李毅嘉:《試析〈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主題思想進展的螺旋式結構》,《東岳論叢》2009年第12期,第23頁。
其二,把新唯物主義的立腳點解讀為社會現實生活本身,④齊振海:《讀馬克思〈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北京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62年第1期。同樣,西方馬克思主義中另有一脈早就這樣理解,如悉尼·胡克(參見其《對卡爾·馬克思的理解》,重慶出版社1989年版,第301-305頁)。國內權威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史》(一卷本)是這樣解讀的:“舊唯物主義不懂得人的實踐性,因而也不了解人的社會性及其歷史發展,它的立腳點是脫離社會關系的抽象的個人;而新唯物主義的立腳點則是人們的實踐活動以及由此而產生的人們之間的全部社會聯系和關系,也即社會化了的人類。”⑤黃楠森主編:《馬克思主義哲學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47頁。另外一本較權威的教科書闡明得更清晰:“舊唯物主義的立腳點是市民社會中的‘市民’,即對市民社會成員的抽象的、孤立的理解。新唯物主義重視的是市民社會中人們的感性活動,它的立腳點是人們感性活動所形成的各種關系。”⑥莊福齡主編:《馬克思主義史》第1 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19頁。
“新唯物主義的立腳點”究竟是現實的社會,還是理想的社會?或者說,這樣追問本身就是不恰當的,應該作一種新的理解。筆者認為,從歷史語境中來說,難以說明新唯物主義的立腳點是一種未來社會,大致來說,可以理解為社會現實生活本身,但第二種觀點亦有其不足之處。為此,我們需要追溯和建構馬克思寫作的原初語境,考察破解這一難題。
二、選擇“立腳點”歷史語境的追溯及建構
在歷史語境中,我們很難認同傳統的習見:費爾巴哈固守市民社會的立場,馬克思則選擇了共產主義立場或人性的社會立場。歷史表明,從費爾巴哈也可以到達共產主義的立場,而且費爾巴哈比馬克思更多強調人性。如果我們對馬克思為何與費爾巴哈分道揚鑣、對其內在的演變邏輯和動力基礎如何作一番梳理,可以更易看清這一點。
回到歷史,我們知道,《基督教的本質》的出版引發了極大影響和爭論,費爾巴哈聲名大噪。馬克思、恩格斯堅定支持費爾巴哈,表達了熱烈歡迎的態度,馬克思甚至被費爾巴哈的論戰對手施蒂納看作是費爾巴哈的追隨者。回到文本,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對費爾巴哈這樣評價:“對國民經濟學的批判,以及整個實證的批判,全靠費爾巴哈的發現給它打下真正的基礎。”⑦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頁。費爾巴哈批判國民經濟學家什么呢,馬克思在手稿寫道:“在國民經濟學家看來,社會是市民社會,在這里任何個人都是各種需要的整體,并且就人人互為手段而言,個人只為別人而存在,別人也只為他而存在。”①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34頁。也就是說,按照馬克思的理解,國民經濟學家站在了市民社會的立場上構建整個經濟學體系,而費爾巴哈對此進行了人本學的社會批判。
那么,費爾巴哈有何發現?1844年8月11 日,馬克思致信費爾巴哈說:“您(我不知道是否有意地)給社會主義提供了哲學基礎,而共產主義者也就立刻這樣理解了您的著作。建立在人們的現實差別基礎上的人與人的統一,從抽象的天上降到現實的地上的人類這一概念。如果不是社會這一概念,那是什么呢?”②《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 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73-74頁。“人類”這一概念,是現實差別的人與人之間的統一,也就是“社會”,馬克思特意將此概念著重標出。在馬克思看來,費爾巴哈的唯物主義與此前的唯物主義有極大的不同,在費爾巴哈的哲學中,希望達致的正是人性的社會,類本質的實現。我們看費爾巴哈在1845年為自己《基督教的本質》的辯護,他說:“費爾巴哈把人的實體僅僅置放在社會性之中——,他是社會的人,是共產主義者。”③《費爾巴哈哲學著作選集》下卷,榮震華譯,商務印書館1984年版,第435頁。以費爾巴哈為出發點,舉起社會主義的旗幟,在當時是一種事實。馬克思早期的同路人赫斯正是在費爾巴哈的哲學基礎上,倡導真正的社會主義,即以博愛原則為基礎的人道的社會主義。
然而,問題就出在這里。馬克思在《手稿》中把費爾巴哈引為同道時,在某種程度上其實是對費爾巴哈的“誤讀”。馬克思所說的社會與費爾巴哈的理解已經不同,他對于社會的理解進入到社會核心經濟關系體系中,實際上已經超越了費爾巴哈的視野,只是沒有自覺意識到而已。這就造成了當時有些滑稽的局面,馬克思比費爾巴哈扎根更深,但還不能完全從費爾巴哈人道主義的邏輯中擺脫出來。
頗有意思的是,歷史的機遇恰在此刻出現,當馬克思在1844年底讀到施蒂納的《唯一者及其所有物》對費爾巴哈的激烈批判時,顯然自身也受到了強烈沖擊。施蒂納在書中對“社會”概念進行了解構。首先,施蒂納批判人們把社會神圣化的后果是作繭自縛:“我們能從中擁有一切的社會,是一個新的主子,一個新的幽靈,一個新的‘最高本質’,它把我們置于‘效勞與義務之中’!”④[德]施蒂納:《唯一者及其所有物》,金海民譯,商務印書館1989年版,第133頁。其次,施蒂納論證道,所謂社會,不過是外在于人的空洞概念:社會的詞源乃是大廳,是容納各個個體的人的場所而已,“在此表明了社會并非是通過我和你創造出來的,而是通過一個把我們組成兩個社會成員的第三個要素”⑤[德]施蒂納:《唯一者及其所有物》,金海民譯,商務印書館1989年版,第236頁。。施蒂納以近乎夸張怪誕的形式傳達了一個現實,在市民社會里,重要的不是社會,而是市民,獨立的、利己主義的個體是不能逾越的樞紐。
不能不說施蒂納擊中了費爾巴哈的要害。費爾巴哈從感性出發,直觀到的是獨立的個人,而非社會。按照費爾巴哈的理解,作為原子式的個人個體雖不完善,但卻是可以互補的。不幸的是,人把個體互補而來的完善投射為虛幻的上帝,即自身異化出去的類本質。因此,費爾巴哈強調回歸人性,將類實現是費爾巴哈提出的哲學任務。由于愛是從屬神領域過渡到屬人領域的最好橋梁,費氏的結論就是人們應該進行倫理實踐,建構愛的社會。個體與個體之間在此意義上聯接起來,費爾巴哈甚至說:“是個體,就意味著是‘利己主義者’,但這同時卻又意味著是共產主義者,不管愿意還是不愿意。”⑥《費爾巴哈哲學著作選集》下卷,榮震華譯,商務印書館1984年版,第426頁。這種說法無法真正有效回應施蒂納的批判,反而證明費爾巴哈的社會的虛幻和空心化。費爾巴哈沒有理解物質利益及其沖突的現實性,因而并不能有效批判國民經濟學,亦無法抗衡施蒂納極端利己主義的沖擊。
施蒂納《唯一者及其所有物》對馬克思的刺激無疑是巨大的,它迫使馬克思重新審視自己與費爾巴哈的關系,重新定位自己的哲學視野。⑦單提平:《重新檢視施蒂納對馬克思的意義》,《哲學動態》2009年第12期,第13-20頁。馬克思隨即發現了自己的優勢,他所贊揚費爾巴哈的恰好是他自己獨特的東西。他此前已經意識到只有人植根于社會現實的經濟關系中,人才能真正發現自己的真實存在,經濟關系乃是左右其他一切社會關系的基礎性的關系。費爾巴哈認識不到這一點,是其理論落入倫理說教的一個根本癥結。
這樣,馬克思因施蒂納的點醒(馬克思當然也不同意施蒂納的觀點,因為他也沒有深入論述到現實的交往,《德意志意識形態》論述甚詳,此不贅言)開始對費爾巴哈進行深刻批判。馬克思認識到,自己不是以費爾巴哈為前提和基礎,毋寧說是從社會現實生活中為費爾巴哈所論證的人奠定更深刻的基礎。那么,是否現實生活本身就是新唯物主義的立腳點呢?筆者認為問題也并非如此簡單。我們可以借助《提綱》提供的文本語境分析以及相關文本支持加以闡釋。
三、新唯物主義移動的“阿基米德點”
在“立腳點”的選擇上,不在于費爾巴哈與馬克思對未來社會的選擇是不是共產主義,而在于為共產主義論證的基礎是否可信。在《提綱》第10 條簡短的表述中,馬克思的辯證論述瓦解掉了“直觀”與“實踐”對立的思考方式、“實體”和“關系”對立的思考方式、“應然”和“實然”對立的思考方式,在人與社會的動態張力中把握著能夠撬動社會變革的阿基米德點。
首先,新唯物主義揚棄了對人感性直觀和對社會抽象觀察的思維方式。按照馬克思的提示:“從前一切唯物主義(包括費爾巴哈的唯物主義)的主要缺點是:對對象、現實、感性,只是從客體的或者直觀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們當作感性的人的活動,當作實踐去理解,不是從主體方面去理解。”①《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 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99頁。由此我們可以看到,面對同一事物,身處同一環境,費爾巴哈與馬克思的解讀就具有本質的差別。在舊唯物主義的視野里是感性直觀的表象,在新唯物主義看來則是主體實踐的活動。
馬克思把人安置在具體的實踐的活動中,社會不再虛無化。早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馬克思已經認識到:“正是在改造對象世界中,人才真正地證明自己是類存在物。這種生產是人的能動的類生活。”②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8頁。同樣的,社會與個體之間也在實踐活動中得以生成存在。馬克思強調:“正像社會本身生產作為人的人一樣,社會也是由人生產的。”③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83頁。因此,馬克思特別提出:“應當避免重新把‘社會’當作抽象的東西同個體對立起來。個體是社會存在物。”④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84頁。這些論斷所包蘊的意義在費爾巴哈的著作中是找不到的。因此,在《提綱》中,馬克思批判費爾巴哈的類是“內在的、無聲的,把許多個人自然地聯系起來的普遍性”、費爾巴哈“只能達到對單個人和市民社會的直觀”⑤《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 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01、502頁。。
第二,新唯物主義的立腳點重心在把握社會與人的辯證聯接關系。費爾巴哈實體性的思考方式導致社會與人是割裂的,即人被定義為原子式的個人,人與人之間的聯系是外在的必然性。而我們看馬克思對新唯物主義立腳點的界定,die menschliche Gesellschaft oder die gesellschaftliche Menschheit,英文對應是human society or social humanity⑥恩格斯第三處改動,把“社會的”改為“社會化的”對馬克思社會與人的相互生成反而起了干擾,此處不用。。權威譯文是“人類社會或社會的人類”,但中文語境中“人類”和“社會”都是集合名詞,有同義反復之嫌,不妨譯作“人的社會或社會的人”。只有兩個辯證關聯的事物他才如此安排,這蘊含著馬克思特有的思路。society(社會)與human(人)相關而不能等同,這里可以把human 看作現實的個人,與作為集合名詞的society 正好相反相成,它們正是在相互界定中的張力中生發出意義來。“人的社會”強調社會由現實的個人的生成性,“社會的人”強調社會對現實的個人的制約性。這種辯證關聯在歷史實踐中體現為動態的點,把握人就是立足于人在社會關系中表征為怎樣的歷史的存在、實踐的存在。所以在《提綱》中,馬克思強調:“在現實性上,人的本質是社會關系的總和。”⑦《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 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01頁。
關于這一點更為清晰的論述,可以在《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中找到補充佐證。馬克思在那里再次對割裂社會與個人的市民社會觀進行批判,認為孤立個人的立腳點不過是“美學假象”⑧《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 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頁。,因為他們看不到“產生這種立腳點(Standpunkt)的時代,正是具有迄今為止最發達的社會關系(從這種立腳點看來是一般關系)的時代。人是最名副其實的政治動物,不僅是可社會化的動物,而且是只有在社會中才能個體化的動物”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 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頁。譯文依據德文原文作了相應改動。參見Karl Marx,Grundrisse de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konomie (Rohentwurf)1857-1858,MELI,Moskau,1939,S.6.。
第三,新唯物主義的立腳點是從現實實踐維度中生成未來向度。既然新唯物主義的立腳點在于人與社會之間因實踐構建的充滿張力的動態關系,那么它本身就提示了一種可以改變的可能。在人與社會內在矛盾的交匯處,個體與社會作為不斷變化的函數項,生成了這一個確乎是移動的阿基米德點,在此基礎上新唯物主義哲學的開放性與實踐性品格得以體現。
馬克思在《提綱》最后提出改變世界的任務,社會本身就在變化中,個體與社會之間總是處于實踐的辯證關聯中,問題在于怎樣把人們自發創造的社會關系真正納入人的自覺掌控之中。馬克思強調:“共產主義對我們來說不是應當確立的狀況,不是現實應當與之相適應的理想。我們所稱為共產主義的是那種消滅現存狀況的現實的運動。”①《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 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39頁。實體化地理解新唯物主義的立腳點反而是不牢固的,實踐唯物主義立足于現實,在人與社會辯證發展的張力中向未來開放。它的開放性在于沒有封閉費爾巴哈人性社會的理解,但只有在馬克思奠定的基礎上,費爾巴哈的哲學才會重新煥發生機,在這一層面上,恩斯特·布洛赫所強調的費爾巴哈化的馬克思特別是提出的“社會化的人類,聯合著以自身為中介的自然,乃是家園世界的重建”②Ernst Bloch,The Principle of Hope,I ,Trans.by Neville Plaice,Stephen Plaice and Paul Knight,The MIT Press,Cambridge,Massachusetts,1986,p.286.的觀點顯得尤其意味深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