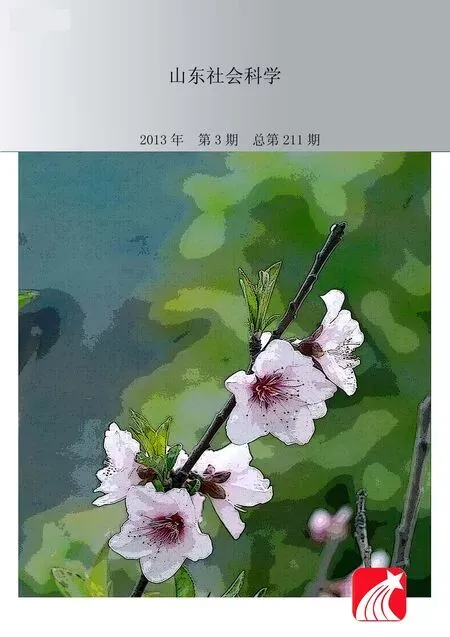荷爾德林:重建神話世界
李永平
( 中國社會科學院 外國文學研究所,北京 100732)
“現代性”作為一種現代世界觀,其最突出的標志,是它對人的主體地位的強調。從笛卡爾開始,近代哲學轉向了對作為主體的自我的探討,笛卡爾以“我思故我在”規定自我的本質,在他那里,“我思”成為上帝及自然世界存在的基礎,一切皆可懷疑,唯獨那個思維著的“我”不可懷疑,作為一個非肉體的、精神性的“我”,人可以憑借他天性中的“理性之光”①約翰·科延漢:《理性主義》,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4頁。,自由地塑造和主宰自己的命運以及宇宙的命運。因此,黑格爾說,笛卡爾使“哲學一下子轉入了一個完全不同的范疇,一個完全不同的觀點,也就是轉入了主體性的領域”②黑格爾:《哲學演講錄》第4卷,商務印書館1981年版,第4-5頁。。這個“主體性”(Subjektivit?t)即意味著獨立自主、自我決定、自由、能動性、自我、自我意識或自覺、個人的特殊性、以個人的自由意志和才能為根據等等。③張世英:《天人之際——中西哲學的困惑與選擇》,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1頁。“現代性”從一開始就是受這種主體性哲學支配的,它從根本上改變了人對待宇宙、自然以及上帝的觀念方式和態度,人不再是像以往那樣,在一個更大的秩序關系中來規定自己,而是擺脫了一切束縛,成為一個可以自我決定的主體,他的存在價值、意義和目的都必須在自我中尋找。人的主體地位的上升,同時也就帶來了自然地位的下降,自然成為不同于主體的客體,由作為主體的人去認識、利用、統治和征服。現代世界呈現出一種人與自然分裂的特征。
作為詩人,荷爾德林敏銳地體驗到了現代世界的這一分裂特征。在小說《許佩里翁》中,他寫道:
我們與自然分裂了,人們相信曾經為一的東西,現在自相矛盾,主仆雙方轉換。我們往往如此,仿佛世界是一切而我們為無,可往往也如此,仿佛我們是一切而世界為無。④Friedrich H?lderlin,S?mtliche Werke und Briefe in drei B?nde,Hg.v.Jochen Schmidt.Frankfurt am Main :Deutsche Klassiker Verlag,1994,Bd.2,p.256.
荷爾德林相信,人與自然原本是統一的,彼此和睦相處,人并沒有把自然當做統治和征服的對象。但在現代世界,這個原初的統一卻消失了,原來順從于自然的人,現在成了主人,役使自然為人服務,主仆關系發生了根本轉換。究竟是什么造成了這樣一種人與自然的分裂狀況?荷爾德林明確地將之歸結為人的理性和科學:
唉! 但愿我從來沒有走進你們的學校。科學,我追隨它走下隧道,帶著青春的憨愚,期待著證實我那純粹的歡樂,而它敗壞了我的一切。
我在你們那里變得真正理性起來,學會把我徹底地與我周圍相區別,現在孤立于美的世界,被這般拋出自然的花園,我曾在那里生長、盛開,而今枯萎在正午的烈日下。①Friedrich H?lderlin,S?mtliche Werke und Briefe in drei B?nde,Bd.2,p.16.
自17世紀啟蒙以來,現代人最引以為豪的東西,就是理性和科學,對其大加贊嘆。培根相信,唯有喚醒人身上的理性之火,才能夠讓人類駕馭自然。但恰恰是這個理性,在荷爾德林看來,卻把人與周圍的一切區別開來,人類用理性和科學征服自然的結果,最終是將自己拋出了“自然的花園”。荷爾德林和諾瓦利斯一樣,都將理性認識等同于一種分析的、邏輯的認識,它看不到世界是一個整體,是多樣性的統一,而是習慣于把事物分解為它的各種要素。因此,荷爾德林把現代看做分析的時代,在這個時代里,存在的完整性和統一性不復存在。
現代世界的分裂狀況,不僅構成荷爾德林那一代人的痛苦經驗,同時也決定了他們對彌合分裂、尋求統一的渴望。與黑格爾的概念化表達不同,荷爾德林以詩性的語言,把人與自然的分裂,表達為“諸神的逃逸”。荷爾德林的“諸神”,不是那些高高在上的、超驗的神,而是統御著人類生存的大自然的元素和力量,它們是大地與光、天空與海洋、河流與山谷、友誼與愛,所有這一切都被稱之為“諸神”。諸神的遠去意味著人與自然的分裂,而且因為人與諸神的疏遠,世界也變成了一個無神的世界。這一切,對荷爾德林來說,都是一種“神話狀態”(mythischer Zustand)的喪失。他相信,人曾經生活在“神話狀態”里:
當我還是個孩子的時候,/一位神常常救我/脫離人們的叫罵和鞭笞,/于是我安心而友好地/跟林中的花兒嬉游,/天空的微風/也來跟我嬉戲。
就像草木向你/伸出溫柔的手臂,/你使草木的心/感到高興,/父親赫利俄斯! 你也曾使我/心里高興,而且,/神圣的路娜! 我做過你的寵兒,/像恩底彌翁一樣。/哦,一切忠實的/親切的諸神! /但愿你們知道,/我的心多么喜愛你們!
雖然那時我還沒有稱呼/你們的名字,你們也從未/叫過我的名字,像人們相識時/彼此稱名那樣。
可是,我對你們的認識/比我向來對世人的認識更深,/我理解天空的寂靜,/我從不理解世人的語言。
沙沙的森林的知音/陶冶過我,/我在花間/學會了愛。/我在諸神的懷抱里長大。②Friedrich H?lderlin,S?mtliche Werke und Briefe in drei B?nde,Bd.1,pp.208-209.
在這首詩里,荷爾德林召喚出對童年的回憶,這不僅是他本人的童年,而且也是人類的童年。在這個童年時代里,人類受到諸神的庇護,他們純潔無邪,以愛的方式與諸神交往。但荷爾德林不得不痛苦地看到,人類已無法返回童年,因為他知道,“從童年到完滿”,所有人都必須“經過一條離心的軌道”③Friedrich H?lderlin,S?mtliche Werke und Briefe in drei B?nde,Bd.2,p.256.,此外別無他途。作為詩人,荷爾德林賦予他自己的偉大使命就在于,在歷史的更高階段上,重建業已失落的“人與諸神的關聯”,重新找到希臘人那種與自然和神靈的無拘無束的關系。
然而,在一個啟蒙的時代,荷爾德林如何可以重建一個神話世界?神話和啟蒙不恰恰是格格不入的嗎?正如啟蒙反對宗教一樣,它也將神話拒之于千里之外。啟蒙高標“理性”精神,認為只有理性才可以認識真理,只有以觀察為基礎的自然科學方法才是唯一可靠的求知方式。它把神話解釋成人類愚昧的產物,認為神話純屬臆造,充滿了迷信和謬誤。例如,豐坦涅說:“除了人類理性的迷誤的歷史之外,我們在古代傳說中找不到任何其他東西。”④《謝林傳》,商務印書館1990年版,第12頁。德國的早期啟蒙主義者戈特舍特也認為,神話低于理性,在發現和檢驗真理的過程中,必須將神話逐出理性話語的領域。⑤Manfred Frank,Der kommende Gott,Vorlesungen über die Neue Mythologie.Frankfurt am Main:Suhrkamp Verlag,1982,p.121.
盡管如此,在荷爾德林之前,針對啟蒙對神話的貶抑和拒斥,我們可以不斷聽到種種為神話正名的聲音,例如像維科、哈曼、赫爾德等人。維科在他的《新科學》中,試圖恢復“神話”精神與“理性”精神平起平坐的地位,他反對簡單地將神話看做無理性的幻覺,認為神話源出于人的一種天生的綜合能力,即想象力,它具有一種理性所不能達及的世界視野,可以把理性所分解離析的東西,重新融合,統一在一起。在神話中,人與自然達到統一。在德國,哈曼是最早批判啟蒙主義的神學家和哲學家,用以·伯林的話來說,“他是第一個以最公開、最激烈、最全面的方式向啟蒙主義宣戰的人”①以賽亞·伯林:《浪漫主義的根源》,譯林出版社2008年版,第53頁。。哈曼最初是啟蒙運動的信徒,但在經歷了一次深刻的精神危機之后,他轉而反對這場運動,與他的同鄉康德分道揚鑣。后者肯定啟蒙和理性主義,而哈曼則對理性主義的攻擊不遺余力。他的主要觀點是,所有的真理都是特殊的而不是普遍的,因此,理性沒有能力證明任何事物的存在,理性只不過是一個方便分類和組織材料的工具而已。無論自然還是歷史,都充滿了神奇而玄妙的意義,不是數學和邏輯的方式可以理解的。為此,哈曼為神話辯護,最早提出了神話不是關于世界的虛假陳述的觀點,他認為,神話既非虛妄之人的邪惡發明,用來迷惑人們的視聽,也非詩人憑空捏造出來的巧言麗詞,以便粉飾自己的詩作,神話是人類對大自然神秘感受的表達。哈曼將神話與詞語相比較,認為詞語言不及義,過于理性化,它總是根據分析模式,將紛繁的萬物加以分類,納入一個個嚴整的范疇之中,如此一來,詞語便破壞了對象本身,也就是說,破壞了生命和世界的統一性和連續性。相反,神話則是使用藝術意象和藝術象征而非詞語來傳達生命和世界的神秘,把人同自然的神秘性連接起來。②參見伯林關于哈曼的論述。維科和哈曼都超越了啟蒙的觀點,影響了后來浪漫主義的神話觀。荷爾德林是否直接受到過維科和哈曼的影響,我們不得而知,但他的“新神話學”與二人的觀點有頗多暗合之處,則無異議。
對荷爾德林有直接影響的是赫爾德。除了席勒,荷爾德林最為服膺的人,大概就算赫爾德了,他研讀過赫爾德幾乎所有發表的著作,在耶拿聽費希特的哲學講座期間,亦曾到魏瑪拜訪赫爾德。赫爾德關于神話的觀點,主要是文學的,而不是像維科和哈曼那樣是哲學和社會理論的,但他討論的是在啟蒙的條件下,神話在文學中的可能性,主張要創造性地運用古代神話,尤其是他看到了神話中所包含的“宗教價值”。而且,他認為,任何神話都是在民族的土壤中生長的,所以現代人不應僅僅在古代的神話中汲取材料,而應“為自己創造出一種全新的神話”③Manfred Frank,Der kommende Gott,Vorlesungen über die neue Mythologie.P.131.。這無疑啟發了荷爾德林和施萊格爾等人后來創造“新神話”的努力。當然,赫爾德對荷爾德林的影響更在于,他的整體生命觀。赫爾德反對啟蒙運動的人類學把人分割為肉體和靈魂、情感與理性,認為生命是一個充滿了創造力的整體,是不能用因果概念來解釋的,因為在因果關系中,一切都是可以預料的,而生命則是一個超出邏輯的神秘主義的過程,在這個整體生命中,每一個個體的多樣性都得到了充分的發揮,但個體又是相互關聯的。荷爾德林后來提出的“新神話學”就包含著這樣一種生命的整體關聯。
弗·施萊格爾1800年發表了《關于神話的演說》,他把詩看做神話,認為現代同古代的區別就在于,神話構成古代文化的內核,而現代文化所缺少的正是這樣一種神話,因而現代社會失去了中心。因此,現代人的任務就是為自己創造一個神話:
我們的詩,我斷言,缺少一個猶如神話之于古人那樣的中心,現代詩在許多本質的問題上都遜于古代詩,而這一切本質的東西都可以歸結為一句話,這就是,因為我們沒有神話。但是,我補充一句,我們幾乎快要獲得一個神話了,或者毋寧說,我們應當嚴肅地共同努力,以創造出一個神話來,這一時刻已經來臨。④施萊格爾:《浪漫派風格——施萊格爾批評文集》,李伯杰譯,華夏出版社2005年版,第191頁。
但施萊格爾認為,古代神話生長的土壤已無跡可尋,現代文化只能借助于唯心主義哲學從精神深處創造出一個新神話來。這個“新神話”已不再像古代神話那樣,是從感性土壤中生長出來的花朵,而是包容了感性和理性,因為“凡是意識永遠抓不住的,在神話中都可以通過感官和精神看到”⑤施萊格爾:《浪漫派風格——施萊格爾批評文集》,李伯杰譯,華夏出版社2005年版,第194頁。,它來自于那首唯一的無限之詩:
神話就是自然的這樣一種藝術作品。在神話的纖維組織里,最高者真的形成了。一切都是聯系和轉換,成形后又變形;而且我敢說,這種成形與變形正是神話最獨到的行為方式,是它的內在生命,它的方法。⑥施萊格爾:《浪漫派風格——施萊格爾批評文集》,李伯杰譯,華夏出版社2005年版,第194頁。
在施萊格爾那里,神話作為詩發揮著一體化的力量。不過,早在幾年前,這種“新神話”就已經由荷爾德林提出來了。這就是他表達在《德國唯心主義最早的體系綱領》中的觀點:
這里我首先要談到一個理念,就我所知,還沒有人想到它——我們必須有一種新的神話,而這種神話必須服務于理念,它必須成為理性的神話。
在我們使理念變得富有審美性,這就是說,具有神話性之前,理念對于民眾來說沒有意思,反之,在神話是理性的之前,哲人必定羞于此道。于是,開明之士和蒙昧之士終將攜起手來,神話必須變得富于哲理,以使民眾理性,而哲學必須變得具有神話性,以使哲人感性。然后永恒的統一親御我們之中。①Friedrich H?lderlin,S?mtliche Werke und Briefe in drei B?nde,Bd.2,p.577.中譯參見《荷爾德林文集》,戴暉譯,商務印書館1999年版,第282頁。
關于《德國唯心主義最早的體系綱領》的作者問題,歷來是眾說紛紜、莫衷一是。在上個世紀初的一次文獻拍賣中,普魯士王室圖書館在一堆手稿中發現了一頁發黃的手抄稿。精通古典文獻的弗蘭茨·羅森茨威格辨認出它出自青年黑格爾的手筆,并根據手跡確定它寫于1796年。但在細細讀完之后,他大吃一驚,因為從內容看,它不符合對黑格爾的一貫印象。羅森茨威格崇敬謝林,于是認為發現的這頁手稿為謝林所作。但是,研究者又注意到,謝林盡管具有詩人的氣質,盡管具有發達的美感,但在青年時代,他并沒把美學擺在自己哲學體系的中心。如果說,手稿中贊頌詩是精神的最高潛能的話,那么,出自荷爾德林的手筆似乎更為恰當。盡管如此,研究界仍有學者傾向于認為該頁手稿的作者是黑格爾,將其看做黑格爾早期的思想。所以,現在該頁手稿,均收入黑格爾、荷爾德林、謝林各自出版的全集中。
不管《德國唯心主義最早的體系綱領》的作者是誰,是黑格爾、是謝林,還是荷爾德林,抑或是他們中的兩人或三人的合作,這都無關緊要,重要的是其中提出的“新神話”的觀念,而這個觀念正是荷爾德林試圖跨越康德和費希特的界線,并超越席勒所孜孜追求的。在《判斷與存在》中,荷爾德林就已經以表達主客體統一的“存在”作為自己思想和詩的出發點,并認為只有在“理智直觀”中才可以通達“存在”。如我們已經說的,“理智直觀”并不是荷爾德林所首先提出的概念,在他之前康德就已經首先提出了,但康德認為,人只有感性直觀,而沒有“理智直觀”,只有上帝才有“理智直觀”,在費希特那里,“理智直觀”是對本源行動的自我的直觀,謝林則認為,意識發展的最高階段是“理智直觀”。在“理智直觀”中,主觀和客觀、意識內容與無意識的事物、自由與必然等區別都消融了。但“理智直觀”不是抽象的,而是具體的,因此,謝林也把“理智直觀”稱為“藝術直觀”,它既是主觀的,也是客觀的,既是自由的、有意識的,也是不自由的、無意識的,它是無限者的有限表象。荷爾德林的“理智直觀”與謝林接近,但在他看來,康德和費希特的“理智直觀”是在主體性哲學的框架之內,而謝林還游移在主體性哲學和他所欲建立的“統一性哲學”之間。荷爾德林本人則將“理智直觀”看做“存在”的直接顯現的場所,它根本上是一種“審美意識”。在荷爾德林之前,從鮑姆加登到康德再到席勒,美一直是在認識論范疇加以考察的,而荷爾德林則將美從認識論范疇轉換到了存在論范疇,美不再屬于人的主體認識和感知范疇,或者如席勒認為的,是人的一種“心靈狀態”。荷爾德林認為,美就是存在本身,或者說,是存在的顯現。后來海德格爾批判現代美學,就受到荷爾德林的影響。
在《德國唯心主義體系綱領》中,荷爾德林將這種“審美意識”進一步發展為一種“新神話”。在這里,“新神話”具體指的就是“理性的神話”。在荷爾德林的時代,啟蒙已將理性推至無以復加的高度,一切都要在理性的法庭上受到檢驗。啟蒙強調理性,其目的在于實現人的自我決定,因為在它看來,只有理性能夠使人自主地掌控世界和生活。這樣,人就從一個整體關聯中脫離了出來,如荷爾德林所說的,理性“把我徹底地與我周圍相區別”②Friedrich H?lderlin,S?mtliche Werke und Briefe in drei B?nde,Bd.1,p.16.。人成了一個可以自我決定的主體,自然則作為客體成為被統治的對象。因此,啟蒙強調理性的全部奧秘,用笛卡爾的話說,就在于征服自然。正是因為如此,荷爾德林要求對啟蒙理性神話化。但“理性的神話”,并不是拒絕理性,而是將理性看做“新神話”的一部分,在這里,啟蒙并未被消解,也沒有失去其意義,只不過是經由“理性的神話”,理性不再被置于絕對的高度,而是相對化了。因此,“理性的神話”所包含的一個根本意圖,用荷爾德林在他的《論宗教》一文中的話說,就是“更高的啟蒙”(h?here Aufkl?rung)③Friedrich H?lderlin,S?mtliche Werke und Briefe in drei B?nde,Bd.1,p.565.。所謂“更高的啟蒙”,就是對啟蒙進行啟蒙,其目的在于修正和調節啟蒙,補其不足。
《論宗教》是荷爾德林思想真正走向成熟的標志。我們知道,1796年2月24日,荷爾德林曾寫信給尼特哈默,說他計劃寫“新審美教育書簡”,其中“會從哲學談到詩和宗教”④Friedrich H?lderlin,S?mtliche Werke und Briefe in drei B?nde,Bd.3,p.225.。但這個計劃并沒有完成,然而他的核心思想后來卻表達在了《論宗教》中。這個思想不僅滲透在他此時正在創作的書信體小說《許佩里翁》中,也決定了他后期詩歌的創作。
那么,什么是《論宗教》的核心思想呢?荷爾德林開宗明義,一開始就斬截地指出,人與世界處于一種“更高的關聯”(h?herer Zusammenhang)中,并將此稱之為“無限的生活關系”:
人因其天性而超越必然,與他的世界處于豐富多彩而更為內在的關系中,就人超越自然和道德的必需而言,他始終過著一種人性上更高的生活,于是一種大于機械的更高的關聯,一種更高的天命存在于他和他的世界之間,因為人感覺到自身和他的世界以及他之所是和所有的一切都融合為一,這種關系對于他的確是最神圣的。①Friedrich H?lderlin,S?mtliche Werke und Briefe in drei B?nde,Bd.2,p.562.
正是這種在“更高關聯”中的生活,成為“前現代”與“現代”的區別。在前現代,人們認為,宇宙充滿了意義和秩序,人的認識就是去觀察、把握這個宇宙的意義和秩序。但到了現代,例如在康德那里,卻完全顛倒了過來,宇宙是雜亂無序的,是多樣的,只有當人以先驗的范疇去把握宇宙的雜多時,才能獲得知識。于是,人成了自然的立法者,而不是像以前那樣,去符合和順應宇宙的秩序和法則。人因此而失去了在“更高的關聯”中的生活。在此,荷爾德林顯然是針對康德,尤其是費希特而來的。費希特把自我作為哲學的最高出發點,這個“自我”,自己設定自身,是純粹的活動,并憑借這種純粹的自身設定而存在。這恰恰為荷爾德林所反對,他認為,費希特的自我是無世界的,而這樣的自我其實并不存在。
在荷爾德林看來,并沒有一個純粹自己設定自己的自我,每一個人都不是孤立的存在,他必然處于一個更大的關聯之中,即一種“更高的生活”之中,這也就是海德格爾后來所說的,人是“在世界之中的存在”②海德格爾:《存在與時間》,陳嘉映、王慶節譯,三聯書店1987年版,第66頁。。但是,人在這個無限的關系中,卻常常將其中的一個方面絕對化:
而我們確實已經把更精粹更無限的關系一方面變成一種傲慢的道德,另一方面變成一種浮華的標簽或者淺薄的趣味規則,并且相信憑借鐵一般的概念我們比古人更開明了。③Friedrich H?lderlin,S?mtliche Werke und Briefe in drei B?nde,Bd.2,p.564.
在1794年的《論自由的法則》中,荷爾德林就針對康德的道德律令,提出了批評。康德認為,人要獲得人性的尊嚴,在于過一種道德的生活,真正的人性是具有道德的人性。因此,他將自然存在與道德存在截然分開,自然存在是受欲望和貪婪支配的,而道德存在則是對欲望的擺脫,人是根據理性法則,不受欲望束縛而生活的。因此,康德認為,一個理性的人就是一個道德的人。他在《實踐理性批判》中寫道:“人通過絕對命令而發現自己是一個自由的存在。愛好始終是受人的必然束縛的,義務則是道德自由的表達,通過道德,人超越了必然,而成為一個理性的人。”④康德:《實踐理性批判》,商務印書館2003年版。在《優美與尊嚴》中,席勒將理性的自由視為對感性的壓制,他試圖克服康德的二元論,“在美的心靈”⑤席勒:《秀美與尊嚴》,張玉能譯,譯林出版社2009年版,第266頁。協調義務和愛好,從而賦予人以真正的自由。荷爾德林的思想既不同于康德,也不盡同于席勒,在他看來,無論是康德的道德,還是席勒的優美,都不是自由的空間,只有在“更高的生活”中才是自由的,因為在這里,人同時超越了“自然和道德的必需”⑥Friedrich H?lderlin,S?mtliche Werke und Briefe in drei B?nde,Bd.2,p.562.,他既遵守“自由的法則”⑦Friedrich H?lderlin,S?mtliche Werke und Briefe in drei B?nde,Bd.2,p.496.,又考慮到了“充分運用法則的特殊世界”⑧Friedrich H?lderlin,S?mtliche Werke und Briefe in drei B?nde,Bd.2,p.564.,正是在這里,荷爾德林說:
那種更無盡的,大于必需的關系,人在他的元素中獲悉的那種更高遠的天命,也將更無盡地為他所感受,更無盡地滿足他,從這種滿足中得出精神生活,于此他仿佛重溫現實生活。⑨Friedrich H?lderlin,S?mtliche Werke und Briefe in drei B?nde,Bd.2,p.263.
在《論宗教》中,多次用過一個詞“innig”,是意味深長的,這個形容詞和荷爾德林使用的名詞“Innigkeit”都是他思想尤其是詩歌中的基本詞語。國內有人將“innig”譯為“深情的”,將“Innigkeit”譯為“情志”,均未能理解荷爾德林。實際上,“Innigkeit”在荷爾德林那里,指的就是存在的一種更為豐富的關系,也就是《論宗教》中的“更高的關聯”和“更高的生活關系”。在1799年的一首詩歌殘稿中,有這樣一句詩:“萬物皆親密”(Alles ist innig)⑩。這正是荷爾德林的基本思想。因此,“Innigkeit”可譯為“親密性”或“親緣性”,荷爾德林用它來表示“萬物一體”的思想,即一切都是相互聯系、互為一體的,天地間沒有任何獨立無依的東西,天、地、人、神共屬一體,荷爾德林認為,詩的本質即在于此。
處于“Innigkeit”(親緣性)之中,或處于“更高的關聯”之中,就是人的一種“詩意的”(dichterisch,das Dichterische)存在。在荷爾德林那里,詩與神話是一回事,不可分割。因此,“Innigkeit”、“更高的關聯”既是“詩意的”,也是“神話的”,即荷爾德林所說的“神話狀態”,在這里,每一物和每一個人都可以從神話世界的親緣整體中獲得其意義。不僅如此,正如赫爾德在神話中看到“宗教價值”一樣,荷爾德林也將神話與宗教視為是同一的,在小說《許佩里翁》第一卷的結尾,荷爾德林寫道:
神性的美的第一個孩子是藝術。在雅典人那兒就是如此。……美的第二個女兒是宗教,宗教是對美的愛。沒有這樣的對美的愛,沒有這樣的宗教,每一個國家都是干枯的骨架,失去生命和精神,而一切思想和作為都是一棵沒有樹冠的樹,一根被砍掉頂冠的石柱。①Friedrich H?lderlin,S?mtliche Werke und Briefe in drei B?nde,Bd.2,p.90.
據說,荷爾德林的宗教觀受到施萊爾馬赫的影響,他曾研究過后者的《論宗教——對蔑視宗教的有教養者講話》。我們稍加比較,就可以看到他們二人之間的一致性。施萊爾馬赫認為,宗教源自人類心靈中對無限的渴望,它是對宇宙的直觀,“宇宙”在施萊爾馬赫這里,不是物理學的對象,而是有限的個人企圖超越提升自己而追求的“無限”或“整全”之目標。荷爾德林則認為,是一種“精神生活”,在宗教中,“人在有限的生活中也能夠無限地去生活”②Friedrich H?lderlin,S?mtliche Werke und Briefe in drei B?nde,Bd.2,p.566.,即讓人能夠進入一種“更高的關聯”。宗教本質上就是人的神性存在,正如荷爾德林在一首短詩中所寫的:“在一體中存在就是神性和善”③Friedrich H?lderlin,S?mtliche Werke und Briefe in drei B?nde,Bd.1,p.222.,或者如他在《許佩里翁》中所說的:“與萬有合一,這就是神性的生命。”④Friedrich H?lderlin,S?mtliche Werke und Briefe in drei B?nde,Bd.2,p.16.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荷爾德林說,“一切宗教本質上都是詩”⑤Friedrich H?lderlin,S?mtliche Werke und Briefe in drei B?nde,Bd.2,p.568.。在宗教中,“每個人以神話的方式慶祝他的更高尚的生命,而人人也以同樣的方式慶祝一種共同的更高遠的生命,這生命的節日。”⑥Friedrich H?lderlin,S?mtliche Werke und Briefe in drei B?nde,Bd.2,pp.568-569.
在這里,我們看到,荷爾德林以他自己特有的方式將現代啟蒙納入一個神話視野之中,他認為,在一個諸神逃逸的“黑夜時代”,詩人的使命就是為這個時代重新解釋神話,處處“更可證實地”⑦Friedrich H?lderlin,S?mtliche Werke und Briefe in drei B?nde,Bd.3,p.315.描寫神話。荷爾德林相信神話是真實的,而且也相信一個“未來之神”,即那個“諸神復歸”的神話世界是可以建立的。在這一點上,他與席勒不同,席勒認為神話是虛構,諸神已一去不返,現代人只能在詩歌的世界里,在一個想象的、假象的王國里,尋找諸神的蹤跡,重溫諸神所在的那個“美”的世界。他在《希臘的群神》里這樣寫道:
美麗的世界,而今安在? 大自然/ 美好的盛世,重回到我們當中! /可嘆,只有在詩歌仙境里面,/還尋到你那神奇莫測的仙蹤。/大地悲慟自己的一片荒涼,/ 我的眼睛看不見一位神道,/唉,那種溫暖的生機勃勃的形象,/ 只留下了幻影縹緲。
一切花朵都已落英繽紛,/受到一陣陣可怕的北風洗劫; /為了要抬高一位唯一的神,/ 這個多神世界只得消滅。/我望著星空,我在傷心地找你,/ 啊,塞勒涅,再不見你的面影; /我在樹林里,我在水上喚你,/ 卻聽不到任何回音!⑧《席勒詩選》,錢春綺譯,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年版,第22頁。
但在荷爾德林那里,諸神并沒有消失,只是遠離我們而去,他們仍是活生生的現實的存在:
可是朋友! 我們來得太遲,諸神還活著,/卻在我們頭上的另一個世界,/他們在那里威力無邊,似乎很少留意/我們存在,神靈就這樣庇護我們。⑨Friedrich H?lderlin,S?mtliche Werke und Briefe in drei B?nde,Bd.1,p.289.
而且,荷爾德林也沒有像席勒那樣,將基督和諸神對立,基督也同樣屬于諸神,只不過他是在諸神之白晝消失之時,最后一位到來的神,他和狄俄尼索斯一樣,都是宙斯之子。
在荷爾德林看來,歷史乃是由人與諸神之間的關系構成的,他的頌歌《自然與藝術或薩杜恩與朱庇特》集中表達了這一神話式的歷史理解理解。荷爾德林認為,歷史的發展分為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農神階段,處在這一時代的人,還沒有時間和空間的意識,一切渾然一體,人與諸神和睦相處,第二階段的宙斯時代,人有了意識,意識到了時間、空間,于是有了人與神之間的區別,但在此一時代,又分為兩個階段,即希臘階段:人與諸神是親密的,但到了西方時代,人與諸神則分離了;第三個階段,人與諸神又重新和諧統一。
因此,以這樣一種神話式的理解,歷史表現為一種循環的時間結構,在荷爾德林的詩歌中,最常見和最重要的象征,就是晝與夜循環往復的交替。白晝是諸神的時間,在白晝中,諸神對于人是無處不在的:
諸神曾在人間游蕩,那些美麗的繆斯,/還有新生子阿波羅,撫慰和鼓舞人。①Friedrich H?lderlin,S?mtliche Werke und Briefe in drei B?nde,Bd.1,p.215.
而黑夜,則是人與諸神分離的時間,荷爾德林把他自己所處的時代,就看成是一個彌漫著黑夜的時代。在這個時代,諸神遠逝而去,但諸神的離去,在荷爾德林看來,是因為人不再以神話的方式與諸神打交道,他們以傲慢的態度利用和盤剝自然。但荷爾德林也認為,黑夜同時也是一個“神圣之夜”②Friedrich H?lderlin,S?mtliche Werke und Briefe in drei B?nde,Bd.1,p.290.,因為當黑夜達到最深只是,很快將為另一個新的白晝所代替,諸神即將回歸:
因為神靈正在歸來,在黑夜里,/他們的白晝已準備降臨人間。③Friedrich H?lderlin,S?mtliche Werke und Briefe in drei B?nde,Bd.1,p.288.
實際上,荷爾德林認為,當白晝消失、諸神離去時,他們已經通過他們留在人間痕跡預示了還會歸來:
當一位默默無聞的神最后一次出現,帶來天使般的/安慰,宣布白晝消失后離去,/并留下痕跡,表明他來過,天國的諸神/還會再來,并留下一些饋贈物,/讓我們仍能像往常那樣享有天倫之樂,/因為再大的饋贈給人的歡樂會變得/過量、失當,還沒有,沒有強者能承受/最高的歡樂,但某種默默的感激并未泯滅。/面包是大地之果,卻是光的賜予,/葡萄酒之歡源自怒吼的雷神。/因而我們也聯想到天神們,他們/來過這里,適當的時候還會再來。④Friedrich H?lderlin,S?mtliche Werke und Briefe in drei B?nde,Bd.1,p.290.
但諸神只是在“適當的時候”才會歸來,也就是說,諸神不是在任何時候都可以歸來,只有當人以柔和的心靈感受諸神時,他們才會歸來,因為諸神需要“富有感情的人的心靈”⑤Friedrich H?lderlin,S?mtliche Werke und Briefe in drei B?nde,Bd.1,p.255.。而現代人恰恰因為追名逐利、精打細算,心靈變得枯萎了。在這個“貧乏的時代”⑥Friedrich H?lderlin,S?mtliche Werke und Briefe in drei B?nde,Bd.1,p.290.,詩人最深刻地感受到了時代的貧乏,他們“像酒神的祭司一樣,走遍大地”,保持著對遠去諸神的回憶,并為諸神在“適當的時候”的到來準備好居所:
你們詩人,裸露著頭顱,/迎承神的雷霆,用自己的手/抓住天父的閃電,把它裹入歌中/將神靈的禮物帶給民眾。⑦Friedrich H?lderlin,S?mtliche Werke und Briefe in drei B?nde,Bd.1,p.240.
我們看到,在荷爾德林的神話世界里,他的歷史思想,一方面是循環論的,即從和諧統一到分裂再到和諧統一;但另一方面又是目的論的,即一切發生的東西,無論是希臘文化的興起、繁榮和衰落,以及后來開始的諸神之夜,和在西方大地上所期待的未來的諸神之晝,自始至終都有一個內在的意義。二者看似是矛盾的,但是從神話的視野看,它們卻又是辯證統一的,如果說循環論追求的是歷史的差異性,那么,目的論追求的則是歷史統一性,同時又表現出了差異中的統一和統一中的差異,用荷爾德林的話說,二者是“對立之和諧”,是“自身差異中的一”,它們成為荷爾德林神話歷史觀的實質性內涵。當然,就荷爾德林的歷史思考重心而言,自“基督贊美詩”以后,他更傾向于歷史目的論。在這一神話目的論的歷史哲學視野中,荷爾德林將狄俄尼索斯和基督合二為一,并借由他們,使人類與諸神,即與自然重新達到和解。而這一切皆是荷爾德林“重建神話世界”的根本意旨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