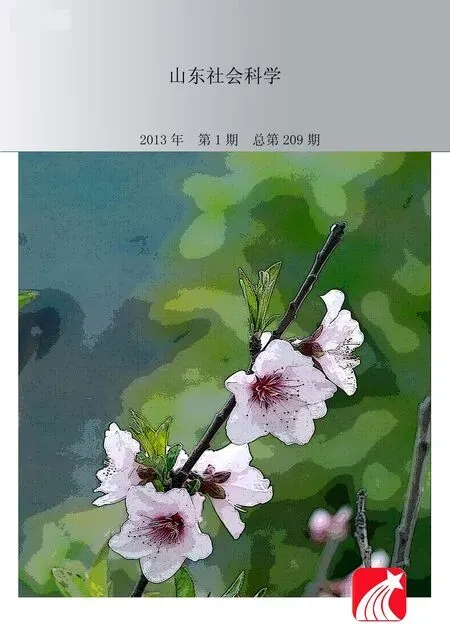國家、個人及民間社會的內在秩序
——試論天津皇會中各階層之間的互動關系
蒲 嬌
(天津大學 馮驥才文學藝術研究院,天津 300072)
媽祖作為民間神受到百姓信仰崇拜,對天津本地的城市文化性格產生重要影響,是地域文化認同的精神載體,被親切地尊奉為“三津福主”,本地更有“先有天后宮,后有天津衛(wèi)”的說法。為媽祖誕辰舉行的大型祭典儀式——皇會,也在天津地域文化發(fā)展中起著重要的作用,可謂記錄歷史、文化、經濟、政治、信仰、風俗及社會變遷的活化石。媽祖信仰在天津的扎根并非偶然,一方面,作為一位外來之神,媽祖樂善好施、扶危濟困的神性與天津百姓的人格模式不謀而合,很快便融入包容性極強的天津本地文化中;另一方面,慶典儀式本身的性質決定了有組織的活動往往需要調動地方社會的多種力量共同參與才可完成。因此,媽祖慶典儀式便具有了廣泛吸引社會力量、促成社會各階層頻繁互動的特點。不同群體的加入壯大了皇會的勢力,但矛盾也相應產生。如何協(xié)調好不同階層人群之間的關系,如何建立并運行一套具有廣泛適應性的內在秩序,都是在皇會各階層關系中值得研究的問題。
一、國家意識與鄉(xiāng)土觀念
媽祖信仰在天津是一個不斷發(fā)展和深化的過程,逐漸完成由單純的護航神到萬能地方神的轉化過程。信仰的生發(fā)及傳播必定同此區(qū)域內社會人群的精神追求相呼應,某種民間信仰的發(fā)展或消亡,極大程度是社會自主選擇的結果。①具體見鄭振滿、陳春:《民間信仰與社會空間》,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最初媽祖祭典儀式處在“娘娘會”階段時,多半是民眾自發(fā)組織參與,帶有濃厚的民間色彩。雖然常有官員參與,但大多是以個人身份出現(xiàn),官府操持的情況較為罕見。清康熙年間,因娘娘會已具較大規(guī)模,引起了政府關注,逐步獲得來自官方的支持與宣傳。媽祖作為神祇,自北宋宣和五年(1123年)起便多次受到皇封。天津的鄉(xiāng)紳與官員自媽祖入津伊始,便為此具有文化正統(tǒng)性、符合儒家教義的神明扎根天津而苦心經營。當媽祖信仰被當地民眾普遍接受后,所傳遞的有關于“國家”與“民間”的關系也發(fā)生了巨大變化,官員、民眾和地方精英對待媽祖的態(tài)度隨之產生微妙變換。在中國歷史上,統(tǒng)治階級多次改朝換代,但對于專制政權的掌控權卻沒有一刻放松過。統(tǒng)治階級反復強調“禮”的教化,利用“儒學”為統(tǒng)治工具的同時,也力圖在民眾心中營造“禮治社會”的假象。然而,傳統(tǒng)中國國家與社會的松散關系,致使在某些歷史階段內中央集權階層的權力被架空。因此,必須出現(xiàn)一種能被各階層所接受、能平衡各階層關系的交流方式。顯而易見,對民間文化的認同和參與只是一襲華麗的外袍,獲取民眾對國家的支持和忠誠才是統(tǒng)治階級的真實目的所在。這或許才是皇會能得到國家重視,并如火如荼開展起來的真正原因。此類事件在清帝的加封、賞賜物品,甚至親自參與等行為中表現(xiàn)得尤為突出。國家正是利用了有良好群眾基礎的傳統(tǒng)文化和社會活動,將本階級的意識滲透其中。在必要的時候,他們還會適時調整政策,通過主動示好來達到籠絡民眾、維護專制統(tǒng)治的目的。以1936年皇會為例,從組織籌備到具體實施都由官方出面全盤布置,甚至天后出巡散福的路線也由政府定奪。官方介入皇會籌備會,意味著皇會受到官方的實際控制,成為傳達統(tǒng)治階層意志的載體。
媽祖信仰的在地化很大程度上受益于同“碧霞元君”信仰的融合,但在之后的發(fā)展中,媽祖保持了獨立神格而未被碧霞元君同化,甚至民間出現(xiàn)了將碧霞元君訛傳為媽祖娘娘的傳說。通常而言,在強勢信仰的已有神靈空間內,外來神靈會被同化。但媽祖信仰在天津的發(fā)展狀況卻截然相反,筆者認為有以下原因:首先,媽祖信仰特性的保持,很大程度上有賴于民眾心理的基本需求。天津地處海運與漕運的雙重要塞,本地居民家中大都有從事航運和腳行的人,因而媽祖佑護水運安全的核心神職顯然是必需的。至今尚存的天后宮“海門慈筏”牌坊,以及配殿內所供奉的木船模型①天津本地由此傳說:面對神靈許愿必定還愿,否則就會遭受報應。商賈如在出海前對媽祖許愿祈求護佑,必須要在平安歸來后到天后宮還愿,并進貢一條小船模型,意為將整船的寶物都獻給娘娘,日積月累,天后宮內的小船模型越來越多。就是歷史見證。其次,從封建社會國家政權與民間社會之間的關系來分析,媽祖是經歷代王朝政府封贈而進入國家“正祀”體系的民間神,這對于保持其獨立神格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媽祖頻受“敕封”這一點,在其傳播過程中被大肆宣傳。民眾相信,被統(tǒng)治階級認可的正祀威靈更強。而從媽祖被加封的過程與天津民間信仰逐步融入“國家”體制的過程來看,二者基本是同步的。因此雖然經過歷朝更迭和復雜動蕩的政治局勢,但在鄉(xiāng)民對文化價值的認知層面上,對于“正祀”的信念并沒有產生動搖。歷次皇會出巡,隊伍最前必定要掛一條寫有“上造娘娘敕封,世人念到,就知娘娘常常顯圣,才受敕封”②據西碼頭百忍老會時任會頭殷洪祥先生口述。的門幡。這些舉措在強調媽祖信仰靈驗的同時,也是國家傳遞階級意識的過程,通過在文化意識方面的反復加強,使得人們對既定秩序產生自然認同。
二、媽祖信仰與民眾之間的互動
媽祖信仰在天津地區(qū)的發(fā)展傳播,經歷了一個“民眾出于不同的心理需要賦予天后多種職能,并在其神靈譜系中加入不少天津本地的世俗神靈”③侯杰、李凈昉:《天后信仰與地方社會秩序的建構——以天津皇會為中心的考察》,《歷史教學》2005年第3期。的過程,這同民間信仰的實用功能密切相關。中國民眾的信仰大抵限于與生活關系密切的原因,所表現(xiàn)出來的趨利效應嚴重。通過對信仰體系的改造,不僅鞏固了媽祖的基本神職,更派生出了許多更廣泛、實際的功能,如繁衍求子(“拴娃娃”功能)與祛除疾病(斑疹及天花等疾病)方面。在媽祖神職擴大的過程中,盛大的皇會儀式無疑起到了一種最為直觀、立體、真實的宣傳作用,民眾對其產生的強烈認同感與好感便不足為奇了。
皇會中的玩意兒類花會表演,不僅為民眾帶來娛樂效果,更在潛移默化中強化了人們對神靈的認知,為他們親近神靈提供了一條捷徑。在皇會儀式中,常有數目眾多的“巡風會”、“愿心會”、“頂馬圣會”、“寶塔花瓶”等會種參與,此類花會都是以答謝神靈庇護、宣揚神績?yōu)橹饕康摹!芭c日常禱祀儀式不同,廟會活動以極具感染力的方式在一個較短時期內向社會公眾集中展示神靈及與神靈有關的各項內容。”④吳效群:《皇會:清末北京民間香會的最高追求》,《民間文化論壇》2005年第3期。在行會過程中,一方面進行表演,另一方面向民眾傳播媽祖的靈應事跡。這種宣揚效果直達社會的每一個階級、每一個角落,無論是政府官員、地方紳士還是民眾,都會被神通廣大、普濟天下的神靈所感染。
誠如劉魁立先生所言,民間信仰構成了中國民眾精神生活與民俗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⑤參見劉魁立:《中國民間信仰》,浙江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在民眾心中,能參與酬神、敬神、敬神的演出是一件無比榮耀的事情。儀式過程中,民眾在身臨其境享受表演樂趣、滿足自身興趣的同時,也可以實現(xiàn)情感之中對媽祖強烈的歸屬感與貢獻感。這些平時處在社會最下層的百姓,終日辛苦,很難有機會參與到社會集體文化活動中。但皇會的狂歡正可以創(chuàng)造這樣一個機會,他們可以以神的名義發(fā)出吶喊,發(fā)出內心深處的自我宣泄。“在他們的世界中,民眾的文化活動能夠被納入到皇朝的儀式范圍,自身的價值追求能夠得到皇朝政府的認可和贊賞,這不啻于證明了自身的追求和行為的合法性。”①姚旸:《論皇會與清代天津民間社會的互動關系——以〈天津天后宮行會圖〉為中心的研究》,《民俗研究》2010年第3期。在現(xiàn)實世界中,統(tǒng)治階級的地位不容質疑,大部分民眾過著屈從、忍耐的生活。但在皇會儀式所營造的第二世界的理想生活中,民眾可以在表演活動中打破等級界限。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民眾參與皇會是渴望獲取社會地位、平等自由的一種表現(xiàn)。
皇會的參與者中,有部分人身份特殊,被稱為“吃會兒的”或“扒會兒的”。此類人不參與演出也不出資,甚至并不信奉媽祖,作用卻十分重要。他們大多出身貧寒,無正式職業(yè),但卻精通皇會中的儀式、禮儀、會規(guī)、人情及忌諱等事。每逢會期,他們便借辦會之名四處籌備資金、募捐銀兩,然后私藏部分收歸己有。這些人沒有固定收入,但是所獲“報酬”卻極為可觀。雖然社會各界對這些人的行為心知肚明,但對他們卻睜只眼閉只眼。據傳統(tǒng)社會的結構特點來看,出現(xiàn)“吃會兒”群體是時代的必然。從生產方式上來說,在生產力水平低下、社會分工粗放的傳統(tǒng)農業(yè)社會中,生活與生產問題大多依賴宗族互助解決,社會聯(lián)系的渠道方式相對缺乏。因此,這種能自如游走于社會各階層、社會交際能力強大的群體,所發(fā)揮出來的便是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他們的活動雖是利益驅動,但最終使得皇會能夠充滿生機和活力。故而,在經濟匱乏的時代,生活在下層的貧困百姓,為了現(xiàn)實利益而加入某種團體或宗教組織也是常見之事。此類現(xiàn)象的產生,也可認為是中國民間宗教信仰活動中,一種實用特征和功利性格的異化表現(xiàn)形式。
三、地方紳士在皇會中的價值實現(xiàn)
皇會在清康乾年間的興盛,與天津民眾對媽祖的篤信、地方經濟的繁榮及國家的統(tǒng)治意圖幾方面都有極大關系,但興辦與停辦卻與地方紳士②參見費孝通:《中國紳士》,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年版。費孝通將中國的紳士階層定義為:紳士階層有時也叫士大夫,“學者——官員”。的態(tài)度有著直接的聯(lián)系。“當民間社會集中崇拜某一官方認可的神祇時,也就等于國家間接地控制了地方信眾的宗教及社會行為。”③迪生:《香港天后信仰》,三聯(lián)書店2000年版,第12頁。天津皇會因統(tǒng)治階級的認可,打上了標志性的正統(tǒng)符號,描上了濃郁的政治色彩,成為地方紳士階層參與其中的源動力。
皇會是地方紳士階級表現(xiàn)及確定自身社會地位的重要途徑與有效方式。地方紳士試圖進入皇會的組織管理機構,進而構建一個由管理皇會的精英團隊與普通信眾共同參與,并達成自身目的的社會組織。在皇會中,紳士群體所掌管的組織被稱為“掃殿會”,他們所重視的是如何靠近地方政治及博得社會聲望。普通民眾所參與的組織稱為“花會”,他們所關心的是會與會之間的關系、村落之間的關系及村落中人與人的關系,并注重內心宣泄的實現(xiàn)及對媽祖信仰的虔誠。此外,參加掃殿會的紳士可以根據興趣選擇參加花會組織,掃殿會卻絕不允許處于社會底層的花會成員隨便參與進來。從另一個角度說,參與花會活動的民眾比紳士們在行動上可以更為自由,他們可以選擇參加皇會或者不參加,可以選擇改為參加其他廟會,如碧霞元君廟會、妙峰山廟會、葛沽皇會等。但紳士們卻要對自己的行為深思熟慮,他們的離開可能會導致皇會在資金方面的瞬間垮塌、組織系統(tǒng)混亂、安置工作失靈等后果,進而影響到他們在本地的社會聲望。因而,其自身所背負的道德、信義方面的責任便更加重大。雖然在行為上受到極大的約束,但紳士階層也絕不輕易放棄參與皇會的機會。“眾位爺,每多有舉、監(jiān)、生員人物上會,俱是袍套靴帽,各有頂戴職分,尊為會中領袖。”④許青松、郭秀蘭:《天津天后宮行會圖》,香港和平圖書公司1992年版,第202頁。清代以后,掃殿會全部是由身有功名的官、商兩界的上層人物組成,這個階層的人群在本地有著廣泛的社會影響力和號召力。“在國家與社會關系相對疏離,社會化程度較低的中國民間社會……‘社會聲望’是中國傳統(tǒng)社會的核心價值。”⑤吳效群:《妙峰山:北京民間社會的歷史變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頁。在當時的社會中,個人的社會地位及名譽直接決定了其社會關系的廣博度、精神滿足感和各階層人群的認可度,但最終還是歸結為對經濟利益的追求。紳士階層依靠自身在本地的聲望廣泛吸納各類組織力量,募得最佳、最為廣泛的社會資金支持。因而,掃殿會在皇會中所擁有的至高無上的地位,被譽為“會中領袖”,可謂皇會真正的領導者、策劃者及組織者。
綜上所述,雖然各個階層參與的是同一場皇會,但管理者和參與者所處的社會階層與政治范疇卻是截然不同的。為媽祖誕辰舉行的皇會祭典儀式,可以認為是紳士階層所操控的一個集體符號,但并不是所有民眾都會認同這一符號,民眾之間、民眾與精英之間、民間社會與國家之間仍然存在一定矛盾。但不可否認的是,掃殿會領導地位的確立,對于保障皇會組織的凝聚力、執(zhí)行力方面的確具有積極意義,在某些方面,還加強了官、商階層對地方社會事務的滲透能力和處理能力。如:行會過程中,若各花會之間產生矛盾摩擦,負責協(xié)調解決的是掃殿會成員,一般情況下,各會成員都會服從此類安排。此外,隨著皇會繁榮和影響力的與日俱增,一些皇會外的民間組織深感身單力薄,積極向皇會靠攏,也希望籍此平臺提升社會名望,使自身組織得到更好發(fā)展。在皇會舉辦的過程中,掃殿會成員能夠與各類人群產生接觸,從而促進了官與商、官與民、民與民、民與商和會與會等不同階層、各個群體之間的互動交流。
四、皇會對世俗社會秩序的重構作用
廟會的普遍社會功能在于——酬神、謝神、賄賂神靈。據人類學儀式研究學家特納的儀式理論,這些儀式活動反映了古代民眾在特定時節(jié),對過渡階段、對自身生存狀態(tài)所作出的調適性努力,反映出民眾企圖通過人類自創(chuàng)文化體系來駕馭宇宙、實現(xiàn)愿望的不懈追求。①參見[美]維克多·特納:《儀式過程:結構與反結構》,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往深層功能意義方面探究,群體性的祭祀儀式在鄉(xiāng)土社會中還具有對社會秩序網絡的消解與重構作用。只是這種暫時的、顛覆性的文化展演被有效整合在高度秩序化、整肅性的祭典儀式中了。中國的民間信仰具有強大的包容性,有組織的儀式活動往往需要調動自上而下的多種社會力量共同參與。因此,皇會中各階層人士的有機聚合,導致了地方社會秩序在建構和維持上所產生系列的變化。
媽祖信仰深切地植根于天津民眾心中,這是皇會生發(fā)、繁榮及相關民俗活動有機傳承的動力源泉。但由于中國民眾的信仰意識較為不自信,他們認為普通人與擁有超自然力量的神靈直接交流是不可實現(xiàn)的事情。這時,在民眾與媽祖之間就自然引入了溝通媒介——道士。早期的道士是溝通世俗與神圣儀式的執(zhí)行者,又是現(xiàn)實生活中民眾信仰生活的引導者,同時也掌握著較多的文化知識,因而在民間社會受到尊重。雖然在皇會的決策層中逐漸加入了官府、商人,但調度、請會、提會、派帖和張貼黃報等一系列的聯(lián)絡協(xié)調工作仍需要道士來完成。作為皇會的重要參與者,在建立民眾和神靈聯(lián)系的作用中,道士階層也可歸為社會精英的范疇,對建構世俗社會的秩序也有重要的作用。
筆者在這里特別提到的是女性信眾的作用。在中國民間信仰中,女神的數量占據了很大比例。女神及女神信仰的存在與中國婦女特殊的生產生活和精神需求關系密切,女神也就相應地被賦予了滿足與女性需求相關的職能,其中保佑生育是最重要的一項。受傳統(tǒng)倫理的影響,中國婦女參加社會交往和公開娛樂活動的機會十分有限,但若是替家庭成員的平安祈福、為傳宗接代祈禱的宗教活動就變得十分合理。事實上,在對待皇會中是否允許女性參加的問題上,一直是十分矛盾的。一方面,“女子不能拋頭露面”是幾千年來封建社會對女性不成文的道德觀約束,皇會期間眾多女性的涌入,無疑是對“男女授受不親”傳統(tǒng)儒家道德規(guī)范的挑戰(zhàn)。但女性群體作為媽祖信眾中的主體,是媽祖信仰在天津地區(qū)得以存續(xù)的關鍵力量。這也是媽祖信仰扎根天津后,派生出其他分身娘娘功能與各種民間生育民俗的主要原因。因此,皇會組織者對于女性信眾的參與始終是不鼓勵也不禁止,而持無奈又容忍的態(tài)度。從社會進步的角度分析,傳統(tǒng)社會中的女性面臨來自社會各方面的約束,學習與交流的機會較少,合理的出行可以使她們廣博視野,獲得更多接觸社會的機會。
皇會的舉辦,直接受益者當屬商人。他們既從皇會中獲得了經濟方面的實惠,又通過對皇會的熱心參與和鼎力支持,獲得不同程度的社會聲望與號召力,鞏固和提高自身在民間社會中的地位。當然,這其中不乏別有用心之人,某些懷有政治理想的商人借參與皇會的機會,作為與官方靠近的手段,最終達到官商勾結、贏取私利的目的。但正是因為商人階層對于皇會的熱情與動力,才最終形成皇會刺激經濟、拉動商業(yè),商業(yè)資助皇會的獨特運作模式。最終,商業(yè)的發(fā)達及商人的社會角色“善”化,必然會對天津地域文化、城市性格、民間風俗造成一定影響,傳統(tǒng)的社會秩序也會受之影響,作出相應的調整及重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