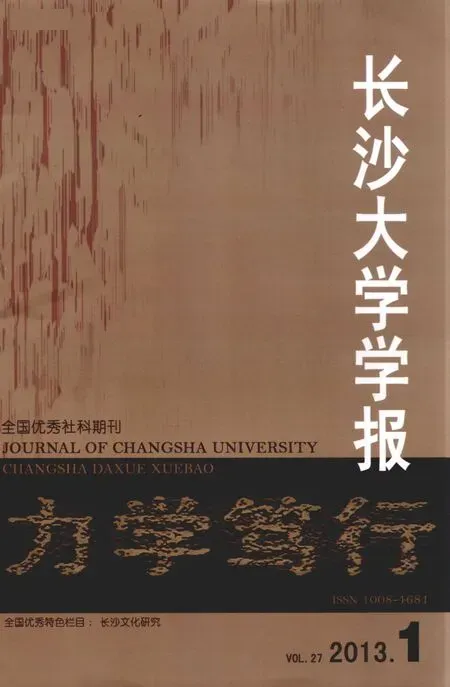愛德娜性覺醒的自然主義解讀
鄧 治,彭 凌
(長沙大學公共外語教學部,湖南長沙410003;國防科技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學院,湖南長沙410073)
發表于1899年的長篇小說《覺醒》,是十九世紀美國著名女性主義作家凱特·肖班的代表作,描寫了一位中產階級女性從禁錮自由的婚姻和家庭制度中覺醒后,追求身體和精神解放,進而放棄生命捍衛其剛剛萌芽的主體意識的抗爭歷程。對于涉及彼時社會禁忌的女性意識和婚外戀情,肖班采取了一種“超道德”的態度,她不對女主人公的行為進行倫理價值判斷,甚至沒有任何的主觀評價,只是超然地解釋說:“我從未想到愛德娜·蓬特利爾夫人會惹出這么大的亂子,招來如此多的詛咒。”[1]肖班因此備受評論界的冷落和攻訐。但是,隨著學術界對《覺醒》的不斷研究,人們發現肖班對其女主人公不加任何道德評判的態度,正是當時逐漸興起的自然主義文學思潮的重要特征之一。
自然主義是19世紀中期形成于法國、后傳入美國的一種文學流派。當時歐美文壇涌現出了左拉、德萊塞等一批自然主義作家,極力追求忠實地反映現實生活,像醫生那樣冷靜客觀地對人進行生理層面的探究和動物式的剖析,不帶任何主觀傾向地揭示被原始欲望和社會環境所束縛的人們的無奈、無助和無望。因此,我們有理由認為,在19世紀90年代正處于文學創作高潮的肖班,自然地受到這股文風的影響,從摒棄了道德和倫理范式的自然主義角度來敘述她的女主角的身心覺醒經歷。本文闡析了愛德娜在生物本能和自然環境的雙重作用下、性意識萌發直至完全綻放這一過程,揭示了十九世紀末期女性生活真相的角度,探討了《覺醒》的自然主義內蘊,從而拓展人們的閱讀視閾,充分認識其在美國文學史上開創描寫女性意識先河的顯著地位。
一 性欲覺醒:自然主義的宿命論
西奧多·德萊塞認為,“每一個人的行動都是對一連串內在沖動和外在誘惑的直接反應,所以沒有一個人能夠深思慎行,能夠進行選擇”[2]。追求愛與被愛是每一個正常人的內在需求,這是理智無法排斥或挑選的。愛德娜從年幼時缺乏家庭關愛,到青春期憧憬浪漫的愛情,再到接受蓬特利爾先生的求婚,最后情不自禁地與羅伯特陷入情網:這一連串的行為都是她追求被愛的沖動的必然結果。愛德娜出生在一個宗教氛圍濃厚的長老會家庭,父親嚴厲刻板,姐妹們保守內斂。母親在其年幼時去世,愛德娜的內心因而充滿對愛的渴求。步入青春期后,她開始接連不斷地暗戀上青年異性:曾迷上一位“目光威嚴而憂郁的騎兵軍官”。一度愛上一個和她姐姐的好友訂婚的“年輕紳士”,一位悲劇演員也長期激起她無限的遐思。這時,蓬特利爾先生出現了,他對愛德娜一見鐘情,并對她展開熱烈的追求。蓬特利爾的無限忠誠和崇拜讓愛德娜陷入被愛的虛榮和幻想之中,她不顧家庭的強烈反對、沖動地投入他的懷抱,可最后遺憾地發現:她對丈夫僅僅是喜歡,沒有思想和情趣的共鳴。嫁給蓬特利爾純屬偶然,可是自然主義告訴我們,人物的悲劇命運往往為某種無形的不可知的力量所左右,“命運和偶然性剝奪了人的自由意志,決定著人的生死沉浮”[3]。可以預見,沒有覓到真愛的愛德娜將在命運和內在沖動的驅使下,經歷性欲的復蘇,陷入一場婚外戀情之中,而這場婚外戀其實也是格蘭特島上那充滿誘惑環境下的“直接反應”。
島上風景如畫,陽光、沙灘、藍天、白云和遠處海面上的三角帆船構成一座人間天堂。在這樣的美麗環境中,人們會不知不覺勃發天性。對美極為敏感的愛德娜也感到“緊緊包裹在身上的那層矜持的外衣慢慢松開了”。更重要的是,島上回蕩著神秘的大海那永不停息的誘人的濤聲,像情人一樣呢喃低語,感性的海水“把愛德娜的身體擁入它那溫柔而親密的懷抱中”。毋庸贅言,作為動物的人的原始欲望在愛德娜身上漸漸復蘇。與此同時,島上的克里奧爾居民浪漫自由,坦誠開放:人們毫無拘謹地談論有關性的話題,公開評議愛德娜只敢在“僻靜的角落里偷偷看的書”,女人向異性朋友講述自己的妊娠過程,“連細枝末節都不漏掉”。在這種氛圍親密的文化語境中,愛德娜也禁不住敞開心扉,向好友阿黛爾坦露了自己少女時代的三次暗戀經歷。此時愛德娜的性意識覺醒了,她在本能驅使下開始追求愛情,命運安排她愛上了房東太太的大兒子羅伯特。他風趣幽默,給愛德娜讀小說,豐富她的精神世界;他坦率真誠,教愛德娜學游泳,點燃她的愛情火花。“注視著羅伯特在月光中時隱時現的背影”,愛德娜“第一次感到內心欲望的悸動”。
在當時,肖班對于婚外情欲如此直白的描寫自然激起了軒然大波,夫權文化的衛道士們叱責《覺醒》為“淫穢作品”。然而,這些攻訐可以詮釋為對于自然主義文學理念的無知,因為“作為被無法控制的力量所支配的生物,人顯然不能自由選擇,也不能對自己的行為負責”[4]。愛德娜性欲復蘇是內部生物因素和外部客觀環境共同作用的結果,并不受自己的意志支配,正“如硫酸和蔗糖那樣是必然的產物”[5],本質上沒有好壞之分。因此,從自然主義視角來看,愛德娜的婚外戀并非刻意的主觀行為,對她的道德抨擊有失偏頗。
二 性欲描寫:自然主義的典型性
在自然主義之前,“作家們在描寫人的時候,往往總是限于表現人的‘靈’,善的‘靈’,美的‘靈’,惡的‘靈’,丑的‘靈’,怪的‘靈’,正常的‘靈’,反常的‘靈’,等等”[6],往往忽略了人作為自然界高級動物的物質性和生理性的一面。而自然主義在表現人、塑造人的時候,把“血”、“肉”引入文學,注重描寫“情”、“欲”,挖掘生理要求與精神滿足、動物性與靈性之間的二元關系,試圖說明感官和本能對人物命運的決定性作用,從而打破文學表現的禁區,開創了從生理機體的角度來理解、闡釋人的范式,為人類文學的發展帶來了新氣象。肖班為了展現女性對自我解放、自我實現的人生價值的追求,突破社會禁忌,大膽地描寫愛德娜性欲的覺醒和婚外性行為,這無疑決定了《覺醒》具有明顯的自然主義特色。
覺醒后的愛德娜伸直自己的兩只胳膊仔細觀察,第一次發現它們是那樣的結實、細膩而滑嫩,“一股難以言說的欲望之流襲過全身”。她想翻過小山去海邊的渡口,看那在陽光下的海水中上下翻騰的金蛇和蜥蜴。愛德娜在幻想著激情四溢的做愛,“金蛇”和“蜥蜴”象征著男性性器,渡口則是女性的私處。愛德娜體內開始散發出動物的原始欲望和氣息,正如曼德拉醫生觀察到的,她像一只“皮毛光滑而漂亮的雌獸在陽光下蘇醒”。憑著直覺,醫生知道愛德娜和花花公子阿羅賓有染了。阿羅賓行為放蕩,終日縱情聲色,與已婚女性調情和通奸更是家常便飯。這個好色之徒以邀請愛德娜去觀賞賽馬的方式接近她,蘊含在這其中的隱喻意義是顯而易見的。當阿羅賓彎下身來吻她時,愛德娜主動迎上,“這是她人生中第一次滿足了本能的吻”,“像一支火把點燃了熊熊欲火”。此后,愛德娜不可避免地順從了阿羅賓“溫柔、誘人的”性要求,兩人如縱馬馳騁,不時傳來馬蹄快速落在堅硬路面上的尖利聲音,阿羅賓發現愛德娜體內的肉欲像一朵遲開、熱情而敏感的花兒一樣完全綻放。至此,愛德娜的性欲已經完全覺醒了,她發現自己的生理之愛可以獨立于精神之愛,她的肉體屬于阿羅賓,可精神屬于羅伯特。她雖然渴望純潔的愛情,但是又無法抵制身體的欲望,那種用肉體的滿足來彌補精神追求的做法令她悔恨不已,卻又無法自拔,因為她已被性欲本能完全控制。正如左拉所言:“我筆下的人物完全受他們神經和血液的支配,被剝奪了自由意志,情欲把他們推向一個又一個宿命的行動中去。”[7]最終,愛德娜不得不選擇死亡來縫合精神與肉體的錯位,這種由動物本能注定的悲劇恰恰契合了自然主義宿命論。
三 揭示女性生活真相:自然主義的寫實性
《覺醒》的自然主義特色不僅表現在描寫愛德娜的性意識從復蘇到怒放的發展過程,也體現在反映女性生活真相、揭示生命尊嚴的寫實風格之上。左拉認為“小說家最高的品格就是真實感”[8],小說家應該如實地感受自然,如實地表現社會,把生活如他親眼所見的那樣移植到讀者面前。肖班從小博覽群書,從現實主義作家福樓拜、進化論科學家達爾文以及社會學家斯賓塞那兒習得了遵循現實、探求真理的性格和作風。她尤其崇拜自然主義作家莫泊桑,喜歡他力求逼真自然的寫實方法。她采取莫泊桑的寫作模式,仔細觀察和體驗周圍的人們和社會實際,并通過愛德娜的思想和行為反映出她所耳聞目睹的時代風貌。首先,十九世紀末期雖然仍舊為男權所壟斷,但是女性追求性自由已不再是罕見現象,這是女性渴望擺脫家庭束縛、獲取生命自由的呼聲。肖班自己就曾和相鄰莊園主關系曖昧,引起過社區的側目[9]。這種社會價值觀念的變化,也在女性文學中得以體現。美國女性主義批評家伊蓮娜·肖瓦爾特在《她們自己的文學》中把西方女性文學史分為三個階段:1840-1880年“女性特征階段”,這一時期的女作家遵循男權標準,大力頌揚純潔、溫柔、善良、順從等充滿母性特征的家庭婦女的世界;1880-1920年“女性主義階段”,一批如《覺醒》中曼德拉醫生所提到的“新女性”作家在這一階段迅速崛起,公開表現女性自我意識的逐步蘇醒,倡導爭取女性的主體價值和社會權力;1920年以后,女性文學進入將婦女生活、生理和心理經歷作為創作源泉的“婦女階段”。肖班正是第二階段“新女性”作家的杰出代表。此前的女性作家通常把女人描寫成沒有性欲的“體面”的貴婦人,與丈夫做愛是奉獻自我。而“新女性”們開始采取完全不同的態度和看法,認為性冷淡不是女人的天性,而是男權文化壓抑的后果,“健康女性的性欲和男人一樣旺盛”,她們試圖通過揭示、解釋和提高女性性意識的方式來表達對男權社會的不滿。作為代言人,肖班以毫不妥協的筆調,通過眾多的意像和隱喻,采用印象主義的手法,展示了愛德娜蟄伏的性欲逐步復蘇直至完全綻放的曲折過程。
其次,當時的婦女的社會狀況已經發生了顯著的變化,愈來愈多的女性認識到自尊、自愛、自立、自強等人格價值,并開始走上追求自我實現的道路。愛德娜正是反映這一時期美國婦女文化價值提升的文學形象之一。因此,正如1898年發表在《哈珀集市》上的一篇文章指出:“(愛德娜)是實際生活中眾多不知名的女性的代表……”[10],她個人的覺醒實際上是“譴責了嚴重制約女性表達自我和實現其精神追求的文化體制”。我們可以認為,肖班那已內化為其本能的求真求實的寫作原則,和十九實際末期的女性生活現實共同促成了《覺醒》問世。《覺醒》直到今天仍被推崇為女權主義的經典作品,是與它開門見山地揭露女性受虛偽道德之戕害分不開的,而這種真實的揭露也為該作品增添了鮮明的自然主義元素。
[1]Martin Wendy.New essays on the awakening[M].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8.
[2][3]許慶紅.人的困境與人性的悲哀──論英美文學自然主義的共同主題[J].安徽教育學院學報,2002,(4).
[4][5]利里安·R·弗斯特,彼特·N·斯克愛英.自然主義[M].任慶平,譯.北京:昆侖出版社,1983.
[6][8]柳鳴九.西方文藝思潮論叢:自然主義[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
[7]埃默里·埃利奧特.哥倫比亞美國文學史[M].成都:四川辭書出版社,1994.
[9]朱剛.新編美國文學史(第2卷)[M].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2.
[10]Beer Janet,Nolan Elizabeth.The awakening:A sourcebook[M].London:Rouledge,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