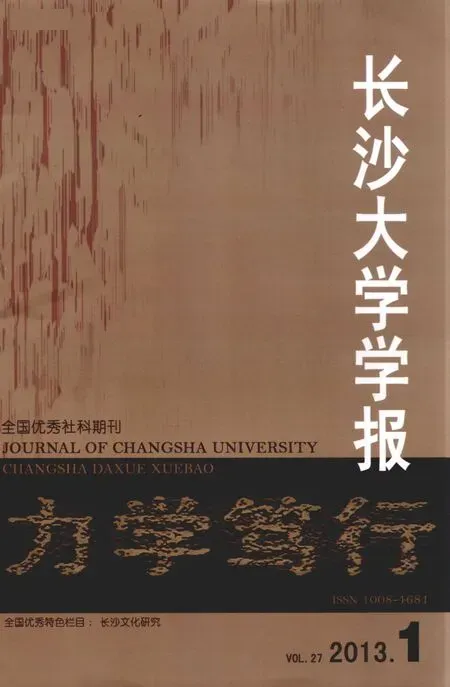言說的德性——南湖藏書樓上談著書
余三定,石運佳,柳春蕊,等
學術研究要關注社會關注現實
余三定
(湖南理工學院《云夢學刊》,湖南岳陽414006)
第一,關于南湖藏書樓。修建南湖藏書樓純粹是個人的愛好,主要是為我們自己的閱讀和研究服務。在今天的社會環境下,這種觀點很能給我們以警醒和啟迪,那就是自己把書讀好就行了,不要去勉強別人。近三四年來,南湖藏書樓成為了學界同仁和文友們快樂聚談的一個場所。
第二,為什么選擇“南湖藏書樓上談著書”這個主題呢?原因有二:一是考慮研討會的連續性。第一次的主題是“南湖藏書樓里話藏書”,第二次的主題是“南湖藏書樓上好讀書”,今年是第三次。三次研討會既各有側重點,又有一定的連續性,以前已經談過“藏書”、“讀書”的話題,所以這次就談“著書”的話題。二是考慮研討會主題的社會性、現實性。現在真正的讀書人是越來越少了(我個人認為真正的“讀書人”應該具備四個條件:一是真正喜歡讀書;二是同時讀專業以外的書;三是具有一定的藏書;四是能寫書,這個“寫書”是廣義的,包括寫文章、寫筆記、寫日記、寫博客等等)。目前,是一個言說充分自由的時代,著書已不復性命之學,而與商業行為緊密相連,只要有錢出版社都愿意出。這導致大量的紙張浪費,也混淆視聽,讓人無所適從。所以,我認為要在心態上嚴肅看待著書,著書要盡可能認真,文章不寫半句空,既為自己負責,更為讀書人考慮。
第三,談談我個人著書的一些體會。其一,我認為知識分子應當主動關心社會、關注現實。知識分子關心現實似乎主要有兩種途徑:一是直接參與現實變革,比如直接為官,直接干預社會,這樣做也許對社會的作用更直接、更大;另一是做學術研究,知識分子用自己的學術成果影響社會,推動社會的前進。我對自己的定位是盡可能用自己的學術成果去影響社會,為社會的前進貢獻微薄之力。因此我的學術研究大都具有現實針對性,我選擇的研究課題大都具有時代性。比如我出版的第一本書《文壇岳家軍論》(1994年)是一部專門研究新時期岳陽文藝現象的書(可謂是對現實問題的近距離跟蹤研究),我和幾位同事合著的《新世紀文論》(2007年)是一部針對新時期重要文藝現象發言的論文集。我在當代學術史研究領域出版的幾部書如《學術的自覺與學者的自立:當代學者研究》(1998年)、《新時期學術發展的回瞻》(2005年)、《當代學術史研究》(主編,2009年)、《當代學術史研究八年論壇》(主編,2012年)、《中國新時期學術熱點研究》(2012年)等等,從書名就可見出其突出的時代特點。其二,我在文風上堅持不說套話、空話,一定要說實話、真話,說自己的話。總之,自覺地關心社會、真誠地講實話,就是我的著書(寫作)追求和特點。
堅定的信念和遠大的目標
石運佳
(北京大學團委會,北京100871)
作為一個北大的學生,要有堅定的信念和遠大與宏偉的目標。因為作為北大人,在一定程度上講,所承載的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歷史責任,因為你們處在高等教育金字塔的頂端,是來自全國各地的精英中的精英,那么就不可避免地承載起更多人的希望。北京大學110多年的歷史發展進程中,始終與國家繁榮、民族昌盛共呼吸,共命運,始終挺立在歷史發展的潮頭!作為在不斷發展和成長中的北大學子,只有樹立正確的人生觀和價值觀,有了堅定的信念,有了豐富、扎實的知識,有了基層生活的歷練,才會擁有真正的家國情懷,才會實現個人目標和報效祖國的人生理想。
今天從著書這件事來講,我個人認為,著書質量的提高要經得住時間的考驗,要尊重事物發展和學術發展的規律,求真務實,強調以學術質量為核心的觀念。你的文章和著作只有經得起時間的考驗,才能得到他人的尊重,才真正是學術發展和創新的完整體現。人是萬物之靈,正在不斷地改變舊世界創造一個新世界,在這個學術不斷創新、科技不斷進步、信息不斷快速膨脹的現代社會,著書從過去主要作為一種學術創新和傳播的手段,又被賦予了新的含義,出書成為一種熱潮,使得書變得良莠不齊,而且讓讀者覺得手足無措,難以分辨!對于這種風潮,有志于學術探索和創新的青年人,如何來著書,我個人的觀點就是,以人為本,在思想上樹立學術為先的意識,兼顧社會實踐活動對學術創新的有效補充,之后把著書立說的工作做好、做扎實,把事做好。在學術傳播和創新過程中,提升個人的理論基礎,在學術知識的普及過程中,實現個人價值!
言說的德性
柳春蕊
(北京大學中文系,北京100871)
早先有竹帛,后來有紙張,現在是網絡,人們言說的方式更為自由方便。人們言說的內容廣為流播,其影響別人或后人者,大抵都可歸入著述之列。古人強調著述者的心志,譬如寫詩,要“發乎情,止于禮義”,有幾層:一是強調詩歌言說主體要心志平和,順乎天地四時的和氣,把自己情志置于先王制定的大禮大法中醞釀,這樣的言說中正不偏。二是強調主體的言說對社會造成的影響。本來,人們的言行舉止也是一種言說,影響他人,但能留傳下來的書籍對人們的思想影響更為深遠。三是人們的情感或偏或正,或激或忿,一受制于同時的名賢領袖,二受制于書籍傳播,傳統儒家注重心性之學,強調中庸不倚,立足的是全社會的情感,這種社會情感又常被指稱為風俗。風俗關乎教化,教化常起于先儒的禮義。這是傳統言說的重要經驗。
在這個前提下,便有“說什么”和“如何說”的問題。人的才性有上中下,故古人常有無言、不言破和“委婉”說。“無言”就是不說,對自己洞見的歷史或真理不予表述,他認為這種洞見或真理如果被言說,會引出更多的誤解和謬見,真理就被曲解,甚而掩沒,或只有等到幾百年后,出一大圣,方能明悟,所以他對于現時段的歷史政治及人物很少評述,更不留一絲一毫言論,飛鴻雪泥,東西無跡,如幻夢境,留與后世大賢以參悟;同時,“無言”也指一種言說方式,一種同乎“無言”的方式。這種方式看似輕松、灑脫,實則沉痛。因為世人多有俗見,他的言說只能戲游人世,任高明的人予以高明的理解,任低俗的人予以淺顯的認識。這種言說,可以看出苦口婆心,可以看出用心良苦,可以看出圣者的言說是一種智慧,是“道”的言說。每每讀這樣的文字,都感受到我們這個民族真了不起,只惜陋儒或經解家將這些瑰寶誤讀或遮蔽了。
不言破,就是言說主體把握住了言說對象,而采取的一種空缺和留白,一鱗一爪,聲東擊西,玩世不恭,詼諧戲謔,言無定所。這是因為世人理解的偏差,更是因為言說主體直接面對的是君主和權力擁有者。先秦的韓非和縱橫家,以及后來的策論,都是勸百而諷一。由此中國的智謀術、心術者愈來愈多,這是“道”下移“法”與“術”的層面。正因為不言破,注意言說效果和言說方式,所以讓人猜忌讓人詮釋的空間也就更為豐富。
“委婉”說,在“道”日益被言說,被公認為是某種“知識”或者常識時,“道”的神秘性和不言說性遭受弱化,這個時候有所擔負的思想家往往將言說內容和言說方式下移,即當將言說內容的價值被界定為“道”,是常識性的“道”,且被認為是遮蔽,人們就不再因言說什么而用心,而是將注意力集中在如何言說這個常識性的“道”上,即如何言說日常倫理——這是自8世紀至20世紀前夜,即從韓愈古文運動到桐城派被“五四”健將宣告為“謬種”,橫貫在中國歷史上長達12個世紀的重要思想問題。圍繞這一問題展開了諸多重要討論,比如說,言說主體究底是以個體為本位,還是以儒家倫理為本位?即“情”的歸屬問題(明代中后期有集中論爭)。討論不外乎兩方面,一是強調言說主體要有很高的道德修養,在12個世紀歷史中,這個道德修養是按照“道統”譜系規定下來的潛在文字里的一種德性,傳統的“文如其人”,也被界定在這一領域;一是言說方式上,要“誠”。即修辭問題,“修辭立其誠”。從這里引申開來的有,“言之有物”,言說內容是“及物”的,是有調查的有研究的言說,文從字順,深入淺出,不以文淺陋,用語清明,文法雅訓,合乎漢語言的表達規律。這個時期,作出最大貢獻的是古文家。今天我們的寫作和言說,受古文家思想的恩澤尤多。
現代社會強調的是個體的獨立性,“我手寫我口”,彰顯的是人的存在,人人都有表述和被表述的權力。在近一百年進程中,個體的表述力空前壯大和集體強化,“語言”的彈性和張力被空前拉大。語言作為一個世界,潛在進行了一場革命,不再是人們在表述語言,而是語言表述我們的意志,“語言”本身已構成一種模式和結構,它的精致和絢麗,讓人們驚奇、懷疑和順從,甚而歸順。如果說,“五四”前后,新舊言說習慣和理念之爭構成思想家論衡的焦點,那么今天所討論的早就不止于言說自身,早已不是新舊問題,而是語言與圖像、語言與其他物質媒介的爭論與襲蝕,包括身體、建筑、城市、環境、性別、網絡,長達12個世紀積淀和探索下來的古典言說經驗,在語言將被驅逐世界之外,在被緊縮成邊緣化之時,它們在今天的意義,是將被重新提出遭受“落水狗”的奚落?還是索性把它們歸入自然博物館?人們順著這無休止的圖像和其他媒質一起瘋狂、漂泊、集體迷茫下去嗎?
這是一個考驗群體知識分子的新時代,同樣是一個偉大的時代。在“言說什么”和“如何言說”的問題上,我們是否如“五四”健將們的努力?有他們的身姿,嘗試創造這個世紀的新言說呢?今天的討論,若是進入這個話題,那么它的意義早已超出“著書”、“讀書”、“藏書”的范圍,而是一個太陽即將破曉,躍出東方地平線,有思想且能開啟新思想新潮流的時代了!
著書三境界之我見
王 巍
(中共中央黨校馬克思主義理論教研部,北京100091)
王國維提出的“讀書三境界”是為人們所熟知的。在《人間詞話》中,王國維說道:“古今之成大事業、大學問者,必經過三種之境界:‘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眾里尋她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此第三境也。”應該說,讀書、著書和藏書,是人類同書打交道的三種最常見的方式,互相之間也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關系。因而,同讀書一樣,著書也可以分為不同的境界,大致來看,有如下三種。
第一種境界是龔自珍說的“著書都為稻粱謀”。在發生學上,這種境界需要從兩個角度來看待,一方面,這是社會環境和學術環境使然,從古至今,絕大多數學者都不得已為了謀生而寫書。甚至常聽到一些學者說:“寫書就是混口飯吃”,這大概就是更為直白的表述了。另一方面,很多人為了沽名釣譽,將“出書”看作謀取其他利益的工具。因而,有“為術”的著書,亦有“為道”的著書。這第一種境界大致還屬于“術”的層面。
第二種境界就是《左傳》中所說的:“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在“三不朽”中,“立德”有賴于見仁見智、標準不一的社會道德評價,“立功”則需要由“內圣”開出“外王”,這些往往需要諸多機緣的共同作用才能完成。于是,文人們多以“立言”為矢志不渝之目標,以求通過著述和學說的流傳來達及不朽。這種境界已經超越了為生存的物質條件而寫的層面,但依然沒有擺脫“揚名后世”的功利色彩。這是介于“為術”和“為道”之間的著書。
第三種境界:“板凳甘坐十年冷,文章不做半句空。”可以說,這是著書的最高境界,既不為物質利益,也不為聲名鵲起,已經超越了名與利的羈絆和束縛。同時,這種境界也是做學問的最高境界。做學問,注定了寂寞和孤獨,但這份寂寞與孤獨也是常人所無法體認和理解的。守得住寂寞,耐得住浮躁,忍得住清貧之人,才能體驗到著書的真正樂趣。在當代學術界,這種境界愈發難以尋覓了,我們也期盼更多的學者能夠以這種著書精神為圭臬,至少做到“雖不能至,心向往之”的敬畏和追求。我們也更期盼現行的社會和學術體制能夠給這樣的學者以寬松的環境,使他們能夠心無旁騖地為“不做半句空”的著作而努力。這第三種境界是“為道”的著書。
是不是說著書只有這三種境界呢?當然不是,可以說,每一個著者都有自己心目中的一種“著書觀”。更何況,中國文人還有著“述而不作”的傳統。劃分著書境界的標準千萬種,以上只是我的一些淺見,請各位批判指正。
如何開展研究工作和著書
程 熙
(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北京100871)
我講的東西僅限于社會科學領域。對于社會科學而言,一本好的著作就是一項出色的研究工作。書的各個章節乃是研究工作不可缺少的環節。
首先要指出的是研究并不等于出臺政策和擺事實。每年社會科學都會出版大量的新書,但是關于某一個議題的書又大同小異,就是因為這些書只是政策報告和事實陳述,而非研究著作。幾周前我師兄博士論文開題,內容關于水利建設中的政治與治理模式。評審的一個老師就他的開題報告說,不要整什么大理論、大方法,就某一個地方的水利建設通過調研,提出一個切實可行的方案,無論是國家、市場還是社會,怎么組合,最終把問題解決就算一篇成功的博士論文了。這樣博士論文豈不變成了一篇政策報告?政策報告和事實羅列不需要創造知識,這是區別于研究的最重要的一點。
創造知識就需要知道知識的邊界在哪里。但是知識是無窮盡的,就像社會事實也是無窮盡的,我們做研究不可能關注每一個細節性的東西,因為沒有“意義”。什么東西可以區分有意義還是沒有意義呢?這就是問題。問題是一本書的靈魂。找到好的問題、有意義的問題是一本書成功的一半。
在問題的指引下,就需要對前人的文章、著作進行梳理,為了找到知識的邊界。文獻分好幾種。一種是純理論,比如我們本科時候學的一些大理論,結構主義、統合主義以及新制度主義等等。讀這種純理論,直觀的感受是很難應用于實際研究。然后就是中層的研究論文。這類文獻的一個主要特點是:即使限定為中國研究,文獻仍浩如煙海,一不小心就很容易淹死。所以關鍵是讀該領域引用率較高的經典論文以及最新論文。最關鍵的是要根據問題有選擇性地梳理文獻。
接著就是在前人的基礎上,提出你的見解。一般以命題假設的形式出現。然后書的主體部分就是論證你的這些假設是可以得到支持的。目前國內絕大多數博士論文之不能稱之為研究,因為他們的工作基本是從國外販來一個新的分析框架,然后使用一些比較簡單的資料(二手或者政府報告等),最后得出一個結論。這種研究基本沒有知識的貢獻。所謂研究,乃是要有知識貢獻的論文。
最后談談什么是好的研究,即什么是好書,值得讀、值得買的書。真正好的研究不在于方法論之爭、不在于事實之爭,而是重新帶給人洞見。社會科學雖然是對于社會事實的描述和解釋,但是如何解釋以及解釋的深度卻因人而異。高水準的社會科學作品乃是一件藝術品,而非標準化的工藝品。當然,我覺得博士階段要先學會做工藝品,不能盲目追求藝術品,否則很可能變成次品。
從人類學思考著書以及人類學家如何著書
范忠秀
(北京大學社會學系,北京100871)
雖則人類學一向給人專注研究“無文字社會”的感覺,但還是有許多人類學家致力于思考文明滄桑變遷中“書寫的魔力”。在此,我愿意提出四位學者的事跡,這四人雖然不都是人類學家,但其思想對后來的人類學思考甚有啟發,在人類學界引起了相當的共鳴。
其一為張光直先生。張先生長期致力于上古中國文明的探尋,在其研究商文明的力作中,張光直先生提出古中國的王權一直與對書寫的權力之控制不可分,而這種控制,導源于古人對書寫撰述的敬畏(倉頡造字“天雨粟,鬼夜哭”的神話,即為其體現),認為書寫乃是天地人神交通的重要組成部分,文字構筑的世界自有其靈力,是王權宇宙觀圖示的再現。這一系列思考近年得到美國人類學大家薩林斯的回應,更將其拓展至對“神圣他性”的比較文化研究框架中。其二是沈從文先生。沈從文先生不僅以小說創作名世,其晚年論述尤多對文藝理論和美學的深刻思考。我在此提請大家注意的,是他的兩個文本。一是抗戰勝利后他自西南回到北平,在一封致友人的信中呼吁“我們現在要提倡一種新神話”;另一是1959年左右他在一封私信中提出似可將古代知識分子感時憂國的諸多思考視為一種“抽象的抒情”。沈先生對于著作的抒情本色,對于書寫之“物色緣情”而深具神性的特質極為注意,后來治中國思想史與文學史者進而提出中國的“抒情傳統”這一宏觀命題,而此一傳統對于人類學對中國的文化想象,是極大的挑戰,尚未得到充分回應。其三為李澤厚先生。李澤厚先生在上世紀80年代的若干著作可以說總結并進一步闡揚了兩位前輩的觀點,以“巫史傳統”回應張光直,以“情本體”的總體美學—哲學框架回應沈從文,但李先生將之進一步推進至“文化心理積淀”的層次,實指出著作之所以是足以讓人不朽的立德大事,就在于其展現了一個人完整的意義理性世界。在此,李先生的判斷與今日人類學中文化心理學一翼的若干論說若合符節。其四是余國藩先生。余先生久居海外,擅于從比較文學與文化的視角來討論傳統中國思想的若干命題。其對中國文學撰述的宗教性的闡發最為精妙,而能自覺地將古代知識分子的“宗教意識”與其對“情”的理解放在一起加以討論,起到相互發明的妙處,由此,余先生提出,中國古人的著述亦有其宗教情懷在,而這種情懷的核心,還是一種對“情”的認知。
總結這四位學林先賢的思考可見,前人對著書的神圣性、對其中的道德體驗和情感內蘊有著充分的體會,這是今日我們值得注意的。
人類學家的著書,有一獨特的文類,即為民族志。考其語源,此詞指稱的實是常人生活世界的總體描述的意思。人類學家通過長時期的田野工作,進入一方人民的生活世界,試圖寫下一部深描與深思兼備的作品,以其對人文世界的反思性考察和對大量充滿意義細節的鋪陳引起世人的關注。其中精義,或可以“漂泊的洞察”概括之。這樣的著作,需要想象力與思辨的能力,但又不僅僅是空幻的想象或空疏的玄思,更是懷有同情之理解的深入求索,保持反省能力的一種精神對話。近年人類學界開始興起“寫文化”之風,詩學與政治的交響成為新的人類學書寫的主旋律,但這種著書的新風格是不是一種價值觀的暴力,引起諸多憂思。在此時刻,以“情”為關鍵詞的中國書寫著作傳統,似乎更有引起對話的價值。
問題意識和著書
俞 祺
(北京大學法學院,北京100871)
我此次帶來了兩本書,一本由中國學者撰寫,另一本由美國學者撰寫。僅從兩本書的目錄看,我們似乎便可以發現一些不同。最大的區別在于中國學者的問題意識并不足夠清楚,基本還是采用了一種教科書式的寫作方法;相比較而言,美國學者的著作更注重對于問題的梳理,而不是對概念的界定。前一種寫作方式不利于論文邏輯結構的充分展開,嚴格來說不能算一種學術論文的寫作方法,但長期以來,在本學科內,這種形式的論文或著作卻長期存在,不知其中原因何為?
另外,學術研究某些時候似乎和時代的命運緊緊相連,在一個問題集中發生的時代中,學者們是幸運的,因為有許許多多的問題可以研究。但是在一個相對平穩的時代中,重大問題極少,作為一個學者所能做出的貢獻也相對會受到限制。這與詩人寫詩有異曲同工之處,所謂國家不幸詩家幸。
從語言學角度來看著書寫作的多維面向
武宏琛
(北京大學對外漢語教育學院,北京100871)
從語言學角度來說,著書寫作和日常交談一樣,也是一種借助語言傳遞信息、表達思想感情的途徑,因此也存在著會話的發送者、接受者、媒介三大主體,包含編碼、解碼等傳遞流程。就此而言,著書寫作,發出者都是作者本人,然而接受者,或者說是寫作的對象則是有多重面向的。粗略分來,有個人化的內向型寫作和群體化的外向型寫作。
面向個人的寫作可以說是最為包容的,一條微博、一篇日記皆可稱之為自我的言說和記錄,是個人化的寫作;因人而異、因時而異。因此對于這種類型的寫作,我們作為讀者的時候,也要以更包容的心態去看待,寫作是人人都有的權利,表達所思所想所見所聞也是人人都有的權利。
而面向群體或者他人的寫作,則是受限的。正如會話交際原則中要求的那樣,面向他人的寫作,要想作品不是文字垃圾、有一定的讀者群體,就一定要保證寫作符合“質量、數量、方式、關系”四方面準則:首先要傳遞的是有效信息,不是假信息、舊信息;其次要保證語言的精煉,不是過分地堆砌或者流水句;再者要以適當的語體表達出來,不能將日常用語、網絡用語過多地出現在學術寫作中(當然,如果寫的是網絡用語調查報告,則另當別論);此外,還要保證寫作的針對性,例如,寫給小孩子看的科普書,就不適宜出現過多的學術名詞。面向群體著書寫作的發出者遵守這些準則,雖不能完全保證著作的高水準和思想性,但起碼能保證著書寫作的良好風氣,日積月累,自然有經典奉獻于世人。
著書的態度與快樂
李燦朝
(湖南理工學院文學院,湖南岳陽414006)
現今著書的環境、著書目的與傳統的著書有了很大不同,那么我們該持一種怎樣的著述態度?當今時代言論充分自由,學者文人不復有龔自珍詩所言“避席畏聞文字獄”之苦。著述環境寬松、出版門檻降低,這是一把雙刃劍,某種程度上可以說它促進了學術文化的繁盛,但另一方面也導致泥沙俱下,產生了大量的泡沫文字、泡沫學術。著書、出書不再是學者文人的專利,誰都可以公開出版著述,這便不可避免地導致大量無創造性的重復勞動。
在著書目的上,現代學人帶有較強的功利性,“著書都為稻粱謀”。高校工作者大多為職稱而著述,以適應現行的評估體制,因為論文、著作的數量在高校成為了衡量一個人學術水平的重要標桿。文學創作上也是適應市場需求,追求利益最大化,擺出所謂先鋒的姿態,用身體寫作,兜售個人隱私和瑣屑的日常生活以搏眼球。當今的學術氣候、學術機制已經很難讓人把著述當作一項神圣、莊嚴的事業。中國古代儒家倡導“三不朽”的價值觀——立德、立功、立言。著書為了立言,立言為了傳世,像《史記》“藏之名山,傳之后世”,追求的是不朽。當今不為稻粱謀,真正把學術作為一種“志業”,作為自己安身立命之所的乃為少數,余三定《論胡繩的治學精神》一文中,認為胡繩是為了時代和人民的需要而進行學術研究,此乃真正的學者,大多數人對學術的終極目標很迷茫,難以達此境界。
古人將“立言”視為“三不朽”之一,認為文章乃”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對待著述的態度是謹慎的。孔子堅持“述而不作”(孔子整理六經實際上是寓作于述,或曰既述又作),雖是一種自謙,但表明了一種態度。一些大學者也不輕易著書,如黃侃先生“不到五十不著書”,此論不一定可取,但對著述我們確應懷著一顆敬畏之心。急功近利、剽竊抄襲的速成產品難免“速朽”。在著書態度上,每個人都應該做到有學術感悟、學術沖動才執筆,情動于中不得不發,就如春蠶吐絲欲罷不能,這樣的著述經過才不會是苦差事,才能“找回失落了的學術情趣”。就個人體會而言,我在寫作《越水悲歌——明末清初越中文人及文學研究》(南京大學出版社)一書的那段日子,是我人生中最充實的一段時光。心無旁騖地閱讀、思考、寫作,別有一番滋味,那種靈光乍現、豁然開悟的文思,以及吉光片羽的思想火花的迸發,讓我感受到了寫作中最深刻的快樂。正如南湖藏書樓主余三定老師所言,著述的快樂,是進取的快樂,探索的快樂,發現的快樂,成功的快樂。
為中國的學術文化建設事業盡綿薄之力
盧英宏
(湖南理工學院期刊社,湖南岳陽414006)
我在讀歷史著作時發現,有宋一代為何文人揚眉吐氣?那是他們真正是在讀真書,寫真書。我所知道的范仲淹、歐陽修、蘇軾、蘇轍、王安石、周敦頤、程頤、程顥等等,他們都是有自己的深刻思考和見解的。這點可以看到我們與古人(特別是宋人)的差別。而學術重鎮北京大學的老師們在今天也不能說沒有差別。是正規軍,可以寫出很有學術價值的著作,也可以寫出為人詬病的膚淺的書。所以,下筆之前,你必須為生民立命而寫,為萬世開太平而寫,為個人尊嚴而作。至于我自己,也曾想在讀書著書方面獨步天下,也曾想在某個領域笑傲江湖,但這只是一個夢想,因為畢竟學識、學養根基不牢,能力也成問題。因而我的讀書與著書實際上是我個人的精神文化享受。但我還是找到了一塊不為人知或被人熟視無睹的學術處女地,那就是中國反戰文學研究,并已寫出《中國反戰文學史》初稿。我覺得,在我們為稻粱謀的著作行動中,一定有被普世公認的價值所在。我們發現這樣的有價值有意義的主題,并為之而發掘,那就是在為中國的文化事業作貢獻。在文化事業遭受不斷沖擊的當下,需要有擔當的學人為之奮斗。讓我們一起行動,為中國的學術文化建設事業盡綿薄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