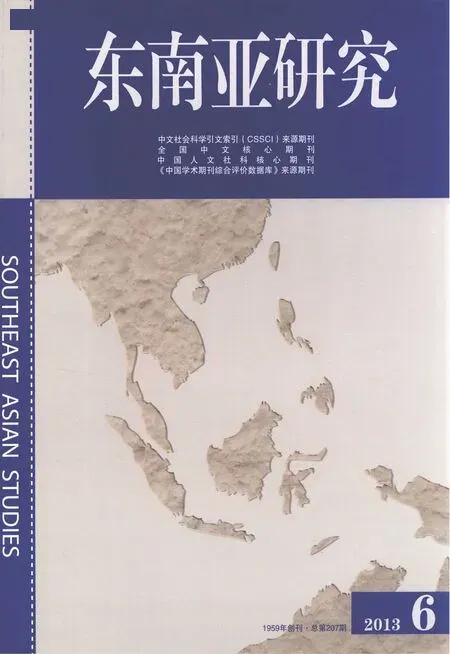革命路線與外交合作:20 世紀60年代初期的中印(尼)關系發展
張小欣
(暨南大學華僑華人研究院 廣州510630)
1960年后中國發展對印(尼)政策面臨著復雜的國內外環境。大躍進所帶來的農業生產衰退嚴重困擾中國社會經濟穩定,對“三面紅旗”如何認識在黨內產生巨大分歧,而美蔣對大陸沿海地區的軍事侵擾、中蘇分歧加劇和中印邊界爭端所引發的“反華大合唱”,使中共中央最高領導人認為階級斗爭長期存在的現實性和支持世界范圍內民族民主革命運動的必要性。而印尼總統蘇加諾借爭取民族獨立和亞非世界的領袖地位,來進一步爭取國內左右政治力量和強化民族凝聚力,并用反帝反殖運動所掀起的民族感來掩飾國民經濟的不斷衰退,收復西伊里安等就是其具體舉措。在中國大力支持印尼民族民主革命運動的過程中,雙方結成了亞洲國際格局中的特殊關系。本文在已有研究基礎上①相關研究見Ide Anak Agung Gde Agung,Twenty years Indonesian Foreign Policy,1945 -1965,The Hague:Mouton & Co,1973;DavidPaul Mozingo,Chinese Policy in Indonesia,1949 -1967,A Dissertation for the Degree Doctor of Philosophy in Political Science,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1973;黃阿玲:《中國印尼關系史簡編》,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1987年;聶會翔:《蘇加諾時期中國與印尼關系探究》,湘潭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8年;許振政:《印度尼西亞華人中的親臺灣群體:境遇與應對(1949—1960)》,廈門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8年;周陶沫:《華僑問題的政治漩渦:解析1959—1962年中國對印度尼西亞政策》,《冷戰國際史研究》2010年第1 期;李一平、曾雨棱:《1958—1965年中國對印尼的援助》,《南洋問題研究》2012年第3 期等。已有研究對20 世紀60年代初期中國與印尼關系發展的時代背景、政治理念以及印度因素對中印(尼)關系影響等問題的考察還有待進一步深入。,根據中方相關檔案資料等對該問題展開具體探討。
一 中國的革命外交路線
中國對印(尼)政策是中國外交政策的組成部分,受中國國內政治路線變化影響深刻,特別是進入20 世紀60年代,中國國內政治逐漸出現激進化現象,并在外交路線上通過黨內批評“三和一少”和“三風”問題實現了思想意識統一,同時在中蘇辯論中,中共中央將支持民族民主革命運動的重要性,提升到與國際社會主義革命運動相當的理論高度,并由此成為指導中國外交工作總路線的組成部分。
1960年以來中國對外友好關系處于活躍階段,不僅在社會主義陣營內部與蒙、朝、越簽署含有軍事援助條款的友好同盟互助條約[1],加強了與阿爾巴尼亞、古巴等國友好關系,而且在推進民族民主革命運動方面,支持亞非拉國家的反帝反殖民運動,同時在解決邊界劃分和僑民問題基礎上,繼續拓展睦鄰友好關系。而中國大規模對外援助成為鞏固此類友好關系的重要舉措。正如周恩來所說:“我們的政策是加強社會主義陣營的團結,加強社會主義陣營的力量,堅定立場,靈活地利用帝國主義矛盾,堅決支持亞、非民族獨立運動和一切反帝和平力量。”[2]就對外援助問題而言,“對社會主義國家,實行互助,互相支持,增強團結;對民族獨立國家,支持他們取得獨立,擴大和平地區。”[3]
在上述指導思想下,自20 世紀60年代初期起,中國對外援助的廣度和深度得到空前提高。例如,繼1955年7月中國向北越提供8 億元人民幣無償援助,及1959年2月提供3 億元人民幣貸款和1 億元人民幣無償軍事援助[4],1960年10月和1965年7月中國又分別向北越提供6 億元人民幣貸款[5],以及10 億元人民幣無償援助[6]。1960年3月中國向尼泊爾提供1 億印度盧比無償援助,1961年9月中國再次提供350 萬英鎊無償援助,支持尼方修筑從加德滿都到科達里的公路。1960年12月中國向柬埔寨提供400 萬英鎊無償援助。同年9月中國與幾內亞簽署經濟技術合作協定,向幾內亞援建火柴廠、卷煙廠、水電站、茶葉試驗站等。1961年9月向馬里提供700 萬英鎊無息貸款,用于工業項目建設和農業技術援助。1963年10月中國向阿爾及利亞提供2.5 億法郎無息貸款用于援建成套設備[7]。因阿爾巴尼亞在中蘇分裂中支持中國,中阿關系獲得快速發展,1961年2月中國向阿方提供相當于5 億元人民幣的無息貸款,1965年又向阿方提供相當于7.14 億元人民幣的貸款等等[8]。
中國大規模的對外援助與大躍進后日漸衰退的國內經濟狀況形成鮮明對比。1960年后中國工農業比例失調和農業生產下降情況愈發嚴重。1960年8月10日中共中央在發出的《關于全黨動手,大辦農業,大辦糧食的指示》中承認:“一九五八年和一九五九年連續兩年,在青黃不接時期,都出現了糧食緊張的局面。一九六〇年麥收之后,收購不快,庫存減少,調撥不靈,某些城市糧食供應仍然緊張。”[9]盡管《指示》采用“緊張”一詞來委婉說明國內農業生產下降所造成的后果,但緊接著11月中共中央發出《關于立即開展大規模采集和制造代食品運動的緊急指示》,直接明確要求各地抓緊秋收完畢時機,大規模動員群眾,采集和制造代食品,以克服困難,渡過災荒。中央根據科學院建議,推薦玉米根粉、小球藻等為代食品[10]。而1961年1月周恩來在接見越南副總理阮維楨時坦承,中國建國11年來,每年都出口,從未進口過糧食,今年被迫進口糧食了。3月1日周恩來向毛澤東報告糧食進口問題,說明截至2月22日的統計,中國在當年第二、三季度的糧食供給尚差74億多斤,因此決定當年進口糧食100 億斤(合500萬噸),已經簽好合同的有52.4 億斤,正在談判的還有50 億斤[11]。
中國經濟的困難與萬分沉重的外援負擔在黨內引起深刻反思。1962年3月31日中聯部部長王稼祥主持撰寫和審定了《關于支持別國反帝斗爭、民族獨立和人民革命運動問題——實事求是,量力而行》,文中提出: “我們應該支持別國的反帝斗爭、民族獨立和人民革命運動,但又必須根據自己的具體條件,實事求是,量力而行。特別是在我國目前處在非常時期的條件下,更要謹慎從事,不要說過頭,做過頭,不要過分突出,不要亂開支持的支票,開出的支票要留有余地,不要滿打滿算,在某些方面甚至需要適度收縮。預見到將來我們辦不到的事,要預先講明,以免被動。”[12]而在此之前的2月7日,王稼祥還主持撰寫和審定了《關于我國人民團體在國際會議上對某些國際問題的公開提法》,其中認為世界戰爭并非不能避免;武裝斗爭并非是爭取民族獨立的唯一道路,因而不反對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在爭取民族獨立斗爭的過程中與帝國主義談判;在和平組織中,不要把民族解放運動講得超過了和平運動,等等[13]。
王稼祥的報告反映了中國經濟困難與大規模外援之間的客觀矛盾,以及黨內對大規模外援和中國多方面展開反帝反修外交路線的不同看法,這是繼七千人大會后黨內同志對中央外交路線的一次坦誠批評,不僅要求中央高層領導在中印1962年邊界爭端、中蘇分裂和國內經濟蕭條等情況下,制定適合中國實際國情的外交政策,同時要求中央重新審視對世界大戰在即的形勢判斷,以及社會主義、資本主義間是否可以較長時間和平共處等理論問題,其實質是要求中央慎重判斷中央工作的重點是革命還是發展的重大問題。王稼祥作為主管外交一線工作的黨內重要領導人,其言論和判斷在當時無疑具有合理性,同時也是借七千人大會后中央一度形成的民主風氣,以及最高領導在前期工作自我批評基礎上形成的較好政治氛圍,來表達自身對外交工作的意見。但是王稼祥的報告遭到黨內嚴厲批評,被稱為“三和一少”修正路線。中國超越既有條件而實施面向亞非拉、不計成本式的外交政策,是當時國內革命思想在外交領域延伸的主要標志。
1962年7月28日下午在北戴河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毛澤東提出“國際上的外交、外事工作方面,也有右的苗頭。”[14]8月6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中心小組會議上講話,提出階級(即究竟有沒有階級,社會主義社會究竟存不存在階級)、形勢(即對國際國內形勢究竟怎么看,國內形勢是不是一片黑暗,還是有點光明)、矛盾(即社會主義社會是不是就沒有矛盾了,有些什么矛盾)三個問題。此后毛澤東在多次談到這三個問題時,進一步把部分中央同志對經濟形勢的估計批評為“黑暗風”,把支持“包產到戶”批評為“單干風”,把彭德懷等要求中央重新審查歷史問題的訴求批評為“翻案風”。而周恩來在會議上提出:“階級斗爭是長期的,階級貫穿在各個時期;形勢一改變,我們的同志就模糊了。”[15]中央工作會議的召開為即將開始的中共八屆十中會議奠定了重要思想基礎。1962年9月14日在八屆十中會議華東組開會期間,外交部主要領導人就“三和一少”問題做了重要發言,并獲得毛澤東的肯定。該發言談到:
現在有一股風,叫“三面和一面少”。意思是說我們對美國斗得過分了,對修正主義斗得過分了,對尼赫魯斗得過分了,要和緩一點。一少,是指我們對亞洲、非洲、拉丁美洲支持太多了,要少一點。這種“三和一少”的思想是錯誤的。大量的事實說明我們同肯尼迪、赫魯曉夫、尼赫魯聯合戰線的斗爭是躲不掉的,是非常必要的,但是我們的斗爭又都是有分寸、有約束的,不能說已經斗過分了。對于民族解放運動,隨著我們力量的不斷增長和技術的提高,我們還應當給他們以更多的支持。在這個問題上,我們不能目光短淺,不能打小算盤,要打大算盤,不能只算經濟帳,要算政治帳。所以又吹起了“三和一少”那樣一股歪風,主要是三年的暫時困難,把一些馬列主義立場不堅定的人嚇昏了。要批駁這種意見。現在我們的外交政策是正確的,它有助于我們爭取時間,克服暫時的困難。如果采取機會主義的政策,不僅會影響對外斗爭,而且也會影響國內局勢。[16]
在上述會議基調影響下,9月29日正式公布的八屆十中全會公報中提出:“在五項原則的基礎上,爭取和社會制度不同的國家和平共處,反對帝國主義的侵略政策和戰爭政策;支援各國被壓迫人民和被壓迫民族反對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的革命斗爭。”而“在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整個歷史時期,在由資本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的整個歷史時期(這個時期需要幾十年,甚至更多的時間)存在著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斗爭,存在著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這兩條道路的斗爭。”[17]
八屆十中全會的政治影響極為深遠,不僅將階級斗爭作為長期存在的歷史現象提升為全黨工作的中心問題,將支持民族民主革命運動作為取得國際共運勝利的戰略措施給予肯定,而且在黨內統一了發展與革命何者重要的看法,在國際共運中樹立起與帝國主義、反動派和修正主義“大反華”力量相抗衡的中國革命大旗。這一點表明中共中央領導人已認為:蘇聯修正主義無法正確詮釋國際革命形勢和充當社會主義陣營的領導角色,對蘇聯一邊倒的外交政策徹底結束,而在外交路線中堅持國際共運和支持民族民主革命運動,逐漸成為中國推進世界革命的兩大主要任務,正如鄧小平所言,中國外交“不能一邊倒”,劉少奇則認為, “全世界絕大多數人民總是要革命的,革命這是最根本的,要有代表革命的方針,有代表反對帝國主義的方針”[18]。
針對蘇共中央的修正路線,1963年6月14日中共中央發表了《關于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的建議》,其中提出: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廣大地區,是當代世界各種矛盾集中的地區,是帝國主義統治最薄弱的地區,是目前直接打擊帝國主義的世界革命風暴的主要地區;這些地區的民族民主革命運動,同國際社會主義革命運動,是當代兩大歷史潮流;這些地區的民族民主革命,是當代無產階級世界革命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在一定意義上,整個國際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終究要以占世界人口絕大多數的這些地區的人民革命斗爭為轉移;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人民反對帝國主義的革命斗爭,絕不是一個區域性的問題,而是關系到整個國際無產階級世界革命事業的全局性問題[19]。
上述對20 世紀60年代初期中央關于支持世界民族民主革命運動思想變化的梳理,其用意在于:(1)中共中央有關階級斗爭長期存在的理論判斷是導致革命化外交路線的根本原因,而毛澤東在1962年9月29日《外事簡報》第137 期的批語中指出,“國內外修正主義都要里通外國”[20],點明了在全黨范圍內重視階級斗爭的客觀原因和階級斗爭的艱巨性;(2)八屆十中全會是明確中央外交戰略的關鍵會議,同時中央外交路線的確立是通過黨內路線批判和人事改組獲得的,王稼祥的報告被定性為“三和一少”,其本人被要求在中聯部檢討,全會增選陸定一、康生、羅瑞卿為中央書記處書記,同時決定撤消黃克誠、譚政書記處書記職務,以此獲得黨內思想意識的統一; (3)國際社會主義革命運動和世界民族民主革命運動是中共中央要全力支持的兩大國際任務,而民族民主革命作為國際無產階級革命運動的組成部分,在國際人口數量和地理分布上占有優勢,因此在本質上有利于推進社會主義革命運動; (4)亞非拉反帝革命斗爭不是孤立的,是相互聯系且能夠影響全局的國際問題,因此中共中央認為全力支持亞非拉反帝革命斗爭是最終能夠戰勝帝國主義的根本保障; (5)在階級斗爭尚存和帝國主義沒有消滅的階段,革命應該是一以貫之的主題,發展應該服從革命的需要。因此,將中共中央外交主導思想的確立與下文中對印(尼)關系探討結合起來就能進一步理解,當印尼因收復西伊里安等而掀起全國性的民族獨立運動之時,中印(尼)關系在反帝反殖革命紐帶下走向合作的原因。
二 印尼的反帝反殖外交路線
當印尼在蘇加諾領導下實施“有領導的民主”后,西伊里安問題不可避免地作為考驗蘇加諾對國家領導力和處理對外關系能力的核心事件,而美國初期采取偏袒荷蘭的所謂中立主義態度,以及聯合國大會多次就西伊里安問題辯論未能通過的事實,一再表明印尼通過西方國家設定的解決途徑根本無法迫使荷蘭回到談判桌前。而更為重要的是,在經歷外島叛亂、排華運動和馬斯友美黨、社會黨政治對抗后,蘇加諾已經確認印尼的革命道路遠未完成,如何能將不同立場的個人、政黨、派系糅合進統一的印尼民族意識,如何實現國家凝聚力,是蘇加諾思考的大問題。為此,他在20 世紀60年代初期提出不以階級劃分而以不同信仰融合為基礎的“納沙貢(NASAKOM)”思想(民族主義、宗教信仰、共產主義的一體性)[21],而這種一體性在外交領域的反映就是為實現收復西伊里安和清除殖民主義所做的群眾動員。在此情況下,蘇加諾試圖采取軍事對抗方式并在理論上提出新興力量概念來解決印尼的國際困境,而此舉先后得到印尼共產黨(以下簡稱“印尼共”)和印尼陸軍的支持。
1960年8月17日蘇加諾在印尼獨立日演講中強調:“在對外關系方面,我們也仍然堅持著革命的主要精神,這就是團結國內和國際上的一切力量,反對以至最后消滅任何形式、任何地方的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我們特別地把重點放在解放西伊里安的斗爭方面”,而在此方面“民族力量是起決定作用的,民族力量是國家和民族中的一切政治力量、經濟力量、社會力量、民事力量和軍事力量的總體,我們用這個總體來對付荷蘭帝國主義力量!”[22]但是何者為印尼在國際社會能夠團結的力量,顯然成為蘇加諾有關國際局勢判斷的主要問題。同年9月蘇加諾在聯合國大會上發表的題為“重建世界”的演講中提出,他作為“第三種力量”的代表盡管接受世界三分的觀點,但是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才是國際關系的主要問題[23]。顯然,蘇加諾不認為冷戰中的意識形態對立能夠涵蓋世界上的主要矛盾形式。1961年9月蘇加諾在貝爾格萊德召開的第一屆不結盟國家領導人會議上,明確提出:
當前的世界觀點認為,國際緊張和沖突的真正根源在于大國間的意識形態分歧。我認為這并非真實。這是一種深入肉體的沖突,是一種在追求自由和公正的新興力量,與一方面無情剝奪他國,而另一方面不顧一切地維護既得利益、阻礙歷史進程的舊有勢力之間的沖突。……不要為意識形態的沖突所迷惑。這個問題要留給各國。新興力量與舊有勢力之間的沖突已為越來越多的國家所接受,因為舊有勢力在利用民族國家保持舊有平衡的同時,新興力量卻致力于發展這個世界。…… (因此)世界必須承認,新興國家作為一種協調力量,致力于一種新型穩定平衡的建立,……在每一個個案中,國際緊張的根源和原因都是帝國主義以及民族國家的被迫分裂。過去的歷史和今天的現實證明,不同的社會制度可以共存,但是獨立公正與殖民主義、帝國主義絕不能共存[24]。
貝爾格萊德會議所體現出的印尼外交政策特點和影響在于:
第一,用新興力量和舊有勢力概念來重新劃分國際社會,不認為意識形態對立的兩大陣營是主宰國際社會運行的根本因素,而將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作為國際危機根源,視反殖民主義和反帝國主義力量為真正影響國際社會的因素。此種劃分不僅有利于提升以印尼為代表的新興力量的國際地位和外交能動性,而且有利于爭取社會主義國家對印尼反帝反殖運動的支持。蘇加諾的外交概念和計劃通過貝爾格萊德會議前的一系列雙邊互訪,實際上已經獲得很大范圍的認同和支持。1960年9月幾內亞總統杜爾訪問印尼,雙方表示反對殖民主義的斗爭是國家獲得獨立的前提。1961年1月阿爾及利亞總理阿巴斯訪問印尼,蘇加諾再次強調萬隆會議的精神體現了反對帝國主義和反對殖民主義。同年5月蘇加諾先后出訪安哥拉、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6月訪問羅馬尼亞、蘇聯、中國、南斯拉夫、日本等國。貝爾格萊德會議后的9月21日,蘇加諾在東京向印尼留學生發表講話再次強調,“新興的力量”同維護過去的舊制度的沖突才是國際社會帶有根本性的問題。
第二,印(尼)共和印尼陸軍先后表示支持蘇加諾的外交政策。印(尼)共總書記艾地從貝爾格萊德回國后即表示:“印度尼西亞共和國、蘇加諾總統和印度尼西亞人民認為,不結盟國家必須同社會主義國家一起反對帝國主義,這種態度是正確的”;“不結盟國家會議的精神是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革命精神”[25]。印尼陸軍對于蘇加諾的支持更集中地表現在西伊里安問題上,正如國防部長納蘇蒂安提出的“中間道路”概念,軍隊在印尼事務中應該居于重要角色,但并不占據排他性的統治地位[26],因此對于總統的政策持支持態度。1961年1月納蘇蒂安率軍事代表團訪問莫斯科,獲得蘇聯4.5 億美元軍事貸款,用于購買蘇制坦克、火箭、戰斗機、中型轟炸機等,貸款期12年,年利率2.5%,且有數百名軍事人員陸續被送至捷克斯洛伐克等國接受軍事訓練[27]。盡管納蘇蒂安一直希望美國能提供重型武器援助,但是艾森豪威爾在執政末期,因為顧及荷蘭在北約防務中的地位和警惕蘇加諾領土擴張的野心,而始終沒有提供[28]。1961年底,印尼成立“解放西伊里安戰區司令部”;1962年1月由蘇哈托少將任戰區司令,通過空降傘兵和突擊隊滲透西伊里安而開始登陸作戰[29]。
第三,與尼赫魯的外交觀點產生沖突。尼赫魯認為不結盟會議的職責和功能就是告訴大國必須進行協商,而國際問題的解決主要在于美蘇兩個大國,會議應該促使它們盡快締約以減少戰爭及維持和平,同時不結盟國家應該致力于減少柏林危機等可能引發新型戰爭的危險,而不是形成新的軍事陣營,并且目前典型的殖民主義根本不存在。尼赫魯與蘇加諾截然不同的觀點使得會議形成不同的支持派別,大多數激進的非洲國家、南斯拉夫、埃及等都支持印尼,而塞浦路斯、摩洛哥、埃塞俄比亞以及部分亞洲國家則支持印度,以至于在會議各專門委員會的討論中都很難形成一致意見,甚至印尼認為收復西伊里安就必須采取對抗荷蘭的政策,而印度則質疑對抗的含義。細究兩國爭論的背后原因可以看出,蘇加諾為收復西伊里安而有意倡導第二次亞非會議,欲借助亞非國家集團的力量實現國家統一并進一步樹立印尼的國際地位,但是尼赫魯認為萬隆會議已經充分體現亞非國家的團結,如果再開第二次會議可能將印中就西藏問題引起的爭端公開化,有損印度的外交利益。因此,印尼與印度外交利益的差異使兩國原本親密的關系變得疏遠,從而在尋求塑造新型國際關系的道路上,印尼必須在新興力量中尋找到新盟友[30]。
第四,中國對蘇加諾的外交政策和國際力量劃分新提法給予了積極和正面呼應。1961年6月15日蘇加諾訪華期間發表的聯合聲明就提出:“印度尼西亞政府再一次明確表示,全力支持中國人民為收復自己領土臺灣的斗爭。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再一次明確表示,全力支持印度尼西亞人民為從外國統治下解放其一部分領土西伊里安而進行的斗爭。”“雙方重申,決心團結世界上一切進步力量,不斷向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及其一切表現進行斗爭;并且堅決支持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國人民為爭取和維護他們的完全獨立和實現美好生活而進行的每個斗爭。”[31]同時在此次訪問中,蘇加諾獲得了中方此前已經答應的3000 萬美元貸款,用于援建印尼的紡織工業[32]。而對于貝爾格萊德會議,8月17日陳毅外長在會見蘇卡尼大使時就表示,中國政府完全贊同第二次亞非會議,并希望即將召開的不結盟國家首腦會議能在反帝國主義、反殖民主義方面起到良好的作用,警惕帝國主義企圖轉移會議斗爭目標來破壞會議的陰謀[33]。周恩來于8月31日也致電不結盟會議表示:“愿會議對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國人民爭取和維護民族獨立、反對帝國主義的侵略和干涉、反對新老殖民主義、保衛世界和平的事業做出貢獻。”[34]而在評價新興力量時,周恩來還曾談到:“新興力量在開始出生的時候,看起來總是比老的力量弱一點,小一點,這是很自然的。社會現象同自然現象一樣,一個嬰兒剛剛出世時總比老人又小又弱,但誰最有生命力呢?是嬰兒,不是老人!誰最有前途呢?是嬰兒,不是老人!”[35]中方不僅明確接受蘇加諾的新興力量概念,而且贊同印尼運用革命手段對抗新老殖民主義。
貝爾格萊德會議所反映出的印尼外交政策變化內涵極為豐富。蘇聯在提供軍備銷售方面奠定了印尼對抗荷蘭的武力基礎,此舉一方面提升了軍隊在印尼的重要性,但在另一方面可以通過對反殖民主義的支持,既反駁中國對蘇聯的批評,又提升印(尼)共在國內的地位,使印(尼)共認識到不必通過國內的階級斗爭,而通過類似爭取西伊里安的政治姿態所博得的廣泛認同,仍然可以促使印尼和平過渡到人民民主階段[36]。而事實上,沉重的還貸壓力以及赫魯曉夫對蘇加諾擁護社會主義的質疑(如赫魯曉夫私下里認為: “蘇加諾所采取的立場相當靈活,雖然他嘴上說原則上擁護社會主義,但擁護什么樣的社會主義,還很難說”[37])使得蘇印(尼)關系在實用層面上的意義更為突出,而其引起的印尼內部矛盾也更為復雜。印尼與印度的矛盾是兩國對東西方陣營和亞非集團國際職責不同看法的結果,且對亞非集團團結性的破壞以及改變印尼和平中立外交形象的影響極為深刻。印尼與中國在對外革命政策上極為接近,且中國作為社會主義大國和在亞非世界有巨大影響力的國家,加強兩國關系能夠彌補印尼與印度外交疏遠的負面后果;同時在臺灣與西伊里安問題上的相同命運,使得兩國合作具有現實基礎,而中方也通過安撫僑民以及提出穩定印尼國內經濟的建議等,為印尼收復西伊里安創造條件。
三 中印(尼)外交關系的加強
1962年1月20日印尼華僑的選籍工作告一段落,其中除100 多萬屬于“不言而喻”的無須選籍者外,在152 萬具有雙重國籍的華僑中,有108萬選擇了印尼國籍,16 萬選擇了中國國籍,未按期選籍者有8 萬,未達到選籍年齡者有20 萬,他們要待成年后的一年中再行選籍[38]。而此前周恩來在接見印尼駐華大使蘇卡尼時曾表示:“如果經濟上不擺脫殖民主義的控制,就不能算做真正的獨立。我們發展國民經濟的方針是以農業為基礎,工業為主導。工業的發展是很重要的。對于印尼籍華裔,應當由你們去勸導。對于華僑,我們愿意勸導他們幫助印尼發展工業。”[39]蘇加諾對于華僑的態度也在發生變化。1963年初新一波反華浪潮在西爪哇、中爪哇開始蔓延,此時蘇加諾發表演說,不僅指斥社會黨和馬斯友美黨兩個非法政黨是運動背后的煽動者,下令逮捕暴力活動的領導者,而且宣布排華是違背國家利益和受帝國主義挑唆的[40]。他警告“反種族行為將危害印尼根基,要求人民防止類似事件再度發生,呼吁印尼人民及華裔印尼人民團結起來。”[41]由此,排華活動得到制止。在中印(尼)雙方合作解決華僑問題的基礎上,中國在黨的路線、雙邊關系和亞非國際論壇等三個層面大力推動有關西伊里安問題的解決。
1962年9月29日公布的中共中央八屆十中全會公報,將印尼人民為收復西伊里安進行的勝利的斗爭,作為全世界人民反對美帝國主義的侵略政策和戰爭政策、反對新老殖民主義斗爭繼續高漲的實例,在黨的路線中要求對其加以支持[42]。
在雙邊關系上,除1962年初中方派出以吳階平為首的醫療組赴印尼為蘇加諾總統醫治腎病外,1962年9月蘇加諾夫人哈蒂妮訪華,劉少奇、周恩來等國家領導均予以熱情接待,10月印尼駐華大使館在華舉辦慶祝印尼共和國建軍17 周年招待會,楊成武上將、羅瑞卿大將等到會并重申對西伊里安問題的支持,1963年1月印尼副首席部長兼外長蘇班德里約訪華。中方對蘇班德里約此次訪華給予了高度重視,中國外交部提出:“蘇班德里約1959年以外交部長身份訪問中國時,正值印尼掀起排華時期。蘇返國后認為我接待安排簡慢,表示不滿。1961年陳毅副總理訪印尼時,還有人企圖以冷遇報復,后經蘇加諾阻止,才給予陳毅副總理隆重接待。根據目前形勢和中、印尼兩國關系,此次蘇班德里約訪華,建議給予熱情、隆重的接待,禮遇方面擬按照我對外國副總理訪華的接待規格略為提高。”[43]此外,外交部在地方的接待宣傳口徑上要求:“指出兩國人民在反對帝國主義、殖民主義的斗爭中,在收復臺灣和西伊里安的斗爭中,一貫相互同情,相互支持”; “贊揚印尼政府和人民在蘇加諾總統的領導下堅持執行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及其成就;肯定印尼人民在亞非人民團結反帝的共同事業中所作出的貢獻;支持印尼方面提出召開第二次亞非會議的主張”等[44]。蘇班德里約此時也極為重視對華關系,其在印尼外交部會議上就曾提出: “現在的國際關系不再只是美蘇兩方的關系,而是美、蘇、中三方的關系。”[45]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先后會見了代表團。1月8日兩國發布聯合聲明提出:“雙方對兩國友好合作關系的發展深為滿意,作出一項有利于兩國經濟發展的、新的貿易安排”;“印度尼西亞政府重申支持中國人民收復臺灣的斗爭,感謝中國對印度尼西亞解放西伊里安斗爭的支持。雙方聲明,將繼續同世界上一切其他進步力量一起,為反對帝國主義、殖民主義和新殖民主義而堅持不懈地進行斗爭。”[46]
在亞非國際論壇方面,1963年2月4 -11日在坦葛尼喀共和國的莫希舉行第三屆亞非人民團結大會,共54 國250 余位代表出席,在中印(尼)合力推動下,大會通過有關西伊里安問題的決議:
歡呼印度尼西亞人民在迫使荷蘭殖民主義者于1963年5月1日最后放棄對印度尼西亞的合法領土西伊里安的統治方面所取得的勝利,并認為這是非洲和亞洲一切反對殖民主義和愛好獨立的人民的勝利。
完全支持西伊里安人民所要求的迅速結束在西伊里安的聯合國臨時行政管理機構的過渡時期,立即把西伊里安歸并入印度尼西亞共和國,宣布西方殖民主義者關于舉行“與印度尼西亞共和國合而為一或成立自己的國家”這種公民投票的要求為無效。大會抗議1963年1月在當地聯合國當局縱容下射擊和平示威者的事件[47]。
在印尼的不懈斗爭和國際社會的廣泛支持下,荷蘭于1962年10月1日將西伊里安領土主權移交聯合國臨時管理機構,次年5月1日由聯合國將西伊里安移交印尼,并決定在1969年12月31日前由該地居民自決歸屬。1963年5月1日在印尼實施接管當天,中國國家主席劉少奇和國務院總理周恩來向蘇加諾發出賀電:“我們深信,在閣下的領導下,印度尼西亞人民和政府保持警惕、堅持斗爭,一定能夠取得解放西伊里安的徹底勝利,一定能夠實現建立一個從沙璜到馬老奇統一的共和國的正義事業。” “中國人民一向把印度尼西亞人民的斗爭看成是自己的斗爭,把印度尼西亞人民的勝利看成是自己的勝利。中國人民將永遠同印度尼西亞人民站在一起,在反對帝國主義和新老殖民主義的斗爭中互相支持,共同奮斗。”[48]
小結
20 世紀60年代初期中印(尼)外交關系的強化,不僅是兩國國內意識形態和政治道路發展方向和目的的重要產物,也是東南亞冷戰發展時期東西方對立的重要產物。其影響不僅在于進一步加大了美國面對的印支戰爭和印尼民族主義勃興所帶來的外交壓力,還在于進一步疏遠了印尼與印度的外交關系,造成第三世界國家關系發生分化并形成愈加復雜的新形勢。同時,這一影響還改變了東南亞冷戰的格局,使得中國的外交影響延伸至中南半島地區之外的東南亞最大國家印尼,東南亞半島地區與海島地區反西方主義的思潮以及亞洲共產主義影響顯然逐步增大,東南亞冷戰進入快速發展時期。
【注 釋】
[1]《對締結中蒙友好合作條約問題的批語》(1960年3月21日),《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九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第88 頁。
[2][3][5][8][9][10][11][15][34][35][39]《周恩來年譜(1949—1976)》 (中卷),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第415 頁、第387 頁、第362 頁、第387 -388 頁、第338 頁、第369 頁、第388 -394 頁、第492 頁、第431 頁、第574 頁、第447 頁。
[4][6][7]《方毅傳》編寫組:《方毅傳》,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46 頁、第281 -315 頁、第289 -302頁。方毅,1953年9月擔任中央人民政府財政部副部長;1954年8月由中央委派擔任越南政治顧問團團長、黨委書記;1956年5月任中國駐越南經濟代表;1961年任國家計劃委員會副主任和國家對外經濟聯絡總局局長,兼任國務院外事辦公室副主任;在1961—1976年期間主持中國對外經濟援助工作;1977年當選為中共第十一屆中央政治局委員;1978年被任命為國務院副總理。
[12][13]徐則浩編著《王稼祥年譜(1906—1974)》,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年,第489 頁、第486-487 頁。
[14]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傳 (1949—1976)》(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第1235 頁。
[16]《在中共八屆十中全會華東組情況簡報上的批語》(1962年9月),《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第188 -189 頁。
[17][42]《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十次全體會議公報》 (1962年9月29日),北京大學歷史系編《中共黨史學習文件匯編(社會主義革命時期)》,北京大學歷史系,1973年,第167 -174 頁。
[18]《少奇同志接見各民主黨派、無黨派、民主人士、工商聯負責人座談會上的講話》(1963年1月14日下午),廣東省檔案館藏廣東省工商聯合會檔案248 -1 -48,第1 頁。
[19]《關于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的建議》 (1963年6月14日), 《關于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的論戰》,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12 頁。
[20]《對〈外事簡報〉第一三七期的批語》 (1962年9月29日),《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第199 頁。
[21]〈澳〉J·D·萊格,上海外國語學院英語系翻譯組譯《蘇加諾:政治傳記》,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356 -361 頁。
[22]〈印尼〉蘇加諾: 《我們的革命道路》 (1960),《蘇加諾總統演說集(1959—1963)》,雅加達:翡翠文化基金會,1964年,第64 -68 頁。
[23][28] Rex Mortimer,Indonesian Communism Under Sukarno:Ideology and Politics,1959 -1965,Ithaca and London: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74,p.179,p.187.
[24][27] [30] [32] [36] [40]Ide Anak Agung Gde Agung,Twenty years Indonesian Foreign Policy,1945 -1965,The Hague:Mouton & Co,1973,pp.330 - 331,pp.294 -299,pp.328 -338,p.430,pp.296 -297,p.431.
[25]《艾地談不結盟國家首腦會議 會議宣言是獨立外交政策的勝利和對修正主義的打擊 某些人想使會議離開目標的立場遭到強烈反對而失敗》,《人民日報》1961年9月23日第5 版。
[26]Harold Crouch,The Army and Politics in Indonesia,Ithaca and London: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78,p.39.
[29]〈印尼〉蘇哈托自述,居三元譯,黃書海校《蘇哈托自傳——我的思想、言論和行動》,世界知識出版社,1991年,第87 -93 頁。
[31]《中國印度尼西亞聯合新聞公報》, 《人民日報》1961年6月16日第1 版。
[33]劉樹發主編《陳毅年譜》 (下),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886 頁。
[37]〈蘇〉赫魯曉夫著,述弢等譯《赫魯曉夫回憶錄(全譯本)》(第三卷),社科文獻出版社,2006年,第2636 -2637 頁。
[38]聶功成:《關山度若飛:我的領事生涯》(新中國外交親歷叢書),新華出版社,2009年,第14 頁。聶功成,1958年畢業于外交學院,1960年赴中國駐印尼棉蘭領事館工作,1961年改任中國駐印尼巴厘省首府登巴薩市選籍辦公室主任,后又在雅加達總領館和馬辰領事館工作,1964年底返國。
[41]《印尼總統蘇卡諾指責兩個非法政黨(社會黨、右派回教黨)是最近排華運動的煽動者》 (1963年5月19日),《中華民國史事紀要(初稿)》(1963年1 至6月份),臺北:國史館,1999年,第494 -495 頁。
[43]《關于印尼副首席部長蘇班德里約訪華接待計劃的請示》 (1962年12月31日),廣東省檔案館240 -1 -1341,第1 -2 頁。
[44]《關于印度尼西亞共和國副首席部長兼外長蘇班德里約訪華的宣傳通知》(1962年12月29日),廣東省檔案館240 -1 -1341,第5 頁。
[45]《蘇班德里約SUBANDRIO》 (1962年),廣東省檔案館240 -1 -1341,第12 頁。
[46]《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印度尼西亞共和國政府聯合公報》,《人民日報》1963年1月8日第1 版。
[47]世界知識出版社編《第三屆亞非人民團結大會文件匯編》,世界知識出版社,1963年,第21 頁。
[48]世界知識出版社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外關系文件集(1963)》(第10 集),世界知識出版社,1965年,第247 -248 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