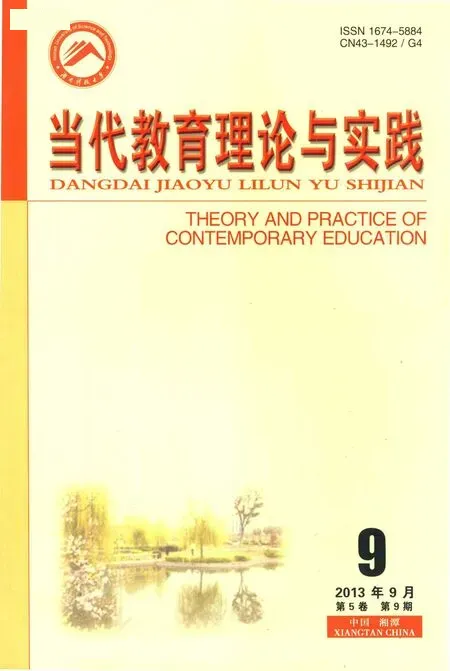本雅明論“都市大眾”
唐 博,常遠佳
(1.湖南藝術職業學院 黨政辦,湖南長沙410012;2.湖南師范大學 外國語學院,湖南長沙410000)
在“論波德萊爾的幾個母題”一文中,本雅明寫道:“大眾——再也沒有什么主題比它更吸引19世紀作家的注目了。”[1]愛倫·坡、馬克思、恩格斯、波德萊爾和雨果等作家不約而同地在他們的作品中描繪了大眾。“大眾”何以成為19世紀代表作家和本雅明的關注對象?這里的大眾并非指抽象意義上的人民,而是指伴隨著工業化進程出現的都市大眾。都市大眾是資本主義時代的新興產物,有著新的生產和生活方式,是新型的人,有著不同以往的心理機制。通過評述、分析和對比不同藝術作品中的“大眾”,本雅明將讀者的視線引向形成“大眾”的社會。王才勇在譯者前言中指出,本雅明關心的“并不是孤立的藝術現象本身,而是由該現象折射出的文化內涵”,目的是“揭示出這種變化之后蘊藏的社會之變”[2]。
波德萊爾生活的19世紀中葉和本雅明生活的20世紀上半葉,都是西方現代化進程得到全面展開和鼎盛發展的時期。盡管往往由波德萊爾的詩入手,但本雅明去展示的主要并不是這些詩本身,而是產生這些詩的時代,是這個時代給人特有的精神體驗。“因而本雅明意欲展示的其實就是現代人心底深處的一種精神體驗,并將這種心理過程展現為現代人之所以為現代人的根源所在。”[2]本雅明意欲展示資本主義工業化是如何影響和形成現代人特有的心理機制的。
在資產階級放聲歌頌進步神話時,本雅明無比清醒地看到了這種神話的虛幻和矛盾;同時,他努力將現代人從這種進步神話的迷夢中喚醒,進而意識到工業化進程對人的異化和摧殘。
一 都市大眾形象
在本雅明列舉的作家作品中的大眾形象中,愛倫·坡的《人群中的人》呈現的大眾形象是最令人震撼的。故事敘述的是一個大病初愈的敘述者追蹤一個老年人在都市人群中穿行的經歷。這個老人不斷地追尋著人群,在一個人群散去之時又去追逐另一個人群,如此循環往復,永不疲倦,只有在人群散去之時,才會倍顯絕望與疲憊。老人對人群無比迷戀,而人群對于老人既不相干,也全然陌生。
愛倫·坡對于行人的描寫很令人費解和震撼:
行人中的很大一部分都顯出一種心滿意足、有條有理的神態,似乎他們所思所想的就只是穿過那蜂擁的人群。他們的眉頭皺在一起,他們的眼睛飛快地轉動;被人推搡碰撞之時他們也不急不躁,只是整理一下自己的衣服又匆匆前行。另有數量也不少的一部分人姿態中透出不安,他們紅著臉一邊走一邊自言自語,比比劃劃,仿佛他們在摩肩擦背的人流中感到寂寞。當行路受阻時,這些人會突然停止嘀咕,但會比劃得更厲害,嘴角露出一種心不在焉且過分夸張的微笑,等著前面擋路的人讓開道路。如果被人碰撞到,他們會毫不吝嗇地向碰撞人鞠躬,顯得非常地窘迫不安……[3]
新型大眾的特征形象而生動地在愛倫·坡的筆下展現。這些“上等人”在街上行走時不但行色匆匆,而且神情恍然,如在夢中,即使被人沖撞,還“會毫不吝嗇地向碰撞人鞠躬”。本雅明稱贊愛倫·坡的描寫是大手筆,如此傳神地描繪出現代人的形象。
恩格斯在他的《英國工人階級的狀況》一書中寫道:“二百五十萬人口這樣聚集在一個地方,是這二百五十萬人的力量增加了一百倍……。好像他們彼此毫不相干……誰對誰連看一眼也沒想到。所以這些人愈是聚集在一個小小的空間里,每一個人在追逐私人利益時的這種可怕的冷漠,這種不近人情的孤僻就愈使人難堪,愈是可怕。”[1]人群的近距離接觸和人與人之間的冷漠形成巨大的反差。人能夠相距如此之近,卻彼此毫不關心,這樣的景象使人充分感受到人群中“丑惡和違反人性的東西”。
二 工業化勞動與都市大眾
在追尋都市大眾形成的原因時,本雅明受馬克思的影響,將眼光轉向工業化勞動。在生理作家們大唱新型勞資關系贊歌的時候,馬克思一針見血地指出了資本主義社會勞動的異化本質:勞動成果無法由工人自已支配;生產資料私有制是勞動異化的根源;工人勞動越多,越是使自己成為被壓榨的對象。
資本主義無限追求勞動效率和勞動成果的最大化,因此工業化勞動無限崇尚效率,流水作業應運而生。流水作業本身使勞動成為一種機械運動,使傳統意義上的勞動技藝不復存在。勞動的創造性和勞動產品帶給勞動者的滿足感,在流水線上消失殆盡。本雅明引用馬克思的理論評價說:“不是工人使用勞動工具,而是勞動工具使用工人。但是只有在工廠系統內這個轉變才第一次獲得了技術和可感知的現實性。”在流水線上工作的時候,工人們不得不學會了調整他們自己的運動“以便同一種自動化的統一性和不停歇的運動保持一致”[1]。“這些話揭穿了那種荒謬的統一性,坡想把它加于大眾——那種行為和打扮的統一性,以及面部表情的統一性。”“坡的作品使我們懂得了野性與紀律之間的真正聯系。他的那些行人的舉止就仿佛他們已經使自己適應了機器,并且只能機械地表現自己了。”[1]在生產機械化的同時,工人們為了適應這一進程,也被機械化了。坡筆下那些神情恍惚的行人如此成功地被訓練成了工作的機器,以至于他們在工作之余還處于機械的狀態之中。
本雅明進而將工業化勞動與賭博進行類比,將秉性高貴的勞動與臭名昭著的賭博并置一處,這一類比令人震驚。但工業化勞動的某些特質又的確與賭博有某種相似性。勞動從一種藝術或技術變成了一種機械運動。“賭徒的樣子甚至應和了那種工人被自動化造就的姿勢,因為所有的賭博都必不可少地包含著投下骰子或抓起一張牌的飛快的動作……機器旁的每一個動作都像是從前一個動作照搬下來的,就像賭博里擲骰子的動作與先前的總是一模一樣,因而勞動的單調足以和賭博的單調相提并論。”[1]
賭徒們被“信奉的機制攫獲了他們的身心”,即使在私下里,“他們只能有反射行為。他們的舉動也就是坡的小說里行人的舉動。他們像機器人似地活著,像柏格森所想象的那種人一樣,他們徹底消滅了自己的記憶。”[1]時間對于這二者來說是同質的,每一秒都是上一秒的重復,是線性的、空洞的、重復的、沒有記憶的。時間的積累在手工業勞動時代是有價值的,而且是成為熟練工人必須要有的的錘煉,在這個意義上,過去是“工作賴以建立的基礎”[1]。而在工業化勞動中,時間的記憶被消滅了。時間和經驗不再有意義,經驗被剝奪,時間只是無限機械的重復。
機械化大生產在極大地促進了生產力發展的同時,也造成了人的異化和人與人之間的隔絕。在本雅明生活的時代過去了半個多世紀之后,我的手機上出現了一條時尚新詞——工業化冷漠的釋義:高速發展的現代化工業將人當作生產中的一個螺絲釘,而忽略了人的情感因素。工廠的管理也過分物質化和標準化,以致人在工作過程中像一個機器零部件一樣冷冰冰,員工之間的關系也因這種高效的管理變得冷漠。這種環境中的人們感覺不到成就、尊重,只有挫折與疲憊,嚴重的則會導致自殺等極端行為。而富士康事件為這種工業化冷漠的極端后果做了一個注解。
三 商品拜物教與都市大眾
資本主義社會組織嚴密,運轉自如,生活其中的人大部分如本雅明筆下的賭徒一般,被這種機制所攫獲,皆因有商品這一極具魔力的東西。馬克思稱之為商品拜物教。簡言之,商品拜物教是商品生產關系的產物,是在私有制為基礎的商品經濟條件下,人們對商品的崇拜和迷信。商品本為人手產物,但一旦貼上商品標簽,便不由人控制,反成控制人的力量。具體而言,就是商品的運動,即價值運動,貨幣的運動,表現為不依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必然性,甚至表現為物對人的支配過程。商品的價值規律作為一種自發的、盲目的力量支配著商品生產者的經濟活動,因而使人們產生對商品的盲目崇拜,以為商品有一種神奇的力量支配自己。而當商品生產者通過交換來表現自己的勞動的社會性質時,就不再表現為他們之間的社會關系,而是表現為他們與物的關系和物與物之間的關系了。總之,商品生產者之間的勞動關系,表現為商品之間的價值關系;人和人的生產關系,則表現為物和物的關系,甚至是物對人的統治關系。
商品和都市大眾互相依存。本雅明敏銳地指出:大眾形成市場,物品成了商品,人群成了顧客,陶醉于商品的魅惑之中。商品對人群展示種種虛幻的滿足。商家會想方設法使人的需求移情于商品,使人陶醉于商品的魅力,成了商品的奴隸。從而鑄就了繁榮的商業文明。人群是這個商業鏈條中的不可或缺的一環。人群也是使自己成為商品奴隸的最關鍵的一環。
本雅明要做的是把人從這個商品的迷夢中喚醒。他幾乎是咬牙切齒地寫道:“只要一個人作為勞動力還是商品,他就沒有必要在這商品中置入自己的東西。他越意識到自己的存在方式是那種生產制度強加給他的——他越是使自己無產化了——他也越加被冰冷的商品經濟所攫住,也就越加不會移情于商品。”[2]如果不能認清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下商品拜物教的本質,都市大眾就成了壓迫自己的同謀。
有意思的是,在商業時代,在面對“現代化進程中勢不可擋之自我失落現象”時,本雅明看到了“現代人對留下個體痕跡之物品的收藏所作的保存個體性的努力”,也通過“指出當時出現的時尚現象的實質做出了暗示”[2]。現代人對工業時代的自我失落現象的抵御是消費性的。為彰顯個性,他們裝飾時尚的居室,穿著風行的服飾:“在資產階級的餐室內的那里,設置了一個來自塞沙·鮑吉亞喜慶廳;走出家庭主婦的閨房,有一個哥德式的小教堂;家庭主人的書房那邊,安頓著波斯酋長的套房。”某些服裝隱藏著它們里面的東西:“他們帶著木然、瑣碎和世俗,交換著會意的目光。這種虛無主義是資產階級自得其樂的最深層核心。”[4]
商品符號代表的個性毫無疑義也是具有統一性的,正如坡筆下不同階層的職員身上具有標志性意義的不同著裝一樣:
職員是人群中一個明顯的部分,我看出他們分為引人注目的兩類。一類是住寄宿房間的低級職員一群西服緊身、皮靴锃亮、油頭粉面、自命不凡的年輕紳士。……他們的風度在我看來完全是流行于十二個月或十八個月以前的優雅風度之惟妙惟肖的模仿。……
那些精明強干或“老成持重”的高級職員不可能被人誤認。辨認這些人的標志是他們那身剪裁得能很舒服地坐下的黑色或棕色的衣褲,配著白色的領帶和西服背心,以及看上去很結實的寬邊皮鞋和厚厚的長統襪或者腿套。……總是用一種結實的老式短金表鏈系表。
所以,在今日消費文化以銳不可當之勢影響著我們的時候,我們應該有清醒的認識。
四 “人群中的人”與“游蕩者”
本雅明刻意地區分開了“人群中的人”與“游蕩者”。“人群中的人”任人推撞,而游蕩者身上尚存“個體意識”,刻意保持“回身余地”,雨果遮蓋了個人與群體之間的門檻,而波德萊爾刻意區分這個門檻。
波德萊爾認為,“把坡的敘述者窮形盡相地描繪出來的夜間倫敦的‘人群中的人’同‘游蕩者’相提并論是頗恰當的。”而本雅明認為這一觀點“難以接受”;而且“人群中的人絕非游蕩者”。因為,本雅明認為,“在人群中的人身上,沉靜讓位于狂暴行為。”[1]“行人讓自己被人群推撞,但游蕩者卻要求一個回身的余地,并且不情愿放棄那種閑暇紳士的生活”[1]。本雅明如此執著地將行人與游蕩者區分開來,是為了區分兩類人,一類是完全已經被人群同化,另一類人還在竭力抵御這種侵襲,保持著自我意識。然而正如弗里斯比指出的那樣“真正的閑逛者是一個受大眾和生產商品化威脅的臨時現象”[1]。真正的閑逛者在商品社會是不可能存在的。那些刻意讓自己與大眾保持距離的英雄也只能是反英雄。“因為資產階級的價值和道德早已站在了人類自由的反面;在一個由物和金錢統治的世界里,洞察真理或僅僅是體驗真實的角度并不是人的角度,而是物的角度,商品的角度,是‘異化了的人的角度’。”[1]
資本主義所創造的巨大的生產力是難以否認的,它創造的技術進步給人類的生產和生活方式帶來了極大的改變。但同時,也把人放在了自然的對立面。在征服自然、掠奪自然的過程中,資本主義社會更進一步把人變成了資本、生產、商品和消費的奴隸。本雅明敏銳地洞察到了資本主義進程中的這種“功利性的謀劃”以及這種迷夢對人的異化和消極影響,他要做的就是使人們從這種迷夢中覺醒。而本雅明的深刻洞見即使在今天也有很強的現實意義。
[1]漢娜·阿倫特.啟迪:本雅明文選[M].張旭東,王斑,譯.北京:三聯書店,2008.
[2]瓦爾特·本雅明.發達資本主義時代的抒情詩人[M].王才勇,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8.
[3]愛·倫坡.人群中的人[J].曹明倫,譯.名作欣賞,1999(3).
[4]戴維·弗里斯比.現代性的碎片[M].盧暉臨,周 怡,李林艷,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