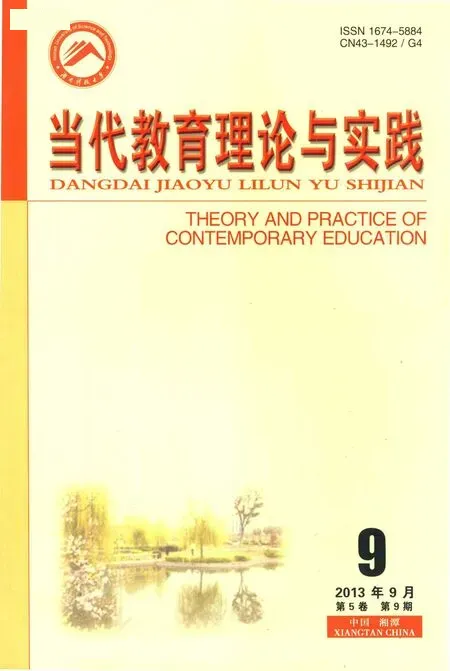論文學功能結構的多樣性與功能的多元化
肖祥彪
(湖南科技大學中國古代文學與社會文化研究基地,湖南湘潭411201)
在正式展開論述之前,有一個問題需要注意:文學功能的多元化與功能結構的多樣化是相互聯系的兩個問題;前者是指文學具有多種功能,后者指文學功能的結構形態和表現形式具有多樣性。
關于文學功能的多元化,經過了20世紀80年代的大討論之后,學界基本上達成了共識,即文學有三大功能:“認識作用、教育作用、審美作用”,它們的關系是:“認識作用是基礎,教育作用是目的,審美作用是手段。”[1]這種歸納表述雖然差強人意,但修正了文學功能單一化的理論模式,在認定三大基本功能的前提下,確認了文學功能的多元化特征,擺脫了“文革”期間政治對于文學的桎梏,為文學的發展繁榮提供了理論上的支持。
孔子說:“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論語·陽貨》)美國學者韋勒克、沃倫也說:“實際上文學顯然可以代替許多東西——代替在國外旅行或羈留;代替直接的經驗和想象的生活;還可以被歷史家當作一種社會文獻來使用。”[2]文學的功能具有多樣性,文學甚至可以代替很多東西。在文學中,可以宣講政治,弘揚道德,傳播宗教;看《紅樓夢》能夠學到很多歷史知識,讀《魯賓遜漂流記》能夠體驗滯留荒島的寂寞,車上拿本《女友》雜志可以消磨時間。
人有多種多樣的需要,充分認識文學功能的多元化特征是非常有意義的,但同時,我們需要防范這樣的危險:文學“是這”、“是那”,唯獨沒有了“自身”。之前的“政治工具論”和現在某些人心中的“功能多元化”,實質都是工具論,如果我們不加以警惕,就會在放縱功能結構某一項或某幾項功能的過程中,弱化甚至取消文學的本體規定性,造成文學本身和人自我的雙重迷失。譬如在今天的消費時代,人們內心的操守、把持少了,外在的訴求、欲望多了,快餐文化、消遣文學特別地活躍了起來。文學在莊與諧、雅與俗、純與不純的“左走”與“右走”間搖擺不定。我們知道文學應有歷史的擔當和社會的責任,但文學不應當給人精神愉悅甚至消遣嗎?形式上的“失語”緣于認識上的模糊。我以為,要解決好諸如此類的問題,還得從最基本的理論建設著手,而對文學功能結構形態的分析,就是突破口之一。
一 顯性功能與潛在功能
文學功能的顯性不顯性、潛在不潛在,主要是由文學文本的結構決定的,在文本結構中處于顯性位置的自然容易被接受者所感知,而處于深層隱含狀態的則難以被察覺。
在波蘭理論家羅曼·英加登提出的文學文本層次構成理論中,一個作品“它包括(a)語詞聲音和語音構成以及一個更高級現象的層次;(b)意群層次:句子意義和全部句群意義的層次;(c)圖式化外觀層次:作品描繪的各種對象通過這些外觀呈現出來;(d)在句子投射的意向事態中描繪的客體層次。”最后形成“質的整體的結晶的核心”,在有些作品中是“具有審美價值的情感性質構成質的綜合整體的價值核心”,或者是“一個陷入悲劇沖突的人物性格”,或者是“表現在一種形而上學性質的形式中”[3]。概括地說,第一層為語音層次;第二層為語義層次;第三層為作品世界層次;第四層為作品觀念層次;最后是取決于以上層次的“有機合成”形成的“復調和聲”才得以呈現的“形而上”層次。在他的逐層遞進的作品構成理論中,我們可以看到,前四個層次,可以說任何文學作品都具備,而最后一個“形而上”層次,則不是一般作品所能具有的。
透過最表層的語音和文字,我們得到了語義;透過語義的層面,我們得到了“作品的世界”;透過“作品世界”的層面,我們得到了“觀點”;但只在少數作品中,我們透過“觀點”的層面,得到了“形而上性質”那種崇高的、可怕的、神圣的或悲劇性的等等言說不清的東西,而在大部分作品中,我們只能兩手空空。前面的四個層面與最后的“形而上性質”并不構成直接的因果關系,也就是說,崇高的、悲劇性的、可怕的、神圣的等“形而上性質”,必須來之于“語音”、“語義”、“世界”、“觀點”四個層面,但這四個層面的組合并不必然地都能產生“形而上性質”。如果說語音和語義的字面義構成了作品的最穩定的“顯結構”,那么,語義的聯想義和觀點則構成了作品的變化著的“潛結構”。這“潛結構”只能“寄生”于作品的“顯結構”之中。
按照金健人的理解,文本結構產生相應的意義結構。根據“顯”與“隱”的關系排列,它們是“題材”層、“字面形象”層、“特殊問題”層、“一般問題”層、“普遍問題”層、“基本問題”層、“終極問題”層共七層[4]。盡管這七層的歸納不夠簡明,但卻能夠說明作品意義的層次關系。前三層是所有作品共有的,即一切作品都得寫人和事以及由“此人”、“此事”體現的“這個”問題。越往下,能夠具有的作品就越少。多數作品只停留于通過特殊的人和事反映社會的一般問題,只有少數作品才能透過上述層面進入到對人類基本問題、人生終極問題的思考與追問。這也就是“快餐”、“流行”與“經典”的區別。
文學功能的發揮,需要在作品與讀者的互動關系中進行,缺少任何一方,都只能是空談。相對說來,作品表層結構的顯性意義具有自動呈現的特性,讀者容易接受顯性義的作用,從而形成對具體的人、事、現象的“看法”。而處于深層結構的隱性義,則具有“阻拒”的特性,它是經由表層結構的“誘發”、“召喚”,通過讀者的聯想、想象而形成的,它作用的往往是人的世界觀、人生態度這些帶有根本性的問題。因此,文學的顯性功能具有及時性、膚淺性的特征,而隱性功能才是恒久和深刻的。
在接受美學理論中,文學欣賞的過程是作品與讀者“視界融合”的過程。視界融合的前提之一,就是作品要有這樣的“視界”,即作品要有一種“既有”,讀者才能將其主體情感和體驗“投射”其中,在“對話”中進行“填空”,否則,讀者的聯想與想象就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也就是說,文學作品的隱性功能必須是作品“潛在”的,是作品本身具有而非外加的;它之所以處在“潛在”狀態,其一是它隱含在深層結構中難以被發現,其二可能是受主體心理因素和時代的制約,接受者不具備發現的能力。就是在這種意義上說,文學具有“超前性”和“預言性”。理想的狀況是,作家通過自身的努力,使作品具有形而上的層次和功能;讀者通過自身素養的提高,具有創造性發現作品潛在義的能力,從而使作品的功能最大化。
二 靜態功能與動態功能
上面我們所作的,實際上是從面與層兩個維度對文學進行共時性的靜態分析。
在面的分析中,我們認識了文學的多功能特性。文學有政治功能、道德功能、宗教功能、文化功能、情感功能、心理功能、符號功能等等,文學能夠多方面地滿足人的精神需要。正是這種特性,使文學在生活中扮演了許多種角色,文學的張力、魅力、重要性,從這里可見一斑。
在層的分析中,我們則把握到文學功能的層級性。翻開任何作品,讀者首先接觸到的是“作品世界”,感受到的是作品形象系統所提供的感官滿足。這里有五顏六色、多姿多彩的生活現象,有美麗如畫的自然風景,有個性鮮明的人物形象。“栩栩如生”、“躍然紙上”、“如在目前”、“真實再現”等等術語,都是對文學感性功能特征的描述。透過形象系統,我們接觸到的是作家作品的“觀點”。作家在描繪生活現象的過程中,自覺與不自覺地要流露出他的是非判斷、好惡評價和美丑評判,所謂“揭露”、“批判”、“贊揚”、“歌頌”等詞匯就是對作品觀點的歸納與抽象。作家在作品中所表露的情感態度必然會對讀者產生這樣或那樣的影響。當我們的思維進一步深入,在優秀的文學作品中,我們就能感觸到其“形而上”的性質。作家不一定是哲學家,但他們一定有良好的思維素養。無論是他們的主觀愿望還是他們的無意識的創作沖動,都會指向事物的本源、本質、本原、本體,從而在讀者面前敞開一個“新的世界”。所謂“靈魂震撼”、“人生啟迪”、“生命感悟”等,都是對作品“大象無形”式的形而上思想在讀者靈魂和觀念上產生作用的寫照。
然而,文學的多種功能既不是均衡地分布在每一篇作品之中,也不是均衡地存現于每一個時代的文學之中。我們可以對文學的功能作靜態的分析,更應該用辯證的眼光對之進行動態的把握。
人類社會在發展,人類生活在變化,作為“生活的反映”的文學自然也在不斷地發展變化之中。唐詩、宋詞、元曲、明清小說,真可謂“一代有一代之文學”(王國維)。文學的變化既表現于形式也體現在功能。在不同的人類歷史發展階段和社會形態中,文學的功能是有所側重的。從實際生活出發,提高生存的能力,對于原始人類來說,可能比什么都重要。“斷竹,續竹,飛土,逐肉。”(《彈歌》)記敘的就是打獵的過程和技巧。盡管今天的人們看來原始藝術是多么的富有“藝術性”,美對于原始人來說無疑不是最重要的。即便到了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初期,“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的文學的認識功能,仍然還是最主要的。而“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杜甫)應當是封建士大夫的普遍心態。封建社會的文學,主要充當的是關于道德倫理的文明教化功能。我國的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時期,階級矛盾、民族矛盾空前尖銳,政治是社會生活的軸心,文學則是“匕首”,是“投槍”(魯迅)。
而且,從讀者接受的角度看,“文本一旦和讀者發生關系成為審美對象,它就不再是一種孤立的存在,而是成為讀者在感悟、闡釋后形成的情感與形象。這種情感與形象,很難判斷哪是作品本身,哪是讀者的再創造。這兩者已經水乳交融,難分彼此了。”[5]從接受美學角度來看,作品的意義來源于兩個方面:一是作品本身,一是讀者的賦予。伊瑟爾說:“作品的意義只有在閱讀過程中才能產生,它是作品和讀者相互作用的產物,而不是隱藏在作品之中,等待闡釋發現的神秘之物。”[6]可見,文學的功能并非由文學作品單方面決定的。一部文學作品內容即或再好,也無法自身發揮其功能,而只有在被人閱讀的時候,作品的社會功能才能從潛在的可能性轉化為現實。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主旋律,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生活方式,這些都決定著不同時代的人們其主體心理結構是有差異的。這些差異,影響著他對作品的“投射”和“賦予”。即使同時代的讀者,由于生活經歷、情趣愛好等心理因素的不同,對相同作品的理解也會有區別。同是《紅樓夢》,“經學家看見《易》,道學家看見淫,才子看見纏綿,革命家看見排滿,流言家看見宮闈秘事……。”[7]這些對作品的不同閱讀和理解,自然會使作品產生不同的功效。
三 常態功能與特殊功能
文學功能是一個有機的整體,各功能之間相互制約、相互依附、相互映襯。就像店鋪林立的商業街,到底是大店還是小鋪、是新會所還是老招牌使整條街呈現了繁華?誰也說不清:都是,都不是。格式塔心理學派有個觀點,叫“整體大于部分之和”。整體來自于各個構成要素,但各個構成要素的機械累積不是整體;當各要素有機地組合在一起的時候,它就產生了“格式塔質”——一種新的質。正是這種“新質”的出現,使它與原來的構成要素有了本質上的區別。一雙筷子是筷子,十雙筷子綁在一起時,它所充當和呈現的決不可能再是筷子的功能。文學有政治功能、道德功能、宗教功能等等,但文學不是政治功能、道德功能、宗教功能,也不是所有這些功能“之和”,而是這些功能的有機整體。這個“整體”、這種“新質”,是這樣的難以命名,以至于我們只能說,“文學就是文學。”[8]各種功能有機地組合在一起,是文學的常態;置身于有機整體中的文學功能,就是常態功能。相反,人為地割裂各功能之間的聯系,孤立地對待各種功能要素,把它放在顯微鏡下來觀察,這是“特別”所需,這時的功能就是特殊功能。
出于特別的需要對文學進行特殊的研究是允許的、可以的。有人研究《紅樓夢》中藥方的醫用價值,有人研究賈府膳食的營養之道,這都未嘗不可。正如筷子是用來吃飯的,特定的時候拿來燒火一樣的可以。只是拿來燒火的筷子就已經不是筷子,作醫學、營養學對待的《紅樓夢》就已經不是作為文學名著的《紅樓夢》。花園中的花朵競相開放,好一派生機勃勃的春天景象,但當你把一支玫瑰摘下來送給女孩子的時候,它已經既不是玫瑰,也不是春天,而是“愛情”了。只可惜,有不少人把文學功能的這種有機構成錯當成倉庫儲物式的堆放,不顧及作品由表及里逐層深入所形成的“復調和聲”的機理,機械地把作品的各個部分各個層面視為倉儲式的羅列堆積,隨意地抽取或者政治、或者社會、或者文化、或者哲學宗教之類的層面孤立地進行分析。這樣的研究,充其量也就只能分別稱之為單一的政治研究、社會研究、文化研究、哲學研究或宗教研究。一句話,不能稱之為“文學的”或“審美的”研究。
文學作品的各種結構要素和功能要素的“總體”生成了“文學”或“文學性”。文學是藝術,文學是審美,但這種給人帶來無限精神愉悅的美不是漂浮在空中五光十色的云朵,它有著人性光輝和生命靈動的深厚根基(即使浮云也不是“無根”的)。“文學是人學”,離開了人,文學無從產生;離開了人的生命,就無所謂藝術,無所謂美。文學的每一種功能都是人性光輝的閃亮,文學的每一種功能都是生命活力的噴發;反過來,文學又以其美、以其多元化的功能服務于人,服務于人的生命。人的生命生成了文學,文學照亮了人的生命。在這種“生成”與“照亮”的不斷循環中,人的生活才是真的、善的和美的。
假如我們在欣賞天空的彩虹時連同山間的清流、湖面的波光、大海的蔚藍一起欣賞,得到的美與美的體驗會成倍的增加;假如我們在分析理解文學的多元化功能時,將使功能成其為功能的本源一同納入視界,對文學功能的認識勢必更加深入和全面。
回到篇首的話,文學功能的表現或顯或隱、或靜或動、或常態或特殊,使本來多元化的功能變得更為復雜。“詩無達詁”、“常讀常新”,正是多元且復雜的文學功能產生的蘊藉性、張力場所致,也是文學的魅力所在。同時,文學的功能并不是雜亂無序的,每一種功能在結構體系中都有特定的位置。認識了文學功能結構形式的多樣性,就能給文學的各種功能進行相應的定位。就像消遣文學,它所發揮的是文學顯性的、淺層的功能,是一種被放縱了的文學的娛樂性,雖然不乏現實存在的客觀依據,但它既與文學深層的形而上思考有相當的距離,也與文學常態的生命關懷精神相左右。現實存在的某種文學形式與本來應該有的文學形態可能存在這樣和那樣的差距,理論的任務就是使文學之“當然”最大限度地接近文學之“應然”。
[1]十四院校.文學理論基礎[M].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5.
[2]韋勒克,沃 淪.文學理論[M].三聯書店,1984.
[3]英加登.對文學的藝術作品的認識[M].北京: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88.
[4]金健人.文學經典的結構與功能[J].文藝理論研究,2008(5).
[5]王紀人.文藝學與語文教育[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5.
[6]胡經之,張首映.西方二十世紀文論史[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
[7]魯迅全集(第 8卷)[M].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02.
[8]王乾坤.文學的承諾[M].三聯書店,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