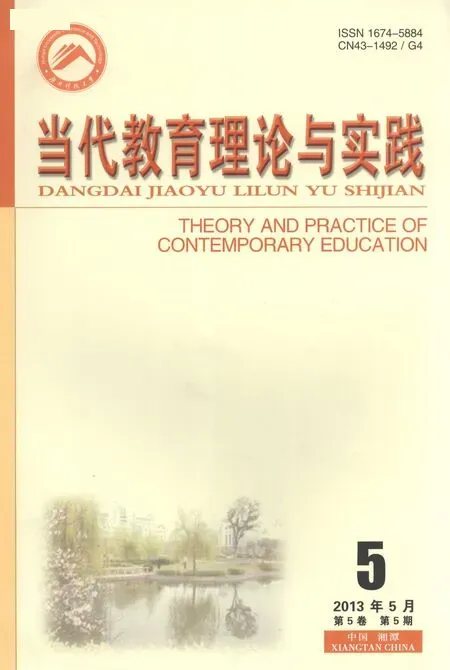論南縣地花鼓的藝術特征及其局限
董 曉
(河南大學 文學院,河南 開封475001)
湖南南縣古稱“南洲”,地處湘鄂邊界,北鄰湖北公安,西臨常德漢壽,東接岳陽華容,南望益陽沅江,身處洞庭腹地,土地肥沃,一馬平川,河湖交錯,農業興盛,有“洞庭明珠”之美譽,無愧農業大縣之贊許。南縣居民多為省內外移民,文化風俗豐富而多元。在這片農耕文化繁榮的沃土上,一種極富湖湘特色的民間歌舞藝術——地花鼓——孕育、產生、迅速發展。
“地花鼓”之“花鼓”代表著這種藝術形式明艷歡快的基本風格和以鼓為主的伴奏樂器。而“地”字即揭示了地花鼓的表演環境為地面,而非舞臺,從而與其他花鼓藝術相區別,又昭示了地花鼓起源于田間地頭,產生于農人的勞動生活。地花鼓是湖南花鼓戲的前身,對花鼓戲的形成影響深遠,卻因其獨特的藝術魅力和廣大的受眾基礎得以保持本色,繼續流傳。南縣地花鼓與湘西、衡陽、邵陽之地花鼓多有相似,又融入了南縣人獨到的藝術創造和生活體驗,因而別有風味。
南縣地花鼓的歷史發展是可喜的,它備受當地民眾喜愛,充當著南縣乃至周邊地區文化生活的重要組成,自清嘉慶至今,綿延近兩百年而不衰;南縣地花鼓的命運現狀是堪憂的,受現代文明沖擊,近年來的南縣地花鼓已趨式微,在文化邊緣的地位上苦苦掙扎。除開外部因素的影響,其本身的藝術魅力與局限是造成這對矛盾的根源。
一 南縣地花鼓之內容:勞動者的田園歌
“根據有關專家分析,地花鼓的產生與插秧歌有關。人們在進行農業生產勞動時,插秧是一種較為繁重而又乏味的勞動。人們為了解除疲勞而唱歌,久而久之這種唱歌形成一種娛樂,再在這基礎上形成一種曲調和舞蹈,加上化裝而逐步發展為一種較完整的歌舞形式,這就是地花鼓。”[1]由此可知,農人的勞動生活是地花鼓生存的土壤,發展的根基,勞動生活的內容在南縣地花鼓表演中處處可見。
有些劇目直接以勞動生產為題,再現勞動過程,表現勞動艱辛。如《采茶》中開頭即唱道:“正月里采茶是新年,兄妹雙雙進茶園,十指尖尖把茶采,采起細茶轉家園。”配以模擬采茶勞動的舞蹈動作,采茶歸來后喜出望外的面部表情,將一對勤勞樸實的采茶兄妹形象展現于觀眾面前,細膩真實地搬演出茶農們的農事生活。該劇中另一句唱詞:“采茶辛苦吃茶甜”被演唱時伴奏稍緩,情感由喜轉為喜中帶一絲悲苦,用淳樸而富哲理的言語傳遞出勞動者的辛酸感嘆。但是,南縣地花鼓中其他大部分劇目并不直接以勞動為題,而是有意或無意地將勞動內容融入其中,如《五瞧妹》中有一段說的是婦女身上花衣破敗不堪,原因是她在“廚房之中多,繡房之中少”。劇中婦女的傾訴既揭示出農村婦女忙于家務的生活狀況,贊美女性的勤勞,又傳達出對勞動婦女悲苦命運的些許同情。又如《新拜年》中有“家家戶戶把田插”的勞動場景歌唱。
南縣地花鼓表演中常常以月份或節令起興,如《送財》里的“一月里來好送財… …二月里來好送財… …”;《十二月望郎》里的“正月望郎是新年… …三月里望我的郎是清明… …”。農事活動中,月份、節令等時間因素占據著重要地位,深深根植于農人心中,因此地花鼓中頻繁出現月份、節令是勞動生活在藝術創作中的必然體現,是農耕文化在民間藝術中的不滅印記。
南縣地花鼓的內容多為勞動者代言,抒發的是農人真摯而樸實的渴望。《送財》抒發了新時代農民對富裕生活的向往,以十二種不同的“吉利話”如“天官賜福”、“一年四季”共同強調著同一句唱詞:“送喜又送財”。地花鼓表演時間多集中在傳統節日里,這類吉祥又朗朗上口的唱詞能夠利用節日喜慶的氣氛將農人們生活富足的美好愿望烘托至最高點,引起共鳴。而《鬧五更》、《十二月望郎》等劇目傳達的是勞動者對男女愛情的渴望,愛情是人類生活不朽的母題,更充當著勞動者勞作之余的主要生活內容,旦丑二角在觀眾前再現、吟唱愛情,符合著最廣大受眾的口味,因而愛情題材(或是情愛)的地花鼓作品數量最多。
可見,正因為南縣地花鼓多再現勞動生活,為勞動者代言,所以能贏得眾多勞動者的喜愛,擁有強大的藝術生命力。
二 南縣地花鼓之語言:平白出詼諧,排比現喜慶
不論是唱詞還是念白,南縣地花鼓的語言往往能通過俚俗的話語達到令人捧腹的效果。由于演出時間多為節慶,因此地花鼓表演以歡鬧、添喜為主要目的,感情基調輕松明快,多有滑稽調笑的精彩唱段。《鬧五更》以“白描”和擬聲營造詼諧效果。“三更那個喵兒,喵喵喵喵喵喵喵喵,鬧翻了三更天”,這句唱詞生動而形象地再現了貓兒半夜出聲,吵得閨中少女難以入夢、思念情郎不止的現實生活場景,惱人的貓叫如在耳邊。唱這句時,扮演母親丑角不斷展現各種滑稽動作,引人發笑之效果立出。《五瞧妹》則以擬人和夸張送出笑料,其中丑說起旦的頭發,稱其用了許多油來梳,令“虱婆子(虱子)上來戳拐棍,飯蚊子上來打飄飄”,此語一出,勾起觀眾翩翩聯想,旦的滑稽形象頓時鮮明無比。綜觀以上之唱詞,可以發現其遣詞造句未加點染,用的都是農村生活中的常見詞句,樸實無華。這些唱詞有節奏而無格律,有語氣詞如“哎嗨喲”,而無戲曲之套版,詼諧幽默的運用無拘無束,揮灑自如,具有原生態的藝術美,彰顯出“下里巴人”的語言魅力。至于南縣地花鼓的念白,用的是更純粹的生活語言,如“妹子,拜噠堂搭咯”(出自《新拜年》)與鄉村生活十分貼近。
南縣地花鼓多用排比,不斷重復的詞句強化了唱詞的表現力,與節日的喜慶氣息相協調。前文所提到的《送財》便是典型,茲不贅述。值得注意的是,南縣地花鼓常把數字融于排比句唱段中,如《五瞧妹》按“一瞧”、“二瞧”至“五瞧”的順序唱出,從五個方面表現旦的形象;《十二月望郎》按一至十二月的順序演唱男女相思;《送子》從送“老大”唱到送“老五”,詠唱出五子登科的祝福。地花鼓的創作者和接受者多為文化水平低的民眾,而用數字排序既能使創作者容易找到寫唱詞的線索又讓農民觀眾容易梳清唱段中的邏輯,簡明易懂,況且數字排序便于表現唱詞中并列或遞進的語義關系,加強節奏,此二者不外乎數字排序多見于南縣地花鼓唱段的原因。
三 南縣地花鼓之歌舞:形式自由,粗中有細
南縣地花鼓有“對子地花鼓”、“竹馬地花鼓”、“圍龍地花鼓”等多種樣式,其中“對子”是基本形態,為一丑一旦對唱,其他樣式皆為在此基礎上與其他藝術形式自由組合而成,這些藝術形式以民間雜技居多,如“竹馬”中的雜技動作表演,“圍龍”中的舞龍表演,“蚌殼地花鼓”中“蚌殼夾人”的滑稽動作。有時,為了迎合節日喜慶時觀眾愛熱鬧的需要,地花鼓表演常常突破一丑一旦的套路,讓多對演員同時登場表演,甚至出現“二旦一丑”的組合,地花鼓之所以能夠實現組合的高度自由,得益于它簡短的結構和簡單的內容。
南縣地花鼓的樂曲多用民間小調,如流傳于湖湘的“采茶調”,這些調子對于格律平仄無要求,甚至可以不用押韻,令地花鼓的歌唱自由隨意。但長期以來,被用來演唱地花鼓的民間小調數量不多,未能充分挖掘民歌資源,致使南縣地花鼓在音樂上呈現出單調的毛病。地花鼓所用的樂器以嗩吶、鑼鼓為主,與湖南花鼓戲一脈相承。
地花鼓的舞蹈雖然動作滑稽,充滿鄉土氣息,但實際上是十分講究的。“地花鼓的表演傳統上,講究‘三節’、‘六合’。”[2]所謂“三節”指演員手腳各三處關節,要求表演者運用此六處關節作動作時協調連貫,舞姿優美;“六合”在外要求表演者巧妙結合手腳“三節”,在內要求表演者的“精、氣、神”,力求完美的舞臺表現。地花鼓的舞蹈動作中,有著大量的程式化動作,各有用途,如丑角的“矮子步”,模仿武大郎,起滑稽調笑作用;旦角的蘭花手,以表現曼妙的體態;旦角的“柳葉掌”,專用于待字的少女。
地花鼓表演所用的道具以扇和巾為主,通常旦持巾、丑持扇。旦舞巾時巾隨其舞步、手部動作、面部表情而翩然飛舞,借以修飾各類程式化舞蹈動作,更可表現女主人公多種情緒,如《五瞧妹》中旦用巾揮打丑,表現嬌羞之態,又如《鬧五更》中旦唱到“叫醒奴的干哥哥”時,以巾捂心,顯出傷心之情。丑之扇用途更廣,表現更為生動靈活,當扇展開時可配合舞步揮舞,為歌舞增添明艷的色彩、亮麗的點綴,又可與旦之巾搭配,擺出各種造型,帶來形式上的美感。同時扇可以化為各種物件,由丑隨手化用,如《采茶》中展開的扇曾當做采茶的籮筐,又如《新拜年》丑唱:“家家戶戶把田插”,閉合的扇便成了丑手中的秧苗,此外,“可以將扇收攏代替刀槍劍戟使用,也可以作為禮物相贈。”[2]
四 南縣地花鼓之局限
(一)重歌舞而輕情節
南縣地花鼓通常以一曲民歌小調貫穿始末,借男女對唱簡單敘述某一生活片段,勉強稱之“以歌舞演故事”,但離真正的戲劇仍有距離。某些地花鼓表演是沒有情節的,如《送財》、《十二月望郎》,通篇以唱詞抒情,無意敘事。縱然些許地花鼓有情節,其情節也是斷零或是單調的,如《新拜年》中雖有丑與旦相互打情罵俏的情節,但短短幾分鐘唱段竟可拆分為數段情節——“正月拜堂”、“二月買姜”等,僅有邏輯上的聯系,缺乏情節之間的合理過渡。又如《鬧五更》里雖有少女不堪夜里噪音侵擾而向母親傾訴的情節,卻無高潮。若說其有高潮,則其整段皆是高潮,五小段都在訴說少女夜半難眠思情郎的苦悶心情,但整段在結構上缺少“起承轉合”,情緒上沒有高低變化,與長沙花鼓戲《六月雪》里高潮迭起的情節不可同日而語。由于情節的嚴重不足,地花鼓只能依靠精彩的歌舞、諧趣的唱詞吸引觀眾,離開了花鼓戲般復雜的情節、生動的敘事,南縣地花鼓的藝術感染力嚴重受限。
(二)思想內容上的淺俗
縱觀南縣地花鼓,題材太少,內容多有雷同。就“望郎”一題材,便出現了《十二月望郎》、《十月望郎》兩個版本,唱詞大同小異,除《送財》外,還有《送恭喜》等送字當頭的地花鼓劇目,唱詞結構幾乎沒有變化。而且就現有題材來看,基本不出愛情(情愛)、喜慶、調笑、農事四大類,花鼓戲中出現過的社會、變革、歷史、公案等題材皆未見于地花鼓。現存的南縣地花鼓在思想內容上深度是不夠的,大部分作品在表演過后只留下歡笑,未能帶來思想上的啟迪,即使是有著表現應珍惜勞動的《采茶》,也只留下“吃茶容易采茶難”的只言片語引人進一步思考。
在某些作品中,甚至有價值取向畸形、內容低俗的唱段,如《燒火歌》表現的是公公與兒媳之間的曖昧關系,文本不僅沒有對此批判或諷刺,反而給予一定程度的粉飾。這類低俗的表演在民間不足為奇,卻難登大雅之堂,不便公開傳播,不能與地花鼓俚俗的主流相提并論。同時它如一劑慢性毒藥,侵蝕著農村觀眾尤其是青少年觀眾的心智,可能帶來不良影響。思想內容上的淺俗凸顯出地花鼓創作群體水平有限的硬傷,這與地花鼓創作者多為業余而非專業有關。
(三)受眾的單一化
南縣地花鼓大多由農人創作,在農村傳播,被農民接受,無論其形式或內容都堪稱為農民量身打造。這有利有弊,能貼近農民生活,保存農耕文化下的南縣民俗,卻把受眾的圈子固定在農村勞動者這一單一群體。一旦將南縣地花鼓搬出農村,一些城鎮觀眾會產生審美疏離感,無法充分消化地花鼓中的藝術養料,難以產生認同。
總之,無論從內容、語言還是歌舞上來看,南縣地花鼓都有著別具一格的藝術魅力,但我們也應清醒認識到它缺少情節、思想淺俗和受眾單一的局限,其成功與衰落皆有動因。如今,南縣地花鼓當之無愧地被評為“非物質文化遺產”,受到政府和一批專家學者的高度重視,也有一批文藝工作者嘗試著用不同的方式傳承、發揚這一筆精神財富,如將現代戲劇元素融入地花鼓藝術,用高科技手段改造地花鼓藝術,以期博取當今觀眾的認同,激發人們對地花鼓的興趣,不少人的嘗試取得了成功,令地花鼓開始走出南縣,走出益陽,走出湖南。可是,在一些改編作品中,筆者發現一些原生態的地花鼓藝術遭到破壞,原有的鄉土特色所剩無幾,淪為傳統與現代雜糅的“四不像”。
[1]向智星.地花鼓與花燈的特征探析[J].貴州工業大學學報,2006(4):33.
[2]劉 科.淺談湖南地花鼓的藝術表演特征[J].黃河之聲,2010(2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