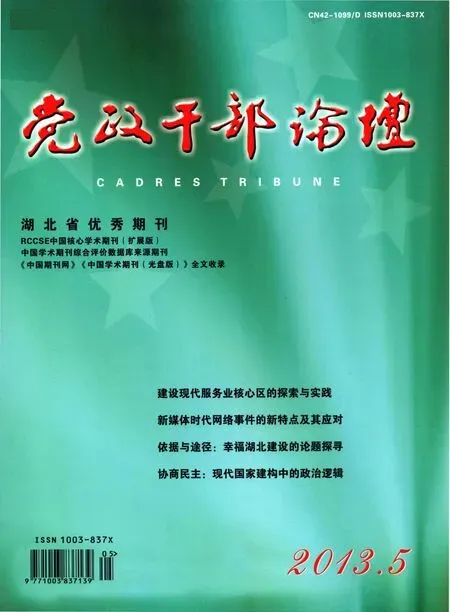新媒體時代網絡道德張揚的消極影響及遏制對策
○ 林細妹
新媒體時代,網絡日益成為人們日常生活、學習與生產的重要工具,網絡生活已經成為人們一種獨特的生存狀態。而網絡社會從來都是現實社會的虛擬表達。近年來流行的“網絡道德張揚”這一現象及其理論范疇,就是現實社會中各種道德張揚現象的具體反映。本文擬從現實生活出發,從網絡道德張揚的具體主體入手來較為深入地探討這一現象的成因及其深刻影響。
一、網絡道德張揚的內涵及主要群體
學術研究話語下的張揚,它是指社會主體(個體或集體)突出地表現或展示自己的特定行為。文藝復興時期,人性的積極張揚,是人自身對神性的否定,是人性覺醒的基本標志,是人之所以為人的重要衡量,是人獲得自由的基本前提。從這個角度看,張揚內蘊肯定與積極的意義。
然而,當張揚行為超越了一定界限后,便具有了否定意義。亦即它往往是個人中心主義、絕對自由主義的理論思想依據。本文所謂的“網絡道德張揚”中的“張揚”,就是在此語境下使用的。具體來看,我們所指稱的“網絡道德張揚”,它是指這樣一種網絡行為,即少數人或特定群體利用網絡這一時代載體,來大肆發表相關個人言論、傳播非真實性消息、展示個人相關才能技能等,以此獲得“網友們”的普遍關注,進而賺取大量的“道德人氣”和獨特的道德力量。當然,網絡總是與現實遙相呼應的,故而,獲取網絡“道德人氣”與“道德力量”的根本目的,還是為了獲取現實的各項利益。網絡道德張揚的社會群體,主要有以下三種類型:
(一)社會弱勢群體
網絡道德張揚的弱勢群體具有如下特征:他們在現實生活中可利用資源缺乏,社會地位低下,社會關系網薄弱,等等。由此,他們的社會權利與權力得不到及時保障和使用,他們的個人利益難以便捷獲取。進而在現實的無奈處,在網絡如此便捷的時代,他們便試圖通過尋求一種網絡途徑,來表達甚至發泄自己的不滿。本來,這種行為是正當合法的,但由于這些群體在表達或發泄的過程中,帶有強烈的情緒,且由于他們缺乏對客觀事實的正確評估,故而,他們在網絡上發表言論時往往大肆張揚自己“利益欠缺度”,任意放大社會體制內在的客觀缺陷,進而試圖以此來博得多數網民的道德同情和道德支持。
(二)社會強勢群體
這一群體是相對于弱勢群體而言的。他們在社會地位、個人財富、權力與權利、社會關系等方面居于社會優勢主導地位。這些群體不僅容易操控網絡媒體,而且還特別擅長利用網絡媒體,以此來無限制擴大、甚至是放大自己的相關慈善行為和正義之舉,進而博取更多道德光環。
(三)社會“網絡紅人”
顧名思義,它是指在網絡中因為某個事件或者某個行為而被網民關注從而走紅的人。他們的走紅皆因為自身的某種特質在網絡作用下被放大,與網民的審美、審丑、娛樂、刺激、偷窺、臆想以及看客等心理相契合,有意或無意間受到網絡世界的追捧,成為“網絡紅人”。因此,“網絡紅人”的產生不是自發的,而是網絡媒介環境下,網絡紅人、網絡推手、傳統媒體以及受眾心理需求等利益共同體綜合作用下的結果。
二、網絡道德張揚的行為表現
(一)隨意發表網絡言論
網絡信息技術的迅猛發展,一方面給人們生活帶來諸多方便,提供更多快捷的網絡交流工具,如QQ、博客、BBS、E-mail及微博等等,加速并擴張了網絡信息的傳播速度和時空。但另一方面,這些網絡工具也日益成為個人進行網絡道德張揚的重要媒介,網絡道德張揚主體利用網絡工具的快捷性、交互性、共享性、傳播范圍廣泛性、跨時空性等特性,大肆任意發表一些關涉價值判斷和道德選擇的事件。例如,少數人利用QQ群交流工具散播自身不切實際的道德評判,大肆傳播自身的生活和生產困境,等等;部分人通過發表微博或者網絡文章,緊緊抓住某一道德個案不放,無限制放大這一個案的社會效益。
(二)廣泛制作網絡視頻與圖片
網絡道德張揚主體不僅通過語言,還利用制作各種視頻和圖片來增強其張揚效果。因為視頻具聲、色、行于一體,具有直觀生動性。不僅如此,視頻還能突破文化水平的限制,有效擴展受眾面。具體來看,不同的“張揚主體”會依據自身特點和能力來利用不同的途徑制作視頻和圖片。但他們制作方式大致總是沿著如下路徑展開,即先在現實生活中故意制造某些事端,然后將此制作成視頻或圖片,再上傳到某些著名的網絡論壇、QQ群、微博中,以此達到廣泛傳播與迅速擴散之目的。
(三)任意進行網絡惡搞
所謂的網絡惡搞,“是指在高科技互聯網支持下的一種新型的惡作劇搞笑行為。網絡惡搞科技含量較高,參與者文化程度較高,參與人員多,傳播的時效性比較持久。它是一種帶有游戲性質的、很隨意、非理性的言行舉止或藝術行為”[1]。也就是說,網絡惡搞主要是用滑稽或者搞笑整蠱的方式來表達自己對某些社會現象的看法。其主要形式包括:移植相關圖片、剪輯相關影片、歪曲人物照片、篡改動畫歌曲,等等。良性的網絡惡搞,可以有效緩解人們對現實的不滿,獲得道德上的自慰。然而,惡性的網絡惡搞,卻往往是社會穩定的重要隱患。
(四)大肆放大社會陰暗面
社會的不斷發展,愈加凸顯資源有限性與人的需求無限性的矛盾。在此情況下,那些直接掌握資源的生產單位或職業,其對資源占有的便捷性更為突出。加之社會監督機制尚未健全,這種便捷性很有可能異化為自我獲取社會暴利的通途。毋庸置疑,憑借自身在社會整個生產體系中的特殊位置,或憑借職業選擇的先天優勢而逐利的行為,自然具有非道義性和非正義性,它們是社會的陰暗面。本來,不管在哪個時代都存在這種社會陰暗現象。可是在當今高速發展的網絡時代,部分處于弱勢地位的社會群體,滿懷對這種非正義行為的道德義憤,盡管他們無法辨別相關信息真假,但他們卻借助于某一線索(或許這一線索還可能是假想的),以進入網絡的低成本和低門檻,到處廣泛傳播“傳說中或想象中的社會陰暗”。有些網絡謠言便是按照這種機制生成和擴散的。
三、網絡道德張揚的消極影響
一定意義而言,一定程度和范圍內的網絡道德張揚具有積極的社會意義,它可以使得在現實生活中被人們忽視的人和事,被重新“記起”和“撿起”,使得那些非正義的事得以鞭撻。然而,網絡道德張揚的消極影響,卻往往壓倒了其積極意義。
(一)個體角度視野中的網絡道德張揚的消極影響
在張揚行為受到眾多網友關注后,網絡道德張揚主體必定存在三方面的反映態度。一是假如行為成功博取了某些網民的道德支持與道德同情,那么,張揚者必將愈加“肆無忌憚”。二是如果其行為沒有得到網友的關注,或者網友們對此抱以不屑一顧、置之不理的態度,那么,張揚主體必有挫敗感和承受新的心理壓力,這使得他們要么放棄張揚行為,要么重新以全新的方式再次進行新的“網絡張揚”。三是倘若網絡張揚行為受挫,即受到網友們的普遍質疑,甚至是有意識地排斥,那么,網絡道德張揚主體的選擇不外有二,要么主動放棄“張揚”,回歸理性現實,要么變本加厲,更加“猖狂”。而這種“猖狂”的后果,要么是傷害他人、報復社會;要么是傷害其自己、產生性格扭曲。
(二)社會角度視野中的網絡道德張揚的消極影響
某些道德張揚行為,使得含有道德判斷和鮮明價值取向的網絡虛假信息到處傳播,這對社會穩定構成嚴重威脅。一方面,某些網絡虛假信息會使得社會大眾產生社會恐慌,造成社會秩序的無序,影響社會穩定,更有甚者,有時某一網絡虛假信息,很有可能就會引致某一社會群體性事件;另一方面,某些道德張揚主體的言行不斷消解著主流意識形態的說服力。比如,近年來,部分官員的貪污腐化行為,使得部分基層政府官員的道德水平成為社會大眾質疑的對象。借此形勢,一些網絡主體便把對現實的不滿歸結于國家、政府,然后通過網絡媒介大肆傳播,這無疑壯大了反主流意識形態的網絡力量,加大了進一步增強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吸引力、凝聚力和說服力的難度。一些別有用心的人還充分利用這一“契機”,在網絡上大肆宣傳所謂的“民主、自由、人權”等西方“普世價值”[2]。
(三)道德角度視野中的網絡道德張揚的消極影響
道德是一種社會意識,它的生成和變遷受制于社會關系的發展,特別是受制于社會物質經濟關系的發展。它是以提供“善惡”標準、依賴社會輿論等方式來調整人與人之間關系以及人與社會之間關系的,在此意義上,道德也是一種工具,人們利用它來為社會生產和日常生活服務。然而,網絡道德張揚行為卻使得道德逐漸喪失崇高性,逐步完全淪為人們的獲取自我利益的純粹工具,成了一方利用另一方的隱形手段。從而可見,網絡“這個虛擬世界使得人類的交往關系處在極不確定的狀態,使千百年來已經確立起來的、規范人們之間關系的倫理道德觀念處于危險境地”[3]。一旦如此,整體的網絡道德也就無從存在了。
四、網絡道德張揚的有效遏制
(一)高度關注并盡力滿足弱勢群體的利益訴求
對弱勢群體而言,在實際的物質生活中,他們相對缺乏獲得利益、實現權利的機會,即“有怨沒處發,有恨沒人吐,有話沒人說”,而網絡以其便捷性為他們提供了發泄道德義憤、獲得相關利益的機會和平臺。相對現實的物質生活而言,虛擬的網絡生活更加具備自由與平等的特性,人人都可以進入網絡,人人都可以在網上自由發言。另外,網絡還具有匿名性,這就像網友們常常說的那樣,“在網絡上,沒有人會知道你是一條狗”。對于那些現實生活中的弱勢群體而言,網絡的這些特性正好為他們滿足“強大”自我、實現“自我”提供了便利快捷的途徑。特別是對于那些在現實生活中遭遇極端不公平的人來說,在長期的心理負荷作用下,即使在現實生活中他是一個誠實、正直、公正的人,在寬松的網絡環境下,也很容易將個人的怨恨和仇視,通過網絡來擴散到整個社會。
所以,消除弱勢群體的網絡道德張揚,需要高度關注他們的合理利益訴求。為此,至少要從以下幾個方面努力。一是建立和完善弱勢群體利益訴求機制,暢通他們的利益訴求通道。各級基層政府組織和各類社會群眾團體,要真正發揮其扎根群眾的特點和優勢,及時了解群眾利益訴求,反映他們的思想愿望,解決或協助解決他們的現實困難。二是要建立健全弱勢群體社會保障的財政機制。維護弱勢群體利益,關鍵是雄厚的財力支持。發達國家的經驗表明,扶助弱勢群體的財力,主要來源于政府的二次分配機制。在我國總體財力日益增強的形勢下,政府要加大對農村和城市貧困群體的財政投入傾斜。
(二)建立健全網絡監管機制
對有些人而言,其網絡道德張揚的主要原因就是想借機出名,滿足虛榮心,從而獲得利益資源。從世界發展的整體態勢而言,我們還處于馬克思所指稱的“以物的依賴為主”的社會。特別是資本與市場成功聯姻后,資本為了增值,便不斷借助于市場載體來無限制擴大人們的物質占有與消費的欲望。也正是在此意義上,西方思想家(如鮑德里亞)才把我們這個社會稱為“消費社會”。為更大程度占有物質,滿足自己的欲望,一些人便利用網絡這一最好平臺來大肆張揚自己。特別是網絡自身的特性,為一些人的張揚行為提供了更大便利。這就像一些學者所說的那樣,“在網上隱姓埋名、解除對輿論監督和評價的顧慮后,……一個在公眾心目中高尚的正人君子,可能在網絡這個虛擬世界里,如同打開了潘多拉的盒子,釋放出長期被社會道德規范所壓抑的人性中的‘劣根性’,口是心非,言行不一”[4]。
可見,進一步建立健全網絡監管機制勢在必行。為此,至少要做到如下幾點。一是進一步批判相關觀點。有人認為,對互聯網監管是干涉自由,妨礙人權。這是一種錯誤的觀點,要大力批判。實際上,不管任何國家,都有嚴格的網絡監管機制。可以說,網絡越是發展,越要加強網絡監管。二是修訂完善相關監管制度。現行與網絡監管最為直接的法律法規,主要有三個,即《互聯網信息服務管理辦法》(2000年)、《互聯網上網服務營業場所管理條例》(2002年)、《非經營性互聯網信息服務備案管理辦法》(2005年)。與飛速發展的互聯網技術相比,這些網絡監管辦法很難適應新的現實。所以,國家立法機構和國務院法制機構,要總結經驗,及時開展立法調研,進一步完善現有相關法律法規。三是要擴大監管對象,改進監管手段,調動多方監管力量。我國的互聯網監管仍處于初級階段。隨著網絡覆蓋面的擴展和網絡技術的發展,互聯網監管機構要不斷擴大監管范圍,加強和改進監管的隊伍建設和技術力量。
[1]詹珊:《析評網絡惡搞現象》,《福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7年第4期。
[2]劉慶豐:《對近年來國內關于“普世價值”問題研究的述評》,《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湖北人民出版社2011版,第342頁。
[3]徐鴻:《論網絡道德》,《倫理學研究》2005年第6期。
[4]李衛東:《網絡道德與社會倫理沖突瑣議》,《陜西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