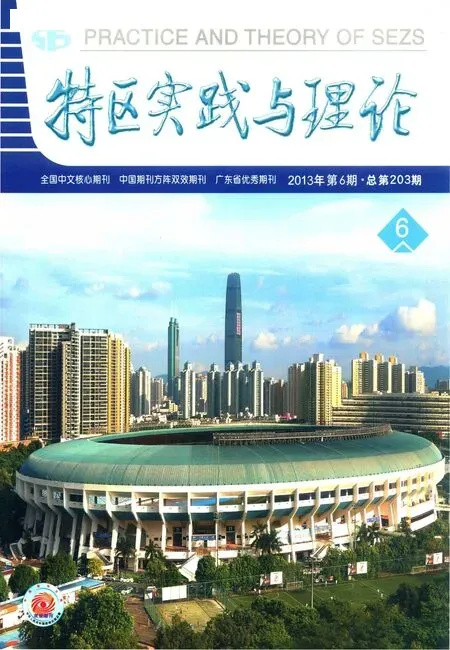城市社區管理體制研究
龔建華 傅小隨
城市社區管理的目的原本是為了實現城市基層社會單位的良性運轉,但城市化的快速發展以及社區理念的錯位引發了眾多問題,而這其中,社區管理體制問題最為根本也最為突出。
一、城市社區的“名實論”分析
(一)我國城市社區的發展演化
“社區”一詞,源于拉丁語,最早出自德國社會學家滕尼斯1887年的《社區與社會》一書,后經由費孝通先生借以翻譯“community”引入中文,成為國內學界話語體系中指代由相對固定區域及人群構成的最基層社會單位。作為引入概念,社區在很長時間內都未被我國行政話語體系所接納,在鄉村,我們依舊是沿襲以往的“村”、“莊”的概念并據此施以管理;在城市,則以居民委員會的方式對基層社會加以社會控制。直至1986年,民政部在進行城市社會福利工作改革時,為了引進社會資本進入福利事業,同時又將其與國家操辦的社會福利相區分,提出“社區服務”這個說法,由此,社區一詞進入到我國行政話語體系。1991年民政部又提出“社區建設”的概念,1998年《國務院的政府體制改革方案》中明確民政部在原基層政權建設司的基礎上設立基層政權和社區建設司,意在推動社區建設在全國的發展。2000年11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關于轉發《民政部關于在全國推進城市社區建設的意見》的通知中特別強調了“社區建設”的重要意義,此后,城市社區逐漸浮出水面,所有的居民委員會前都被冠以“**社區”,從而在形式上完成了社區概念的行政話語植入,但這種植入是不成功,或至少是不完整的。
(二)城市社區的名實相錯
如前所述,作為社區的內涵,地理要素和人群要素很容易被行政話語體系接納吸收乃至運用,而共同體要素由于無法像前兩者那么明晰且難于實現則容易被忽略。事實上,作為社區的本源詞匯,“commuinty”原本就有共同體的內涵表述,只不過在轉譯的過程中出現了部分的信息失真,這種失真傳導到行政話語體系中就成為割裂二者聯系的壁壘,以致出現現實社區的“名實不符”。現實政治中的社區僅指代生活在某個固定地理區域范圍內的特定人群,至于這部分群體能否實現齊格蒙特·鮑曼所描繪的共同體[1]則是第二位的問題,這就導致我國當前社區管理體制的諸多不順。
二、當下城市社區管理體制存在的問題
(一)快速城市化引發的社區管理不適應
我國的城市化是在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國民經濟面臨崩潰邊緣的情況下起步的,那時我們對恢復和促進經濟發展引起的快速城市化過程并沒有做好充分的思想準備和制度安排,對繼起的城市急速擴張過程只能以欣喜加焦慮的態度采取一些被動適應式的調整和管理措施。快速城市化與世界城市化進程遵循著同一個規律,即由工業化引領發展方向。工業化既是城市化的引路者,又是城市化的動力源泉。這樣的城市必然按產業的輪廓塑造成型,打上工業化的深深印記,使其在特征上表現得更像一個龐大而畸形的產業怪物而非宜人的生活空間。同時,由于城市化進程具有超常規高速擴張性,相應的社會體制變革卻嚴重滯后,因而給城市和城市社會帶來一系列問題,也暴露出城市社區管理在目標追求、重點內容、體制機制和方式方法上的許多不適應性。
(二)社區管理的國家控制導向與基層自治導向的不兼容
改革開放之后,城市基層社區有了一定的自主發展的能動性,在1989年法律上確定社區居委會為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之后,基層自治合法性給社區社會發展帶來了更多的空間與內生動力。城市社區中的個體出于社會交往的需求和個人權利的需要開始主動自覺地加入這一基層自治的過程中來,并逐步扭轉社區居委會上傳下達的二傳手定位。此外,治理理念的傳播及城市社區管理的現實也使得政府逐漸意識到,無法依靠既往的管控來實現基層社會的有效治理,城市社會管理的有效達成必須在一定程度上依賴于社區自身力量,或者說政府管理和社區自治攜手才能實現社區的善治,保證城市社會管理目標的實現。因此,政府也積極鼓勵引導社區實現基層自治,這也符合社區自治內生力量的需要,也涌現出眾多的現實表述。
然而,當前我國城市社區管理沿襲的是計劃經濟體制下的“街居制”理念,“街居制”作為城市地方管理方式并非當時的主體管理模式,而僅僅是作為國家控制的“單位制”管理模式的一個有效補充,即個體與社會必須納入到國家設定的具體單位之中才能實現存在,其生產生活以致社會交往都必須依賴于代言國家的單位才得以可能,居委會則作為橫向層面的國家代言人彌補單位制管理的缺漏,是作為國家在基層社會單位的立足點出現的。作為街道居委會的現代政治表述,社區先天地包含有國家控制導向,并在當下逐步加強了這一趨勢。城市市民不再依托于單位制而存在,國家對于個體的約束力大為減弱,原有的戶籍管理制度由于受到人口流動的沖擊已然無法實現國家對個體的有效控制,這對社會管理的有效性提出了強力挑戰,這就使得國家原有的個體管控模式必須發生改變,轉為群體管控,最小最合適的社會群體就是社區,也因此,國家在90年代逐步退出村落后又在新世紀開始逐漸加強對于社區的管理:一方面,國家通過各部門的政策執行方式進入社區,另一方面,原有的自治組織居委會逐步演化為國家管理與服務的接盤手,在這一過程中,主客易位,已經脫離單位制聯系的社區轉而加強了直接與國家的聯系。深圳某社區掛37塊牌子也就具有了正當性。
(三)現行管理體制中的人群分治政策引發的社區管理沖突加劇
社區理念中“共同體”要素在現實政治中的缺失,使得當前社區管理體制人群分治情況更為突出,特別是在深圳這樣的超大型移民城市,社區中的外來人口與本地居民原本就存在身份認同的差異,基于戶籍制度而非社區理念制定的管理體制不但沒有將這些分裂的群體凝聚成具有共同體效應的社區,而且還在加深相互之間的裂痕,使得其內部沖突不斷。這種情況在“村改居”社區中表現的最為明顯,以深圳市WL社區為例,該社區原住民有2100多人,外來人口約24000人(其中約40%在該社區居住生活超過兩年以上),依照現有管理體制,社區居委會選舉中僅有原住民具有選舉及被選舉權。如此一來,WL社區居委會當然成為原住民的代表,以致發生了政府公共服務項目進入時,部分原住民要求其只能面向原住民群體,這種排他性直接導致群體沖突。由此甚至產生管理主體和對象的分離,社區管理的對象是外來人的“他們”,實施主體是本地人的“我們”,“我們”與“他們”之間雖然共同生活于同一社區,但并無認同,政府的社會管理落足于社區這個城市基本單位時卻發現地基不穩,繼而引入更多的力量、資源進入社區,意圖能將其筑牢,但依舊是沿襲以往人群分治模式進入的各類力量與資源卻在繼續拉開社區群體間的距離。
三、營造“共同體”以應對社區管理的失序
首先,推進原住民與外來人口的融合共生與合作共治,提高原關外地區基層群眾的社會參與能力,活躍基層社會,繁榮基層社區文化體育生活。充分發揮已建成居民議事會的作用,將其打造成社區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服務的有效載體。進行社區服務管理體制改革,探索社區行政與基層群眾自治的并行模式,形成效果良好、可持續和可推廣型的社區基層群眾自治方式,增強城市社會活力;統籌考慮社區股份公司改制工作,將其與社區基層群眾自治有效途徑的探索結合起來,實行政企分離、政社分開。
其次,轉變社會管理觀念,調整社會管理格局,培育社會管理多元主體,特別注重通過全面政務公開和探索基層群眾自治的有效途徑落實群眾主體地位,按照十八大的要求發揮群眾參與社會管理的基礎作用。缺乏群眾參與的社會管理體系是不完整且沒有活力的。我們雖然面對著一個利益多元的社會局面,但城市公共服務設施建設和管理、環境保護、社會治安、市場物價、教育衛生事業發展、社區公共事務等眾多領域都是將不同階層、不同訴求的城市人聯結在一起的最大公約數,也是城市居民參與社會管理的廣闊領域。只要在實踐中找到合適的方式和途徑,群眾廣泛參與的局面是完全可以形成的。所謂轉變觀念,主要是要求黨委和政府部門破除習慣性的自我本位思維,以開放式社會管理格局和寬闊的視野將自己和城市社會各主體團結在一起、融合為一體,分工協作、互相支持和配合,服務和管理共同的城市家園。這樣的城市社會管理體系才具有不竭的活力,才可以最大限度調動居民群眾的協作動力,將虛擬參與為主的方式轉變為投身現實為主的參與方式。
再次,城市黨委和政府部門應當在社會管理中調整身姿,改變陳舊單一的工作方法,特別是那種以我為中心的、居高臨下揮舞指揮棒式的方法,積極探索適應高度城市化地區居民行為方式的新方法,發展新的合作、溝通和參與方式與多樣化社會動員方式,包括善用社區社會組織、居民議事會、新興媒體等途徑。與管理相伴的是細致的服務。城市社會管理特別要注意寓管理于服務之中,通過優質的公共服務創造社會管理的有效載體和方式。城市更要以大力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緩解城區之間、社區之間和不同人群之間因政府政策和服務原因帶來的福利差距,以及由此造成的群際關系不睦和各種矛盾糾紛。特別是要縮小中心城區與邊緣城區之間業已形成的政府公共服務差距,為集中居住在某些邊緣城區、棚戶區、工廠宿舍區、雜亂出租屋內的低收入居民提供更多的政府公共服務,以專門的人力物力財力和規劃措施加快解決進城務工人員完全融入城市的市民化過程,將他們的當前生活、教育醫療和社會保障納入一體化的城市公共服務范疇,并為他們的未來發展和子女徹底市民化做好各種物質條件和制度準備,防止他們成為城市的邊緣群體甚至不穩定、不和諧因素。
最后,城市社會管理體系應當依據已經深刻變化了的城市社會構成、交往方式和人際關系模式,改變逐級下伸的單一行政化管理架構,按照城市本身的形態和人群聚焦類型,重新進行社區劃分,實施分類管理,采取針對性的方式方法,滿足不同類型的服務需求,提高管理效率。在此基礎之上,積極采取軟性的制度安排和工作措施,努力促進城市社會階層之間、群際之間的縱向流動和橫向融和,構建交流暢通、溫馨和諧的城市社會氛圍。
[1]齊格蒙特·鮑曼,歐陽景根譯.共同體[M].鳳凰出版傳媒集團,江蘇人民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