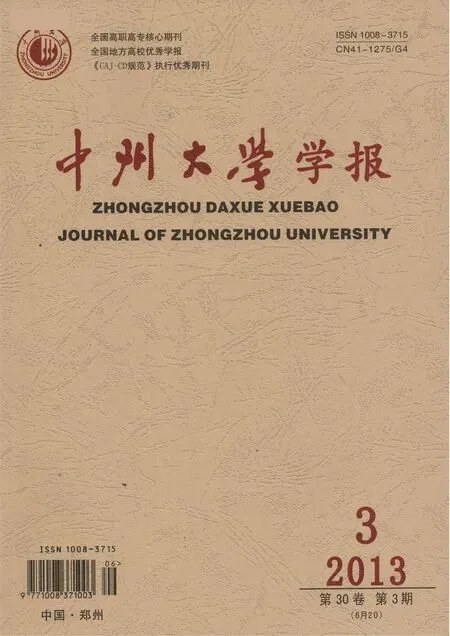新文學史寫作實踐與知識型構
劉 忠
(上海師范大學人文學院,上海200234)
“五四”前后,西學東漸在為國人送來“民主”、“科學”觀念的同時,也改變著人們對文化、文學的認識。如果說“五四”新文化、新文學、新道德提倡的是“新知”,那么“昌明國粹”、“整理國故”、“讀經頌典”鼓勵的則是“溫故”。盡管“文學革命”大潮沖決了“復古守舊”的樊籬,產生了一批經典作家作品,但新文學的歷史化進程并不順利。起初,作為古典文學的自然延伸,滿足教學之需;后來,退去古典身份,學科意識覺醒,進入一個學科建設時期。
一、借鑒模仿時期的文學史寫作
中國的文學史寫作醞釀于晚清的改良運動,受“師夷長技以制夷”、“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新民說”影響,西方近現代教育思想和體制涌入國門,大學堂、師范館取代傳統的私塾、經館,成為學校教育的主要形式。1901年清廷下興學詔,鼓勵地方辦學;1902年京師大學堂(即現在的北京大學)成立;1903年“癸卯學制”(即《奏定大學堂章程》)頒布推行①,規定大學堂設經學、政法、文學、商學、格致、工學、農學、醫學八科,其中“文學科”設中國史學、萬國史學、中外地理學、中國文學、英國文學、法國文學、德國文學、俄國文學、日本國文學九門。為了滿足教學之需,“章程”指出“日本有《中國文學史》,可仿其意自行編撰講授”[1]24。正是在這樣背景下,西方的文學史觀念和研究方法為中國文學研究注入了新鮮血液,文學史寫作開始步出傳統的“詩文評”、“文苑傳”、“仿古制”范式,迎來了學科化、專著化的契機。誠如陳平原所言:“晚清學部(以及民國教育部)對于課程的設置、教科書編寫和學生考試方式的規定,乃‘文學史’神話得以成立的決定因素。”[2]換言之,中國文學史寫作的興起不僅是西向而學,而且是服務于晚清學制改革所需,完全是被動的、仿造的、亦步亦趨的。
戴燕在《文學史的權利》一書中說:“文學史本是由西方轉道日本舶來的。以文學史的名義,對中國文學史的源流、變遷加以描述,在中國始于20世紀初。1904年及以后的兩年,福建人林傳甲從南方來到北京,出任京師大學堂新設師范館的國文教習,他參照張之洞主持修撰的《奏定大學堂章程》,編寫了一部7萬字左右的《中國文學史講義》,大約同一時期,受聘擔任有著教會背景的東吳大學國文教授的黃人,也開始編寫另外一部篇幅更大的《中國文學史》,這一南一北的兩種教材,是現在仍能看到的中國文學史的開山之作。”[3]文中,戴燕顯然是把林傳甲和黃人的《中國文學史》誤認為是中國最早的文學史著述,是仿照的“講義”,還不是今人所言的觀念現代、體例健全、系統規范的文學史專著。后來,郭延禮、李明濱、黃霖、陳國球等人對“最早”進行考證,把國人撰寫的文學史時間提前至1897年。
竇警凡的《歷朝文學史》脫稿于1897年,1906年出版;林傳甲的《中國文學史》編寫于1904年,當年印成講義,1910年正式出版(國學扶輪社);黃人的《中國文學史》由于體量大、篇幅長的緣故,編撰時間從1904年持續到1909年,正式出版已是1911年(武林謀新社)。從撰寫時間上看,竇警凡的《歷朝文學史》無疑是最早的。不過,從“志文字原始第一、志經第二、敘史第三、敘子第四、敘集第五”的體例來看,《歷朝文學史》沿襲的仍是傳統的文史不分“大文學”、“雜文學”觀,離今日所言的“純文學”還有很大的距離;同時,竇警凡的論文以“理”、“利”為首,“文”的成分稀薄,選文以史傳、詩歌為主,戲曲、小說鮮有提及,尚未脫離“詩文評”舊習;加之,出版后,流通甚少,影響遠不及林傳甲和黃人的《中國文學史》。
與竇警凡的《歷朝文學史》相比,林傳甲的《中國文學史》在史論結合和文學性上明顯增強。從“史”的角度看,《歷朝文學史》在描述經、史、子、集各體文章時,雖顧及其源流變化,但何以變化卻語焉不詳,常常歸因“時運不濟”。林傳甲的《中國文學史》論述文學演變時,兼及文學與時代之關系,史論結合,更像一部文學史。從“文”的角度看,《中國文學史》遵循“經史子集”模式,但在詩、文之外,給了戲曲、小說一定篇幅,有著“文”的某種自覺。如果說竇警凡的《歷朝文學史》尚停留在“理”上,林傳甲的《中國文學史》開始移至“文”上,黃人的《中國文學史》則又前進了一步,觸及到“美”上。卷首語中,黃人指出:“人生有三大目的:曰真,曰善,曰美,文學屬于美之一部分,從文學之狹義觀之,不過與圖畫、雕刻、音樂等。自廣義觀之,則實為代表文明之要具,達審美之目的,并以達求誠明善之目的者也。”[4]7應當說,黃人的文學觀已經相當“現代”,幾與我們相同。在對待小說文體上,竇警凡的《歷朝文學史》棄而不談,林傳甲的《中國文學史》貶斥否定,黃人的《中國文學史》跳出積淀已久的“經史子集”窠臼,一改前人“小道”、“稗事”認知,給予小說很高評價,認為“小說能掃蕩唐宋歷來之稗官家”,“小說之長,當不令和美爾、索士比亞專美于前也(即荷馬、莎士比亞,引者注)”[4]342。這一認識相當超前,與梁啟超的“新民說”有一脈相通之處。
從竇警凡到林傳甲再到黃人,時代在前進,文學史觀念在變化,文學史寫作從最初的“講義”之用開始走向“講義”與“史著”兼而有之的格局;同時,文學史的傳播與影響也漸次擴大。在觀念移植、借鑒模仿的推動下,中國的文學史寫作有了躍出地表的沖動與意愿。此后,王國維的《宋元戲曲史》(1913年)、王夢曾的《中國文學史》(1914年)、曾毅的《中國文學史》(1915年)、朱希祖的《中國文學史要略》(1916年)、劉師培的《中國中古文學史講義》(1917年)、吳梅的《中國文學史》(1917年)、謝無量的《中國大文學史》(1918年)等相繼出版,形成了一次“中國文學史”編寫熱。這些史著或以國學和史學為基礎,借用二者的研究方法進行文學史研究;或吸收西方美學思想,以進化論視角梳理中國文學發展進程,為清末民初學校教學提供學術資源。
溯源國人撰寫的文學史寫作,面臨的第一個棘手問題就是“誰是第一部”。從編撰時間上看,林傳甲的《中國文學史》之前,已有竇警凡編寫的《歷朝文學史》,之后又有黃人的《中國文學史》,但是,今人在論及文學史知識型構的時候,多提林著而少提或不提竇著和黃著。分析原因,除了林著挾“京師大學堂國文講義”之名,給人以欽定色彩之外,林著的廣泛傳播及其仿造日本《中國文學史》引發的爭議亦是不可忽視的因素。竇著《歷朝文學史》系他在無錫東林書院講學所用教材,1906年出版,傳播范圍有限,外界知曉者甚少,隨著作者1909年病逝,著作和作者堙沒不彰。至于黃人的《中國文學史》,與竇著一樣傳播有限,另一個問題是它的多卷本,出版周期長,現存全本少而又少。與此二者相比,林著《中國文學史》不僅受眾廣泛,而且版本眾多,既有京師大學堂油印講義本,又有《廣益叢報》的連載本,還有國學扶輪社本。另外,林著在“五四”之后屢遭批判,這在一定程度上反而擴大了它的知名度。鄭振鐸就曾評說林著:“名目雖是《中國文學史》,內容卻不知道是些什么東西!有人說,他都是抄《四庫提要》上的話,其實,他是最奇怪——連文學史是什么體裁,他也不曾懂得!”[5]
回答完國人最早的文學史之后,還有一個問題需要明確,這就是影響研究中借鑒對象的選擇與互設問題。如前所述,在國人的文學史寫作起步階段,從觀念到實踐都受到西方和日本影響。
從目前掌握的史料來看,最早譯介到國內并產生影響的中國文學史著述是日本人笹川種郎(1870—1949)撰寫的《支那文學史》(1897年),該書1904年1月由上海中西書局出版發行。林傳甲在《中國文學史》的卷首語中曾說:“傳甲斯編,將仿日本笹川種郎《中國文學史》之意,以成書焉。”[1]1《支那文學史》把中國文學分為九期,時間跨度從“春秋以前的文學”到“清朝文學”,吸收法國人丹納的“人種、環境、時代”理論,在詩、詞之外,開列專章描述中國古代戲曲、小說發展流變。遺憾的是,林傳甲的《中國文學史》雖然多次引用笹川種郎的見解,但并未沿著他開放的思路走下去,而是批評其對小說、戲曲的重視,認為是“識見污下”。其后,黃人的《中國文學史》、曾毅的《中國文學史》不同程度地吸收了另外一個日本人兒島獻吉郎《支那文學史綱》(1891年)的成果,兒島獻吉郎把中國文學史分為上古(秦焚書坑儒以前)、中古(至唐初)、近古(至明亡)、今世(清代至今)四個時期。1913年,古城貞吉的《支那文學史》(1895年)由南社社員王燦翻譯成中文,改名《中國五千年文學史》,在上海開智公司出版,該書從章節名目到具體內容都扣緊“文學”兩字,是一部較為純粹的文學史著,對“五四”前后國內的文學史寫作產生了積極影響。
晚清以降,西學東漸經由日本傳入我國成為常態,文學史亦然。20世紀初,日本學界一度出現“中國文學史”研究熱,除了上述翻譯到國內的幾部之外,還有末松謙澄的《支那古文學史略》(1882年)、中野重太的《支那文學史》(1894年)、藤田豐八的《支那文學史稿》(1895年)、中根淑的《支那文學史略》(1900年)、久保天隨的《支那文學史》(1903年)、宮崎繁吉的《支那文學史》(1904年)[6]等。此一時期,日本出現中國文學史研究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文化的同根同源是一個方面,許多日本學者自幼就學習漢語,對中國文學有著濃厚的興趣,運用西方思想觀念解讀中國文學,本身也是一種文化認同。另一方面,作為甲午戰爭的勝利國,日本需要重新認識和評價中國,以確立新的文化坐標。反過來,他們編寫的中國文學史又憑借東西方觀念的互滲互融優勢,為中國學者所接受,成為學習西方同時又保有文化自信的窗口。筆者認為,這是“五四”前后國內學者選擇日本人著述“中國文學史”作為仿照對象的主要原因。
與日本學者的“中國文學史”研究熱幾乎同時,俄國、英國、德國學人也開始踏上“東向而學”之路,只不過沒有形成集群之勢,而是散兵游勇,并且他們的文學史書寫也沒有日本學者那樣幸運,在東方古國產生深遠影響,直到今天,才出土文物般被學者們發現,重估其開創性價值。這些學人中,有英國人赫伯特·阿倫·翟理斯(Herbert Allen Giles,1845—1935),他寫作的《中國文學史》出版時間為1897年,與日本學者古城貞吉的《支那文學史》同年。他曾翻譯《莊子》、《聊齋志異》等中國古典文學作品,編著過大量與中國文化有關的著作,如《古今姓氏族譜》、《中國文明》。翟理斯對于自己撰寫《中國文學史》自信滿滿,在該書序言中,他不無自負地說:“這是用任何語言,包括中文在內,編寫一部中國文學史的首次嘗試。”翟理斯的《中國文學史》依據自己對中國文學的理解,梳理了從公元前600年到公元1900年間中國文學的發展進程,附以若干中國古典小說、戲劇的翻譯片斷,很適合西人的閱讀習慣,面世之后,多次再版,直到1973年佛蒙特州查爾斯·E·塔特爾出版公司還在出版修訂版,由此可見該書的學術價值。但是,翟理斯的《中國文學史》在它的故鄉——中國,似乎并不怎么受歡迎,鄭振鐸曾在他的《中國俗文學史》和文章中提及,說“Giles實毫無可以供我們參考的地方”。
與翟理斯的《中國文學史》命運相似,1902年德國人威廉·顧魯柏(W·Grube,1855—1908)編著的《中國文學史》由萊比錫阿麥朗格斯出版社出版,該書用德語寫成,在中國譯介甚晚,影響不大,其價值主要表現在學術史上。
事實上,世界上最早寫作《中國文學史》的人既不是英國人翟理斯,也不是日本人笹川種郎、德國人顧魯柏,而是俄國人瓦西里·巴甫洛維奇·瓦西里耶夫(Василий Павлович Васильев,1818—1900),早在1880年,他就出版了《中國文學簡史綱要》。瓦西里耶夫1840年隨東正教傳教士團來華,在北京居留十年,精通漢、滿、蒙、藏、梵文等多種語言,1880年圣彼得堡斯塔秀列維奇印刷所出版了他撰寫的《中國文學簡史綱要》。與前述英國人、德國人寫作的中國文學史相比,該書特點之一是對中國文學的主要樣式——詩詞、歌賦、小說、戲劇,都給予了高度評價,“像普希金、萊蒙托夫這樣的抒情詩人,在中國兩千年的詩歌作者中很多很多,這里只需要舉出司馬相如、杜甫、李太白、蘇東坡就可以了”。特點之二是在敘寫文學演變的時候,引述史料有據,他說:“在書中不轉引其他歐洲學者的著作,我所論析的作品,幾乎沒有一部不是我親自閱讀過的。”特點之三是以儒學為線索,評介《詩經》、《論語》、諸子百家,以及《史記》、《資治通鑒》等歷史典籍,為“美文學”確立了廣闊的文化語境。他說:“全部中國文明,整個廣博而多樣的中國文學,其基礎是儒學”,因而不能按古希臘、古印度那樣依樣畫葫蘆,把“文學史”定格為介紹長詩、小說和戲劇這樣狹小的范圍。這些種類在希、印文學中占了主要的地位。相反,在中國文學史上,“擺到首位的應該是儒學,而不是詩歌、小說、戲曲這類美文學”[7]。此說雖然不免偏頗,有把學術史、文化史與文學史等同起來的嫌疑,但綜合起來看,該書在結構框架、敘述方法上具備了文學史的基本規范。遺憾的是,這部世界上最早的“中國文學史”沒有適時譯介到中國,國內學者知之甚少,直到近年才引起關注。
中國文學史寫作初興時期借鑒模仿對象鎖定日本而非其他國家,除了上述所說的翻譯原因外,我想還有一個接受心理因素。理性上,學人們清楚地知道西方近現代思想的先進性,認識到中西文化融會的必要與重要;但情感上,半殖民地的屈辱和民族文化的自尊很難讓他們放下身段,接受“先生老是侵略學生”的強者邏輯,而是轉向近鄰日本,借鑒其迅速崛起的文學資源,建構自己的文學史話語。“五四”之后,這種既“尊西”又想“制夷”的心態,從文學層面擴展到社會變革層面。
二、學科自覺時期的文學史寫作
一番模仿和實踐之后,20世紀30年代,中國的文學史寫作迎來了一個自我建構的爆發期。隨著北京大學、燕京大學、輔仁大學、北洋大學、中央大學、東南大學等學校開設中國文學課程,編寫《中國文學史》成為學人們的自覺行為。
首先,在“文學革命”的催動下,文學史編寫體例的章節化被賦予更多的“現代”意義。這種既能夠發揮時間敘述功能,又兼具空間延展功能的體例,有著傳統“文章流別體”無法比擬的優越性,把古代的紀傳體、紀事本末體的優長發揮到極致,同時,附錄、補正等形式也保留了“考據學”發現、辨偽、精審、爬梳等部分功能。
其次,西學東漸之風向縱深處勁吹,文學史寫作開始從語言到文體全面轉型。如果在林傳甲、黃人、曾毅、劉師培、謝無量等人的文學史中,語言尚不構成問題,那么在胡適、魯迅、周作人、譚正璧等人筆下,語言不僅是文學史書寫的工具,而且事關思想的傳播、生命力的延續甚至是審美的表現。古與今、傳統與現代、文言與白話的對峙考驗著每一個修史者的神經,胡適、陳獨秀、魯迅、周作人、吳虞、錢玄同們倡導并實踐的新文學雖遇到林紓、吳宓、胡先骕、梅光迪、章士釗等保守勢力的強力狙擊,但新文學還是挾民主、科學之力一路高歌猛進,給文學史撰寫帶來清新之風。為了彰顯古典文學的生命力,也為了總結古典文學的成就,確立學科地位,20世紀20年代中后期,涌現了一批文學史著,如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1923年,新潮社)、胡適的《國語文學史》(1927年,北平文化學社)、《白話文學史》(1928年,新月書店)、謝無量的《中國大文學史》(1928年,中華書局)、譚正璧《中國文學進化史》(1929年,光明書局)。這些著作大都以詩歌曲賦為主,間或論及白話通俗文學的興衰,在史料整理、觀念闡釋上有著較高的學術價值。
最后,文學史寫作不僅面臨啟蒙思想和白話語體的強力介入,還要解決如何“歷史化”的問題,呈現出前所未有的糾結。1920年9月,“文學革命”參與者、新潮社骨干成員羅家倫發表長篇論文《近代中國文學思想之變遷》,在進化論觀念的指導下,首次把中法戰爭以來的文學作為一個整體進行考察,認為近代中國文學思想經歷了一個從“文以載道”到“進化論”的轉變過程。新文學面臨的危機是受到舊思想“輕佻、謾罵、武斷、籠統、空泛、不合邏輯”等遺毒的影響,為了趕上世界潮流,惟有大量譯介西方文學,使中國文學適應時代的進化。很顯然,羅家倫文章的指向并不在“史”上,而在文學革命這個“點”上,為白話新文學尋找經驗和理論依據。該文在文學史上的價值主要表現為進化論觀念的指導和時間起點的下移。兩年后,胡適發表《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時間分期和文學觀念明顯受到羅家倫文章的影響。
1922年3月,《申報》舉行五十周年紀念活動,胡適應邀著文《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文章選取桐城派代表人物曾國藩去世、戊戌維新前夜的1872年為起點,以新文學、新道德倡導已經五年的1922年為終點,全景式地描述了從文學改良向文學革命轉型的艱難過程。當時,新文學剛剛起步,新舊文學之爭相當激烈,文學創作還不夠強大,文章前九節都在講述今日我們劃歸近代文學的文事活動,只有第十節給新文學以少許的關注,可謂是“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的一條尾巴。不過,幸運的是,“當著新文學幾乎還在學步的時候,早早地就被人恭請坐上了歷史寶座”[9]2。從此,文學史話語的叢林就有了新文學的一席之地。同時,從語言上看,文學史書寫也進入了一個白話與文言并存時期。作為古典文學的最后一代傳人,嚴復、林紓的譯文,譚嗣同、梁啟超的議論文,章炳麟的小學依然精彩,但都無法阻止古文學的落幕。“章炳麟的古文學是五十年來的第一作家,他的成績只夠替古文學做一個光榮的下場,仍舊不能救古文學的必死之癥,而新文學僅僅幾年就佳作不斷,從四年前的《狂人日記》到最近的《阿Q正傳》,雖然不多,但差不多沒有不好的”。[10]
《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的發表為新文學爭取到了語言、思想、生氣方面的合法性,邁出了新文學研究的重要一步,但此一時期的文學史寫作仍停留在用現代觀念詮釋古代文學經驗層面,新文學史還未獲得獨立的話語權,或者說,僅僅是“附驥式”,沒有形成一個獨立、完整的體系,大多數學者在編寫文學史時,只是把新文學作為古代文學的尾聲進行評述。1924年商務印書館出版的胡毓寰的《中國文學源流》,1926年大光書店出版的趙景深的《中國文學小史》,1929年中華書局出版的陳子展的《中國近代文學之變遷》、《最近三十年中國文學史》,1932年北新書局出版的胡云翼的《新著中國文學史》,1932年世界書局出版的劉麟生的《中國文學史》,1932年北平樸社出版的鄭振鐸的《插圖本中國文學史》,1932年大江書店出版的陸侃如、馮沅君的《中國文學史簡編》,1933年北新書局出版的陳子展的《中國文學史講話》,1929年開明書店出版的朱東潤的《中國文學批評史大綱》,1934年商務印書館出版的郭紹虞的《中國文學批評史》,1935年光明書店出版的譚正璧的《新編中國文學史》,1935年世紀書店出版的蔡振華的《中國文藝思潮》,1936年北新書局、中華書局出版的趙景深的《中國文學史新編》、《中國文學史綱要》,1938年商務印書館出版的楊蔭深的《中國文學史大綱》,1938年商務印書館出版的鄭振鐸的《中國俗文學史》,1939年上海合作出版社出版的朱維之的《中國文藝思潮史略》,走的都是“通史”一路。
新文學僅是文學長河中的一朵不起眼的浪花,區別在于談論方式不同、側重點有別罷了。如趙景深《中國文學小史》關注胡適、劉半農、冰心、宗白華、郭沫若、徐志摩、聞一多、朱湘、汪靜之、李金發等人的詩歌,魯迅、郁達夫、葉圣陶、王統照、魯彥、張資平等人的小說。較之胡適的《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陳子展的《中國近代文學的變遷》、《最近三十年中國文學史》把近代文學的開端鎖定在1840年的鴉片戰爭,時間跨度縮小,增加了“五四”之后革命文學的內容,認為文學革命的發生源于“文學發展上自然的趨勢”、“外來文學的刺激”、“思想革命的影響”、“國語教育的需要”。應當說,這些分析還是很有見地的。陸侃如、馮沅君的《中國文學史簡編》用專節論述“文學與革命”的關系,書中除了介紹馬克思恩格斯的歷史唯物論常識,還觸及蘇聯文藝理論家普列漢諾夫、波格丹諾夫的藝術論知識。談到無產階級文學運動,該書認為“白話文學運動是成功了,但是這個成功是有限制的。固然,十余年來的詩歌、小說、戲劇,形式上都是白話的,然而內容上呢?內容上,說來可惜,還是千篇一律的風花雪月、佳人才子——雖然是歐化了的佳人才子,但是我們不但要求新的瓶,并且要求新的酒!這個新的酒的給予,卻有待于無產階級文學”[11]。比較而言,譚正璧的《新編中國文學史》是當時新文學所占篇幅最長的一部,全書共七編,前六編講述秦漢到近代的文學發展,第七編分“文學革命運動”、“文學建設運動”、“革命文學運動”三章,全面闡述新文學發展進程及內在邏輯。從文學觀念上看,該書明顯受到左翼文學及蘇聯拉普理論的影響,褒革命文學貶文學革命,認為“五四”文學是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的文學,需要繼續革命,無產階級文學取而代之是歷史的必然趨勢。
1933年上海世界書局出版的錢基博的《現代中國文學史》是最早在“中國文學史”前面冠以“現代”的史著,敘述時間大體在1911年至1930年間。關于“現代”一詞,錢基博解釋說:“吾書之所為題‘現代’,詳于民國以來而略推跡往古者,此物此志也。然不提‘民國’而曰‘現代’,何也?曰:維系民國,肇造日淺,而一時所推文學家者,皆早嶄然露頭角于清之末年,甚者遺老自居,不愿奉民國之正朔,寧可以民國概之?”其后他又說:“現代文學者,近代文學之所酦酵也;近代文學者,又歷古文學之所積漸也。明歷古文學,始可與語近代;知近代文學,乃可與語現代。”[12]可見,錢基博所寫“現代中國文學史”,是基于對古今文學演變軌跡的歷史把握和深入洞察上的,“現代”指向的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近三十年時間。書中,錢基博表達了對新文學的明顯不滿,“新文化、新文學者,胡適之所以嘩眾取榮譽,得大名者也”;自由體詩“光怪陸離”,無足取者;散文“競相歐化,佶屈聱牙,過于《周誥》”。該著思想保守,不無遺憾。
總的來說,此一時期的文學史寫作呈現兩個顯著特點:一是文學史學科意識覺醒,文學史教學和研究成為一大熱點;二是文學史寫作趨于多樣化,通史、斷代史、專門史、文體史的出現標志著古代文學敘述模式基本成型,新文學史書寫漸露端倪。
三、觀念新變時期的文學史寫作
進入20世紀30年代,文學史話語的古今分野在加劇,新文學史書寫進入到一個集中爆發期,學科建設、知識型構等問題提上了議事日程。一方面,新文學的存在已毋庸置疑,從歐化移植到強身健體,新文學學科進入到了一個建設期。另一方面,新文學創作經過十余年的發展,積累了豐富經驗,亟需總結和評估。
歷史有著驚人的相似,林傳甲的《中國文學史》是在京師大學堂“文學科”講義基礎上整理而成,無獨有偶,新文學史的撰寫也是由大學講義開始的。1929年,新文學第一個十年的重要詩人、散文家朱自清在清華大學開設“中國新文學研究”課程,自編講義《中國新文學研究綱要》。據他的學生王瑤回憶,“綱要”沒有公開出版,只發給學生作為講義使用。今天我們能見到的稿本主要有三種:“一為鉛印,一為油印,第三種雖有部分油印,但以手寫為主”[13]。置于新文學研究史上看,《中國新文學研究綱要》首開文體分類先河,全書分“總論”、“各論”兩部分,“總論”三章分述文學運動、論爭、社團、流派,“各論”五章分論詩歌、小說、戲劇、散文、文學批評。“綱要”時空敘述集中于戊戌變法至1930年間,是一次名副其實的新文學之旅。不過,令人惋惜的是,“綱要”僅存目次,沒有細化,是一部未完成的新文學史著。若干年后,受“綱要”影響,王瑤編寫了一部完整的新文學史《中國新文學史稿》,算是彌補了這一缺憾。
1932年9月,周作人應邀在輔仁大學演講“中國新文學的源流”,同年,北平人文書店出版由講演稿整理而成的《中國新文學的源流》。從書名上看,理當是一部相對規范的新文學史專著,實則不然,出于講演的需要,該書“論”的成分過多,“史”的脈絡不清,大部分篇幅都在論證中國文學源頭之一“言志”,為“五四”性靈散文尋找理論和實踐的雙重支持;極為有限的文字也被用來論析“五四”文學與明代公安文學的關系,“胡適之的所謂‘八不主義’,也即是公安派的所謂‘獨抒性靈,不拘格套’,和‘信腕信口,皆成律度’的主張的復活”[14]。從學理上看,《中國新文學的源流》更像是一篇學術論文,是在為中國文學的“言志”傳統尋找注腳,而不是立足東西文化碰撞語境,闡發新文學與舊文學、外國文學的關聯,同時,專著對新文學作家作品的選擇與評價也不夠公允,很難想象沒有魯迅、郭沫若等人的新文學史會是一個什么樣子!僅憑胡適、冰心、徐志摩、俞平伯、廢名等人的抒情傾向,就武斷地把新文學源頭歸于“言志”麾下,也很不科學。該書出版不久,就遭到尚在清華大學讀書的錢鐘書的批評,認為該書從“概念理解”到“史實運用”都混亂不清,載道與言志不僅在新文學中不是對立的,而且在古代文學中也是并行不悖的[15]。
在新文學編撰史上,1933年北平杰成書局出版的王哲甫的《中國新文學運動史》是第一部體例周全、內容詳實、線索清楚的新文學史專著。黃修己說:“在新中國成立前出版的僅有的幾部新文學史專著中,《中國新文學運動史》是流傳較廣、影響較大的,首先給人的印象,是內容比較豐富,凡是有一些影響的作家作品都給以一定篇幅;凡是認為應該記述之事,也都收入書中。”[9]32繼朱自清《中國新文學研究綱要》之后,《中國新文學運動史》在詩歌、小說、戲劇、散文、文學批評等文體之外,增加了翻譯文學、古典文學整理、民間文學收集、兒童文學創作等內容,注意到了新文學與中西方文學傳統的復雜關系,達到了當時人們認識的最高水平。
人們常說,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中國新文學運動史》之后,這種以思潮流派為主體框架、作家作品為血肉的文學史寫法引來了許多仿效者。1934年現代書局出版的伍啟元的《中國新文化運動概觀》、1935年北平新新學社出版的王豐園的《中國新文學運動述評》、1936年上海亞細亞書店出版的吳文祺的《新文學概要》等,都不約而同地把書寫對象鎖定在新文學思潮上。
伍啟元的《中國新文化運動概觀》分上下兩篇,上篇描述思潮,下篇介紹論爭,雖然書名為“文化史”,但所涉內容與脈絡和新文學發展軌跡高度重合,例如:文學革命運動與新文化運動、實驗主義及其他、疑古思潮的澎湃、國故整理與其批評、唯物的辯證法、人生觀的論戰、東西文化的討論等章節均取文化、文學、思潮三位一體的復合視角,把社會變革、文化變遷和文學變化作為一個整體來考察。貫穿全書的一個基本觀點是新文化運動深受西方近現代思想影響,是世界巨變之一部分,“自鴉片戰爭以來,中國學術思想有一個很大的劇變,就是從中國舊有文化轉到西洋近代的文化的蛻變”。在這種文化觀念指導下,作者評述“五四”文學革命受民主、科學的影響,走的是通俗化、民眾化的道路;認為30年代左翼與自由人、第三種人的論爭折射的是思想界的分化、階級論的抬頭。“文藝的論戰雖然只是個人本位主義的文學家和社會本位主義文學家的相互攻擊,但它代表了辯證法的唯物論的抬頭,和社會本位主義的勝利。”[16]應當說,在一個普遍左傾的年代,堅守知識分子的獨立立場,理性地評價革命文學、左翼文學的得失是十分難得的。
作為新文學史從進化論走向階級論、從多元走向一元的過度,王豐園《中國新文學運動述評》、吳文祺《新文學概要》的出版有著非同尋常的意義。與朱自清的《中國新文學研究綱要》、周作人的《中國新文學的源流》、伍啟元的《中國新文化運動概觀》中表現出來的進化論、個性主義文學觀不同,王豐園、吳文祺的史著帶有明顯的階級論色彩,階級分析方法不僅用來解釋文藝運動的前后更迭邏輯,還成為評判文學作品優劣高下的標準。如果說陸侃如、馮沅君等人的史著中階級論觀念已漸露端倪,那么在王豐園、吳文祺的筆下,階級論已經化作一把尺子,用來衡估一切作家作品。例如:界定“五四”新文化運動性質為資產階級的、不徹底的。“因為他們在政治方面的不徹底性,所以也決定在文化上的不徹底性,他們不能提出積極的文化以代替這殘骸朽尸。他們只憧憬著資本主義文化,喊出‘賽因斯’、‘德謨克拉西’等空口號,要在思想上文藝上,及一切觀念體系上,建筑起資產階級的鞏固寶塔。他們對于舊的無批判的放棄了,對于新的也無批判的在吸收。”[17]把文學與政治的關系簡單化,“文學的變遷,往往和政治聚集到變遷有連帶的關系的。因此……要從政治經濟的變遷中,去探究近代文學的所以變遷之故。”[18]
“九一八”事變后,日本加速侵華,東北、華北的相繼淪陷不僅加快了中國社會的殖民化進程,也波及到教育、學術領域,大批高校停課、搬遷,與30年代初期的繁榮相比,此后一段時間,新文學史撰寫與出版明顯放緩。僅趙家璧主編的《中國新文學大系》、李何林的《近二十年中國文藝思潮論》和周揚的《新文學運動史講義提綱》在史料整理、觀念新變等方面有著特殊的價值。
1935年,上海良友圖書公司約請胡適、鄭振鐸、茅盾、魯迅、鄭伯奇、朱自清、周作人、郁達夫、洪深、阿英編選《中國新文學大系》,分理論、小說、詩歌、戲劇、散文、索引等十卷,每卷前置“導言”,“大系”總序由蔡元培撰寫。《中國新文學大系》規模之大、專業化程度之高、影響力之大超出了人們的想象,至今仍是人們研究新文學史必備的參考書,60年代、80年代、90年代香港、大陸曾援例編選第二個、第三個、第四個十年選集,但影響力遠不如前。
從文學史知識型構角度看,《中國新文學大系》的首要貢獻在于史料的整理與保護上,藉此衍生出一門新學科——史料學。經過十年的發展,新文學從當初的搶灘登陸到后來的強生健體,從當初的借鑒模仿到后來的以我為主,許多作家作品在大浪淘沙中經典化,進入史家視野和大學講堂。在這方面,“大系”中的理論、小說、詩歌、戲劇、散文卷全息式地見證了新文學的成長過程,胡適、魯迅、周作人、郁達夫、郭沫若、老舍、沈從文、茅盾、曹禺、徐志摩、戴望舒、朱自清等人的作品也在人們的反復閱讀中走向經典,表現出某種原生、原創、源頭的特點。集合文學思潮、文學現象、作家作品,留存新文學成長的點滴足跡,“大系”為后來者留下一份珍貴的史料。今天,“大系”已經成為中國現代文學史料學的重要組成部分,表現出極高的史學價值。
“大系”的第二個貢獻是由“導言”呈現的新文學經驗和編選者的價值評判,這些個性化的評述從不同角度、不同側面豐富了新文學史書寫。作為“五四”新文學的發起人、親歷者,他們的遴選、評價能夠近距離地觸摸歷史,烙下時代印痕。1940年良友圖書公司將“大系”每卷前面的“導言”集中起來編選成集《中國新文學大系導論集》出版,收到了很好效果,“導言”成為考量新文學第一個十年成就的重要窗口。曹聚仁說:“這每一篇導言,便是最好的那一部門的評介,假使把這幾篇文字匯刊起來,也可說是現代中國新文學的最好綜合史。”[19]今天,這些創造性、個性化、在場感極強的評論文字仍閃爍著智慧的光芒。如郁達夫對“五四”散文成就的總結:“現代的散文之最大特點,是每一個作家的每一篇散文里所表現的個性,比以前的人和散文都來得強。”魯迅對鄉土文學的看法:“僑寓性”、“追憶性”、“風物性”,成為學人們定義“鄉土文學”的通識。
全面抗戰開始后,正面戰場的不斷失利愈加不利于學校教學和研究工作的開展,文學史寫作進入到一個消歇期。置身動蕩不安的環境,從事學術研究殊為不易。1939年上海生活書店出版李何林編寫的《近二十年中國文藝思潮論》,是“大系”之后新文學研究的又一收獲。“思潮”將1917年至1937年的文藝思潮分為三個時段:“五四”前后的文學革命(1917—1925)、“大革命時代”前后的革命文學(1925—1931)、“從九一八到八一三文藝思潮”(1931—1937),援此而來的體例——緒論、概述、社團、流派、作家作品——中規中矩,文藝思潮的發生、發展、走向配合以大量原始資料和自己的評價,勾畫出那個時代相對完整的文藝思潮路線圖。但是,這種看似平衡的時序架構很快就被作者的文學史觀和敘述重心打破,在探究思潮變遷的原因時,由于作者運用的是社會學、階級論方法,把文藝思潮的變化與階級斗爭緊密地捆綁在一起,敘述的重心勢必會向左翼文學傾斜。好在李何林沒有在階級論上走得太遠,而是盡可能地隱潛自我,讓史實本身說法。關于這一點,作者在《重版說明》中曾說:“嚴格來說,這不能算是近二十年中國文藝思想斗爭史,因為我沒有總結出它的‘史’的發展脈絡或規律,我只稍稍提到每次斗爭的社會政治背景和原因,以原始資料為主,因此,只能叫做文藝思想斗爭史資料長篇,不是史。”[20]拋開作者的自謙因素,我認為,作者的這段表白道出了本書的一個重要價值:史實呈現,保存原貌。
當李何林在四川江津白沙鎮克服時局動蕩、資料缺乏等困難撰寫《近二十年中國文藝思潮論》的同時,遠在陜西延安的周揚正在魯迅藝術文學院講授“中國文藝運動史”課程,并自編《新文學運動史講義提綱》。可以推斷,作為權威文藝理論家、魯藝副院長、左翼文學運動的組織者,周揚的課堂一定精彩紛呈,內容豐富不說,單就文壇軼事、掌故、人際糾葛就能讓學生們大開眼界,頓生“余生也晚”感慨。
1940年前后,魯藝推行“專門化”教育,周揚是倡導者和實踐者,他的《新文學運動講義提綱》高屋建瓴,自信而宏觀,有著理論家的氣魄和膽識。遺憾的是,《新文學運動史講義提綱》沒有公開出版,一是當年延安物質匱乏,紙張異常緊張,僅能保證黨的重要文件和理論的出版。二是魯藝的專業化方針很快就受到“關門提高”、“脫離群眾”等批評而暫停,進行整風學習。周揚沒有時間也沒有心思延續他的“講義”寫作。
今天,我們看到的是“講義”僅有引言、第一、第二和第三章的一部分內容。從已有的章節來看,“講義”延續了周揚一貫的社會學、階級論批評方法,及時吸收了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觀點,強調無產階級在新文學運動中的領導地位;高度評價魯迅的地位,認為他是新文化運動的旗手、精神界之戰士。這與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的一段經典評價:“魯迅是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將,他不但是偉大的文學家,而且是偉大的思想家和偉大的革命家。……魯迅是在文化戰線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數,向著敵人沖鋒陷陣的最正確、最勇敢、最堅決、最忠實、最熱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十分契合,兩者的傳導作用相當明顯。
1986年《文學評論》第1、2期上連載周揚《新文學運動史講義提綱》的引言和第一章、第二章原稿,“編者按”中說:“它反映了當時中國批評界所能達到的歷史高度和思想水平,也反映了周揚同志本人的作為文學批評家的風格、批評觀念和批判方法。”“周揚同志的這份講稿,是一篇主要從社會歷史角度著眼的批評文章……表現了一種文藝社會學研究的宏觀氣魄。這與后來被庸俗化了的社會學批評是很不相同的。這份講稿可以幫助我們理解科學的社會歷史批評的特點和優點,也可以幫助我們認識科學的社會學批評與庸俗的、機械的社會學批評的區別”[21]。
應當說,時隔多年,“編者按”從彼時彼地語境出發,以一種理解的心情審視周揚的《新文學運動史講義提綱》,還是客觀、公允的。至少說明在周揚身上,在他的“講義提綱”中,新文學史書寫的“革命化”還走在路上,離“一體化”、“功能化”尚有距離,周揚的“講義提綱”僅僅是新中國成立前馬克思主義文藝史觀的一次成功預演。但毋庸置疑的是,從陸侃如、馮沅君的《中國文學史簡編》到譚正璧的《新編中國文學史》,中經王豐園的《中國新文學運動述評》、吳文祺的《新文學概要》,再到李何林的《近二十年中國文藝思潮論》、周揚的《新文學運動史講義提綱》,革命化敘事在強化,階級論色彩在漸濃,文學史的意識形態化在加劇。②
中國文學史寫作從借鑒模仿到學科自覺用了近半個世紀,期間,有西學東漸的移植,從課堂講義到學術專著的提升,亦有文學史觀從多元到一元的整合,并在20世紀30年代迎來了一個短暫的輝煌期,文學史家輩出,文學史著大量出版。作為文學史長河之一部分,新文學史寫作從最初的“附驥式”走向學科自覺,朱自清、周作人、伍啟元、王豐園、趙家璧、李何林、周揚等人的寫作實踐在為新文學史確立最初的體例范型和時空架構的同時,也在進化論、階級論、革命論的映照下,彰顯出不同的成色。
注釋:
①1902年(光緒二十八年),管學大臣張百熙曾擬訂《欽定學堂章程》,即壬寅學制,未及實行;1903年(光緒二十九年),張百熙、張之洞等人在此基礎上豐富完善,制定《奏定大學堂章程》,1904年初頒布實施,是中國近代第一個正式施行的學制。兩個學制都以日本學制為藍本,而日本學制又是移植西方的,故晚清新學制是學習西方先進教育模式的產物.
②當然,囿于戰爭造成的時空阻隔、國共兩黨政見的不同,新文學史書寫尚有一些裂隙存在,如:1943年世界書店出版的李一鳴《中國新文學講話》、1944年河南前鋒報社出版的任訪秋的《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卷)、1947年上海現代出版社出版的藍海(田仲濟)的《中國抗戰文藝史》并沒有受階級論、革命論影響,在文學流派研究、抗戰文藝評價上仍有所突破。
[1]林傳甲.京師大學堂國文講義·中國文學史[M].廣州:存真閣,1914.
[2]陳平原.文學史的形成與建構[M].南寧:廣西教育出版社,1999:5.
[3]戴燕.文學史的權利[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3.
[4]黃人.中國文學史:第二編·略論[M]//江慶柏,曹培根,整理.黃人集.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1.
[5]鄭振鐸.我的一個要求[C]//鄭振鐸古典文學論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36.
[6]黃霖.日本早期的中國文學史著作[J].古典文學知識,1999(5).
[7]轉引李明濱.世界上第一部中國文學史[J].文史知識,2003(1).
[8]羅家倫.近代中國文學思想之變遷[J].新潮,1920,2(5).
[9]黃修己.中國新文學史編纂史[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
[10]胡適.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C]//胡適全集:第2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297.
[11]陸侃如,馮沅君.中國文學史簡編[M].上海:大江書店,1932:190.
[12]錢基博.中國現代學術經典:錢基博卷[M].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14.
[13]趙園.整理工作說明[C]//文藝論叢:第14輯.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2:46.
[14]周作人.中國新文學的源流[M].南京:江蘇文藝出版社,2007:90.
[15]中書君(錢鐘書).評周作人的《中國新文學的源流》[J].新月,1932,4(4).
[16]伍啟元.中國新文化運動概觀[M].上海:現代書局,1934:3,81.
[17]王豐園.中國新文學運動述評[M].北平:新新學社出版,1935:90.
[18]吳文祺.新文學概要[M].上海:亞細亞書店出版,1936:2.
[19]曹聚仁.文壇五十年(續集)[M].香港:香港新文化出版社,1937:172.
[20]李何林.近二十年中國文藝思潮論[M].西安:陜西人民出版社,1981:1.
[21]編者按[J].文學評論,198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