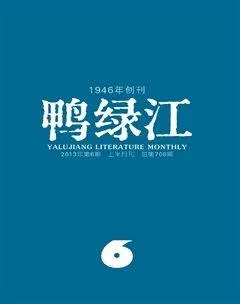河洛文化與閻連科小說創作
吳 燕,1986年生,大連大學文藝學碩士研究生,在《大連大學學報》《文化學刊》公開發表兩篇學術文章,參與完成兩項省級科研項目。
張祖立,大連大學人文學部教授,碩士研究生導師。主要從事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主持完成多項省社科基金項目,主編教材一部,發表學術論文數十篇。大連市文藝評論家協會副主席。
閻連科說過:“地域就是作家的世界,一般來說,一個作家的出生地……對他的影響非常重要。”[1]“河洛文化”對河南作家閻連科有著深刻影響:一方面,河洛的地理情狀、生活習慣、風俗信仰、歷史經驗等都為作家所熟知,成為構成其深層的文化心理結構的要素,經過與作家心智的感應融合生成為一種文化意識,成為作家認識自我和世界的一個基點;另一方面,源于特定地域文化精神影響的文學觀念和審美體驗必然外化在作家的文本中,形成獨特的藝術氣質。
從自然地理方面講,“河洛”主要指在黃河和洛河所形成的夾角范圍內,以洛陽為中心的廣闊區域。文化意義上的河洛地區稱為“河洛文化圈”,其精神范疇遠遠超出地理概念的范圍。有人認為, “河洛文化圈應該涵蓋河南省全部,東與齊魯文化圈相銜接,西與秦晉文化圈相銜接,南與楚文化圈相銜接,北與燕趙文化圈相銜接”。[2]
河洛文化是含英咀華的文化。儒學創基于河洛,周公營建洛邑,在洛陽“制禮作樂”,創立了中國最早的禮樂文化。孔子正是經過中原的游歷,建立了儒家學說。道學產生于河洛,家居河洛的老子創作的《道德經》被奉為道家經典。佛教始傳于河洛,東漢永平年間明帝派人出使天竺,拜取佛法,被認為是佛教在中國傳播的重要開端。永平十一年,明帝敕令于洛陽修建白馬寺,白馬寺因此被尊為佛教的“釋源”和“祖庭”。讖緯神學形成于河洛,董仲舒“天人感應,必有征兆”說首開讖緯之風后,光武帝劉秀進一步發揚,讖緯之學在東漢之初就傳遍全國。理學淵源于河洛,理學代表人物程顥、程頤均為洛陽人,二程之理學又被稱為“伊洛理學”或“洛學”。含英咀華、博大精深的河洛文化對閻連科的文學創作產生了深刻的影響,他的文學創作深深地打上了河洛文化的烙印。
一、獨特的地域文化符號
閻連科堅持以故鄉“耙耬山脈”為地域背景,深情描繪著這里的“土地文化”,其作品充滿著濃郁的地域文化色彩。
(一)耙耬山脈
自然景觀作為自然地理環境的一種外在、形象的組成部分,最能直接表現出地域文化的特點,同時對人們的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也有著重要的影響。丹納論及希臘民族藝術時說到:“在民族的事業上和歷史上反映出來的,仍舊是自然界的結構留在民族精神上的印記。”[3]閻連科介紹過:“我的家鄉就在秦嶺余脈的最末端,屬伏牛山系,那里有一條山嶺叫耙耬山,在我的‘瑤溝系列’中,‘耙耬’作為一個地域性的名詞已經不斷地出現,寫《尋找土地》時,已經是有意識地以這一地域背景作為寫作對象了…… ‘耙耬山脈’已經成為了一個明確的寫作方向。”[4] “耙耬山脈”既貧窮落后,又原始封閉。《情感獄》中的瑤溝、《日光流年》中的三姓村、《受活》中的受活莊、《耙耬天歌》中的尤家村,均坐落與世隔絕的耙耬山深處。這是一片被世人遺忘的土地,現代文明也姍姍來遲,三姓村多少年來沒有接到過到公社開會的通知,國家成立了那么久,村人仍是按老輩習慣把醫院稱為“教火院”。生活在這個世界的人們在精神上也失去了探尋外部世界的興趣,在他們看來,“世界”只是“耙耬山脈”。 “耙耬山脈”成為作品的重要標識。
(二) 河洛風俗
風俗從本質上說是人與自然的關系,是一定區域內的人們在長期特定的自然和社會環境中形成,并代代傳承的群體文化心理的表現和行為方式。作為群體文化的標志,它“層積著人們的生活習慣,也有群體的倫理觀念、價值取向、思維方式和審美情趣”。[5]
生產生活風俗。河洛地區農耕文化烙印鮮明,突出的表現就是重視農歷歷法和二十四節氣。《年月日》中的先爺最需要的就是一本萬年歷,因為沒有萬年歷就不知道玉蜀黍到底啥時候成熟了。河洛人婚嫁、建房、動土用農歷推算吉日。《斗雞》中,“我姥爺”和汪家小女兒行婚事之前最重要的事就是要來對方的生辰八字測兇吉。河洛是小麥、玉米的主產區,人們的飲食以面食為主。閻連科作品中的人們最常吃的就是餅、饃,最愛吃的就是“蒜汁撈面”。除了吃食品種, “飯場吃飯”是一個典型習俗,莊子里有幾個固定的飯場,飯間,人們陸續來到飯場,端菜拿饃,三五一堆,邊吃邊談。《受活》等描述了 “東家短,西家長,端起碗,攆飯場”場面。
人生禮儀。河洛人有重禮、崇禮的習俗風尚。作品中首先體現在對婚禮、婚俗的繁復描寫上。婚禮多依“六禮”而辦,每個環節寫得很細致。喪葬禮俗也別有意味。河洛人順生重死,甚至把死后看得比生前還重,“棺材”在河洛葬俗中被置以特殊的地位,“活有房,死有棺,死人沒有棺就如活人沒有房”是村人們的普遍觀點。河洛人不僅關心到死后的房屋住所,連死后的婚姻之事也一并考慮。“冥婚”俗稱“結陰親”,在河洛地區非常流行,其婚禮儀式幾乎和生人一樣。在《尋找土地》《丁莊夢》等作品中,人們都表現出對“冥婚”的巨大熱情。
信仰習俗。河洛先民“由于知識和經驗的局限,對自然界所發生的現象不能解釋,于是形成對‘天’的敬畏,進而發展為對日、月、風、雨、雷、電、山、川、湖、海、奇禽、異獸的敬畏,再進而乃至巨樹、怪石和各種器物也都成了神靈之物”。[6]《情感獄》中的九爺把老皂角樹的樹根看作災難的根源,《兩程故里》中的村人對古柏的聲音忌諱莫深,《黑烏鴉》中人們把烏鴉當作災難的預兆,其他的如“藥碗摔碎”預兆人命沒幾天,兒童歌謠暗示蝗災來臨,水缸裂口預示主人死亡,等等。人們相信萬事萬物的神力,小心地趨避著,也以毒咒和符咒來傳達自己的心思。《丁莊夢》里“誰家恨了誰家了,就在他家門前深埋一個桃木或是柳木的棒,把木棒的一頭削尖兒,寫上想讓他死的人名”。這種愚昧與鄉情、迷信與純樸融合在一起的民間信仰,正是河洛人某種精神狀態的寫照,作家對此有著深刻而矛盾的感受:“從所有普遍流傳下來的風俗里,我們所能感受到的是農民的‘躲避’、‘乞求’和‘保佑’的苦苦哀求。”“今天的農村……將在很長很長永遠一樣的歷史長河中更集中更神秘地浸泡在風俗的染缸里發酵,久而久之地被一種不知不覺的桎梏所捆束。”[7]
游藝習俗。農民的生活充滿辛勞和苦難,但會承襲著堅強樂觀的生活態度,閻連科理解這種態度,諳熟農民的文化心理和風俗習慣,這突出表現在他對民間曲調的運用和民間廟會的描寫上。“冬天日出地上暖/兩口兒在地上曬清閑/男人給媳婦剪了手指甲/媳婦給男人掏著耳朵眼/村東有一戶大財主/有金有銀住著瓦樓和雪片/可財主一天把媳婦打八遍/我問你誰家的日子苦呀,誰家日子甜?”[8] 類似小調經常穿插文中,“廟會”描寫也是如此。《受活》描繪了“受活慶”這一每年麥后歡慶豐收的盛大儀式。
(三)方言俚語
方言是語言地域性的變體,能折射地域的歷史文化內涵,表達地域特有的自然狀況和民俗風情。在《日光流年》《耙耬天歌》《受活》等作品中,閻連科大量穿插豫西的方言俚語,增添了“耙耬世界”的地域色彩。他筆下的人們把白白錯過叫“白枉枉”,把受不了叫“不消受”,把中心、中央叫“當間”。這些“土得掉渣”的方言俚語,生動地展示了受活人的生活情致。而在“受活”“儒妮子”“圓全人”“熱雪”“死冷”等方言詞語中,我們所感受到的是豫西地域所特有的苦難和凝重。河南是豫劇之鄉,豫劇的語言、唱腔、表現手法都給作家帶來了無形的創作影響。《丁莊夢》的語言就有豫劇“一唱三嘆”的感覺,“一想到讓我爹在全莊人面前磕個頭后去死掉,爺爺驚了一下。驚了一下。驚了一下,我爺也就往莊里走去了。就往我們家走去了。真的走去了。”[9]在《日光流年》的開篇第一句“嘭的一聲,司馬藍要死了。”豫劇形容一個人倒地死掉就是突然的一聲鑼響,“嘭”的一聲,演員就倒在地上了。
閻連科對方言俚語的發掘、運用很自覺:“我就是要強調方言在中文中的作用,如果蕭紅的小說、沈從文的小說沒有大量的方言的運用,他們的小說魅力就會消弱很多。”[10]
二、豐厚的河洛文化精神
作家曾經談到家鄉文化資源對其創作的影響:“從小生活在理學大師的廟宇之下,你會不斷地道聽途說。知道它的大概,時間久了,形成了一種文化浸淫,肯定也是一種情感的壓抑。”[11]博大精深的河洛文化影響著作家文化視野,使他的作品凝聚和表現出豐富深刻的思想。
(一)以人為本的“民本”思想
當代作家中,閻連科格外“迷戀”苦難,執著地關注苦難深重的鄉土大地,將苦難作為一生書寫的“核心”,始終以“令人疼痛和戰栗”的筆觸反映底層農民的生存絕境及其承受的各種苦難,展示了取向鮮明的寫作姿態和立場。
作家故鄉土壤貧瘠,自然災害多發。歷史上特殊的地理位置引發的兵家之爭又不斷地加劇這種苦難。如何生存、生活成為人們最緊迫、最關注的問題。產生于河洛的《易經》被看作是中國人道主義的源頭,西周初年,周公提出“敬德保民”的“民生”思想,至春秋戰國時形成社會思潮,并成為后代知識分子的“精神基點”。《詩經》中反映河洛地域生活的《王風》《周南》等就散發人文光彩。此后,賈誼、曹操、曹植等河洛詩人的作品多反映社會動亂,感慨人民流離失所的悲慘命運。“安史之亂”后,以杜甫和白居易為代表的詩人們發出了關心民生的最強音。這種關注民本民生的精神傳統是河洛文人身上最耀眼的光芒,必然照射著在苦難的河洛大地生長、對苦難有著刻骨銘心記憶的閻連科的心靈,影響著他形成堅定的人文主義精神和寫作立場。他的作品中,可憐的人們總是不斷遭遇天災人禍,在巨大的災禍面前往往顯得那么渺小和無助。閻連科對“人”的關注更體現在他對人的生存價值的思考上。《丁莊夢》中,夏玲玲和丁亮的結合雖有悖于倫理,但無悖于人性,他們凄絕的愛情感動了善良的村民,村民給予他們最大的寬容和理解。面對艾滋病這個人類共同面對的問題,作者的悲憫意識和人道主義的情懷充溢其中,這種對生活熱愛、對生命尊重的創作使作家完成了一次精神上的超越。
(二)堅忍自強的“天行健”精神
因為看到了絕境中爆發的生命力量,閻連科創作注重表達對生命韌性的崇高感。他筆下的耙耬山人,面對命運拋來的生死困境,沒有屈服認同,以一種極端酷烈的方式與命運做殊死的抗爭。他竭力尋找揭示來自多災多難的大地民間的生生不息抗擊命運的潛力和精神。“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堅韌奮進是河洛文化精神內核,誕生在河洛大地的神話傳說、民間故事都充滿了行天之健的文化品格,“盤古開天辟地”“夸父追日”“大禹治水”,無不體現河洛先民的創世精神。作家塑造的主要人物中,除了路六命不堪生活的重負選擇自殺外,其他的都是在絕望中抗爭命運的英雄。《日光流年》從死寫到生的“索源體”結構展現的就是人類生生不息的頑強精神。在閻連科的世界里,尤四婆取骨獻髓,拯兒救女;先爺與天抗衡,以身喂苗;司馬笑笑與蝗蟲惡戰,自殺伺鴉;藍百歲深翻土地,犧牲女兒;司馬藍拼命治水,勞累致死。他們都是集勇氣、智慧與獻身精神于一身的英雄,這種氣概與河洛大地上堅韌自強的“天行健”精神一脈相承。
(三)王都文化下的“權力情結”
洛陽自古為“王者之里”,歷史上有十三個王朝在此定都,這使它逐漸生成一種特有的“王都文化”形態。閻連科曾揭示過:“我從小就有特別明顯的感覺,中原農村的人們都生活在權力的陰影之下,在中原你根本找不到像沈從文的湘西那樣的世外桃源。……這樣的環境,自然就形成了普遍對權力的敬畏和恐懼。”[12]村長這類的“掌權者”是作家筆下集中描寫的典型代表,他們有的可以為所欲為,霸占民妻,決定村民婚姻,甚至決定村中殘娃的生死。老實的村民經常深陷權力的夢魘之中,“朝廷三爺”主宰下的寨子溝少女、寡婦媳婦,《三棒棰》中戴了八年綠帽子的石根子,《天宮圖》中為村長與自己妻子偷情放哨的路六命……在權力的桎梏下,我們看到凌辱中的扭曲惶恐,同時也看到民間對權力的膜拜與向往。《情感獄》中的連科、《堅硬如水》中的高愛軍、《金蓮,你好!》中武老二、《日光流年》中的司馬藍,為了爭奪權力都作出了種種令人感到不可思議的行為。在這種心理驅使下,大隊公章竟然成為了權力的象征而被人們瘋狂爭奪。《耙耬山脈》的大隊公章和記錄返銷糧的賬本成為作品敘述的焦點。《丁莊夢》中的老村長丟了公章一直死不瞑目,直到“我爺”拿一個假公章給他看才閉上了雙眼。這種夸張、喜劇性、隱喻性的寫作顯示了作家內心的透徹感悟。與其他作家書寫權力不同,閻連科注重從底層的生存苦難實際境遇出發看待人們的這種心理和行為,并不直接地從現代啟蒙的角度進行簡單的批判,他把對權力逼仄人性的痛恨、對底層者遭遇權力后無助不幸的憐憫、對民眾麻木糊涂的哀楚混合一起,在更多的理解中,彰顯了人道主義的情懷。
(四)“理學名區”里的“倫理敘事”
河洛地區成為名副其實的“理學名區”。閻連科家幾里遠之外就是二程的故里,當作家“拿起筆,游蕩于‘耙耬山脈’之間時,寺廟才突然出現在他面前,他仿佛看到寺廟的象征意義和無形的力量,看到了人們對‘程寺’的敬畏和對‘程寺’精神的繼承”。[13]這種潛意識的文化浸染,使閻連科的小說世界呈現出濃厚的理學文化色彩。作品中的父母與子女關系,充溢著“孝親情懷“的人倫風情和“父為子綱”的理學脈絡。《情感獄》中,家中雖困苦不堪,但家人在咀嚼苦難的同時也處處感受著家庭的親情與溫暖。除了“父慈子孝”的人倫溫情,作品中著墨最多的還是“父為子綱”的倫理思想。《日光流年》中,司馬藍的父親司馬笑笑臨終向其囑托“要把這個村長要回司馬家”,父親的志愿和教誨成為他一生的精神支柱。當發現母親與人偷情時,他毫不猶豫地把母親逼跪在父親的墳頭邊。家庭倫理關系的另一重要維度便是夫妻關系,“三從四德”“夫為妻綱”“夫婦有別”等倫理規范在“理學名區”的河洛表現尤甚。閻連科坦承“河南作家普遍對女性的漠視”。“骨子里,女性在河南作家的作品中永遠是他者,是屬從。除了周大新對女性有些溫柔情懷外,別的更多的還是傳統文化觀念在作品中的潛意識。是不自覺的。”“我在寫作中只知道女人是人,而沒有意識到女人是女性。”[14]《黃金洞》中的老大媳婦得知老大和桃兒的奸情時,只微微抱怨一句,就被老大“啪的一下在她的臉上打了一耳光”。《日光流年》中三姓村的男人們奉行的是“就是把媳婦打死也行”地觀點。這也種導致了女性對婚姻家庭的集體無意識。《日光流年》中杜竹翠的一席告白道出了河洛女人們的心甘情愿,“你要是娶了我,我會像磨道里的驢一樣侍奉你一輩子”。在這里,女人的所有作用就是對丈夫的侍奉、對公婆的孝敬,她無權干涉男人的外遇甚至甘心等待被另一個女人取代。
面對在現代都市文明沖擊下變得支離破碎的鄉土人倫,閻連科有著自己“理學名區”般的思考。作家在現代人遭遇精神危機、新的精神構建尚未完成情境下,對慢慢消逝的故土文化會有著本能的關注,尤其是當他真切感受到這種文化對自己的曾經滋養,就更容易對身邊的文化傳統產生認同,而難于進行迅捷的現代反思。這是時代的無奈,也是作家的局限。
(五)老莊世界下的“避世思想”
“耙耬世界”呈現了一個自然、自足、與世隔絕的詩性空間。《日光流年》中的三姓村、《受活》中的受活莊、《風雅頌》中的“詩經古城”,都是座落在耙耬山脈的褶皺里的“化外之地”。《受活》中,作家展示了“宛若天堂”的“至德之世”。受活莊地處深山,水足土肥,人們過著一種散淡無束、殷實富足的天堂日子。閻連科作品還經常閃現出老莊“道法自然”“天地有大美”的自然情懷。無論是“藤、葛、蔓”還是“松、柏、竹”的人名取意還是“花嫂坡”絮言中那到處是花紅和柳綠、到處是草木和芳香的迷人風光,都令人頓生莊子“山林與,皋壤與,使我欣欣然而樂與”[15]的陶醉情懷。“小國寡民”“至德之世”是建立在崇尚自然、反對外界干涉和自我欲念的基礎之上。小說《受活》正是展示了一個宛如天堂的“化外之地”在進入現代人類文明的過程中所遭受到的瓦解。入社之后,受活莊人“天堂般”的日子消失了,相繼遭遇了“鐵災”“大劫年”“黑災”“紅罪”,那蓋著“紅艷艷”公章的要糧條子變成對受活莊人赤裸裸的掠奪與搶劫,縣長柳鷹雀更是在個人政治野心的鼓動之下,將受活人推入到了萬劫不復的地獄。柳鷹雀野心勃勃,留給他的是自己撞向車輪的慘烈以及幡然不及的悔悟。而受活莊的那些殘人們,在經歷了外面世界的種種誘惑之后,心靈還能保持與世無爭的平和嗎?日子已經如平靜的池水被突然攪碎般變得面目全非,而那天堂般的“散日子”注定成為不再復現的夢。
閻連科不斷地表現著他對“外面世界”的探究,思考村人與“外面世界”的關系:三姓村的人付出慘痛代價從“外面世界”引來了靈隱渠的水,卻是臭的;先爺最終放棄遷徙到“外面世界”,決定固守舊土;受活莊里的天堂日子因為“外面世界”的介入一去不復返了。作家試圖從兩千年前的老鄉“老莊”那里找到思考的答案,這種追溯有著鮮明的“復古”意識。閻連科描寫的“避世思想”似乎與前面提到的“權力情結”有些矛盾。但這往往是現代人的生存實際,也是當下的真實語境。
三、河洛文化與閻連科作品的藝術特質
河洛文化影響了作家的文學觀念和審美體驗,經過自己的個人體驗和濾化后,必然使作家文本的表現形式、創作風格和藝術技巧,呈現出一種特別的面貌。
(一)神秘詭異的文章氣韻
河洛文化是以“河圖洛書”和《易》為起源的文化,“河圖洛書”表達了遠古先人們的神靈崇拜、祖宗崇拜、物象崇拜以及生命崇拜的信仰,從一開始就具有濃厚的神圣與神秘色彩。在“河圖洛書”神秘思想的暗示和影響下,這方地域的人們格外注重尊神、敬神,好祭祀,多用巫吏。之后,佛教、讖緯神學相繼在這片土地上產生影響,“業報輪回”“天人感應”的神秘主義潛化為河洛人的潛意識。洛陽為王者之里,北邙山水深土厚的地質構造和背山面河的地理特點使之成為皇陵的首選之地。自古的河洛文人們面對這一片茫茫,無不發出人生莫測的感慨。河洛之地孕育著的種種神秘精神與詭異元素使自古以來的河洛文人不免受其熏染,呈現出奇崛詭異、夸張荒誕的美學特色。李賀的詩充滿著離奇想象和荒誕詭異的氛圍,被譽“詩鬼”。李商隱的《無題》化用神怪典故,復雜奇異。唐代還出現大量的以描寫靈異、鬼怪、神佛的“神怪傳奇”。 陰陽相通,人鬼共存,現實夢魘交織,虛假難辨、亦幻亦真,河洛之地充滿了詭異神秘。
很多研究者談到域外文學尤其是拉美魔幻現實主義對作家的影響,但作家非常注重河洛神秘主義文化因子的作用,他說“我的小說,充滿著無數的民間語言和民間傳說,民間的神秘感都在小說中有體現,而且人家都會說閻連科的小說充滿著不可思議的神秘,那是因為在我的生活中遇到的神秘的事情特別多”。[16]閻連科作品中,千年的古柏常常與古廟和陵墓相伴而生,祖傳三代的老屋被蒙上了一層神秘的色彩。《情感獄》中敘述八十二歲的九爺在隆冬的夜里揮刀砍樹,帶有神秘詭異的氣息,而九爺在樹根砍斷之前倒了下去,也驗證了夢中的讖語。《耙耬山脈》里,死去村長的陰魂整夜坐在村邊墳頭滔滔不絕地講話;《黃金洞》里,已吞金而死的爹指揮二憨背著自己的尸體,擺脫女人桃的追趕;《耙耬天歌》里,尤石頭的陰魂長期陪伴尤四婆,看見三女婿拉走了家里所有的糧食,還會哀哀地哭。《受活》開篇就以“天熱了,下雪了,時光有病了”為題,呈現了“酷夏里下雪”的駭人聽聞的氣候,文中蒙上神秘荒誕的色彩。閻連科以對河洛神秘文化因子的超常感悟力和把握度,挖掘出了民間久違的神秘、奇詭和荒誕,在此基礎上“構筑起的是一個更為成熟的藝術形態:一種以現實經驗為根基的充滿河南鄉土味的‘超現實小說’”。[17]
(二)厚重悲涼的創作風格
《日光流年》前言寫到:“謹以此獻給我賴以存活的人類、世界和土地,并以此作為我終將離開的人類、世界和土地的遺言。”作家沉浸在自己的“苦難”世界中,他的文本里充斥了極端的生死、極端的苦難抗爭,呈現出殘酷、冷硬或者是荒寒的美學追求。
河洛大地多發的苦難促生了此地文學厚重、悲涼的底色。建安年間,河洛文人學士目睹社會動蕩和人間苦難,形成慷慨悲涼的創作風格,構建了“建安風骨”。唐“安史之亂”使詩人們飽受干戈離亂、民不聊生之苦,詩中流露出難以抑制的悲愴情懷。抱著以為“勞苦人”寫作為宗旨的胸懷,閻連科所表達的正是與其血肉相連的那片苦難土地的內心,他說“你是農民,在你的內心深處,你就永遠背負著土地與農民的沉重。你的心靈是由土地構成的,是由泥土和草木建造的。這種沉重是無法擺脫的。”[18]
《丁莊夢》開篇寫到:“莊里的靜,濃烈的靜,絕了聲息。丁莊活著,和死了一樣。”一種由苦難衍生的悲涼感浸入其中。《年月中》中,一個孤獨的老人、一條看不見東西的盲狗、一株隨時可能死去的玉蜀黍、一片荒無人煙的干旱原野,在如此荒涼的背景中,當我們發現玉蜀黍的根須“都如藤條一樣,絲絲連連”“穿過先爺身上的腐肉,扎進了先爺白花花的頭骨、肋骨、腿骨和手骨上”時,頓生一股凄慘悲涼的感覺。《日光流年》中,殘疾的孩娃必須扔到深山活活餓死,瀕死的老村長以自己身體作為烏鴉茍延殘喘的食物。這樣的情節讓人觸目驚心。閻連科以慘烈的、酷厲的、極端的方式描述了河洛大地的故事,文本中充斥了對“勞苦人”悲劇命運的深厚同情和無能無力的痛苦心境。
(三)靈活多變的藝術形式
費正清說過,“中國文化中一直存在著兩個對立的傳統,即‘面海的中國’的‘小傳統’和‘占支配地位的農業——官僚政治腹地’的‘大傳統’。‘小傳統’表現為較先進的‘城市—海上的思想’,‘大傳統’則以‘占統治地位的農業——官僚政治文化的傳統制度的價值觀念’緩慢前行。”[19]河洛自然屬于“占支配地位的農業——官僚政治腹地”的“大傳統”范圍之列,因地跨黃河、淮河、丹江三大流域,境內伊、洛、汝、潁等河穿流而過,河洛長期是全國的交通中心。隋煬帝開鑿大運河之后,洛陽更是一躍成為全國交流最便利的地區之一。水陸交通之利大大促進了商業活動的交流,打破了“大傳統”的封閉性,外面世界的融通新潮、勇于創新的“小傳統”融入其中。諸多文化交匯、碰撞,使河洛文化更具包容、凝聚的胸懷,也增強了河洛人對外來文化藝術的認同感、理解力以及自身的創新力。
閻連科一直尋求寫作上的創新和超越。他說過:“新的小說生命元素,才是作品和作家的生命力”“沒有新的小說生命元素,你的小說就只能死亡”“一部小說的價值就在于它的差異性”“當你在這個地方已經成熟之后,你必須要離開它,必須脫離它,否則,你就會落進陷阱里面。成熟最終意味著衰敗,你必須尋找一條新的創作道路”。[20] 他的創新體現在方方面面。在語言上,作家追求讀者不能一開始就輕易辨出是他的小說。因此,他避免用《日光流年》的語言去寫《堅硬如水》,不愿重復“瑤溝人的夢”那樣的敘述風格。寫《情感獄》,他的語言是質樸的細膩的,有種不動聲色的溫情在流動;到了《年月日》《日光流年》,他開始注重語言的陌生化審美,在文本中經常加入奇怪、荒誕式的描摹式語言,比喻、通感等修辭手法比比皆是,語言風格是艱澀、凝重和詩意的;《堅硬如水》幾乎是革命語言的顛狂,革命對聯、語錄歌、樣板戲、政治演講、政治豪言充斥其中,呈現一種汪洋、泛濫的語言姿態;《受活》全部用河南方言寫作,甚至需要不斷地注解才能使人看懂。一路走來,閻連科的語言風格可謂一變再變,不斷激起人們的驚奇感。在文體上,閻連科是一位“文體自覺”的作家。作家曾經談到,“創作上的困難不是故事的問題;故事總有寫不完的故事;最怕的是你找不到一個新的方式去表達它。”[21]他不斷地進行著文體方面的大膽嘗試,于是我們看到了《年月日》中的“寓言體”,《日光流年》的“索源體”,看到了《受活》中正文和絮言的相互補充,《丁莊夢》中夢境與現實交織一起的敘述,看到了《堅硬如水》的“革命敘述”,《風雅頌》的“詩經敘事”。正是這種開放的寫作姿態,使得閻連科的小說能夠取精去糟,博采眾長,創造出屬于自己的獨特世界。
現代化進程日益加快,使得中國作家可能無意中忽略本土的文化和文學經驗,在創作中迷失自我。優秀的作家善于在滋養自己的故土中尋找自信和靈感,構建自己的精神高地和藝術世界。莫言做到了這一點,閻連科也做到了這一點。
注釋:
[1] 閻連科、姚曉雷:《寫作是因為對生活的厭惡與恐懼》,《當代作家評論》2004年第二期。
[2] 朱紹侯:《河洛文化與河洛人、客家人》,《文史知識》1994年第三期。
[3] (法)丹納:《藝術哲學》(傅雷譯)第255-256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86年。
[4] 閻連科、梁鴻:《巫婆的紅筷子》第47頁,春風文藝出版社,2002年。
[5] 韓養民、韓小晶:《中國風俗文化導論》第7頁,山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
[6] 楊海中:《圖說河洛文化》第352頁, 河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
[7] 閻連科:《褐色桎梏》第4頁, 百花文藝出版社,1999年。
[8] 閻連科:《受活》第35頁,春風文藝出版社,2004年。
[9] 閻連科:《丁莊夢》第11頁,上海文藝出版社,2006年。
[10] 陶瀾:《閻連科:方言是種挑戰姿態》,《北京青年報》2004年第四期。
[11] 閻連科、梁鴻:《巫婆的紅筷子》第31、63頁,春風文藝出版社,2002年。
[12] 石一龍:《我的小說是我個人的良知——閻連科訪談》,《人大復印資料(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2002年第三期。
[13] 郜元寶:《論閻連科的“世界”》,《 文學評論》2001年第一期。
[14] 閻連科、梁鴻:《巫婆的紅筷子》第1頁,春風文藝出版社,2002年。
[15] 閻連科、梁鴻:《巫婆的紅筷子》第124頁,春風文藝出版社,2002年。
[16] 韓維志:《莊子》第60頁, 吉林文史出版社,2004年。
[17] 韓維志:《莊子》第126頁, 吉林文史出版社,2004年。
[18] 程光煒:《閻連科與超現實主義——我讀<日光流年><堅硬如水>和<受活>》,《當代作家評論》2007年第五期。
[19] 秦方奇:《地域人文傳統與伏牛山文化圈新文學作家群的建構(上篇)》,《平頂山學院學報》2010年第六期。
[20] 閻連科、梁鴻:《巫婆的紅筷子》第21、47-49頁,春風文藝出版社,2002年。
[21] 閻連科、姚曉雷:《寫作是因為對生活的厭惡與恐懼》,《當代作家評論》2004年第二期。
責任編輯 陳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