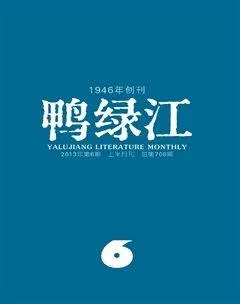站在碼頭上
熊西平,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中國教育學會會員。在《中國作家》《安徽文學》《散文百家》等上百家報刊發表散文隨筆百萬字,出版散文集《金銀花》《根親》《心靈時空》等。曾獲《光明日報》征文一等獎、中國當代散文獎、大眾散文獎等獎項。
1
為等幾個影子,我站在碼頭上。
初夏了,雷聲讓人等得心焦。雷聲響了,那一河渾黃的水就到了。我等著那河晃晃蕩蕩的水。
葉家集在皖西,隔史河望著豫東南。它是皖省的一個跳板,一個堡壘,一個窗口。過去的歲月里,它因是一個碼頭而不同尋常。
史河從這里轉了一個溫柔迂回的彎兒,留下母豬肚兒一樣肥厚的河灘。魚鱗般向遠方推去的清沙河嶺,濕漉漉泥油油的,插根枯枝就能成林。向下游看去,一百里的順水,直達淮河。回首向南,巍巍大別山正架著起伏的屏風。這座江淮分水嶺,是無盡的寶藏。山木、園竹、木炭、板栗、茶葉……下山后找到了歇腳轉運的地方;北鄉的豆類、紅薯、小豬和黃牛,到這里止了步。北貨、南貨,打起旋渦,形成了各自或大或小的市場。葉家集天空的小雨淋漓著中原粗獷漢子的高聲大語和山民委婉急速的討價還價聲,變化多端的手語成交了笆斗和竹筐里的生意。南大街和北大街的行商坐賈,急急如同流水。
一條渡船撐開兩岸,縫合兩省,把客貨的豫東南和華東擺來擺去。
我站在碼頭上的時候,葉家集已三百多歲,每級臺階都長滿盔甲般的苔蘚。
2
葉家集的老北街南北向,離渡口一箭之遙,木柱,白墻,低調的灰磚灰瓦,高翹著的馬頭墻,濃濃的徽派氣息,孤寂地存在著。百年前,滿街流動著長袍馬褂圓頂帽與一團和氣的臉——成功生意人的臉譜化笑容。臺家韋家李家在求富之后的滿足里感到被讀書升官的愿望不安地推動著。這寶壓在孩子肩上,讓他們將來展現家族更為宏闊的前景。孩子們果真在期許中,人生走得很遠很高很燦爛,遺憾的是他們飛翔在另一片天空里。那些馱載著父輩沉重而模糊意愿的孩子,有四人成了中國現代文學史赫然有名的人物,即和魯迅結成“未名社”的四個主要成員:臺靜農,李霽野,韋叢蕪,韋素園。他們來自這條小街,史稱“未名四杰”。
當年四個年齡相仿的孩子從鎮上的明強小學起步。小學還在,可供觀瞻的百年房舍在1990年的洪水中倒掉,所幸前一年我去拜謁過。
像許多老牌學校一樣,明強小學蜷在雞腸巷子深處,高大的香樟樹下,一排古舊的起脊老屋,越發顯得面目灰暗,瑟瑟縮縮。剝蝕殘缺的磚混墻面,掛著一行一行的泥淚,唯對面陪著新起的一排紅色磚瓦教室表明學校還在延續文明。陪同的張校長眉眼憨實,有點無奈地說,只是外地不時有人熱心地憑吊,本地無人問津。不曾想,無情總是說來就來,第二年一場洪水清理走了葉家集鎮百年來最具價值的物件。
回顧“四杰”讀書的歲月,張校長眼睛放光,仿佛被隔著時光的松明子火照亮。他說,那時學風很濃,鎮區的孩子也多寄宿。夜晚,映著松明子的小臉春花般明艷。老師大都是剛剛接受新文化的年輕人,以他們燃燒的心點燃孩子們純凈的靈魂。充滿向往的孩子總是很用功,四個孩子都成績優異。渴望理想的眼睛總在尋找火炬,他們最后在北平相聚在魯迅未名社的大纛之下,成了未名社的干將。四個青年作家,不僅創作,經魯迅策劃還翻譯大量的蘇聯文學作品。在創作、翻譯領域,他們各有獨到的貢獻。在魯迅組織的文學團體中,他們各有獨特的地位。臺靜農、李霽野在百年新文化陣營里,都卓爾不群。
歷史不只是存在于時光的記憶里,應該鮮活在現實中。當我們走出張校長的視野時,渾身被繁茂的商業氣息包裹,一陣陣發緊。
站在街道發一會兒呆,辨一下色彩,辨一下方向。這“皖西門戶”、省級開發區、國家綜合改革試點鎮,宏闊大氣,街如通衢,流淌著炫目的光影。周邊廠區如“郭”,它的“現代”已經“化”到你目光所及的地方。不知怎的,忽然思緒又回放到那條老街和那所踅在雞腸巷里的小學去。
3
去年“五一”,連著幾個晴好的日子。朋友相約去葉家集,和當地的朋友約定鎮區廣場西南角上碰面。廣場很氣派,四周香樟蔥蘢,隔出若干個功能區。廣場告知我們,在這里它不只是一個鎮。朋友問,知道叫什么名字嗎?接著自答。
“未名廣場?”不由心里一驚,吁了口氣。
朋友解釋:“也可以這樣叫。諧音‘為民廣場’。”
哦,復又把氣嘆回去,沒了莫名的激動。看遍廣場,沒有名字鐫刻,就這樣在諧音里叫來叫去。
雖是五月剛一露頭,天氣卻異常熱。香樟樹下議定,先參觀,后喝水。我們徑直去拜謁臺靜農紀念館。
紀念館五間房子,紅磚紅瓦,筒瓦覆脊,多年前常見的農居格局,絲毫未見匠心,總體感覺有點粗糙。門向西開。院里院外各有幾棵新置的松柏,單薄,烘托不出紀念館應有的氛圍。館內很豐富,墻面布滿了各種寫真宣傳品,幾乎都是從臺灣輸來的。參觀了一遍,甚是驚詫。
“未名社”詞條顯示,臺靜農是未名社的重要成員,小說家,與魯迅無關的就不得而知了。魯迅之后的臺靜農在文學史、文化史上一片空白,仿佛夭折的不是韋氏兄弟。魯迅之后的大學教授臺靜農活在臺灣,以名流學者的身份顯赫在那個島上。臺靜農善書法,撲面的學人氣、才人氣,矜持、雋美,浸入骨髓。他的書法扇面和尺牘,一派云淡風清的雅致。臺先生的寫意花鳥也非同凡俗。心追神摹之際,不禁想,我們的一部六十年的中國書法史、美術史太殘缺了。
看臺靜農的葬禮規格,恍然得知他在臺灣影響之大。他去世之后,臺灣所有的上層達官名流,都送了挽幛,評價如五岳巍巍,尊崇似楓滿三山,讓我們深感意外。
出得大門是一面水泥墻,兩米上下高,五六米長,邊上貼著瓷磚,琉璃瓦蓋頂。覺得這琉璃瓦放錯了地方。細看,竟是一面功德墻,一路一行地刻寫著為建設臺靜農紀念館捐資的人名和款數,多的幾千元,少的百十元,幾乎清一色的臺姓自家人。
館長臺建球是位醉心文藝的老人,早年有創作,收集整理出版有《大別山民歌集》《臺靜農書法集》等。他很熱心于臺靜農在本土的宣傳,一邊給我們介紹臺靜農,一邊感慨,覺得工作沒做好,力不從心。看了那面功德墻,看著臺館長惆悵的臉,覺得一個七十多歲的老人把宣傳臺靜農看成葉家集鎮臺氏家族的事情,以家族之力亮出巴掌大的窗口,讓人欽佩。而不明白葉家集鎮,怎么也把介紹臺靜農當成是葉家集鎮臺氏自家的事情去對待呢?
揮手告別農家院落一樣的臺靜農紀念館,臺建球光光的頭頂正在太陽底下流汗,他揮手抹了一把。
4
沒想到雨真的落了下來,濕了躺在道旁的楊樹葉,濕了十月底的茅草,濕了塵土,泥路很快濕滑難行。
五個月以后,相約三五人,再次行走在葉家集鎮的土地上,去拜謁李霽野墓。1949年以后,李霽野在天津從教,后任職天津文化局局長、文聯主席、全國政協常委,是個高官。據說,在他晚年,故舊勸他百年之后回故鄉安息,他沉吟之后說,看中了葉家集北郊丘陵上的一塊地,如有可能,就和妻子一起躺在故鄉的厚土里吧。若干年以后,那片茅草有幸覆蓋了一位顯赫的現代文化名人,很快有很邪乎的傳聞:李霽野的墳堆在一年一年長大,墳前的平臺比過去開闊多了。
作為文學追求者,我們想圍著墳地走一圈。
雨絲毫沒有歇息的意思。車子在濕滑的鄉村公路上搖擺,我們開始棄車步行。雨霧如幕,撲在臉上濕冷。滿地茅草枯黃,退耕還林名義下的楊樹一副死頭孱腦相。朋友說他來過,翻過嶺子就到了。
四處傳來地動山搖的轟鳴,嶺子仿佛一頂轎子,隨時會被抬走。爬上嶺子,心里為之驚怵:目光所及范圍內大小起伏的丘丘陵陵都被推成了一片黃土,這里那里數不清的推土機在雨霧里螞蟻搬家似的蠕蠕而動,只有幾口盛水的池塘靜靜地、無奈地等待著討價還價后命運的歸宿。哪里是溝?哪里是嶺?哪里是那片據說有好風水的李霽野墓地?朋友一再擦拭眼睛,想擦去雨簾,還是想擦去蒙塵的記憶?他搖搖頭苦笑了。
四下里留有些沒鏟平的星星點點,我們幾個人約好分頭去找,找到了打個電話,搖手為號。我往偏東北的方向走。綠瑩瑩的水塘邊有簡易房子,鴨子在水面上縮著脖子浮著。一條狗為我和屋內的主人接上信號。那人搓著臉難為情地苦笑,說沒聽說這個人,沒聽說過這個墓。跨過一道正壘砌的矮墻,我攔住了一輛正推土的拖拉機。司機告訴我,他是外地人,不知道什么野,也沒聽說挖了什么名人的墓。也許在那地方?他隨手一指更前面的地方。浸濕了的黃膠泥讓我兩腳變成了泥坨子,我舉步維艱,大汗淋漓。沿著車道走走問問,再四下里望望同伴的方向,都毫無消息。
一個指揮部模樣的房子矗立眼前,門前掛一塊某某廠籌建指揮部的牌子。幾個年輕人都搖頭,說領導不在,他們不知情。
我猶豫了,朋友搞錯了位置?我撥通電話,他信誓旦旦地保證說沒錯,就在這地方。兩個多小時過去了,我們無功而返,信心還在,可都搖頭嘆氣。
事前遷走了?
晚上,我們喝著啤酒姜湯驅寒的時候,仍在互相詢問著對方的眼睛。
5
已是春末,史河的水還是淺淺地流,仿佛流水就是為了流,沒有了放排的使命,沒有了連綴兩岸的渡船,插秧用水還早了些。流動,是為了防止不流動,這狀態好像是為了靜靜等待什么而特意設置,也好像在淺淺地思想著。
我站在橋頭,心里像那淺淺的流水思想著,思想著農家大院一樣的臺靜農紀念館、隆隆的機器聲中迷失的李霽野墓地和那收藏著孩子們歡笑在洪水中倒掉的民強小學老校舍。是橋的暢通廢棄了碼頭,還是碼頭與橋都應該成為城市的肋骨?交易的繁忙,會讓碼頭變成集鎮;思考的繁忙,才能讓碼頭變成城市。城市有無限的容量,會收藏起發展過程中的每一張名片,哪怕是一些文明碎片。累積產生高度,即使帶銹跡的光斑也會增添它的鱗亮。一個剛登上碼頭的集鎮,來不及思考,奔跑中,一路追逐一路丟棄。
碼頭邊上,我會撿拾到一些貴重的東西,等待河水滿了的時候,有人來尋找。
責任編輯 葉雪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