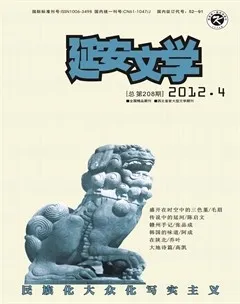盛開在時空中的三色堇
黃延安
閱歷是一筆不滅的財富,它會把時間之河分出上游和下游來,并在前后之間,為你提供一個跨時空的參照,就像我曾在八十年代末來過延安,它正在為我今天的回訪提供著對照的刻度。
那時的延安,是一個渾黃的整體:黃土,黃沙,黃山,黃色的寶塔,街道上,行走著落滿塵土的黃色衣裳,民歌里,唱的是土里刨食的艱辛……延安,讓“華夏文明”、“炎黃子孫”這樣的大課題直接落在了大地上。
它擁有的黃河,是中國文明的主干,配以雷鳴般的壺口瀑布,攜泥帶沙,鋪天蓋地,唱出中華民族的抗戰之聲;
黃河兩岸,那些溝壑縱橫、峁梁相間的黃土高原上,躬耕的農耕文明,綿延出一個中華民族;
人文初祖軒轅黃帝,被黃皮膚的子民,一代代膜拜……
這里的居民不是一支漂流而至的移民,而是徹底的土著,從黃土里面長出來的莊稼般的土著。這不是一片生土,而是祖祖輩輩的體溫捂暖了的熟土,熱土。他們活著耕耘,死了埋骨,生死相許。
所以,中國人沒有猶太人的漂流感,追逐感,無根感。而只有“村橋原樹似吾鄉”的家園感。
身處黃土高原,讓人格外有一種“位置感”。那是中華民族的“位置感”,農耕文化的“位置感”。正是黃土高原,決定了我們在這個世界上獨一無二的生存方式。如果沒有這個地理上的支撐點,我們便無法擁有精神上的支撐點。就像毛澤東初到陜北時說的:這里,既是我們的落腳點,又是我們的出發地。
愛默生認為自然是精神的象征和人生的課堂。我們得在這片黃土上,認識我們出生的自然,并將自然與人的融合當做經久不衰的主題。
如果把大地比作母親,黃土高原是母親脂肪最厚的地方。似乎,走進每座窯洞,都能扶出一位顫巍巍的老祖母,給我們講黃土摶人的故事:華夏民族在這里被黃土摶人,然后,再循著那幾條固定的移民路線,入川,入滇,入關東,顛沛流離到四面八方,綿延成一支中華民族。
在黃土高原,人的存在模式,蘊涵著某種道德行為的模式。他們的一戶窯洞,就占據了一座山,那窯洞怎么會走風漏氣,怎么會不冬暖夏涼呢?在那里住久了,走出窯洞的人,厚道得像山。
路上,不時會看見那些在窯洞前曬太陽的老農,他們隨便抓一把面前的黃土,曬著太陽,久了,太陽曬久了,黃土捏久了,會捏成一個土豆,在炭火中烤熟,圍定一家血親。他們在黃土里刨出土豆,刨出小米,刨出那些由黃土轉化而成的糧食。
他們對農耕真理的接受非常直接:種瓜得瓜,種豆得豆;對大自然的真理認識得也非常直接,用民歌直吼吼地就捅了出來:東方那個紅,太陽那個升……
紅延安
每每看地圖,都會陷入癡想:那么多的地名,讓人一生都走不到,那么多藏在地名后的深情故事,自己都無緣參與……我就這樣馬不停蹄地走過了許多城市,許多地區,在短促的生涯里,去經歷所能經歷的一切,每個城鎮都對我充滿魔力。這樣走得多了,比較就出來了,總結也就出來了,我發現,每個城市,總會在千百年來它自身文化和歷史最為輝煌的那個高度上,停下來,停在它最高的那個刻度上,張望來者……
無疑,延安選擇的是一個紅色的高度,它在這個高度上,將那個年代無形的文化、無形的情結,來了一種無形的集中,凝固,定型。在這個刻度上,你能夠感到,這座城市對自身的使命全力加以傳承,不遺余力……
是的,每個地方都有它在歷史長河中的一個高光點。延安的高光點是紅色,當別的地方都在努力提升自己的知名度時,延安會以寶塔的形式,佇立在每個國人心中。那時候,“黃河之濱,集合著一群中華民族優秀的子孫”,全國的熱血青年飛蛾撲火般,沖破重重封鎖,奔赴紅區,毛澤東在窯洞中,點著煤油燈,吃著小米飯,穿著粗布衣,十三個春秋,在土窯洞里懷世界、觀天下,將黃延安扭轉基調,成為燃燒一切落后與殘渣的紅延安。
當我在紀念館里看到一支步槍交叉地掛著一袋小米時,覺得這個意向最堪比喻:在這片帶電的紅色土地上,每一粒小米都撒豆成兵……
《延安文學》的主編魏建國先生,是位典型的陜北漢子。聽他短短的幾句話就知道,這個陜北漢子的心是熱的,血是熱的。他將剛剛出版的一套《延安文學200期作品選》擺在桌上,說:“出這套不賺錢的書,是與市場效益逆風而動。但人生短暫,總得干點什么,留點什么。光是享受,能有多大意思?”他代表著今天的延安人,做著有關那個時代的薪傳。這里,依然是一片精神的土地。
所謂歷史,無不鑲嵌在時間的鏈條上,如果我們把自我的生命補色其上,對于個體生命來說,實在是一件幸事。
我們探討著延安的紅色。如果說,紅色瑞金是一個剛剛出生的嬰兒,目的是生存的話,到了延安階段,那個嬰兒已長大成人,開始了孕育真理的階段。這種孕育會讓人格外猶疑,不能邁錯一步,方向在哪,出口在哪,亮光在哪?一旦選定了方向,剩下的就是指日可待的勝利突圍了。
綠延安
我因為熱愛綠色,故而熱愛云彩。曾看到人們瘋狂地砍伐樹木時,無奈地想,幸虧,他們不能把云彩砍下來。其實,只有地上的樹多了,綠多了,才能留得住天上的云彩,云彩多了,才終有一塊云彩會下雨,所謂良性循環,是一種天地的對應。
如果說,黃延安是民俗的,生活的,紅延安是革命的,時代的,那么,綠延安則是生態的,人類學的。
延安是黃河上中游水土流失最嚴重的地區之一,自從國家做出退耕還林的決策后,深受水土流失之苦的延安,率先搶抓機遇,經過10年的努力,成為“全國退耕還林第一市”。所以,2012年5月,重返延安,前來紅色采風的我,看到的卻是一個綠無間隙的延安。
我慶幸多年前的那次延安行,讓我此行變成真正意義上的回訪。當我看到滿目皆綠時,得在恍惚中平定一下詫異,在與記憶對比中自問:你確定?確定所有的山頭都是綠的?于是,在參觀一些著名的紅色景點時,我總是走神地極目遠山,尋找答案:為什么山坡能夠變綠?不上山砍伐的人們燒什么?不上山放牧的羊兒吃什么?不上山耕地的農民吃什么?
我得到了許多自豪的回答:十年前延安的群山,是一籠蒸熟的窩窩頭,黃禿禿、光溜溜的。現在,你看,全綠了。
望著漫山遍野的綠,我疑疑惑惑地問,那么大的面積,是怎么播種的?
有的是人工種的,有的是飛機撒的。要是你看遙感地圖,延安的綠一年比一年深呢。
正因為這一年深比一年的綠,吳起縣的楊青流域還出現了壯觀的云海。
哦,這就是地上的樹,與天上云彩的對應關系!
這十多來年,我們幾乎犧牲掉了一個產業。延安羊子的存欄數由1999年的近300萬只降至30萬只。曾經的牧羊人轉而開始棚栽業、林果業、畜禽養殖業,搞第三產業。
我問,燒的問題怎么解決?
他們一口氣地回答:劃出自留柴山,提倡燒煤,推廣液化氣、天然氣、沼氣池……
沒有人上山砍柴,沒有羊上山啃食,沒有了人為的破壞,大自然在靜悄悄地自我修復。十年的時間滿目蒼翠,山的陽面是連片的蘋果園,山的背面、側面是退耕還林地,滿山的松、柏、槐已經成林。
路邊的農民們說:“政策好得很,只要你種樹,自家的門前,自家的墓前,都是免費的樹苗”。
我想,政策初下時,肯定有違規的現象頻頻發生,它不可能一刀切那么整齊。果然,因為羊肉價格的提高,野外放牧時有發生。我聽到曾經下派到這里的陜西省作協王曉渭先生關于八只羊的故事:
早晨我還沒起床,只見窗戶紙上人影攢動,開門一看,坐了一院子的農民,一對夫妻哭哭嚷嚷的。咋回事?原來,村長在望遠鏡里發現山坡上有七只羊,就帶著村干部上山抓羊去了。按規定,抓回來的羊就地宰殺。所以,兩口子又哭又鬧。但政令山大,沒辦法,商量到最后,結果是,留了一只種羊,留了懷羔的母羊,其他的就都宰殺了。
“賣了羊肉的錢呢?”
“當然是給人家戶主,就這,他也損失大啊。”
就是這樣一件件的實例,教會了農民不再放羊上山,而是圈養在家。
“那羊吃什么?”
“人可以上山割草呀,但羊會把草根都給毀掉。”
“后來呢?”
“后來?那家的女人說,他們家是八只羊。村長只好帶著全村的干部上山,找羊去。”
還有一個以糧代賑的故事:
根據退耕還林的政策,村里要把荒山荒嶺分到戶,來進行綠化。一開始,這些荒山荒嶺分不出去,農民不肯多認領。最后,實在分不出去的,村長全部認領了。到年底,開始按山林的畝數發放面粉,有些農民一個板車只拉回一袋面粉,而村長家卻拉了整整兩卡車。村長腰壯了:狗日的,當初就是個不要,不要,現在眼紅了?
第二年,所有的荒山荒嶺嘩啦一下,全部分了出去。
這兩個故事,穿起來了一條政令的兩個階段:政令初下,與政策落實。
我們看見的,是一座座山坡變綠了,看不見的是多少個這樣的故事,這樣的村長。
大面積退耕還林,讓農民背水一戰,集中精力在果業、養蜂等生態致富項目上。我在一路上,都會不斷發現路邊的養蜂人。
你很難想象,光禿禿的黃土高原會山上掛果,山下養蜂?這片貧瘠而流失的土地一下子變得甜蜜起來。
看著滿山的綠,我想起三北防護林的失敗。因為樹種單一,缺乏天敵,爆發了天牛,致使大片好不容易成活的林木慘遭破壞,令人痛心。所以我疑惑地問,“飛播的樹種單一嗎?”
這個問題一開始的確存在:初期,群眾多選擇那些易成活、成本低、成林快的刺槐、沙棘,所以一度形成了大面積刺槐、沙棘純林,埋下了生態隱患。近年來,意識到問題的延安市退耕辦下大力氣,確立了鄉土樹種的主體地位,實行了混交林,其中的常青樹比例達到20%以上,并且要求各縣區加快刺槐、沙棘純林的調整步伐,增加多樣性,優化林種的結構。
像紅色革命摸索著前進一樣,綠色革命也一樣摸索著前進。
西方生態作家提出人類與自然和諧發展的新模式:對立——妥協——平衡。這些,在延安都已達成。
我們在子長縣看到,綠起來的農村青磚灰瓦,小院人家,窯洞成排,整齊的行道樹,寬敞的水泥路,灰瓦藍墻的農家小院,各家各戶都用上了自來水和沼氣能源……在這樣的村莊里,有一些關于秩序、寧靜、樸素,以及深入人心的原則,它淳厚的習俗,一切似乎都是要執拗地發展那種習以為慣的悠久、和平的農耕生活。他們以新的農業生態體系,建構起了新的環境模式,從而帶來了社會關系的重組與自然的重組。
十年的時間,“一任接著一任干,一張藍圖繪到底”,這滿山皆綠的政績,豈是幾座立竿見影的市政建設工程可以堪比。
以綠色為政績的考核,比起任何指標更加福澤萬代,鋪在地上的綠色政績,扎根在人心的大樹,會越長越高,越長越壯。
延安人告訴我說,以前光禿禿的山頭蓄不住水,一下雨就發山洪。現在,我們不怕了。
昔日陡坡耕種、過牧濫牧、砍柴燒火、廣種薄收、“下一場大雨褪一層皮,發一回山水滿溝泥”、“越窮越墾、越墾越荒、越荒越窮”。是退耕還林的政策,徹底改變了黃土高坡的基調。
在資源枯竭、酸雨肆虐、水土流失、淡水缺乏、沙漠擴張、全球變暖、物種急劇減少、有害化學物質導致物種突變、生態嚴重失衡的今天,延河干了,黃河斷流了,壺口用上橡膠壩了。惟其如此,我們才一再深情地回望延安的綠色。但愿山坡上的每一株樹,樹上的每一片葉子,都生發出一顆晶亮的露珠。這些露珠大珠小珠落玉盤,落進山腳下的延河,還延安一條滾滾的延河,還中華一條咆哮的黃河。
從這個意義上說,延安的綠色,不僅僅是一種生態的出路,而且會讓我們去尋求一種文化與精神的出路。因為,生態,終究是人類最為基礎的大地,最為崇高的形態。
留住黃土,我們豐腴的母親,留住根。
如果說,那個黃延安是民俗的中國,貧苦的中國,是質樸的、手工的;如果說,那個紅色的延安從最為貧苦中生發出了革命的種子,讓這塊黃土地的歷史變成紅色,那么,今天的綠延安則是生態的、人類學的。綠延安是對黃延安的反哺與唱諾,是對紅延安的敬意表達。把那些埋有忠骨的黃土地扮綠,難道不是對先烈最好的敬意嗎?
延安不僅是紅色的樣本,也是綠色的樣本。
并不是每個城市都有能力為自己設置新的刻度,尤其是在負載了重大歷史之后。但延安,走出黃色的貧困,走出紅色的歷史,走在了生態的前沿,走進了今天真實的綠樹濃蔭。
我的思想從低處不斷升高,從黃色轉向紅色,從紅色轉向綠色,轉向自然界,轉向事物普遍的體系。
在中國的方塊字中,“茶”字,上草下木,人居草木間。我們怎么離得開草木呢?他們對黃土高原的熱愛,就是對自己家園的熱愛,就是對整個地球的熱愛。或許你一生都不會去一趟延安,但也得對延安的綠色心存感激。因為,我們需要綠色。所以,我能夠掂量延安每一片綠葉的價值。
與光禿禿的貧困相比,我們一定會選擇今天的綠色,選擇綠色大地上“詩意地棲居”。
三色堇
從黃延安,到紅延安,到綠延安,我心目中的三色延安,像一朵盛開在時空中的三色堇,悄悄地打開了它的容顏。
三色堇最初不是三色,而是單純的白色。天使來到人間時,親吻了它三次,天使的容顏就印在花瓣上,變成了三色,所以,每個見到三色堇的人,都會得到幸福。
三色堇的花語是:請思念我。
我會思念延安,目送延安,從淺綠,一棵一棵,走向深綠。
責任編輯:魏建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