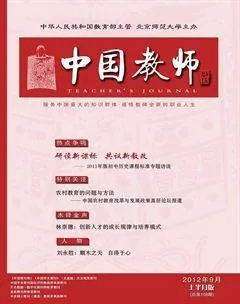語文教材怎么編
2012-12-29 00:00:00於俊杰
中國教師 2012年17期


當談到現在語文課程改革中討論很熱烈的話題時,我們很容易想到古文與現代文的教學、語文學科“工具性”與“人文性”的離合等問題,而這些問題在實踐中很大程度依靠的是語文教材的編選。不過,這些問題并非當代才有,70年前在西南聯大師范學院與文學院合辦的《國文月刊》上,相關學者已經就這些問題做出了積極并具有相當深度的討論,只不過“說法”略有不同。那時也像現在一樣普遍面臨“中學生國文程度低落”的困境。因此他們的討論和思考就彌足珍貴。
《國文月刊》是20世紀40年代西南聯大文學院與師范學院合辦的一份雜志,主要刊載國文教育方面的論文,留存有國文(語文)教育觀念變遷的珍貴資料,是當時持續時間最長、水平最高、影響最大的國文教育期刊。其中朱自清、葉圣陶、浦江清、余冠英等主辦者均參與了教材問題的大討論。討論和爭議的中心是選擇什么語體、體裁、性質的文章作為中學生學習語文的最佳材料。本文試圖從歷史論爭的角度剖析當下的問題,以期為現時語文“課改”提供一些有益的思考。
一、文言還是白話?
談到語文教學(那個時代叫“國文”教學),文言與白話是基礎性、前提性的問題,對它的質疑和探索便首當其沖。雖然在20世紀20年代中國就掀起了廣泛的白話文運動,雖然1920年教育部就正式宣布普通小學須使用白話文教學,但直到40年代,中學語文課仍舊以古典文言為主,正如浦江清先生說的:“小學教育單訓練語體,所以問題簡單,到中學的國文方始迎著復雜的問題。在課本方面,現在初中課本文言語體夾雜著,顯得很不調和。高中課本差不多全是古文,色彩是純粹了,但多數學生是作語體文的,所以課本與作文就脫離了關系”。[1]正如大多討論者所言,學生課上學的是經典的古文,課下看的是白話的文藝,社會上需要的卻是簡潔的“民國文言”——這教與學的分離就成為當時最受關注的重要問題。那么,什么是“民國文言”呢?
葉圣陶曾說,當時的“文言”已經“不該是唐宋的文學,六朝的文學,漢魏的文學,甚至先秦的文學,而該是應用文言字匯,文言調子,條理上情趣上和語體相差不遠的近代文言”“如梁啟超先生蔡元培先生寫的那些”——他稱其為“民國文言”。[2]實際上,最有趣的是,我們如果翻閱當時諸君討論白話文的書信,會驚訝地發現他們使用的竟都是文言。翻閱從五四時期直到40年代的新聞報紙,我們也會發現很多消息都是以半文半白的形式寫出。“民國文言”意味著社會需要。針對這種社會現狀和對語文工具性的要求,語文教材就不光是文言或白話的問題,而是具體到選什么文言的問題。當時很多學者反對通行教材編選過多上古文字的做法,認為這樣不僅不利于傳播文化,還妨礙了語文的社會實用。例如浦江清先生就說:“教本深不足以提高學生的程度,反而可以減低學生的趣味。”[3]多數人認為語文教材應該著重編選近人的、更易懂能用的文言。這不僅反映出當時國文名家對國文教學的關注和思考,同樣也反映出在那個時代,普通中學生難以掌握當時的國文教材,國文水平普遍“低落”的歷史現實。
當時學者們也在刊物上對中學生國文低落現象進行了更深層的分析,正如朱自清所言:“這并不是說現在學生的國文程度低落到不成樣子的地步了,像一些感嘆家所想的那樣;而是說現在學生能夠看書,能夠作文,都是他們自己在暗中摸索,漸漸達到的;他們沒有從國文課程上得到多少幫助。”[4]有識之士便開始重新編選教材。葉圣陶在《國文月刊》同一時期,與朱自清、周予同、呂叔湘、郭紹虞、覃必陶等,嘗試改革,把文言文課本與白話文課本分開,編出了《開明新編國文讀本》《開明新編高級國文讀本》《開明文言讀本》等教材。這是“在文白混編混教占據主流位置二十余年后”進行的大膽嘗試。①與20年代的你死我活不同,40年代后文言和白話在國文教學這一點已經統一到人才培養的大目標上,也統一到國民塑造和文化更新的更宏遠的目標上了。
二、文學還是非文學?
在教材編選上,文學作品作為語文教學92557ad71606a084a75c48b37c6d123d0a270b7ae14042cd735a9a5df161d4cb中特殊的組分一直備受關注,選什么樣性質的文章,選什么類型的文章也一直成為爭議的話題。《國文月刊》從語文教學“工具性”與“人文性”離合的角度對此曾有一次比較大規模的論爭。論爭雙方分別是希望“中學國文應以文藝性的語體文為主要教材”的李廣田和重視學術文章的張清常以及看重應用文的阮真。張的文章是發表在《國文月刊》18期的《對于坊間中學教科書所選“學術文”教材之商榷》,阮的著作主要是《中學國文教學法》一書。論爭中李廣田的特殊性在于,他既反對教材中編入大量學術論文和應用文,同時也對當時“人文性”要求中關于文化傳承的要求表示排斥。
李廣田在1944年11月的《國文月刊》28—30合期上登出了他的首篇討論國文教育的文章:《中學國文程度低落的原因及其補救辦法》,直到1945年4月的34期,他的長篇系列文章才告結束。在這一組文章里,他系統、全面地論述了國文教育教材編制的相關問題,并與之前同期刊的文章以及社會上較有影響的相關論著進行對話。②這一部分我認為是《國文月刊》上最有體系同時也是“最大規模”的爭論之一,因為它不僅形成了直接的、針鋒相對的局面,同時還涵蓋了當時國文教育領域幾乎所有的問題。在談到部頒中學生課程標準中關于文化傳承的一條時,他直接指出:“中學生是不是應當了解‘固有文化’,‘固有文化’是什么西東(注:疑為“東西”),應當如何了解法,現在的中學生是否有力量接受這些東西,接受之后會發生什么效果……這都是很嚴重的問題。只就國文教學的目的而論,也就是只就國文一科的責任而論,我們覺得這被教育當局和一幫國學大師們死咬住不放的‘固有文化’云云,實在并非國文一科的事情。”③
顯然,國文科的確有責任傳承固有文化,弘揚民族精華,但是用什么材料來達到這個目的一直頗具爭議,文學性質的作品與非文學的文章成為其中主要的兩類。葉圣陶曾將教材中文學的與非文學的文化因素進行對比,認為前者的特點是“內容和形式分不開來,要了解它就得面對它本身,涵泳得深,體味得切,才會有所得;如果不面對它本身,而只憑‘提要’‘釋義’的方法來了解它,那就無論如何隔膜一層,得不到真正的了解”。因此他在實踐中一直堅持文學教育要面對文學作品本身,而無法間接受教的原則,也就是“涵泳”“體味”的原則。后者則剛好相反:它們是“并不運用文學形式的固有文化的記錄,只是一種材料,一些實質……它的內容和形式是分得開的”,所以在教材中“僅不妨摘取它的要旨,編進其他學科的課程里去”而“國文一科也就可以不管”。[5]他認為國文教材的內容大致應是“運用文學形式的固有文化的記錄”,也就是主要應該用文學的形式去承載“固有文化”的內容。
在應用文方面,李廣田在乎的是更接近魯迅說的“立人”的目標:“他們也不斤斤于以為‘初中畢業學生出校就業的,在社交上,職業上,處處要用普通應用文;高中畢業生做了區鄉鎮長,工商界職員或普通公務人員’,他們對于中學生的期望較高,他們想較遠較大處看,他們把中學生當做一個高尚的‘人’格的萌芽,而不把他們當做公務員或鄉鎮長的預備員,他們要學生去作很多更有意義的工作,就不忍再用了什末‘書札、電報、報告、告白、柬帖、規章及條例,’……等去糟蹋青年人的寶貴時間與精力。”[6]“立人”就是人格的“塑造”而非社會機器或者專業工具的“制造”。在李廣田看來,國文教育的中心在文學教育,其目的是培養比“區鄉鎮長,工商界職員或普通公務人員”具有更高人格的公民,其關鍵是認為這些公民與文藝之間是有著天然的聯系。從他的語句中可以看出,作為新文藝家的李廣田,潛意識里把“應用文”當做是較文藝文更低等的體裁,且只要文章寫通了,到了社會上“需要”應用的時候,“自然可以應用”;甚至還能打破常規,創造應用文體的新局面,能夠“比舊式應用文更好些,更合理些,更近人情些”。[7]
另一方面,雖然強調學術文的張清常、強調應用文的阮真和強調文藝文的李廣田在文章中都提到了愛國、益智等等塑造人格的共同目標,但是他們對國文課本“假想的讀者”如何接受課本內容有不同的預期。張根本沒有探討中學生對學術文的認知接受過程,阮更接近傳統教學以教為主的思路;而李對于應用文的接受過程的理解,在他那里也和對文學作品的接受如出一轍:先要有興趣,后產生需要,于是會自主地關注和學習。④于是在他那里,文藝——對文藝的認知——文藝的人格塑造功用三者成為自然而然的鏈接,且這個鏈接排斥著一切包括日常應用文體和學術文的非文藝。⑤不難看出,李廣田的主張中也有理想化的成分,但這個理想化與張清常的理想化和阮真的理想化的區別,正表現了文學教育在國文教育中的獨特之處。此外,當時教材的普遍“崇古”也是政治的反映——國民政府對新文學作品在教材中的出現一直抱有意識形態上的壓制。而如今當新文學在中學語文課本里的地位已經不成爭議時,我們需要關心的,則是在課本內外如何使其發揮人文性功能和語文訓練材料之作用的問題。
三、結 語
歷史上很少有對語文水平普遍贊揚的時期,正如70年前一樣,直到今天我們仍被中學生語文水平的“低落”所困擾。十幾年前的討論告訴我們,過往的民國語文教育并非像如今某些人設想的那樣高妙,我們也不用寄希望于神化那段歷史來抒發目前的抱怨;同樣,以為守舊的、文言的教材和惰性的、應用的文字一經變革,語文教學上的作文問題就可以一蹴而就的天真愿望也經不起歷史的考驗。任何現象都掩蓋不了文學教育一以貫之的對文字的審美、感悟、創造之要求,而在這方面進行的訓練的不足,及其導致的課本材料文學性功能和人格培養作用的喪失,并不會隨著舊障礙離開成為舊問題。
在“工具性”與“人文性”的問題上,如今文化傳承的使命與縮減語文科負擔的要求往往被形容成“大語文”和“小語文”的劃分。前者“包括了當時幾乎所有用文字表述的東西,……它實際上是一個民族語言文字的總匯,它體現的是一個民族語言文化的全部,而不是它的一部分”,后者“是一個民族語言文字總匯中的一部分,而不是它的全部,它體現的也不再是一個民族文化的全部,而是它的一種表現形態。”[8]很顯然地,語文科不但不能單獨解決“大語文”的任務,而且與幾十年前甚至百年前一樣,外語和數理化的壓力仍在剝奪語文科的空間。因此這個沖突的緩解,很大程度上并不能靠在語文一個學科上下工夫。我們須認清問題是永恒的,才會有面對問題的正確態度:問題的解決不能靠一蹴而就,而是需要決絕的堅持和永不懈怠的希望,以及一代又一代懷抱知識和德行的人們的系統化的努力。
注釋:
①20世紀30年代,因當時的國語國文課程標準明確了各年級的文白比例,文白混編基本定型,當時流行的一些中學語文教材均按這個比例。1940年,浦江清提出“把中學國文從混合的課程變成分析的課程;把現代語教育和古文學教育分開來,成為兩種課程,由兩類教師分頭擔任”“相應的教材也可以分編成白話和文言兩種”的主張。這是現代以來在對中西母語教育比較的基礎上,第一次明確提出語文課程分科設置與教材分科編寫的主張。……在文白混編混教占據主流位置二十余年后,當初這種做法的倡導者和實踐者葉圣陶等前輩進行了文白分編的探索。最早編輯出版的是供初中使用的《開明新編國文讀本》甲種本和乙種本。甲種本由葉圣陶、周予同、郭紹虞、覃必陶編輯,共6冊,為白話讀本。乙種本由葉圣陶、徐調孚、郭紹虞、覃必陶編輯,共3冊,為文言讀本。供高中生使用的《開明新編高級國文讀本》共6冊,1948年8月由開明書店出版,第一冊由朱自清、呂叔湘、葉圣陶合編,第二冊起增加了李廣田作為合編者。該教材專選白話,而配套使用的《開明文言讀本》則專選文言,由朱自清、呂叔湘、葉圣陶合編。見施平.中國語文教材經緯[M].北京:北京理工大學出版社,2010.第四章第二節。
②大體包括《國文月刊》第3期和克強的《中學生作文成績低劣的原因及其補救辦法》,第10期朱自清的《論教本與寫作》(李誤記作“讀本與寫作”),15期葉紹鈞的《論中學國文課程的改訂》,17期余冠英的《坊間中學國文教科書中白話文教材之批評》,和18期張清常的《對于坊間中學教科書所選“學術文”教材之商榷》,及阮真著《中學國文教學法》一書,后者在北京大學圖書館保存本閱覽室仍可借到當時的舊本。
③它們包括:《中學國文程度低落的原因及其補救辦法》,載《國文月刊》第28—30合期,1944年11月;《論中學國文應以文藝性的語體文為主要教材》,載《國文月刊》第31—32合期,1944年12月;《論中學國文教材中的學術文》,載《國文月刊》第33期,1945年3月;《論中學國文教材中的應用文》,載《國文月刊》第34期,1945年4月。
④李廣田在《論中學國文應以文藝性的語體文為主要教材》一文中對興趣的重要性不無諷刺地舉小學國文教學的例子說:“小學教材中多故事,多歌謠,多比喻,多用草木鳥獸擬人化,這已經是文藝的初步了。必須這樣,小學生才喜歡讀,讀了才有用。順便說一句,最近報上說,‘以后中小學均須用國定課本,據說雖是小學國文課本,也已經充滿了教訓意義,而把鳥唱歌狗說話的荒唐故事都取消了。……’我不知道這消息是否正確,然而我實在擔心,文藝實行起來,那以后恐怕又要鬧‘小學國文程度低落’的問題了。”
⑤在那篇文章的末尾,李廣田明確說道:“我不愿把中學生看作截然的一段,以為有些人或大多數人都必須出學校,入社會,作保甲長,作小商人,或作人家的文牘秘書之類的事業。但從另一方面說,我所期望于中學生達到這條道路,仍不妨礙他去作這些事業,他有一點文學修養,他有一點新的眼光,他可以做一個很好的保甲長,小商人,文牘或秘書,而不至于太卑鄙,太狹隘,更不至于墮落而不成‘人’。”
參考文獻:
[1][3]浦江清.論中學國文[J].國文月刊,1940(10).
[2][5]葉紹鈞.論中學國文課程的改訂[J].國文月刊,1942(9).
[4]朱自清.國文雜志發刊詞[J].國文雜志,1942.
[6][7]李廣田.論中學國文教材中的應用文[J].國文月刊,1945(4).
[8]王富仁.情感培養:語文教育的核心——兼談“大語文”與“小語文”的區別[J].語文建設,2002 (5).
(作者單位:北京大學中文系)
(責任編輯:劉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