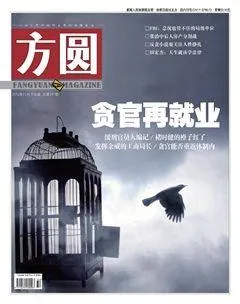身在異鄉為異客
【√】從詩性和哲學的意義上說,我們大家都是身在異鄉,一生都在短暫的時光中漂泊
一個詩人朋友深夜打電話來說感覺自己已經病得很厲害,就像要死的樣子,他描述癥狀時讓我想起了老年的托爾斯泰——手心發涼,四肢發抖,很想哭,很想愛。放下電話我就想到了一個巨大的靈魂在不斷超越自己現實定義的同時,肉體就會成為意識領域的障礙,讓死亡也變得宏大而又神圣。我是一個茍活的人,整日里安身立命,懶得出門,也從不想在開闊的大地上走得更遠。但是我羨慕那些行萬里路者,我總覺著他們有比我更多的勇氣與心力。
日前我在一所大學的文學講座中說到了上個世紀八十年代的詩人海子與他的作品。他的臥軌自殺像是給了詩人海子一枚至高的詩歌勛章。聽眾也像是更加迷戀于我對一個詩人死亡時刻的那些神秘與細致的分解描述,有的感情豐富敏感者還當場流下了淚水。
我也因此而動容,但還是把話題拐到了人世的溫暖上,當然是要面朝大海,春暖花開。我說還是好好的生活吧,用一個生者的信仰化解那些人類的巨大悲情比什么都重要,這是一種生存的智慧,類似那些永恒的星球。我還說到了朦朧派的先驅詩人食指先生與他的相信未來,我先后在山東與北京見過這位先知,他集高大的孤獨與一種普世的溫情于一身,在山東有人背過身來問我他是不是剛從瘋人院里出來不久,我說他看上去是有些憔悴,但語氣鏗鏘充滿了人性的關懷;他走路的樣子是有些讓人擔心,但你能感受到的是他卓爾不群,兩袖清風。
也許在諸多的財富中,孤獨是最為珍貴的一筆,由人類的悲情造就的孤獨是一種神圣的饋贈。不要死,活下去,是天才詩人曼德爾施塔姆對美好世界的召喚。他在百般絕望中寫下:彼得堡,我還不想死∕你有我的電話號碼∕彼得堡,我還有那些地址∕我可以召回死者的聲音。死亡、誣陷、監禁、饑餓、流亡,都沒能讓這個靈魂的漂泊者放棄生命,盡管他因患上精神分裂,從醫院的窗戶跳樓自殺未遂,所幸只是摔傷了胳膊,他活了下來,盡管依舊掙扎在死亡線上,卻進入了詩歌創作的高產期而成為世間一位不朽的詩人。
我的這位詩人朋友顯然也已寫出了驚世之作,他奔走天涯只是為了改善現實的境遇,然而離別自己故土的隱痛并沒有阻止自己巨大的創作激情。另一個好朋友說我們只是想有個好日子可過,所以總是希望眼前能夠更加敞亮些。朋友們之間總是如此,誠摯的人世溫情總能帶給一個異鄉人內心一縷奇異的光束,哪怕讓黑夜中的美夢延續的更長更美妙一些。
我是個厭惡樓宇而眷顧陽臺的人,養養花,種種草,聽舒緩的曲子,讓一條忠誠的家狗感覺自己生活在一個好人家。就有朋友直言說我這樣的一個寫詩的人一般死不了,他指的當然是自殺。
其實我也曾有過這種因為生而糾結才有的舉動,我想過那些曼妙的事件與將肉體投奔下去的深色水域,可是正如我懶得出門,我只是庸俗地生活在一個更加庸俗的地域與人群,所幸還有人世的善舉讓你沒完沒了地去學習與工作,孤獨作為一個豪華的陣容將永遠排布在另一個自我之中了。
從詩性和哲學的意義上說,我們大家都是身在異鄉,一生都在短暫的時光中漂泊。正因如此,親人的關懷,朋友的問候就顯得特別重要。生活中,令我引以為豪的是我的朋友們,他們有的才華橫溢,有的平凡如我,像一條深山里的溪流,需要安靜與鼓勵才得以存在與延展。我一生最大的財富就是他們從內心出發,總是說一些真摯而溫和的話;而這些好聽的話,我很想找個地兒記下來,時常得意地翻一翻,此時,我相信我看見了大海,并相信這就是我們內心不停涌動的溫情的大海。
劉瑜
青年詩人,著有詩集《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