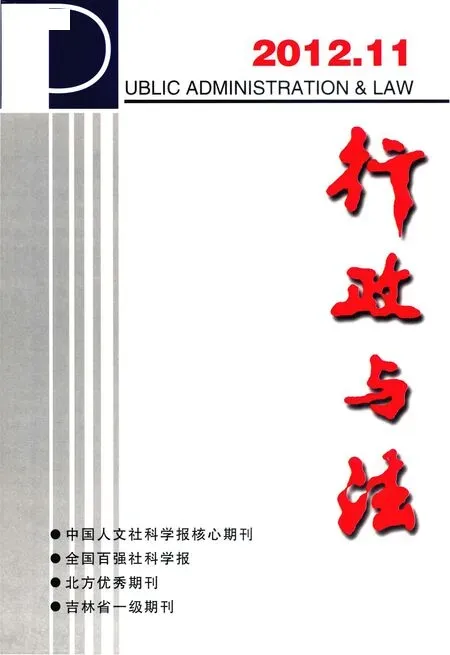風險社會理論視域下的公安機關社會管理創新
□ 周紅
(四川警察學院,四川 瀘州 646000)
風險社會理論視域下的公安機關社會管理創新
□ 周紅
(四川警察學院,四川 瀘州 646000)
基于風險社會理論對現代性的反思和自省視角,加強公安機關社會管理創新是對全球性社會風險以及轉型期中國內生性社會風險的積極應對。據此,公安機關社會管理創新的深層意蘊應包括:化解因社會極化結構所產生的社會焦慮,以消除風險社會的社會心理基礎;化解現代工具理性帶來的信任危機,以消除風險社會的社會倫理基礎;化解社會利益分化帶來的社會認同弱化,以消除風險社會的現實基礎。并提出以下建議:公安機關社會管理創新應以民本導向為核心理念,以平等合作為基本特征,以體制創新推進社會管理創新。
風險社會理論;公安機關;社會管理
自1986年德國社會學家烏爾里希·貝克發表《風險社會:通向一種新的現代化》以來,以貝克、吉登斯等人為代表的社會學家所提出的風險社會理論構成了現代性反思的又一代表學說。風險社會理論既質疑現代科學理性的無所不能導致其無限擴張,又不贊同后現代主義對現代性的全面解構,認為與工業現代化階段相區別,風險社會是現代社會的新階段,是“反思性現代化”階段。[1](p58)風險社會理論解釋了關于現代性的三個敏感問題,即“經濟增長過程中的制造風險的責任、高科技帶來風險的普遍性和抽象科學研究的不充分性”,并以“反思現代性”作為對策回應。[2](p26)
據風險社會理論對現代性的自省與反思,風險社會以社會風險的可能性存在、現實性發生和持續性影響為特征,而“風險可以被界定為系統地處理現代化自身引致的危險和不安全的方式。”[3](p19)全球性社會風險的來臨,中國社會轉型內生的潛在風險,傳統意義上以國家和政府為中心的單一社會治理結構和剛性設計已經無力應對,社會管理創新需要順應國際環境和社會內部結構的深層變化,回歸大眾的日常生活,關照社會秩序的感性基礎。公安機關的社會管理是政府社會管理的重要組成部分,“公安機關社會管理創新,是針對新形勢和新問題公安機關在現有的社會管理工作的基礎上,運用新的社會管理理念、知識、方法和機制等,對公安機關社會管理工作進行調整或改革,進而提高社會管理效能,形成與新形勢和新問題相適應的公安機關社會管理模式”。[4]借鑒風險社會理論的研究視角,分析政府社會管理創新與公安機關社會管理創新之間的內在一致性,通過社會發展過程中秩序和行為的二重性選擇,基于微觀社會環境把握公安機關社會管理創新的深層意蘊,增強社會管理創新的有效性,對于積極應對因全球化可能引發的外發型社會風險,有效化解我國社會轉型期可能出現的內生型社會風險,維護社會的和諧穩定和良性運行,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和現實意義。
一、以公安機關社會管理創新適時應對全球性風險社會
貝克在《世界風險社會》中指出,“現代社會風險是世界性的、全球化的,因此‘風險社會’實質上就是一個‘世界風險社會’”。[5]在全球化時代,國家之間的經濟、政治和文化疆界被逐步淡化,社會風險及其影響力的廣度和深度隨之增加。有學者認為,當代全球性風險主要包括地球生態環境風險、全球經濟風險、世界文化風險、國際政治風險等,[6]其中任何一類風險的任何一個節點都可能波及其他領域和其他國家。風險社會理論把現代社會風險論題同全球化聯系起來,認為現代社會風險不僅關涉一人一國,它將引起全人類生存環境的嚴重惡化,威脅整個人類社會的生存狀態,引發公眾心理恐慌,且形成巨大的精神壓力,導致社會效率和穩定機制的功能失效。“蝴蝶效應”加大了當代社會風險的連鎖性和不可預測性,世界各國的理論機構和實務部門都在對全球性風險社會的來臨進行認真研究和積極應對,形成了以風險社會理論、風險社會文化理論、風險社會不可知論為代表的系列理論成果,而實務部門則多從政府善治的角度強調要加強社會管理,推進社會管理創新。
社會管理是政府、市場和社會組織為了滿足人們的各種需求、維持社會秩序、促進社會進步而通力合作對社會生活系統的組成部分進行組織和協調的過程,它以合作精神和現代公共規則的確立為價值取向。[7]隨著我國現代化速度的加快和程度的加深,關于社會管理創新的觀點不斷見諸于黨和政府的重要文獻。自2002年黨的十六大報告到2011年的“七一”講話,黨和政府對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的科學部署大致體現出以下三個方面的政策理路:一是以科學發展觀作為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的理論基礎;二是在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提出在建立健全“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的社會管理格局”的前提下,立足于不同時期經濟社會發展工作重點,對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明確提出了具體要求;①黨的十六大以來,針對不同時期的工作需要,黨和政府對于社會管理創新要求的側重點有所不同,對社會管理創新的認識不斷深化。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提出 “加強社會建設與管理,推進社會管理體制創新”。黨的十六屆五中全會對于形成覆蓋全社會的管理體系、更好地發揮政府社會管理職能進行了科學布局。十六屆六中全會提出“完善社會管理,保持社會安定有序”。黨的十七大報告進一步明確“完善社會管理,維護社會的安定團結”。2011年2月19日,在中共中央黨校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社會管理及其創新專題研討班開班式上,胡錦濤同志指出:“要針對當前社會管理中的突出問題,著重研究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做好新形勢下群眾工作的思路和舉措,為促進社會和諧、實現‘十二五’時期經濟社會發展目標任務凝聚強大力量。”2011年7月1日,胡錦濤同志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90周年大會上的重要講話中指出:“要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完善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的社會管理格局,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管理體系,全面提高社會管理科學化水平,確保人民安居樂業、社會和諧穩定。”三是以建設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管理體系作為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探索和實踐之基本目標。進入新世紀以來,關于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的科學部署和實踐推進正是黨和政府以全球性視野敢于和善于直面全球性風險,堅持黨的領導,基于政府、社會和公眾的合作精神,遵循現代公共規則,整合社會力量,對風險社會及其影響的積極應對。
公安機關社會管理工作的實質,是從國家武裝性質的刑事司法和治安行政之特殊角度,規范社會行為、化解社會矛盾、解決社會問題、應對社會風險、促進社會公正,在調整各種社會關系的活動中達到維護社會穩定有序的目的。在現代性深入發展的背景下,社會風險的后果最終均無一例外地指向具體的個人,并通過個人在社會交往中的反應,將該后果的持續性影響進一步傳遞開去。由是觀之,公安機關調整各種社會關系,首要面對的是社會風險已經和可能產生的影響,以及因這種影響所導致的人們產生的思想、心理和行為反應。因此,適應全球性風險社會階段人們對社會安全的期待和更高的要求,調整和改革社會管理的內涵和形式已成必然。從隸屬關系上看,公安機關的社會管理職能是政府社會管理職能的重要組成部分,黨的十六大以來,公安機關社會管理創新工作穩步推進,尤其是在2011年12月全國政法工作會議上,周永康同志將社會管理創新定位為2012年全國政法部門三項重點工作之一,并于次年2月在全國社會管理創新綜合試點工作座談會上強調 “要深入推進社會管理創新綜合試點工作,加強整體規劃設計,因地制宜搞好典型培育,積極探索具有中國特色、地方特點、時代特征的社會管理新路子,不斷提高社會管理科學化水平。”孟建柱同志在2011年12月召開的全國公安廳局長會議上要求各級公安機關要“堅持管理與服務并重,維護秩序與激發活力統一,著力破解社會管理難題,切實提高公安機關社會管理科學化水平。”這一系列部署和舉措標志著在我國現代性特征凸顯、社會轉型速度加快的時期,公安機關社會管理創新進入了新的階段,此舉也啟發我們要進一步對公安機關社會管理創新的深層意蘊作深入思考。
二、公安機關社會管理創新在化解轉型期社會風險中的深層意蘊
“風險概念是一個很現代的概念,……各種風險其實是與人的各項決定緊密相連的,即是與文明進程和不斷發展的現代化緊密相連的。”[8](p3)“在發達的現代性中,財富的社會生產系統地伴隨著風險的社會生產。”[9](p15)創新社會管理,不僅要正視社會風險的客觀存在,而且需要提升對風險的認知程度和認知水平。對已然發生風險的評價和對可能性風險的防范決定了人們應對和化解風險的效果,因為“風險是一種現實,但它不是全然本體論意義上的,必須有認識論的參與,也就是說人們需要以一種建構主義的思維方式思考風險。”[10]
我國的漸進性改革和現代化道路是合而為一的,改革所釋放的巨大生產力催生了經濟的快速發展。與先期完成現代化的國家相比較,經濟快速發展使我國的現代化進程在某種意義上呈現出時空壓縮的特點,在較短的時間和有限的空間內,工具理性和科技理性出現了較大擴張和膨脹,而本應并行的科技倫理和制度倫理相對滯后,使轉型期社會風險的結構性因素被放大,社會矛盾和問題相對增多。新時期公安機關社會管理創新具體表現為通過社會管理創新更好地解決各種社會問題,化解矛盾糾紛;最大限度地減少社會的不和諧因素,最大限度地增加社會的和諧因素。而其中隱含的深層意蘊在于公安機關需要以社會管理創新為手段,緊緊圍繞黨和國家工作大局,對社會系統的組成部分、社會生活的不同領域以及社會發展的各個環節進行有效的組織、協調、管理和服務,保平安、保穩定、保民生,有效化解中國社會轉型期的社會風險,切實承擔起鞏固黨的執政地位、維護國家長治久安、保障人民安居樂業的重大政治和社會責任。
⒈化解社會極化結構產生的社會焦慮以消除風險社會的社會心理基礎。社會極化結構引發的社會焦慮構成了誘發和擴大社會風險的主要心理基礎。公安機關社會管理創新的深層意蘊就在于通過有效地排查矛盾糾紛,解決好事關民生的具體問題,以化解社會焦慮,消除風險產生的社會心理基礎。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社會結構出現了新的變化。生產能力、生產要素的擁有量以及勞動貢獻等方面的差別不斷增大,我國分配制度趨于“不平等的改善與合理化”的特點,造成社會財富分配和擁有的差異。“工業社會的核心問題之一是財富分配以及不平等的改善與合法化。那么在風險社會,傷害的緩解與分配則成為核心問題。”[11]社會極化結構是不同階層和社會成員之間物質資料和社會資源占有的距離不斷增大,使貧富差距拉大的一種社會內部關系。由于“先富”政策實施的有效性和“共富”效應的乏力性,使得因收入差距拉大而呈現社會兩極化趨勢及其帶來的社會風險已成為不爭的事實。有觀點認為,對于轉型期的中國,因收入差距產生的貧富階層分化是社會極化的內核。[12]在社會極化結構下,不同社會群體相互間的歧視和排斥、摩擦和對立,特別是社會弱勢群體強烈的相對被剝奪感加劇了社會的結構性風險。
極化的社會結構不僅不能為個人提供本體性安全的條件,反而會凸顯現代性快速發展帶來的不確定性因素。人在其中喪失了賴以存在的根基,猶如無根之萍,失去了心靈歸宿,內心恐懼,情緒不安,這一系列心理感受和心理反應構成風險社會的社會心理基礎。貝克指出,“階級社會的推動力可以用一句話來概括:我餓!風險社會的驅動力則可以用另一句話來概括:我怕!”[13](p137)“害怕”是風險社會個體對社會不確定性所具有的一種典型焦慮狀態。當人在面對未來種種的不確定性,對自身生存安全的擔憂和恐慌成為一種共性時,極易衍生為社會焦慮。當社會焦慮沒有安全而正式的排解和化解方式時,個人往往會依據經驗和非制度化手段來加以表達和解決,這將是社會風險的更大隱憂。默頓認為,社會結構的不協調將導致社會群體之間的關系處在一種對立的、矛盾的或沖突的狀態下,在此狀態下,社會矛盾比較容易激化,社會問題和社會危機容易發生。若社會焦慮普遍性存在,社會風險被誘發的可能和機會均會被放大。
公安機關社會管理創新的具體目標是在流動人口、社會治安、公共交通、消防安全、網絡安全、特殊行業等關涉社會生活的諸多方面提供更優質、更高效的管理與服務。其直接的功能價值在于更好地為公眾排憂解難,通過解決好事關民生的具體問題,以化解矛盾糾紛、調整社會關系的工作過程和工作成效來增強群眾的心理安全感。化解社會焦慮,進而消除誘發和擴大社會風險的心理因素。其深層的價值意蘊在于,在中國社會現代性快速生成而導致的諸多不確定性中,通過創新社會管理,將打擊犯罪和服務群眾有機地結合起來,以國家權力人格化的形式,體現國家權力對公眾安全需求的制度性安排和人性化關懷,使公眾得以形成對社會公共安全和自身本體性安全的內心確證;通過弱化和緩解社會結構性缺陷引致的社會性焦慮與群體性不安,消除風險產生的社會心理基礎。
⒉化解現代工具理性帶來的信任危機以消除風險社會的社會倫理基礎。消除存在性焦慮代之以本體性安全,是降低現代性社會交往成本的基本訴求,也是現代性社會生存的本質要求。信任感是本體性安全之所以建立的依據,包括具象和抽象的信任感兩類。具象的信任感是指在現實社會交往中通過社會關系所體現和維持的信任關系。對于抽象的信任感,有專家認為,“是從象征標志和專家系統的抽象體系中發展出來的信任關系,”“前者的基礎是人的誠實程度,后者的基礎是抽象體系背后的知識狀態,這些知識對非專業人士來說幾乎是無知的。……其知識效度獨立于使用這些知識的具體行為者之外。”[14]
現代工具理性帶來的風險是社會信任危機。現代科學技術快速發展,工具理性迅速膨脹,知識專門化、精深化程度越來越高,普通人在普遍使用著專家系統所提供的知識成果的同時,對這些知識應用成果背后的知識體系卻越來越無知,他們對專家系統提供的知識和知識成果的信任度變得非常脆弱。比如當人們普遍感受到核能高效清潔的同時,對核能使用的原理以及風險防范卻知之甚少,一旦發生安全事故,不僅疏于防范而且無力應對,個體心理安全和社會安全信心也會由此受到強烈的沖擊。又比如當人們普遍享用著互聯網方便快捷的交流交往的同時,網絡信息安全的隱憂卻無時不在。如此的結果便是人們享用并置疑現代科技成果的悖論始終存在,與工具理性伴生的潛在信任危機使現代社會的風險系數不斷增大。
傳統意義上的社會交往以交往雙方共同“在場”為特點,交往過程中人們根據適時、適地的判斷可以確定對自己和對對象建立的信任。現代生活則完全打破了社會交往“在場”的界限,交往雙方通過視屏、微博、微信、QQ、現場直播等現代信息技術,甚至多方可以在不同時在場的情況下進行交流溝通。“即社會關系從地方性的場景中‘挖出來’并使社會關系在無限的時空地帶中‘再聯結’。確切地說,這種‘挖出來’就是我所說的抽離化的內涵,對于由現代性所引入的時空分離的巨大增長而言,抽離化是關鍵因素。”[15](p43)“抽離化”使交往雙方的信任比較虛無。網絡流言、網絡謠言、網絡炒作的迅速傳播卻又轉瞬消弭,使公眾極易對他人、對媒體、對專家系統產生信任危機。一方面,信任危機表現為“輕信”,謠言趁虛而入,不實之詞以訛傳訛;另一方面,信任危機表現為“不信”,社會信心出現離散狀態。在社會流動性增強,社會“碎片化”現象呈現的情況下,缺乏主流價值標準、價值標準混亂的價值判斷和價值選擇是社會風險的倫理基礎;是社會風險得以發生、擴大、延續的道德土壤。
公安機關是政府進行社會管理的重要職能部門,公安機關所進行的社會管理創新無論是理念還是體制,無論是路徑還是方法,從根本上講都應該是在為公眾提供高質量的公共安全服務的基礎上,通過了解群眾的訴求、傾聽群眾的呼聲、解決群眾的困難來取信于人,取信于民,藉此強化和提升政府公信力,化解現代工具理性帶來的信任危機以消除風險社會的社會倫理基礎。
⒊化解社會利益分化帶來的社會認同弱化以消除風險社會的社會現實基礎。在計劃經濟時代,社會的整體利益與民眾的個人利益高度重合,即社會主義工業化和民族的獨立富強,此外無他。但隨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健全,單一的社會階層結構開始分化,逐步轉化成為利益分化較大的、由許多不同利益群體組成的復雜階層結構,這一復雜結構的顯著特點是各個階層在市場化面前有著不同的利益訴求。在市場化面前,人們更多的是追求個人利益的最大化。利益主體多元化,利益差距擴大化,利益關系復雜化,使得新的社會群體和社會階層急需表達自身利益訴求的渠道。利益分化決定了人們對待風險的不同態度,也決定了風險發生的可能性程度,“每一個利益團體都試圖通過風險的界定來保護自己,并通過這種方式去規避可能影響到它們利益的風險。”[16](p31)如前文所言,有一類社會信任感來自于專家系統,然而,若專家系統和決策部門對于風險的定義規則和處理程序是集團利益的代言的話,那么,由此導致社會信任感的坍塌所引發的社會風險將比利益分化本身所帶來的風險要大得多。
在風險全球化加劇的時代背景下,我國社會面臨的國家安全、經濟安全、政治安全、文化安全等各種潛在的風險。在國內,以利益追求為導向的市場化推進給社會和諧穩定帶來了一系列不確定的風險因素,一段時期里以經濟利益驅使而出現的嚴重威脅社會穩定的安全問題,如公共安全、食品安全、金融安全、群體性事件等時有發生。由于社會轉型和經濟轉軌同時并進、相互推動,加之社會建設滯后于經濟改革,在加速轉型的過程中必然會產生文化的交叉錯位和距離落差;結構沖突、體制摩擦和利益分化交織,加之各種利益關系的調整范圍和規制力度極為有限,將使社會認同嚴重弱化。
在社會轉型期,市場化加劇了我國城鄉居民利益結構的變化,一些社會不公現象引起了群眾的強烈不滿。許多群體性事件和突發危機事件均由利益受損所引發。因此,公安機關調整和協調各種社會關系,決定了公安機關社會管理創新的深層指向是如何更好地通過公正執法、公平執法、依法執法,維護社會的公平正義來彰顯民主法治精神,構建社會和諧的基礎秩序,形成良好的社會生態,從根本上化解社會利益分化帶來的社會認同弱化以消除風險社會的社會現實基礎。
三、風險社會理論視域下公安機關社會管理創新的有效性
針對我國社會轉型期制度構建和結構剛性所潛在的社會風險,從風險社會制度主義的理論邏輯探討我國轉型期公安機關社會管理創新的核心理念、基本特征和具體措施,對于增強適合公安機關管理創新的有效性,對于防范、面對和化解當下我國發展進程中的社會風險具有重要價值。
⒈民本導向是公安機關社會管理創新有效性的核心理念。如果說以人為本是我國進入新世紀以來科學發展、和諧發展的核心理念,那么,應對世界性風險社會來臨,民本導向就是公安機關社會管理創新有效性的核心理念。其表現為社會管理創新的制度設計要體現社會的公平正義,真正落實憲法對公民權利的保障,制度的實踐操作要關照民眾的感性需要,聽取民眾意見,以民意為導向,最大限度地保障公民的法定參與權、知情權、表達權。
隨著我國現代化、城市化和市場化的加速推進,社會秩序的理性化設計和社會行為的感性化選擇的雙重特征日益顯現。一方面,以政府推動式的制度設計增強了社會的流動性,其釋放出的活力在提高社會發展的效率和生產能力的同時,也導致了利益分化、貧富懸殊和社會不公等結構性社會風險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中國社會自上而下的市場化改革,傳統社會秩序中的熟人關系、親緣關系、血緣關系所影響的行為選擇不僅沒有被制度理性所規制,反而在某些區域、行業和群體中日益強勢,人們仍然沿襲著自己的感性行為模式、禮俗社會的差序格局確定行為意向和選擇策略,進而直接影響著轉型期中國社會的關系格局和秩序建構。秩序和行為所對應的理性設計和感性選擇具有非同步性,將增加以利益最大化為主導的市場化進程中的許多社會風險的偶發性和不確定性。
加強公安機關社會管理創新,需要注意協調并處理好市場化、城市化、信息化過程中政府的理性設計與普通民眾的深層感性意識,尋求政府主導下的市場、社會和普通民眾利益平衡的社會管理結構,因此,公安機關社會管理創新表現在其理性選擇和制度設計上需關照基層社會成員的情感需要,以增強其在民眾中的影響力,進而將科學有效的理性策略轉化為廣大基層民眾所認同和接納的社會管理創新實踐。反之,如果公安機關社會管理創新的制度化理性設計無視普通社會民眾豐富的、真實的、生動的感性選擇,就可能引發或放大社會秩序的風險因素。為此,需要不斷探索創新社會管理的新目標、新方法和新手段,通過提高社會管理的科學化程度改善經濟發展水平與社會管理水平之間的失衡狀態,只有這樣,公安機關的社會管理創新才能更好地滿足人民群眾的利益訴求,滿足和諧社會以人為本科學發展的基本要求。
⒉平等合作精神是公安機關社會管理創新有效性的基本特征。起源于工業文明的現代化在帶來豐富的物質財富和科學技術進而控制和降低了某些社會風險的同時,也擴大了人類的未知邊界。美國社會學家查理斯·陪羅曾說:“高度發達的現代文明創造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卻掩蓋了社會潛在的巨大風險;而被認為是社會發展決定因素和根本動力的現代科學技術,正在成為當代最大的風險源。”[17]消除工具理性肆意擴張的可能性風險,重建人們的信任感,是社會秩序和個體行為選擇二者融合相洽的內在動力源。
在這樣的前提下思考公安機關社會管理創新的有效性,當以在現代化進程中體現社會管理精髓的平等合作精神作為公安機關社會管理創新的基本特征。2004年,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首次提出,黨的十七大報告中正式明確建立健全“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的社會管理格局”,2011年胡錦濤同志在“七·一”講話中強調:“要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完善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的社會管理格局,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管理體系,全面提高社會管理科學化水平,確保人民安居樂業、社會和諧穩定。”可見,社會管理已不是簡單的管理社會,更不是單純的社會控制,它是政府與人民共同完成的善治。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建設決定了黨的領導是社會管理創新的領導核心;政府是社會管理的主導者;各種社會組織參與社會各種事務的治理;公民有序參與社會管理活動。在黨的領導下,政府、社會和公民共同承擔起社會管理的責任,同時發揮民意評價、民眾監督的積極作用,達成善治目標,建設民主法治、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安定有序、充滿活力、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社會。
據此可見,公安機關社會管理創新應符合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管理體系的根本標準,在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的前提下,同樣應該形成社會協同、公眾參與的格局。以合作的關系、以朋友和伙伴的關系、以平等的關系,發揮基層群眾組織、社會組織、機關企事業單位、社會成員的作用,形成以不同主體協同參與管理社會的新形式。以平等合作精神整合社會管理資源,調動多元主體參與社會管理的積極性,在動態立體的社會管理過程中實現社會運行的良性有序,維護社會的和諧穩定,是應對風險社會背景下公安機關社會管理創新的基本特征。
⒊體制創新是公安機關社會管理創新有效性的現實途徑。總體而言,我國社會轉型和市場化進程速度較快,社會分化和利益失衡加劇,在較短時間內產生了較多的社會問題和社會矛盾,各種潛在社會風險不斷累積。具體而論,微觀社會領域存在著誘發風險的諸多因素,如現代化發展程度不均衡,人口基數大而人口素質低;各社會要素流動性加快,社會信任缺失,社會道德重建迫在眉睫;社會組織因發育不成熟導致其參與社會管理的能力不足,等等。加之自改革開放以來社會管理的組織基礎發生了較大改變,即由以“單位人”為標志的總體性社會向以“社會人”為特征的多元化社會轉變。①改革開放以前,我國社會管理的基本模式是城市中的單位制和農村的人民公社制度。改革開放以后推行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導致人民公社制解體,農民階層分化、流動性迅速增大。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發展,多種社會經濟形式的出現,傳統意義上的單位制社會管理機制逐步走向終結。這一切都要求通過切實的體制創新來解決微觀社會生活中存在的矛盾和問題,有效地化解社會風險發生的各種具體誘因,為此,推進體制創新,增強公安機關社會管理創新的有效性,最突出而迫在眉睫的任務有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公安機關要重視社會公共安全服務的提供,堅持以人為本、服務為先,把民意導向作為衡量和檢驗公安工作的根本標準,努力實現管理與服務的有機統一。要從整體上提高社會管理科學化水平,立足當前、著眼長遠,把解決突出問題與建立長效機制有機結合起來,解決好群眾反映強烈、影響社會和諧穩定的突出問題;解決好制約社會管理長遠發展的全局性問題。
其次,統籌整合各類服務管理資源,全面推廣扁平化、網格化服務管理,把公安機關的各項服務管理措施落實到城鄉社區、基層單位和每家每戶,積極穩妥地推進戶籍管理制度改革,全面實行居住證制度,實現基本公共安全服務由戶籍人口向常住人口全覆蓋,促進流動人口與當地居民和諧相處,增加社會成員的生存安全感。
再次,重視新型經濟組織和社會組織以及其他不同社會組織的利益需要和利益訴求,協助各級政府暢通社會群體利益表達的新渠道,探索社會管理新載體,形成社會管理民主監督新形式。發揮社會協同的力量,在有效規范和正確引導的前提下,積極推動社會自治組織在社會管理中與公安機關的良性互動,發揮其重要的社會整合功能,使其成為防范、減少和化解社會風險的緩沖器。
第四,重視公安機關社會管理創新經典案例的當代適用,如“楓橋經驗”對當前公安機關社會管理創新的借鑒意義。善于在新的時代背景和社會條件下科學總結和積極推廣公安機關社會管理創新案例,深化對公安機關社會管理創新規律的認識,把群眾需求作為第一選擇、把群眾滿意作為第一標準,以人民期盼為念、為人民利益而戰,提高公安機關社會管理科學化水平。
[1]莊友剛.跨越風險社會——風險社會的歷史唯物主義研究[M].人民出版社,2008.
[2]周戰超.當代西方風險社會理論研究引論[A].全球化與風險社會[M].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
[3][9][16](德)烏爾里希·貝克.風險社會[M].何博聞譯.譯林出版社,2004.
[4]毛欣娟,蔡晨昊.公安機關社會管理創新的路徑選擇及相關問題思考[J].北京人民警察學院學報,2007,(04):68.
[5]顧忠華.“風險社會”之研究及其對公共政策之意涵[J].臺北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1993,(20).
[6]洪曉楠,林丹.全球風險社會及其策略回應——烏爾里希·貝克的風險社會理論評介[J].學術交流,2007,(04):6-9.
[7]張青.社會管理創新的現實基礎和三維構建[J].重慶社會科學,2011,(09):114.
[8]烏爾里希·貝克,威廉姆斯.關于風險社會的對話[M].薛曉源,周戰超編.全球化與風險社會[M].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
[10][14]田國秀.風險社會環境對當代個體生存的雙重影響——吉登斯、貝克風險社會理論解讀[J].哲學研究,2007,(06):113-115.
[11]楊雪冬.風險社會理論反思:以中國為參考背景[J].綠葉,2009,(08).
[12]楊上廣,丁金宏.論社會極化及其影響因素[J].社會科學輯刊,2005,(02):76.
[13]貝克.自由與資本主義[M].路國林譯.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
[15]吉登斯.社會的構成[M].李康,李猛譯.三聯書店,1998.
[17]Charles Perrow.Accidents in High-risk System[J].Technology Studies,1994,(01):23.
(責任編輯:牟春野)
Innovation in Social Management of the Public Security Organs under the Theory of Risk Society
Zhou Hong
Based on the theory of risk society reflections on modern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ublic security organs and introspection,strengthening social management innovation is the global risk society and transition of Chinese social risk actively respond to endogenous.Therefore,the public security organs social management innovation connotation should include:dissolve because of social polarization structure produced by the social anxiety,to eliminate the risk of social psychological basis;dissolve modernist tool ration caused a crisis of confidence,to eliminate the risk of social basis of social ethics;social benefit differentiation of social identity weakening,in order to eliminate the risk social reality.And put forward the following suggestions:public security organs social management innovation should be to the people oriented as the core concept of equal cooperation,as a basic feature,with the system innovation to promote the innovation of social management.
risk society theory;public security organs;social management
C916.1
A
1007-8207(2012)11-0022-06
2012-07-13
周紅 (1967—),女,湖南醴陵人,四川警察學院思想政治理論教學部副教授,復旦大學法學碩士,研究方向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理論與實踐、警察教育與管理理論。
——關注自然資源管理